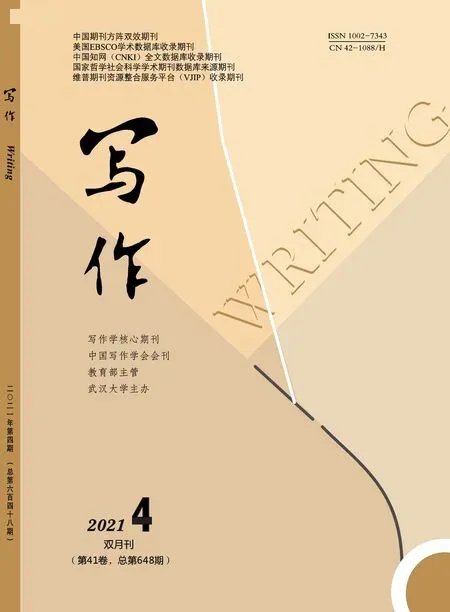李修文《枕杜记》文体特征论析
萧 映 郑 琴
自2017年至2021年,李修文先后出版了三本散文集:《山河袈裟》(2017年)、《致江东父老》(2019年)与《诗来见我》(2021年)。相较于前两本散文集来说,写于新冠疫情之下的《诗来见我》,既延续了以往散文中对人民的关怀以及古典美学风貌,也以更为明确的文体特征区别于前两本散文集。在李修文看来,“因为各种文体的负担,今天,散文成了一件大事。在此前,我们通常认为,矗立在各种文体之间的那个地带构成了散文的主体性,在今天是否可以这样说——此时此刻,散文的主体性恰恰在于抢夺和侵占,抢夺小说,侵占戏剧,抢夺诗歌,侵占电影,才可能真正构成今日散文的主体性?”①李修文:《先锋文学精神与今日生活》,《写作》2019年第6期。《诗来见我》收录的20篇散文,既与小说一样重视叙事方式的构建,又与诗歌一般关注抒情与节奏。对于李修文而言,散文从来不是徘徊在诸文体边缘地带的一种文体,散文尽可以吸收其他文体之长,但仍保有散文自身的主体性地位。
童庆炳在考察梳理了诸多中西方文论后这样界定“文体”,“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②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陈剑晖在《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与文体演变》中指出,“文体是文学作品的体制、体式、语体和风格的总和。它以特殊的词语选择、话语形式、修辞手法和文本结构方式,多维地表达了创作主体的感情结构和心理结构。它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精神的凝聚”③陈剑晖:《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与文体演变》,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结合以上论述,“文体”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长期文学实践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体裁样式;其二是体现着作者个人风格的作品风貌;其三是作品中传递的社会历史文化精神。“文体”既体现着作者的主观世界、创作天赋,又受客观的体裁规范以及现实世界的制约。在《诗来见我》这本散文集中,李修文的文体意识在他对有“我”的写作的重视中显现。李修文指出:“我们每个人却被限制在一个格子间、限制在自己的领域,每个人都怀揣着各种各样的个性靠近彼此,但最终又成为一个苍白的集体。所以在我看来,如何建立一个今天的‘新我’,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不管在写作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要捍卫有‘我’的写作,要重新确立一个新的自我。”①李修文:《山河人间与我——武汉大学驻校作家启动仪式上的演讲》,《写作》2020年第6期。《枕杜记》于2020年3月发表于《当代》杂志“诗来见我”专栏,是散文集《诗来见我》中第一篇面世的文章,于作者李修文、读者以及散文集《诗来见我》本身皆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枕杜记》一文,通过文本细读,分析李修文对散文叙事模式的构建、对“诚意”与“文气”的重视,以及对“真切”与“实在”的追求,并探究作者的文体意识之于作品美学风貌生成的重要意义。
一、真实与虚构:散文的叙事模式
散文叙事对散文的文体特征生成有着重要意义。叙事模式之所以能成为散文的文体构成要素,是因为其包含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元素,关系到散文如何谋篇布局。在《枕杜记》中,作者时而讲述“我”亲眼所见之景、亲身经历之事,时而讲述“我”在幻境之中与唐代诗人杜甫的相遇,时而抒发“我”在虚实之间的内心感受。“我”的想法飘忽不定,叙述视角不断转移,在真实与虚构的巧妙变换之间完成了非线性叙事模式的建构。
以《枕杜记》的开篇部分为例,文章从微山湖旁的一只芦苇小船写起,“我”置身于船中,眼见水光向“我”涌来,想到了杜甫的死。随即文章开始叙写杜甫死前的遭遇与写下的诗句。在杜甫死去的前两年,他曾登上岳阳楼。在充满生命力的自然万物之前,杜甫想到自己已年过半百,浪迹于江水之上,昔日好友音信全无,只有一身病痛与一叶孤舟陪伴着自己,不由泪如雨下。躺在芦苇船中的“我”虽未受疾病所扰,然而这几年的“我”,带着过去“知名青年作家”的光环,行走于各地,却数年没有写出一个字。讲述完“我”的真实际遇以及就杜甫及杜诗展开的联想之后,文章进入了虚与实的过渡地带,也即“我”关于杜甫与杜诗的真实而纠结的内心书写。“我”在此刻坦言,杜诗常常让我感受到痛苦,“过去的好多年里,我一直都在躲避他的诗,那些诗,像是乌鸦,一群群,高悬在头顶,驱赶不去”②李修文:《诗来见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2页。。微山湖旁的芦苇船与湖水为实在之境,“杜甫之死”为幻想之景。“我”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之中,在虚与实之间坦陈“我”对杜甫与杜诗的复杂心绪,也在文章开篇之处留下了一个悬念:“我”究竟为何要逃避杜甫和杜诗?杜甫和杜诗又为何锲而不舍地对我进行召唤?
推至《枕杜记》全文来看,发现全文皆由“实—虚—虚实之间”的叙事结构构成,虚实相生的构造形成景与景之间、事与事之间、人与人之间更多的联想张力。“我”在雪夜工厂遇见狐狸、看见锅炉与衰草,想起了《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的第五首,又在黄河渡口与杜甫进行短暂的对视,未曾想过即便“我”避之不及,但“我”终将会再次遇见杜甫。“我”在河北县城遇见旧日知己,在甘肃陇南的剧组生活中偶遇外出务工归来的年轻人,想到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与《北征》。就在此刻,好友小儿女的沉默与年轻人的嚎哭形成了对比,“我”在这一刻也为强烈的情绪所裹挟,终于明白“我”无法逃避杜甫的诗句——“我”与杜甫一样有着强烈的共情能力,始终心系着身边的草木人间,因他人之哀而哀。意识到自己心甘情愿与杜甫做同路人之后,现实生活中的“我”急匆匆地前往县城,跑遍所有的书店才买到了《杜诗选注》。回到旅店之后,“我”受高热所扰,又迷迷糊糊在渡口再次看见了杜甫,想起了《蚕谷行》,在背诵此诗之时由杜诗在“我”的身体里浇灌深切与实在,与杜甫共同许下了一个朴素的心愿。这种“实—虚—虚实之间”的叙事结构即为:“我”由实在的眼前之景想起杜甫的诗句,因杜甫的平生遭际进入内心的自我审视,眼前所见有虚有实,“我”对杜诗有游离有靠近。文章的内在情绪也随着叙事结构的循环而继续推进,于是也有了不同的“我”:芦苇船中的“我”,对杜甫与杜诗持逃避的态度;雪夜工厂的“我”,在接受杜诗的浇灌与逃避这些诗句之间徘徊;高热之中的“我”,意识到杜诗生长于“我”的内心深处、是“我”身体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终心甘情愿与杜甫一起承担起关怀众生的责任。随着内在情绪书写的完成,“我”也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动态建构,即完成了从“逃离之我”,到“徘徊之我”,再到“同路之我”的历时书写。
《枕杜记》不仅关注“我”的内心书写,也注重以“我”的方式讲述故事与抒发感慨。叙事结构与抒情方式在各自的节点上,相互为用,作者在《枕杜记》的开篇之处留下了悬念,且在后续缓慢而又深情的叙事节奏中回答了最初留下的疑问:“我”逃离这些“乌鸦般的诗句”,并不是因为憎恶杜甫或者杜诗,而是无论“我”身处何时何地,都无法摆脱它们的召唤。随着悬念的推进与揭示,叙述在拆散、分解、交织、融合中转换,也更为自由与灵动。
二、“诚实”与“文气”:散文的写作筋骨
对于写作者来说,散文的叙事模式可以时常翻新,散文的写作筋骨则是贯穿于每一次写作之中稳定的、延续的那一部分,它们是作为写作者的写作观的重要部分而存在的。李修文认为:“在中国古代的散文传统里,两个特质至关重要:一是诚实,所谓‘修辞立其诚’;二是文气,所谓‘直言曰言,修辞曰文’。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态度和审美,这两条文章的筋骨是没有办法变化的,它们绝对不会因为时代和科技的因素而发生主体的崩塌。”①李修文:《写作札记九则》,《新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文章的“立诚”问题,从作家的角度出发,即作家如何在文章中展示真我的问题。作家在文章中展示的“自我”,由于在日常生活与实际书写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往往不会是单纯的“自我”,如钱钟书所说:“见于文者,往往为与我周旋之我;见于行事者,往往为随众俯仰之我。”②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4页。较为难得的是,通过对比阅读李修文的访谈录、创作谈与他的文学作品,从行事到见文,都能读到他的诚实与诚意。在《枕杜记》中,“我”并未在文章中刻意将自我塑造为一个忠实的杜甫跟随者;正如前文分析,“我”一直渴望逃离杜甫与杜诗对“我”的影响,但现实生活告诉“我”,逃之无益,逃也无用。诚实的“自我”之后是李修文写作的诚意。李修文承认,“有的批评家讲《山河袈裟》有一些抒情过度,我承认这一批评。因为在写《山河袈裟》的时候,我有一种对自己巨大的、热烈的欢迎,即我能够重新成为一个作家了”③李修文:《山河人间与我——武汉大学驻校作家启动仪式上的演讲》,《写作》2020年第6期。。于散文而言,“抒情过度”不一定是一种缺陷或者弊端,能通过文字传达出作者本人深厚的情意,是对作者表情达意能力的一种肯定,也是作者抒情风格的一种显现。《枕杜记》中颇有一些蕴含强烈情绪的表达,例如:“我”在东北的雪夜里狂奔,在他乡看见故友懂事的小儿女时流了一脸的泪水,在高热之下跑遍县城的书店寻找一本杜甫的诗集……也许对读者来说,难以想象这些行为能出现在作者的日常生活中。但对“我”来说,在身边之人的际遇与深藏心中的杜诗进行碰撞,从而引起心中强烈而澎湃的情感之时,“我”的一些行为是不可控的,此时的“我”急需一些行动去帮助自我疏泄心中的情感。同时,当“我”在强烈的情绪中感到不安和迷茫,“我”也需要这些行动去帮助“我”在一片混沌之中找回内心的安宁。文学本身具有疗愈的功能,然而只有诚实坦荡地直面自己的困境,文学才能舒缓创作主体的伤痛,以及安抚每一位有着同样困惑的读者。在面对“抒情过度”的批评与质疑之前,李修文仍然坚持有“我”的写作,这也是一位作家面对写作拿出来的最好的诚意。
“文气”,在李修文的散文之中表现为一种诗一般的美学风貌。李修文可说是一位古典型的散文家,他注重字词的锤炼、画面的勾勒,使情感在如诗如画的语言中自然流淌而出,他的散文也自然而然具有了一种诗的气质。
到了这时候,我难道还要将我的命数从杜甫的命数以及这草木人间的命数里挣脱逃离吗?在那些句子里,又有哪一字哪一词不曾见证我的八字以及山河众生的八字?就像雾气空茫却分明沾染了每一桩名物,又像那年轻人的哭声为着一物却又裹杂着多少苦寒与报偿,一字一词,全都真真切切,这真切打哪里长出来的?且容我略作狂想,它是从袒露在脚边的遗骨里长出来的,由是,“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它是从刚刚被饿死的儿子身上长出来的,所以,“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是的,在惊魂未定的羌村,在故旧凋零的夔州,在“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的哀哭声中,在“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的劫后余生中,它们长了出来,只因为,那一具不得安宁的肉身,从未隔岸观火,他是孤城荼毒的一蓬草,也是寒夜荒村里的一碗粥,他是好不容易才得来的黄粱一梦,也是黄粱一梦里死命伸向阳间尘世的一只手。①李修文:《诗来见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8-69页。
在《枕杜记》的这段文字中,李修文用了三个看似松散随意的反问句,在有限的空间之中呈现了情感的递进与话题的转移,文章的重心也由“我”挣扎着逃离杜诗,转换为“我”终于意识到无处可逃,转而思考杜诗之中的真切从何而来;紧接着,他再引用四句杜诗为读者转述杜甫眼中人民遭受的战乱之难与离别之苦。最后,他再用“一蓬草”“一碗粥”“黄粱一梦”“一只手”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他眼中的杜甫。用写物之词来形容人,既形象又陌生,却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杜甫对民众遭遇的不忍,对民众生存的关怀。这些用来描述杜甫的词汇,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但又与普通的一粥一饭、一草一木、一梦一醒相区别,它们在作者充沛的情感的灌注之下,具有了丰富的象征意味。李修文用诗意的笔法,以寻常事物勾勒杜甫的生活图景:他从断壁残垣而来,往孤城荒村而去。此间路上,有战火,有饥荒,有遗骨,有哀哭。他明知前路意味着更多的苦楚与哀愁,而他仍然执笔向前奔走。即便身无长物,他也要用笔为民众送上一蓬温暖的草,抑或是端上一碗温热的粥。原本凄凉冷寂的孤城荒村图,因为“一蓬草”与“一碗粥”的点缀而焕发生机。同时,这一组词汇以共同的数词“一”相串联,又在搭配的量词和名词上加以变换,在形式上前后对应,在音节上错落有致,使散文呈现出如诗般的节律感。“文气”,既包括创作主体之气,也包括作品之气,创作主体特有的思维方式、行文方式作用于作品之上,便完成了主体之气质在作品之气韵上的延伸。李修文精湛的叙事技艺、丰富的学识积累、真诚的人性关怀,在他对自我进行拷问的过程中,全渗入了他的文字。在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在遣词造句上,李修文向诗歌取法,注重句式的均整以及字词的选用,这使得他的散文亦有清晰的内在节律;在深层意蕴上,李修文以古典且诗意的诉说方式,由“我”的个人际遇推及人民的悲欢离合,“我”对生命的思考与理解,因为李修文的诗性关怀而走出了自我的天地,走向了广阔的山河人间。
李修文说,他一直在创作之中“发自肺腑地在渴求某种相对鲜明的个人美学”②李修文:《写作札记九则》,《新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童庆炳认为,“风格是文体呈现的最高范畴。风格的形成是某种文体完全成熟的标志,因此也是文体的最高体现。没有风格的作家,其作品也就谈不到文体,其创作也就没有获得真正的胜利”①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李修文将“诚实”与“文气”作为散文写作的筋骨,贯穿在他每一篇文章的血脉之中,成为他的散文一种不可忽视的个人风格。
三、“真切”与“实在”:散文的内在质感
《枕杜记》以“我”之于杜诗的情感变化过程为线索,串联起“我”的眼前所见之事与杜甫写下的诗句。《枕杜记》并不是在考据杜诗的版本,也并非为杜诗的字词句作注解。文中提到的杜甫的诗句,也与它们本身的文学史地位无关,它们仅是李修文在每一个情之所至的时刻所想到的诗句。《枕杜记》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便是“真切”与“实在”。解读“真切”与“实在”的具体内涵,首先需要回归杜甫其人其诗本身。
冯至在《杜甫传》中写道:“他的诗也有一部分是古典的堆砌,是技巧的玩弄,这些诗都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多半是他为了求得一官半职,投赠当时有权势的王公大臣的时候,当他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只感到‘天颜有喜近臣知’的时候,当他在西蜀荆潭与各处幕府的官僚们相周旋的时候。这些诗,总的来说是不值得我们赞赏的。”②冯至:《杜甫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页。从青年到暮年,杜甫历经数次漫游,辗转于全国各地,为了生计与仕途,也作过许多“不值得赞赏的诗”。在离开长安之后,杜甫因“安史之乱”流亡于各地,才在战火纷飞中近距离接触到了底层人民,才大面积地在诗歌中记录人民饱受战争、贫困、疾病之苦的生活。相较于普通民众,诗人与作家往往比他们多经受几重感受苦难的过程。眼见人民流离失所是为第一苦,提笔言之是为第二苦,思考能言否则为第三苦。叙写苦难,首先必须贴近人民真实的生活感受苦难,其次还需冒着风险直书苦难。细读杜甫的《兵车行》《悲陈陶》《春望》和“三吏”“三别”,字字句句都书写着诗人因人民遭遇而生的切身之痛。然而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亲眼见着“幼子饥已卒”,晚年居无定所,只有一只小舟可以依靠,转徙于湘江之上。杜甫的诗之所以动人,不仅仅是因为杜甫写实的天赋与叙事的技法,更多是因为他即便在自身沦落困顿之时,无论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变故还是年迈出征的士兵,都能引起他最真切的关怀,杜甫的诗句也因此而获得“实在”。对于杜甫来说,诗歌承担着一种关注草木人间、为百姓发声的社会使命。因此,便不难理解《枕杜记》中的“我”最终接受了杜诗对“我”的召唤:
于是,在以上诸地,在真切中,实在诞生了——这实在,绝非虚在,它不是渐上层楼,而是跌跌撞撞,顶多只是吞下了惊恐再往前赶路;不是借酒装疯,而是唯有凭借醉意,才敢吐出一肚子的劳与苦,又或者,根本就不敢醉。这条实在的路,不来自清虚阁,也不来自广寒宫,它来自桑麻糟糠的诞生之地,来自坟丘上的漏洞和从漏洞里钻出的野狐,这条路,十万八万里地向前伸展,只为了等待一个人踏上它,那个人,既是他自己,又是所有人,这个人将成为所有人的分身而获得实在,所有人又将在他的布衣和肝胆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而后,这个人终于出现了,形单影只,自说自话,但是,天若不生他,众生何以为众生,诗又何以成为诗?③李修文:《诗来见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9页。
《枕杜记》得名自《枕中记》。《枕中记》者,“世间一场大梦”之意,《枕中记》之梦,意指富贵荣华皆为虚在,既如此,何为实在?《枕中记》卢生自叹困顿,故道士遗枕,令卢生梦见其纡青佩紫,及寤,主人“蒸黍未熟”,故名曰“黄粱梦”。《枕杜记》中亦有梦,乃“庄生梦”,等齐庄周与蝴蝶,谓之齐物。李修文自言杜甫“既是他自己,又是所有人,这个人将成为所有人的分身而获得实在,所有人又将在他的布衣和肝胆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在这“所有人”之下,隐藏着他“等齐”杜甫的内心驱动。杜甫对于作者而言,并非是历史的符号,他既是被“我”所观照的,在历史之中的“他者”,又是观照我的,现实之中隐含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继承了“蝶梦”的书写传统,解构了“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我”之于杜甫与杜诗的复杂感受是真切的。事实上,“我”对杜诗的逃离,不是出自“影响的焦虑”,而是因为丰富的痛苦。“我”身为知名青年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因为个人的困顿痛苦万分。然而“我”在杜诗所蕴含的巨大苦难之前,“我”之困顿相形见绌,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我一直在躲避他的诗”,不如说“他的诗一直在躲避我”。直到“我”的生命体验推动我将目光从自身看向人间山河,为现实之苦而苦,“我”才能和杜诗同频共振,才能在某种程度上与杜甫对话,这个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所以李修文说杜甫是“好不容易才得来的黄粱一梦”。选择杜甫与杜诗,也就意味着选择了将草木人间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选择了将记录民族苦难作为自己的责任。在直面人生的惨淡之时,即便写作者心中有惊涛骇浪,却难以用言语传递出来。这些苦痛在内心反复盘旋上升,非诉诸于文字而不能解。“实在”则与“虚在”相对应,李修文与杜甫一样,不愿意站在空中楼阁,描绘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他们立足于脚下的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抱有最真挚的关怀。李修文在《枕杜记》中写出的杜甫的那些诗句,虽然不是杜甫诗歌中广为人知的那一部分,但因为李修文在文中展现的与杜甫相同的对生活的忠实,读者并不会因为陌生的诗句感到理解的困难,而且还能在跨越古今的文字之中感受到中国文人厚重的责任感。《枕杜记》的表层情绪链是“我”对杜甫与杜诗由逃避到选择的过程,然而其深层的内在情感却是纯然不变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成长,每一位中国作家的书写,都离不开脚下的这片土地,离不开身边同生同长的人民。书写中国人民真实生活的作品,才是真实而又富有生气的作品。
李修文在交错的时空框架中,展开富有特色的散文叙事实验,它既包含对传统意义上的叙事技巧的转换,又是在新的文体观念下叙事立场的建立。《枕杜记》就像一个有机体,按照自己独有的结构生长,既丰富了散文自身的内容,又为散文的书写拓宽了边界。
——评王新芳、孙微《杜诗文献学史研究》
——以宋代蜀人三家杜诗注辑录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