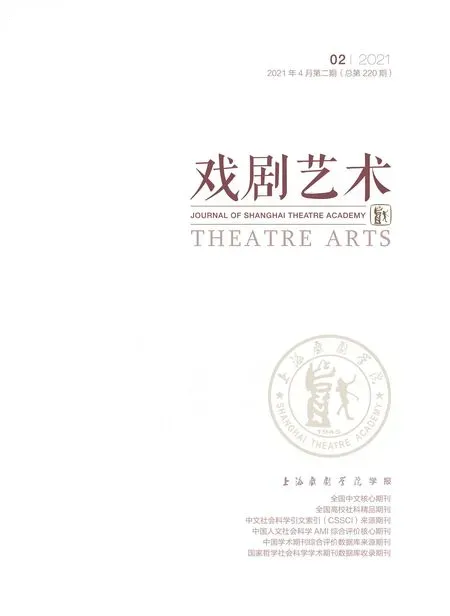“自我惩罚”与“疾病书写”
——田纳西·威廉斯悲剧创作评析
晏微微
古典悲剧、巴罗克悲剧和现代悲剧三者的实质区别在于从神到人到个人。(1)任生名:《西方现代悲剧论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0页。如果说希腊悲剧的主人公的意识具有神性,那么文艺复兴时期悲剧的主人公就具有人性,而资产阶级悲剧主人公则具有个人性,或曰私人性。(2)任生名:《西方现代悲剧论稿》,第92页。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创作是“私人悲剧”这一现代悲剧的代表。(3)(英)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现代悲剧是一种文化象征,它不仅以想象的方式阐释世界的意义,而且为人本体生存的真实状况提供解释系统,是帮助人对待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田纳西·威廉斯认识到人类在对既定秩序的挑战过程中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他以“乱伦”主题和“自我惩罚”的机制来强化欲望书写,以疾病为认识手段,在戏剧创作中积极探索摆脱悲剧宿命的可能性。
田纳西·威廉斯被美国戏剧、文学界推许为尤金·奥尼尔之后的“美国剧坛第一人”,哈罗德·布鲁姆甚至认为,“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置之案头和搬演场上都同样生动精彩,在我看来,他甚至超越了尤金·奥尼尔,是真正的文学戏剧家。”(4)Harold Bloom, ed., 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 Tennessee Williams-Updated Edition,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2007), vii.威廉斯的创作在现代悲剧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学界的相关研究比较薄弱,其中,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的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他指出,田纳西·威廉斯将悲剧的根源归结为“精神介入了性爱与死亡之间本来就是悲剧性的动物性斗争”,(5)(英)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第115页。其悲剧的宗旨是“要越过这些精神幻觉而回到真实的原始节奏”。(6)(英)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第120页。他认为田纳西·威廉斯“不是奥尼尔竭力想做的那种戏剧哲学家,而是只需通过个例进行简单演绎的剧作家。”(7)(英)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第115页。在其戏剧中,“一切被归结为性行为”。(8)(英)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第116页。性的确是田纳西·威廉斯悲剧的核心主题,但认为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法是“通过个例进行简单演绎”这一论断值得商榷。作为美国最伟大、最多产的剧作家之一,田纳西·威廉斯不仅通过描写性爱与死亡之间的斗争来表达现代悲剧意识,更是通过数十载的不懈探索来为现代悲剧诗学添砖加瓦。追寻威廉斯早期剧作到成名期和成熟期重要作品的创作轨迹可以发现,威廉斯将性作为自由和生命力的隐喻,以“自我惩罚”的机制来强化欲望书写,提升了遵循“情欲法则”的牺牲者悲剧的崇高感。在悲剧创作的探索过程中,威廉斯发展出一种关于现代欲望的书写方式。在威廉斯看来,本能欲望受到压抑是疾病产生的根源,清醒认识到自身的本能欲望者为了从精神困境中解脱而采取极端手段,如此所产生的看似悲惨的结局却未必是真正的悲剧。
下文将分析解读《天使之战》(BattleofAngels, 1939)和《净化》(ThePurification, 1940)等威廉斯的早期戏剧,对照《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1947)和《夏与烟》(1948)及其改编剧《夜莺的怪癖》(TheEccentricitiesofaNightingale, 1964)等威廉斯成熟期的悲剧作品,试从“自我惩罚”和“疾病书写”这两个方面来评析威廉斯的悲剧创作。
“自我惩罚”与现代悲剧
从易卜生和斯特林堡开始,西方悲剧进入现代悲剧时期。(9)任生名:《西方现代悲剧论稿》,第104页。雷蒙·威廉斯指出,现代悲剧尽管有多种表现形态,诸如社会悲剧、私人悲剧、个人悲剧等,但本质说来都是一种“自由主义悲剧”。(10)陈奇佳:《欲望的分裂与兽性的剩余——论田纳西·威廉斯剧作的悲剧主题》,《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6期。传统礼教、世俗偏见和民间陋习是现代悲剧所批判的对象,人类为追求自由生存与之对抗而产生了悲剧的结局。洛尔卡等杰出作家将自由生存与社会规则冲突之下人类所经历的痛苦和挣扎揭示得鲜明而深切,威廉斯则通过淡化“荣誉法则”而强化人本体欲望的书写,通过给坚持“情欲法则”者赋予某种“正义性”和“自我惩罚/净化”的机制来强化坚守欲望者的崇高的悲剧精神。
从威廉斯的处女作《这个词就是美》(BeautyIstheWord, 1930)问世到他凭《玻璃动物园》(1944创作,1945年在百老汇演出并大获成功)扬名全美之前,威廉斯创作了至少37部剧作。这些早期剧作可谓题材风格多样、思想蕴含丰富,其中有《开罗!上海!孟买!》(Cairo!Shanghai!Bombay!, 1935)和《魔塔》(TheMagicTower, 1936)等感伤浪漫的悲喜剧,也有《日下残烛》(CandlestotheSun, 1936)和《与夜莺无关》(NotAboutNightingales, 1938)等社会斗争题材正剧,而最能体现威廉斯戏剧独特风格的当数《天使之战》和《净化》(1944)等表现情欲——即人的生命力这种原始力量——所引发的现代悲剧的作品。
《天使之战》描写流浪诗人瓦伦丁来到一个南方小镇,与病入膏肓的纺织品商店店主杰布的妻子迈拉相爱并发生了性关系。迈拉的父亲早年因为拒绝遵从当地的种族戒律而惨遭暗算,所经营的娱乐场也被大火焚毁。得知迈拉怀孕的消息后,妒火中烧的杰布向迈拉坦白她父亲死在自己手里,然后他将迈拉击毙,反诬瓦伦丁是凶手。瓦伦丁被镇民以私刑处死,杰布死于癌症。《天使之战》的悲剧来自作为一种救赎力量的情欲与扼杀生命活力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在威廉斯笔下,瓦伦丁是带来性爱和生命力的“天使”,与天使作战的,是在迈拉与杰布“合法”婚姻的掩盖下充斥着私刑、暴力和种族偏见的黑暗的社会现实。瓦伦丁和迈拉是在这场性爱与死亡的斗争中牺牲的勇士。《天使之战》表现了早期的威廉斯悲剧诗学所体现的与清教社会相抗衡的“情欲法则”。
除了多次提及契诃夫、劳伦斯和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等三位对其影响最大的作家之外,威廉斯自称还受到了洛尔卡等剧作家的影响。(11)Esmeralda Subashi, The Influence of Federico García Lorca on Tennessee Williams' Plays, Juan Carlos University Editors(Santander: King, 2012), 351.情欲法则与荣誉法则的冲突是西班牙作家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的杰出悲剧《血的婚礼》(1933)的中心主题。1937年至1938年,威廉斯在依阿华大学的戏剧艺术系学习,期间曾接触过洛尔卡戏剧,到了1947年,他已对洛尔卡非常熟悉,在当年12月31日给琼斯(Margo Jones)的信中写道:“我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还有我的克莱恩和洛尔卡的诗歌。”(12)Albert J. Devlin and Nancy M Tischler, eds,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Tennessee Williams, Volume 2 (1945-1957),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04), 140.威廉斯糅合洛尔卡戏剧的元素,通过淡化“荣誉法则”并强化人本体欲望的书写,创作出一部意蕴深厚的“私人悲剧”——《净化》。
诗剧《血的婚礼》是洛尔卡的悲剧代表作,描写了安达卢西亚山区村子里的一户农家。丈夫和大儿子多年前被邻居家的男人杀死了,母亲和幸存下来的小儿子相依为命。儿子靠勤劳致富,购置了一个葡萄园,并爱上了邻村一个富裕鳏夫的女儿,两位家长为儿女订下了婚约。姑娘的初恋情人莱昂纳多的父亲是杀死她未婚夫父亲和哥哥的凶手,姑娘与莱昂纳多分手后,双方都在与强烈情欲的斗争中苦苦煎熬。莱昂纳多两年前与姑娘的表姐成了亲,如今姑娘也决定嫁人。在举行婚礼的那天,新娘与莱昂纳多私奔了。母亲知道她将又一次经历“流血的时刻”。事关家族荣誉,她叫儿子和家族的人一起去追赶。两个情敌在树林里相遇,互相用刀刺杀了对方。
威廉斯的诗剧《净化》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美国西南部的一个牧场。时值一场旷日持久的旱灾,镇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来自卡萨布兰卡家族的伊琳娜被杀害了。伊琳娜的家人要求伸张正义,镇上的一个中年贵族牧场主担任法官主持审判。伊琳娜的哥哥罗萨里奥在法庭上形容妹妹拥有自由的灵魂和热情奔放的天性,但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嫁给了卡萨罗哈家族的牧场工人。随后,卡萨罗哈家的印度仆人路易莎透露:罗萨里奥和伊琳娜是一对乱伦的情人。罗萨里奥承认与妹妹发生性爱关系的事实,进而指控牧场工人是杀害伊琳娜的凶手,路易莎是帮凶。牧场工人痛诉妻子的冷酷无情给他们的无性婚姻所带来的巨大痛苦,承认由于目睹妻子与其兄长在谷仓里发生性关系,他动手砍死了伊琳娜。两个情敌在法庭上扭打在一起,被众人拉开了。在戏的结尾,罗萨里奥拔出一把刀刺进自己的胸膛,完成了他的“净化”。罗萨里奥的母亲悲痛万分,她要求递给牧场工人一把刀,他没有接受,而是拿出他自己腰间的佩刀,走出法庭自刎了。此时下起了大雨,干旱结束了。
《净化》与《血的婚礼》在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的设置等方面不尽相同,但在主题、语言、歌队和意象的运用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两剧都描写了由两个男人争夺同一个女人而形成的三角恋的故事;两剧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欲望的必然性和结果。两者都传达了这样一种观点: 无论多么冒进,无论结果如何,都要保持内心深处的本能。(13)Jose I. Badenes and Triangular Transgressions: “Tennessee Williams’ The Purification's Debt to Federico Garcia Lorca's Blood Wedding”, in Old Stories, New Readings : The Transforming Power of American Drama, edited by Miriam López-Rodríguez, etal.,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5), 105-106.两剧都有诗歌般的语言节奏和合唱/歌队的运用,土地、干旱、水、血、荣誉、月亮、马和刀等意象有力地辅助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威廉斯受到洛尔卡的影响,但他的创作从两个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威廉斯风格:一是“乱伦”主题的加入和“自我惩罚”的机制;二是“疾病书写”的悲剧诗学。本文的下一节专论“疾病书写”,在此仅分析威廉斯戏剧的“乱伦”主题和“自我惩罚/净化”机制。
在威廉斯的笔下,“乱伦”是血亲关系人由精神之爱所引发的肉体之爱。乱伦的当事人是脆弱敏感、精神思想高度统一的兄妹二人,他们如同共有一个灵魂。性是自由的隐喻,是蓬勃的生命力的象征,而血亲之间的性爱是被禁止却又不可避免的、致命的欲望的表现,它所隐喻的是对自由精神的极致追求和对现实的大胆反叛。尽管《血的婚礼》没有涉及乱伦情节,但洛尔卡曾根据基督教《圣经》中关于大卫的儿子阿姆农对妹妹塔玛尔的爱的故事创作了诗歌《塔玛与阿农》(1928)。(14)Badenes, “Tennessee Williams’ The Purification's Debt to Federico Garcia Lorca's Blood Wedding”, 108.威廉斯剧作中的主题或许受到了洛尔卡的影响,但威廉斯创作的故事具有独特性。圣经故事和洛尔卡诗歌中的妹妹均未回应哥哥的“不正当的爱情”。洛尔卡诗歌中被欲望吞噬的年轻人假装生病,当他的妹妹来到他的房间照顾他时,他强奸了她。他的冒犯致使他的兄弟押沙龙杀了他,罪恶得到了救赎。《净化》中的乱伦却并非出自其中一方的邪恶的欲望,而是情投意合的兄妹两人热烈地分享激情,剧中“合法的”婚姻反而具有“不正当”的本质——“牧场工人”本是个受雇于布兰卡家族的修理工,对蔑视他的伊琳娜产生了征服的欲望,执意“想得到某种东西,否则就要毁掉它!”他本以为与伊琳娜结为夫妇就意味着攫取了布兰卡家族所拥有的一切,但拒他于千里之外的妻子夜夜与情人(哥哥)同床共枕,牧场工人发现除了用来修理栅栏的那把白色斧头之外,他什么都抓不住。恼羞成怒的他不是出于对情敌的嫉妒而去与之决斗,而是抡起斧头砍向了那个他得不到的女人。除了给乱伦赋予某种“正义性”之外,威廉斯还以“自我惩罚/净化”机制来强化了崇高的悲剧精神。洛尔卡的诗歌和戏剧通过“复仇”(押沙龙杀死强奸妹妹的阿农)和“决斗”(莱昂那多和新郎刺死对方)来实现惩罚和救赎,而威廉斯的《净化》一剧结尾在法庭上将杀妻案的前因后果告白于天下之后,死者的情人(哥哥)和丈夫相继自杀身亡。这种自我救赎/净化实现之后,久旱的小镇立刻下起了大雨。红色是《血的婚礼》的底色,它象征着鲜血和火一样的激情。而白色则是《净化》的底色,剧中身着白色纱裙的伊琳娜的鬼魂两度出现在法庭上,纯净的白色象征着救赎和净化。自诩“对法律程序的了解程度不亚于一只消息灵通的兔子”的法官感慨道:“在这片平原上,在这些山脉之间,我们似乎培育了一种比法律更深的荣誉感。这样很好。”(15)Tennessee Williams, 27 Wagons Full of Cotton: and Other One-act Play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53), 62.
疾病书写与现代悲剧
如上文所言,除了“乱伦”主题和“自我惩罚”的机制以外,《净化》一剧中的“疾病书写”也是威廉斯悲剧创作的重要手段。《净化》女主人公伊琳娜及其丈夫的性格特征与《血的婚礼》中的新娘和新郎相仿佛——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欲望,也有着冲动的个性,但伊琳娜的情人(哥哥)的性格与《血的婚礼》中的情人莱昂那多不大相同:莱昂那多内敛沉稳,娶妻生子之后还多次半夜骑马赶远路到姑娘家的窗外静静地驻足凝视,但他克制了与姑娘发生性关系的欲望。在婚礼当天,私奔的行动也不是由他发起,而是新娘“第一个下楼梯”,给马“换上了新的笼头”,还给莱昂那多“带上了马刺”。(16)(西)洛尔卡:《血的婚礼 加西亚·洛尔卡诗歌戏剧精选》,赵振江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312页。罗萨里奥的个性则明显具有神经质的、非理性的特点。在法庭上当法官要求“谈谈令妹”时,他的诗歌般的碎片化语言和癫狂迷醉的神态,令父母发现他似乎“疯了”。印度仆人路易莎也确信“年轻人疯了,这倒是真的”。(17)Williams, 27 Wagons Full of Cotton: and Other One-act Plays, 37.她的依据是每当他在夜里骑马赶到卡萨罗哈牧场,一路上他都“赤裸着脊背,大声喊叫,做着可笑的手势”。但是随着庭审过程的推进,我们发现,行凶者(伊琳娜的丈夫)和帮助清理凶杀现场的仆人(路易莎)都没有否认罗萨里奥的指控,罗萨里奥的“疯话”都是真的,他的精神错乱是对伊琳娜的情欲所致,疯癫的罗萨里奥洞悉伊琳娜悲剧的全部真相。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认为,艺术家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是在精神上对病患的偏爱。作家多半不是为疾病而描写疾病,而是善于把疾病作为认识手段,让人看清事物背后的真相。(18)方维规:《“病是精神”或“精神是病”——托马斯·曼论艺术与疾病和死亡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曼氏在《维也纳弗洛伊德八十华诞庆贺会上的讲话》(1936)中指出,“病,即神经病被证明是人类学头等的认识手段”。(19)方维规:《“病是精神”或“精神是病”——托马斯·曼论艺术与疾病和死亡的关系》。威廉斯便是一位“把疾病作为认识手段”来进行人物心理探索的艺术家。病态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威廉斯“实现精神、诗意和象征意图而进入文学境域”(20)(德)托马斯·曼:《一本图集的序言》(1921),《德语时刻》,韦邵辰、宁宵宵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79页。的重要手段。
1900年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指出精神病是情感和本能受到压抑的结果,而这种压抑产生于人的本能欲望与社会文明之间的严重冲突。弗洛伊德学说的本质是一种关于人类文明的悲观论,认为对无意识的本能和欲望的压抑是人类必须为文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精神分析学说对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劳伦斯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这种悲观论,他认为可以通过建立男女之间的新关系,通过回归两性之间充分自然的状态,来调和两性关系的紧张、对峙和冲突,实质上也就是主张恢复人的自然生存,来抵抗现代化工业文明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压制,来调和自然与文明的对立。(21)任生名:《西方现代悲剧论稿》,第172页。威廉斯受到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但他的悲剧诗学观点无疑更接近劳伦斯的看法。1942年5月威廉斯将劳伦斯小说《你抚摸了我》(YouTouchedMe!)改编成同名三幕浪漫主义喜剧。在该剧的序言中,他肯定了劳伦斯的性描写所体现的“对生命的赞美和对消极/悲观的憎恨”。(22)Nicholas Moschovakis and David Roessel, “Introduction” in Mister Paradise and Other One-act Plays by Tennessee William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5), xxix.
威廉斯一生都专注于疾病书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把精神病的研究视为毕生的工作和悲剧艺术创作的重要路向。威廉斯的姐姐罗丝在少女时代接受了治疗精神病的脑部手术,那次美国历史上的首例双侧前额脑白体摘除手术以失败告终,术后罗丝的智力永远处于6岁孩童的水平。威廉斯没有做精神科医生,而是把对精神病病因的探索作为艺术创作的内驱力和认识事物本质的手段。在其作品中,精神痛苦变成了无处不在的东西,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有时候,它是一个人物的幽灵般的、脆弱的美;在更多的情况下,身体疾病是它的表征。正如弗洛伊德的临床实验结果所表明的,这种精神痛苦产生的根源是性欲受到压抑。在威廉斯看来,这种压抑若得不到排解,势必会导致悲剧的产生;清醒认识到自身的本能欲望者为了从精神困境中解脱而采取极端手段,可能会得以摆脱悲剧宿命。《夏与烟》及其改编剧《夜莺的怪癖》的对比研究或可还原威廉斯这种悲剧诗学生成的轨迹。
威廉斯曾多次修改甚至重写本人已经发表或上演过的作品。除了《夏与烟》之外,他还曾改写了《天使之战》《满满的27车棉花》(27WagonsFullofCotton, 1945)、《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下文简称《猫》)、《两个人的戏剧》(TheTwo-CharacterPlay, 1967)和《忏悔室》(Confessional, 1967)等剧。(23)威廉斯将《天使之战》改写成《琴神下凡》(Orpheus Descending, 1955),《满满的27车棉花》改写成《老虎尾巴》(Tiger Tail, 1977),《两个人的戏剧》改写成《呐喊》(Out Cry, 1973),《忏悔室》改写成《小手艺的警告》(Small Craft Warnings, 1970)。我们有理由相信,作家对本人旧作的改写主要出自以下考量。一是为了提升作品的接受度,作者依照他人(作者同行或作品受众)的建议所进行的改写。这一考量可以《猫》剧的两个版本为例。该剧有两个发行本,即威廉斯偏爱的原版和1955 年纽约演出版。当年在威廉斯给百老汇知名导演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看了《猫》剧的剧本之后,卡赞明确提出了给大阿爹增加戏份等三条建议。(24)卡赞的三条建议是:其一,他认为第二幕结束之后大阿爹就不再出场这一情节需要做改动,因为他“感到大阿爹这个人物太生动了,太重要了,不能就此在戏中销声匿迹,除非加上他在第二幕结束后在后台大声叫喊这段戏。”其二,布里克在第二幕中跟大阿爹进行了交谈之后,他身上应当产生一些明显的变化;其三,玛格丽特这个人物应当博得观众更明显的同情。详见田纳西·威廉斯:《外国当代剧作选(3)》,东秀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第360页。从威廉斯给纽约演出本所写的作者手记来看,威廉斯对此并不完全认同,但他还是采纳了卡赞的建议,并解释说这是因为他相信能“从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的导演身上学到对自己作品大有教益的东西”。他表示愿意为了推进与卡赞的顺利合作而修改剧本——“虽然卡赞这些意见并不是以最后定论的形式提出的,可是我还是要卡赞来导演这戏,我生怕如果自己不根据他的观点重新审阅一下剧本,他就会对此不感兴趣。”(25)(美)田纳西·威廉斯:《外国当代剧作选(3)》,第361页。作家改写作品的第二个考量是为了使作品更加充分地传达核心题旨,或者说更加接近作家的创作意图。威廉斯的创作意图往往是复杂的,有学者指出:“在处理像田纳西·威廉斯这样复杂的剧作家时,必须了解的是,在他的写作中没有关于意图的绝对性。”(26)Ross Z, “Opening ‘The Notebook of Trigorin’: Tennessee Williams's Adaptation of Chekhov's The Seagull”, Comparative Drama, 2011, 45(3), 247.正是这种创作意图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致使威廉斯在反复修改或重写旧作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创作理念,不断厘清艺术思维的真相,《夏与烟》的改写无疑是出于这一考量。
在《夏与烟》之前问世并让威廉斯名声大噪的《玻璃动物园》和《欲望号街车》都是有关女性情爱经历的大悲剧。人们沉醉于威廉斯给战后美国剧坛所带来的“清新之风”,疼惜劳拉的如同玻璃小动物一般“经不起从架子上挪开”的脆弱的美,为被时代前进的滚滚车轮所抛弃的南方美女布兰奇的悲惨命运而落泪。人们期待威廉斯为优雅没落的南方再谱一曲挽歌,却发现紧随《街车》之后威廉斯所呈现的这个南方故事有些令人费解——它是个悲剧,但又似乎缺乏《街车》那样的社会历史悲剧的感染力。
这部“悲剧”的主人公“阿尔玛小姐”的父亲是密西西比州光荣山的教区长。阿尔玛是父亲的得力助手,她在教堂里布道,在节日活动上献唱,给教区的人们上音乐课,还常年操持家务,照顾神经失常的母亲。清教环境的浸染使阿尔玛格外尊崇精神的圣洁,她多年以来暗恋邻居约翰·布坎南,却刻意与之保持着距离。青年医生约翰曾放荡不羁,他与阿尔玛产生了灵魂与肉欲追求的分歧和争论。约翰带阿尔玛一起去了他常去的斗鸡场和赌场,还试图与她发生更亲密的关系,但阿尔玛拒绝了约翰,因为他表现得“不是个绅士”。(27)Tennessee Williams, Tennessee Williams Plays: 1937-1955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2000), 615.约翰的情人罗莎的父亲射杀了老布坎南医生之后,约翰戒酒戒赌并全心投入工作。数月里闭门不出的阿尔玛找到约翰,向他倾诉说她最终发现“那个说‘不’的女孩……去年夏天在她体内燃烧的某种东西的烟雾中窒息而死了”(28)Williams, Tennessee Williams' Plays: 1937-1955, 635.,但是约翰拒绝了阿尔玛,因为他意识到“我真正想要的不是身体上的你”。(29)Williams, Tennessee Williams' Plays: 1937-1955, 637.得知约翰已与曾跟随自己学音乐的年轻姑娘奈丽订了婚的消息之后,阿尔玛主动与陌生的旅行推销员发生了一夜情。“她爱的人爱上了别人,于是阿尔玛小姐过上了肆意放荡的生活。”(30)C. Robert Jennings, “Playboy Interview: Tennessee Williams”, in Conversations with Tennessee Williams, ed. Albert J. Devlin,(Jackson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6), 228.这样的人生经历的确悲惨,但阿尔玛这个人物不像敏感而脆弱、无法面对这个世界的劳拉,或是在阶级对抗中被野蛮环境所摧毁的布兰奇那样容易博得同情;阿尔玛与约翰两人对性的态度的“互换”则是个难解的伦理谜题——正如1948年《夏与烟》在百老汇上演之际约翰·梅森·布朗所指出的,这个戏“在最必要和最能成功的地方失败了。它表明坏男人可能变成好男人,好女孩可能变成坏女孩,但是他们改变本性这一过程的真正复杂性并没有被揭示出来。”(31)Jacqueline O'Connor, “The Strangest Kind of Romance: Tennessee Williams and his Broadway Critic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ennessee Williams, ed. Matthew C Roudané,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56.或许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夏与烟》在百老汇的接受。
1948年10月6日,《夏与烟》登上百老汇的音乐盒剧院(Music Box Theatre)的舞台,演出了102场,与1945年《玻璃动物园》在百老汇连演561场和1947年《街车》的855场演出盛况不可同日而语。1952年广场圆形剧团(Circle in the Square Theatre)成功演出的《夏与烟》成就了外百老汇的崛起,使该剧成为美国演剧史上的里程碑,但威廉斯本人并不满意,他对《夏与烟》寄予很高的期望,认为这部戏没有完全传达出他所要表达的内容,因而一直在修改这个剧本。(32)Brenda Murphy, The Theatre of Tennessee Williams (London: Bloomsbury Methuen Drama, 2014), 72.时隔16年之后,威廉斯推出了改写本《夜莺的怪癖》,大幅度删减了人物,简化了情节。剧情分幕简介如下:
第一幕,1916年7月4日晚密西西比州光荣山的广场上在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阿尔玛·温米勒献唱结束后到石雕天使喷泉旁与父母会合,一直在旁默默注视她的约翰坐下来与阿尔玛聊起他的医学院假期和阿尔玛心悸的毛病。布坎南夫人走过来带走了儿子。平安夜,阿尔玛在客厅里偷看布坎南家的窗户,温米勒先生严肃地告知女儿镇上有关她的怪癖的传言,责备她组织的文学社是个“怪人的集合”。几分钟后布坎南夫人与约翰来访,在布坎南夫人畅聊儿子的事业成就之际,阿尔玛母亲大谈自己的妹妹与其情人的风流韵事,这让女儿十分尴尬。阿尔玛邀请约翰来参加下一次的文学社聚会。温米勒夫人看到女儿与约翰的手握在一起。
第二幕,约翰与母亲谈论对阿尔玛的看法,约翰认为她很美,而母亲则认为她古怪。第二周的周一晚上文学社成员在温米勒家里举行每周一次的集会,阿尔玛将迟到的约翰介绍给大家。约翰的母亲赶来粗暴地带走儿子。阿尔玛深夜来找老布坎南医生看病,约翰接待了她。他用听诊器检查后说,阿尔玛心底有个微弱的声音在说“阿尔玛小姐很孤单”,两人计划第二天晚上约会。布坎南夫人闯进办公室,阿尔玛愉快地离开了。第二天晚上是新年前夜,罗杰和阿尔玛坐在客厅里一起翻看照片。阿尔玛心神不宁地等着约翰的到来,罗杰认为阿尔玛爱错了人,并说自己愿意永远陪伴她。迟到了25分钟的约翰终于出现了。
第三幕,当晚在公园里,阿尔玛向约翰表示希望在新年钟声敲响时与他做爱。他们来到一家小旅馆。约翰想点燃壁炉,无奈引火的纸和木头都是潮湿的。他把两人的浪漫期待比作这无法点燃的火苗。此时新年的钟声敲响,壁炉奇迹般地点燃,两人慢慢燃起了激情。
尾声。第二年独立日夜晚,阿尔玛坐在石雕天使喷泉旁的长凳上听一位女高音歌手在小镇乐队伴奏下演唱。阿尔玛与一名年轻的旅行推销员攀谈,向他介绍小镇,并提出一起去镇上的“钟点出租房”。在推销员找出租车之际,阿尔玛向石雕天使挥手告别。
《夜莺的怪癖》大体沿袭了《夏与烟》故事的主线——南方小镇教区长的女儿阿尔玛爱上青梅竹马的邻居约翰,但是约翰没有回报她的爱情。在人物设置和情节上《夜莺的怪癖》做了比较大的修改,由原剧描写男女主人公各自生活轨迹的“双线交织”变为集中笔墨进行阿尔玛性心理变化的探索。尽管阿尔玛与《街车》中的布兰奇都是“软弱和分裂的人”,但从悲剧叙事的角度来看,《夏与烟》与强调两性对抗的《街车》相近,而《夜莺的怪癖》则更接近于斯特林堡的《朱丽小姐》。
《夜莺的怪癖》悉数删去《夏与烟》中约翰与阿尔玛和罗莎的感情纠葛、约翰的父亲被罗莎的父亲枪杀、约翰与奈丽订婚等情节,添加了“专横的约翰母亲”这个新的人物。她几次三番在儿子与阿尔玛可能发生性接触的关键时刻出现,对阿尔玛意识到自己的“病因”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上文提到的《夏与烟》中阿尔玛与约翰对性的态度的“互换”这个伦理谜题在《夜莺的怪癖》中得到了解答。正如两剧的剧名所示,剧作家描述的焦点已经从“灵与肉激烈对抗的火焰所散发出来的烟雾”转移到了“怪人的困境”上。《夜莺的怪癖》集中笔墨强调阿尔玛的“古怪”不为人们所理解,这曾给她带来巨大的困扰和痛苦,她的父亲甚至因此而责备她——在他看来,女儿在谈话中使用的“奇妙的夸张的短语”,她的狂野的姿势,她的气喘吁吁,她的口吃以及她夸张的笑声,这些都“只是矫揉造作,这是你可以控制,可以改正的”。(33)Tennessee Williams, Tennessee Williams' Plays: 1957-1980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2000), 445.
威廉斯不断修改剧本的根本动因是要“把疾病作为认识手段”来进行性心理探索,以寻求人的自然本性的释放和摆脱悲剧命运的方法。通过主人公阿尔玛由“性压抑”到“性解放”的痛苦历程的追溯,寄寓人类超越现实、彻底摆脱悲剧命运的理想。而了解“夜莺”(阿尔玛的雅号即“三角洲的夜莺”)的“怪癖”其实就是性压抑所导致的心慌和失眠症等身体疾病,这是解开《夏与烟》中的伦理谜题的钥匙——阿尔玛意识到性压抑是导致这些“怪癖”或者疾病的根源,所以她主动寻求性的救赎。新剧中的阿尔玛直截了当地提议与约翰在新年前夜一起去旅馆,尽管她知道他不爱她,他们的关系会无果而终。约翰对她“像个男人一样的直率”表示了他的钦佩。或许她的“堕落”在人们看来是一场悲剧,但是在采取自我救赎的行动之后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个健康自信的阿尔玛,她摆脱了悲剧的宿命。在又一年的独立日庆祝活动上,她不再是曾经的那位因紧张而呼吸困难的歌手,被动地接受小镇居民的评头论足,而是以她自己的特点作为艺术标准,批评了乐池里那位新的歌手,而这些特点曾遭到人们的嘲笑:“我认为她唱歌时没有任何感情。一个歌手的脸,她的手,甚至她的心都是她的工具,应该用以增强演唱的表现力。”(34)Williams, Tennessee Williams' Plays: 1957-1980, 486.
以古希腊戏剧为发端的西方戏剧有着推崇悲剧的悠久历史和传统。在法国,自17世纪古典主义兴盛以来,悲剧在人们心目中便一直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美国,三大戏剧家奥尼尔、威廉斯和米勒均以悲剧创作见长。威廉斯是成就斐然的“悲剧诗人”,他以悲剧创作为核心,在戏剧的主题思想和艺术表现形式两个方面改造了美国传统现实主义戏剧,拓展了悲剧诗学的空间。
威廉斯在《玻璃动物园》的创作手记中表明他要以“一种新的造型戏剧,来取代业已枯竭的传统现实主义戏剧(the exhausted theatre of realistic conventions)”。(35)Williams, Tennessee Williams' Plays: 1937-1955, 395.家庭生活现实主义是美国戏剧的特色和传统,是美国戏剧创作中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戏剧方法。家庭生活现实主义既被用以表现大萧条等重大社会事件,也用于表现个人精神和心理问题。然而,美国戏剧“在主题视野上,复杂的经济、社会、道德、心理的冲突很容易被简单化为个人与环境的冲突……家庭生活的现实主义加上情节剧的结构,既不可能产生戏剧的诗意,也不可能创造出一种悲剧的崇高与神秘感”。(36)陈世雄,周宁:《20世纪西方戏剧思潮》,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第369页。可见家庭生活现实主义的局限性是不容忽视的,基于此,威廉斯在逾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不断进行着“拯救业已枯竭的现实主义戏剧”的实践探索。
在艺术表现形式方面,威廉斯早年提出“造型戏剧”理念,在其后期戏剧创作中又不断深化这种戏剧观念,力图创作出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等元素与语言文字的地位等量齐观的“形而上”的戏剧。
在戏剧主题方面,威廉斯通过“自我惩罚/净化”机制来强化坚守欲望者的崇高的悲剧精神,“把疾病作为认识手段”来进行悲剧人物的“心理”探索,其剧作体现出了独具特色的“心理现实主义”美学品格。所谓“现实主义”,是指威廉斯作品以反映和表现现实问题为主要内容,而“心理现实主义”则说明心理宣泄和治疗是威廉斯戏剧创作重要的艺术旨趣。在威廉斯戏剧中,本能欲望——尤其是性欲——受到压抑使人陷入精神错乱或精神崩溃,清醒认识到自身的本能欲望者为了从精神困境中得以解脱而采取极端手段,即使造成“悲惨”的结局也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威廉斯年龄的增长,新的戏剧形式成为反映新的时代背景和剧作家生命体验的载体。威廉斯在后期创作中刻意颠覆了其前期感伤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心理现实主义悲剧,用绝望的悲剧主题和滑稽的喜剧形式构造出的互为表里的喜剧——“黑色喜剧”或曰“黑暗喜剧”(black comedy)——来反映对灾难、死亡、恐惧、虚无等黑暗景象的强烈感受。在威廉斯的后期戏剧实验中,他运用荒诞和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后现代社会混乱而疯狂的人类生活,以悲凉而荒诞的“黑色幽默”来表现理想的破灭和精神的失落,表达对后现代社会权力和伦理的思考。美国的“黑色幽默”文学对现代世界文学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威廉斯的“黑色喜剧”则对当代美国剧作家的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融合了批判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戏剧冷峻而不失“残酷”,戏谑中透出阴冷与绝望,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对当代美国剧作家影响深远。
田纳西·威廉斯的悲剧创作在现代戏剧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对其悲剧艺术探索的路向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威廉斯不仅实现了对传统现实主义戏剧的改造,还给现代悲剧赋予了新的意义。威廉斯的悲剧创作拓展了悲剧诗学的空间,在西方现代悲剧史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