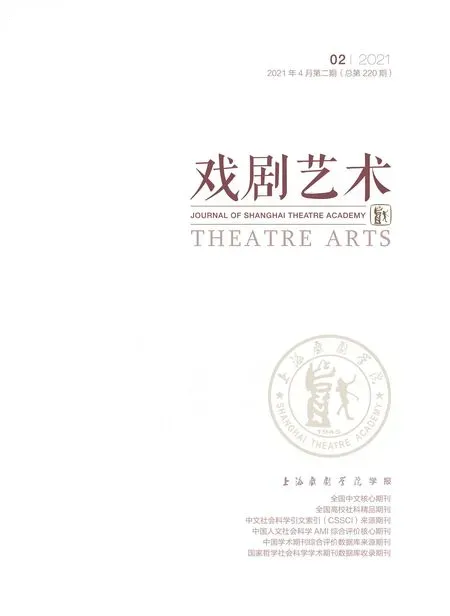布图索夫剧场艺术的视觉创造与美学选择
——以《海鸥》为例
吴沁恬
《海鸥》是契诃夫于1896年创作的四幕戏剧,从其诞生之初至今,许多导演都曾运用全然不同的舞台表现形式来诠释这出震撼人心的、世纪末的悲喜剧。2011年,由俄国当代戏剧导演尤里·布图索夫执导的版本于莫斯科萨基里康剧院(Satirikon Theater)完成首演,并于2012年获得金面具奖。在这一版本中,舞台设计师亚历山大·希什金(Alexander Shishkin)以其高超的艺术设计为这出原属于19世纪的俄国戏剧提供了巨大的现代张力。
这种现代性的视觉艺术张力,正如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彭涛所言,来源于其内在的“狂欢化”特质,而这种特质主要是由戏仿性表演所导致的。在他看来,“戏仿性表演与现实主义表演交融为一体,形成了演出的内在张力”(1)彭涛:《流浪的海鸥》,《戏剧与影视评论》,2020年第2期,第32页。,而这些视觉表现“看似肆意狂放,却又有着内在的缜密逻辑”(2)彭涛:《流浪的海鸥》,第25页。。显然,这种语汇对布图索夫版《海鸥》的形容是准确的,然而它的准确仅停留在诠释这些视觉元素带给观众的第一印象——即复杂拼接而多元的、超离文本规范的视觉印象。对于这种“戏仿性表演”和“狂欢化”是如何在布图索夫舞台被展现的,彭涛教授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和分析。而实际上,这种笼统的视觉印象是可以被进一步解剖的,这种解剖将更好地帮助我们寻找布图索夫在狂欢剧场背后建立的“内在的缜密逻辑”。
彭涛教授所说的“戏仿性”,实际指的是以超越作品本身逻辑的手段来进行二次创作文本内容的方式,这种方式是构成布氏视觉体系的关键——即与现实主义剧场形式形成的鲜明对立。也就是说,这种诠释手段所造就的视觉元素往往是颠覆性且令人费解的,而这种费解则来源于观众不能够单单通过视觉的参与来掌握剧场实践的意义。
然而这种特别的舞台呈现方式并非无迹可寻。事实上,在布图索夫的舞台中,我们可以探索到其视觉风格与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之间不可忽视的联系:作为俄国梅耶荷德派的继承人,布图索夫导演的舞台风格沿习了一部分梅耶荷德的剧场艺术理念。而生活在19至20世纪交界的梅耶荷德作为与毕加索同时期的艺术家,其舞台呈现理念受到了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视觉艺术的影响。显而易见的是,当我们将现代主义的艺术概念引入布图索夫高度风格化的剧场表现中时,这种表现方式方能更容易被理解。
情景式立体主义的舞美风格
布图索夫版《海鸥》的舞美基调是非同寻常的。这种非同寻常一方面表现在它缺乏对真实的模仿——它既没有还原19世纪契诃夫笔下人物的生活样貌,也没有为他们重建起一个当代性的生活场景。在布图索夫的舞台上,人物最基本的活动空间是不明确的;另一方面,布图索夫的舞台并没有完全颠覆原作、建立起一个超越契诃夫的内容体系,因为整体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台词依然来自于契诃夫写作的原文本。脱胎于以上二者,布图索夫的选择是利用舞台空间、置景和道具等剧场媒介,来建立起现实与戏剧之间独特的对话逻辑。
这种对话逻辑与现代主义艺术是相似的,即从本质上否定模仿真实的意义,而后搭建起艺术价值传递的新模式。对于现代主义艺术而言,由于19世纪摄影技术已经造就了一种能指与所指之间几乎零距离的“绝对真实”,故人工绘制的、经过主观编码的“真实”就明显丧失了其价值。于是,仿真的效果便不再是现代派艺术家们所崇尚的绝对圣经,相比较而言,抽象化形式的可塑性更能引领艺术走向积极的价值前景。这是因为这些抽象符号与真实间的距离被迫推动了观者与作品之间的“交流”——即思想通过艺术家的编码以符号的形式呈现在现代艺术作品中,同时这些符号必须通过观众的解码才能被还原成思想本身,从而被领会。这种积极的“交流”过程与作品本身共同组成了现代主义艺术的价值。
立体主义作为现代主义时期的代表艺术流派,推动了一场重塑艺术与现实关系的革命。R.布鲁斯·艾尔德(R. Bruce Elder)在《立体主义与未来主义:精神机械与电影效果》中这样描述立体主义运动:“立体主义,始于一种为带来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的努力……它不会努力呈现现实的镜子般的反映,而是会展示心灵形成视觉感知的过程——从而产生了一种在当时被许多人视为抽象的艺术。”(3)R. Bruce Elder, Cubism and Futurism: Spiritual Machines and the Cinematic Effect (Waterloo, Ontario, Canada: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18), 176.与纯粹复刻真实的作品不同,立体主义艺术的表达口径和表现内容都不是单一的,而是通过分解和拼贴将符号有机地重组,使得各部分的内容之间呈现出互相补充、或完全对立的情景张力——这主要是源于立体主义的“拼贴”艺术形式——即破碎、解析和再组合,故其作品能够在一个空间中被引申出多重的表达语境。
生活在立体主义蓬勃发展时期的梅耶荷德对美术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于1920年提出考虑与立体主义艺术家有未来的合作:“我们邀请立体主义艺术家与我们一起工作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需要这种与我们在将来的演出相类似的置景”。(4)Edward Braun, ed., trans., Meyerhold on Theatr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9), 174.毋庸置疑的是,梅耶荷德非常乐于将立体主义的艺术理念沿用到自己的剧场当中,因此其相应阐发出了一种全新舞台视觉语言逻辑,这种逻辑在梅耶荷德的口中被解释为“图式化”(schematization),即“一种对现实贫困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整体性的降低”。(5)Braun, Meyerhold on Theatre, 138.简而言之,这指代一种利用集成的(synthetical)制作来替代自然主义的美学方式(6)Joseph Garrett Clover, The Cubist Theatre (Michigan: UMI Research Press, 1983), 38.,其目的不在于复刻,而在于拼贴和重组。
英国学者艾米(Amy Skinner)将梅耶荷德所沿用的立体主义舞台理念进一步通俗化了,她利用“情景式立体主义”(contextualizing cubism)一词来指代这种结合并脱胎于分析式立体主义(analytic cubism)和集合式立体主义(synthetic cubism)(7)布鲁斯·艾尔德在《立体主义与未来主义》中表示,一段时间以来,艺术史学家已经接受了胡安·格里斯(Juan Gris)首先提出的立体主义艺术的两个阶段,即分析立体主义(Analytical Cubism)阶段和集合立体主义(Synthetic Cubism)阶段。分析立体主义阶段被约翰·戈尔丁(John Golding)认为是从1910年中期一直持续到1912年底(172),而梅耶荷德与立体主义的合作阶段是在1920年之后,故可以认为其一定受到过两种发展阶段的影响。的梅耶荷德式剧场语言(8)Amy Skinner, Meyerhold and the Cubism, Perspectives on 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Bristol, Chicago: Intellect, 2015), 21.,并将这种语言特点总结为“对表现对象的关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艺术作品和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关注;利用移动空间和多重预设,将画布嵌入有意识的时间和空间元素;对描绘和表面的杂耍;拼贴的使用和画布与其他媒介之间的关系;以及观察者对被观察者的首要性。”(9)Skinner, Meyerhold and the Cubism, Perspectives on 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21.
在“萨基里康剧院”版《海鸥》中,我们可以看到布图索夫建构的这样一套美学系统,其不变的置景大体由这几个基本的元素构成:四只拴在天花板上的绳索秋千、四件木质长方形框架、一扇立于舞台最后方的白色木门,和位于其右侧、一前一后用木头搭成的两个简易十字架。除此以外,每场都有着相对独立的置景手法:比如在第一场中设置了一大面由特里波列夫涂鸦的纸质背景版,而在第二、第三场中则大量运用了白色的屏风背景。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舞台基调总体呈现出一种相当“原始化”的面貌——即舞台上的主要道具均没有经过复杂的工序加工制成,而观众几乎可以一眼看出整套舞台置景的合成工序仅仅通过简单的拼、贴、画、悬挂就可以完成,甚至十字架看上去也仅是两条光秃秃的木棍子而已。
这种“原始化”的面貌一开始就将观众抽离出了原文本的幻象:因为这看上去根本不是个庄园——既没有丛林和湖泊,也没有住宅。同时,舞台的空间是开放且不确定的,观众无法确定演员是在哪个具体的空间内表演。
在第一场中,立于舞台正中央、由特里波列夫绘制的“抽象画”是最主要的构件。在这张挂在木支架上的白纸正中央,我们可以看到一棵大树,树的旁边有太阳和月亮,还有大量飞在天空中的海鸥。树下画了一个男人的轮廓,男人的头上顶着一片乌云,乌云底下正下着小雨,在这片乌云旁边有一个太阳,太阳下贴一张纸条,上面用俄语写着“妮娜”。在树的左侧是一个拿着雨伞的戴帽男人,戴帽男人旁边是一条狗,狗的下面有一个池塘,池塘里游着几条鱼。
这是一幅相当拙劣的绘画,因为无论是从其技法(每一个物体的具体描摹方式)还是比例(戴帽男的个子与狗差不多大,男人轮廓又几乎是树的一半高)上看,都是与真实完全不符的。这种悖反虽然消解了古典美术当中的规范,却恰恰契合了梅耶荷德所提出的“对真实的贫困化”,不过这种贫困化并不代表交流的失去——对于对原著相对熟悉的观众而言,这可以被解读为一幅表达特里波列夫内心真实的画:特里波列夫创作、反思,他的剧本中充斥着大量没有动作的理想主义独白,而当妮娜评论特里波列夫“你的剧本很难演。人物都没有生活”(10)(俄)安东·巴浦洛夫·契诃夫:《伊凡诺夫·海鸥》,焦菊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114页。时,特里波列夫激动地反驳:“表现生活,不应该照着生活的样子,也不该照着你觉得它应该怎样的样子,而应当照着它在我们梦想中的那个样子……”。(11)契诃夫:《伊凡诺夫·海鸥》,第114-115页。也就是说,这幅由特里波列夫绘制的画(在演出开始但剧情未开始前,观众可以看到这幅画是由饰演特里波列夫的演员绘制的)很大程度上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即这些能指的符号本身可能并不具有与现实重合的所指,它们完全是特里波列夫内心的意识流动:树右侧的人影是特里波列夫,深陷苦恋中的他正仿佛淋着乌云下的雨,而乌云旁边的太阳下正挂着这大大的四个字母——妮娜,即妮娜的出现可以被看作驱散他阴霾的太阳。而树和池塘都是契诃夫所描述的花园布局,戴帽男人是退伍的陆军中尉沙姆拉耶夫(通过饰演沙姆拉耶夫演员的着装也可以推断),因为他正放着一条狗来守着他的粮仓。而之所以这些事物之所以是拙劣而失真的,是因为它们恰恰属于特里波列夫“梦想中的样子”。
如果说置景内容总体还算符合观众与作品间“交流”的基本规范,那么布图索夫在舞台上所运用的道具就更像是一种“交流”之上的杂耍:在绳索上系着的白色塑料袋是夜空中升起的月亮,用载货拖车来替代马车,把矿泉水瓶插在雨伞上来表示下雨……有趣的是,虽然在大多数的戏剧舞台上,导演都会因剧场的特殊性进而使用相应的道具来替代实物,但是一般情况下,道具所代表的符号和实物本身之间必须具有所指意义上的重合,同时道具本身大多不具有作为道具本身的意义(比如用巨大的纸板做成月亮,一般而言,它将不具有除了“代表月亮”之外的其他所指性)。然而这种规则却在布图索夫的舞台上被打破了:白色塑料袋和月亮显然是各自具有所指意义的,同时它们之间亦没有任何可能的关联。用塑料袋来表示月亮,仅仅是因为白色塑料袋被拴在空中的样子略微类似于月亮挂在天空中的状态而已,然而这种类似性依然是相当渺茫且出人意料的。
不过,正是这种杂耍般的符号系统进一步促进了布图索夫“情景式立体主义”美学的完善。通过对艾米“情景式立体主义”的概念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对“画布(12)立体主义绘画中的画布,在剧场中应被理解为戏剧舞台。与其他媒介之间关系”的把握,正是布图索夫建立其“舞台拼贴画”的来源:观众无法将无情景下的“塑料袋”理解为“月亮”,这恰恰证明布图索夫不愿将任何一个道具孤立于其他媒介之外,而是选择利用多方的舞台成分(音响里播放出的风声、夜晚的虫鸣是人类共享的经验;饰演麦德维坚科的演员将塑料袋拴在绳索上,并慢慢升起来;再辅以特里波列夫对妮娜说的台词:“月亮升起来了,该开始了”(13)“月亮升起来了”是契诃夫原文本中没有的一句话,此处应为布图索夫为了完善剧场符号情景加上的。)来共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舞台符号逻辑。
帕特里斯·帕维斯认为,戏剧的场景设计与调度是一种实践意义上的符号学分析,同时他提出洞见:“文本和舞台之间的辩证关系、符号系统的组合,以及不同舞台系统和符号之间关系的建立,其中生产的意义往往被同化为一种特定的风格,或一个时期、一个人的品味,从而消除了讨论。”(14)Patrice Pavis, Language of the Stage: Essays in the Semiology of the Theatre (New York,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Publications, 1982), 134.对观众而言,或许我们已经太习惯于舞台符号的一些固定表达和传导,然而这些表达在观者与创作者间一旦被确定和固化,交流就必将不可能产生。于是我们不得不可悲地发现,我们对布图索夫道具运用所感到的诧异,可能只是从逐渐趋近同质化的剧场符号体系中的一次惊醒。
去中心化和偶然性的身体
身体是视觉语汇中的一个重要主体。然而在今天对于视觉文化的讨论中,“身体”(body)一词显得太过确切和单一,这个主体更应当指向的是“身体图像链条”(chains of bodily images)——也就是在关于身体的呈现中,那些被看到、被幻想、被恐惧、被寻找、被否定的一系列身体性表达。(15)Norman Bryson, Michael Ann Holly, Keith Moxey, Visual Culture: Images and Interpretations (Hanover and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7.对梅耶荷德而言,这种“身体链条”的实现被看作是演员对自我身体认知的复述:在梅耶荷德提出的演员训练理论“身体机能学”(Biomechanics)当中,演员必须能够自觉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它具体作用在演员身体的精确性、平衡性、配合性、有效性、旋律性、表达性、回复性、随意性和规范性上(16)Jonathan Pitches, Vsevolod Meyerhold (London,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4), 112-117.,这些特质给予了演员一个共同的要求——对身体巨大的专注度。这种专注一方面要求演员能够在短时间内精准完成导演的指令,另一方面则要求他们的身体能够像机械一样精准地复原做过的每一个动作。乔纳森(Jonathan Pitches)强调,对于以上“身体机能学”的特征,“尽管我们可以孤立地讨论它们,但要在实践中将它们分开要困难得多”——也就是说,这些“身体链条”的各个部分之间通过彼此依存和相互作用,在梅耶荷德的剧场实践中建构起多重的审美语境。
如果说梅耶荷德执导下的身体链条构建是过于集中的,那么布图索夫剧场中的身体就反而是支离破碎的。一方面,布图索夫的剧场实践与梅耶荷德一样,和现代主义艺术,尤其是立体主义之间发生了广泛的关联——即演员需要拥有对自我身体的自知能力,同时能够通过形体的拆解和组装来建立舞台的视觉语言风格;而另一方面,布图索夫的舞台上依然具有着与梅耶荷德“身体”概念相对立的成分,即相比梅耶荷德所强调的的“身体专注力”(concentration),布图索夫导演下的身体状态是破碎(fragmentation)和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
《海鸥》一开场,是特里波列夫在舞台上的长段独白。在这段独白当中,特里波列夫做了许多动作:他先向观众介绍了他的舞台,随后他抱怨了自己母亲阿尔卡基娜的迂腐和吝啬。在说到阿尔卡基娜在敖德萨一家银行里存了七万卢布的时候,特里波列夫走向右舞台的一个不锈钢脸盆,从脸盆里捧起一把硬币,同时把脸靠近它们,再把它们从高处洒落到脸盆里。之后他开始把口袋里的蔬菜掷到地上,口中一边念着“爱我,不爱;爱我,不爱……”(17)契诃夫:《伊凡诺夫·海鸥》,第110页。,直到只剩下一个辣椒,于是他绝望地喊道“你看,我母亲不爱我”。(18)契诃夫:《伊凡诺夫·海鸥》,第110页。他一边喋喋不休地倾诉着对戏剧艺术的看法,一边在舞台前方走来走去,他有时候跪在地上、有时趴下,他走到台侧去亲吻玛莎,随后来到妮娜面前倾诉对她的爱意——他甚至用笔和纸描画出妮娜的脚印。
特里波列夫在这一长段独白当中进行了很多个零碎的动作:洒硬币、掷蔬菜、亲吻、描画妮娜的脚印、跪或者趴下……但这些动作看起来却是零散的、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们都没有进入到真正的戏剧动作中——既没有和剧中人物真正发生关系,也没有进入到表达情节主题的段落里头。而如果将这一系列身体的介入删去,仅仅通过特里波列夫的口头叙述,对情节表达的完整性也可以没有任何损害:特里波列夫不用捧起实质性的硬币,观众也能够知道阿尔卡基娜在银行里存了很多钱;他不用描摹妮娜的脚印,只要对妮娜说一句“我爱你”,观众也能够明白特里波列夫对妮娜的情感。这些零碎的、没有对中心情节起作用的身体表达看上去是非必要的。
布里奥尼(Briony Fer)认为,在对现代主义艺术(视觉类)的评论中,“现代性的表征”被认为取决于“整体的碎片化”(19)Briony Fer,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and Modernism: French Paint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 F. Frascina et a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而卡特丽娜(Catriona Miller)将这种碎片化的倾向与立体主义及其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联系在一起(20)Sara Haslam, Fragmenting Modernism: Ford Madox Ford, the Novel and the Great War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3.。对于立体主义来说,碎片化内容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观众对艺术作品观赏时的失焦——即没有一个总体的、中心性的内容可以被获取。而这种“去中心化”往往更强调一种非恒定的价值取向,它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权威,同时树立起更加无定性的人格特征。
我们可以发现,布图索夫的舞台与现代主义艺术中“拼贴画”的创作结构是类似的,即特里波列夫的身体和行动是零碎的,但这种零碎实质上是通过互相之间的作用来塑造出特里波列夫复杂的人格特质。因为人性本身是抽象的,而这种抽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在面对几种相斥情感状况下表现出的不可调和。例如,特里波列夫辱骂母亲的同时又渴望得到她的爱,于是作为一个软弱的、敏感的艺术家,特里波列夫只能选择用扔蔬菜这样可笑的方式来揣测母亲的心思;他生命中的另外两个女人妮娜和玛莎分别处在舞台的两个角落,玛莎坐在侧台没有光的椅子上,拖着特里波列夫不让他离开,而特里波列夫却掰开她的手,主动走近妮娜。对于妮娜,他甚至愿意跪在地上描她的脚印,亲吻纸张上的足迹……这些碎片化的行动创造出了特里波列夫情感的诸多语境:夹在微贱和不屑中的三角恋情、对母亲的恨与爱、卑下艺术地位中的挣扎……于是,一个懦弱敏感的青年艺术家在这样的多重语境下展现出了相对复杂的人性面貌,而这种面貌是无法被给予一个中心词汇来定义的。
碎片化的身体特征伴随而来的常常是一种“无主体”的身体状态,因为当身体的中心价值被消解,那么它就可以被扩充为任意表达形式。于是在布图索夫的舞台上,身体时常作为一种非知识性的手段出现:它没有扩充原文本的表达内容,同时还突破了原有的规范,因此削弱了身体表达的逻辑性。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对“身体本身”的超越上:在第一场中,契诃夫笔下的特里波列夫的舞台是被火烧光的;而到了布图索夫的舞台上,水浸透了特里波列夫的画纸背景板,随后布图索夫亲自上台,将挂在木架上的画纸“破坏掉”——他从一开始一条条、从上到下地撕去纸张,到后来甚至攀上木架,用拳头捶破画纸的一个角,再把它大片地撕落。这种破坏力是完全由他的身体造就的,布图索夫选择用身体来替代无秩序性的、熊熊燃烧的火,其中的隐含逻辑是用身体来超越“身体本身”——即这种身体的介入并不是以“人”为主体的,人的身体在舞台上可以被用来代表其他超离人类自身的无秩序力量。相同的手法还运用在麦德维坚科的演员饰演狗的桥段中:当妮娜和特里波列夫正在亲热,妮娜提到“打更的会看见你。还有宝贝,它跟你不太熟,会吠起来的”(21)契诃夫:《伊凡诺夫·海鸥》,第114页。,话音刚落,饰演麦德维坚科的演员便从左舞台边蹿出来。他四肢着地,并模仿狗吠的声音,和特里波列夫之间展开了追逐。以人来饰演狗和以身体替代火一样,都是一种对传统剧场身体认知的颠覆,这种颠覆主要表现在其冲破了身体与其他剧场元素之间的界限——只是这种界限在现代剧场中是相对模糊的,它甚至可以抹去“人”的主体性存在。
于是,当“人”的主体意识被一定程度地抹去之后,身体就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偶然发生的状况。在布图索夫的舞台上,身体还经常以一种不可预知的面貌出现:在第一场的结尾,背着手风琴的女郎和布图索夫在破碎的舞台上共同引导了一场众人狂欢的起舞,手风琴女郎先随着音乐的鼓点跳起一段独舞,布图索夫则随着音乐自由地跺脚或扭动。随后其他演员陆续上场,他们在舞台中央无规律地分布着,没有排列成任何规则的队形、也并不共享任何相同的动作,他们各自在音乐的鼓点下随机舞动,有的在小幅度的扭头,有的只是随意地甩动手臂——显而易见的是,除了手风琴女郎之外,所有人的动作都是不精准、且无规律可循的。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视觉风格是偶然的,因为这种混乱的身体合作显然不应该是一出经过编排的舞蹈,而且复刻这样一种无规律的身体状态也毫无意义。再退一步说,即便背手风琴女郎的动作可能被事先设计好,但因其他人身体出现的偶然性,手风琴女郎与其他演员所组成的身体视觉形态也是完全不可预知的。
如果说梅耶荷德剧场中的身体强调了其可被人为掌握的重大意义,那么布图索夫就是在通过去中心的、碎片化的动作来表现一种偶然的身体状态,从而消解一部分“人为”对身体的规训。这种消解与现代主义中具有代表性的偶发艺术是一脉相承的,阿兰·卡普罗(Allan Kaprow)认为,重复在偶发艺术当中是不被需要的。在关于偶发艺术的纲领性文章《集合,环境与偶发》中他表示,“由于人是习惯的动物,表演者总是倾向于陷入固定的模式,无论原计划中给了它们怎样的余地,他们都会坚持这些模式。”(22)Allan Kaprow, Assemblage, Environments and Happenings: Text and Design by Allan Kaprow. With Selection of Scenarios by 9 Japanese of the Gutai Group, Jean-Jacques Lebel, Wolf Vostell, George Brecht ... [etc.].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66), 263这进一步解释了在剧场中塑造偶然性身体的意义。故相比梅耶荷德的身体机能学,布图索夫舞台上的身体即便有自知性,也无法被复制——这是因为它是不受规范且缺乏主体的。相对而言,布图索夫导演下的身体状态与现代主义的艺术内核更加接近。
“参与式”观看机制
艾米在谈到《梅耶荷德与立体主义》中提到了观看机制(spectatorship)在观众与艺术作品二者中的重要性,她表示,(立体主义)拼贴画的审美意义很大程度上是由观赏者来决定的:“在观者接受艺术作品的时刻,也是观者与作品、观者与艺术家、艺术家与作品之间建立起关系的时刻”。也就是说,立体主义作品的审美价值往往通过观看机制来进一步起作用。这种参与式的观看机制与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绘制白色绘画的初衷相仿:面对自己使用白色房屋涂料和油漆滚筒创造出光滑的、没有任何装饰的画面,劳森伯格解释道:“我总觉得白色绘画不是被动的,而是非常……高度敏感的。所以当人们看着它们时,通过阴影的投射,几乎可以看到房间里的人数,或者看到现在是一天中的什么时候。”(23)(美) 阿诺德·阿伦森:《美国先锋戏剧:一种历史》,高子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4页。
从视觉艺术延伸到剧场,梅耶荷德同样主张观众对于作品的“参与”而非“观赏”。在梅耶荷德的剧场理念中,观者的处境应当“位于观赏的过程里,但仍然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24)Amy Skinner, Meyerhold and the Cubism, Perspectives on 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Bristol, Chicago: Intellect, 2015), 129.这种距离感在剧场中往往表现为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即舞台并不完全给予观众明确的提示,而是用相对抽象的方式来引导观众的思考。这种距离的建立与劳森伯格“白色绘画”中的观看机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不是将作品看作单纯的观赏客体,而是要通过作品来与作品外的世界发生广泛的联系。
在布图索夫版本的《海鸥》中,这种“距离”的制造往往表现为文本提示在舞台上的失效。例如在第一场寻找特里波列夫的桥段中,除特里波列夫外的所有演员都站成一排,跟着音乐左右摇摆。相比于寻找儿子,阿尔卡基娜对着话筒呼喊的状态更像是一场“表演秀”,于是在玛莎对着话筒大叫“柯斯加”过后,舞台上的所有演员们几乎跳起了一场群舞。演员们各自挤出夸张的神情,一边叫着“柯斯加”,一边跟着音乐做整齐划一的动作,然而他们身上并没有表现出寻人时应当具备的焦躁或忧愁,反而是激动的,为这场“寻人演出”倾注着热情的——这种舞台形式和台词内容形成的巨大反差,怎么也无法让人相信这是一出真实的寻人的情形,反而像一场具有讽刺性的狂欢表演。而接下来的表演也印证了这一点:在音乐结束之后,幕后工作人员直接走上舞台,递给演员们擦脸的湿巾,于是演员们在舞台上一边喘息、一边擦脸,仿佛正处在后台休整。一方面,这是布图索夫对舞台幻觉的直接打破——直接将表演的全过程暴露在观众面前,让观众意识到“戏剧幻觉”的不存在;另一方面,这一出“舞台上的舞台”与梅耶荷德的“剧场戏剧化”(theatre theatrical)美学(25)莫尔德凯·戈雷利克认为梅耶荷德的主要贡献在于恢复了俄罗斯舞台的“剧场戏剧化”美学, 参见Norris Houghton, “Theory into Practice: A Reappraisal of Meierhold”, Education Theatre Journal 20 (October 1968), 438.是一致的——这场“寻人演出”可以被理解为通过剧场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虽然这场“表演秀”对契诃夫的文本而言是不实的,但对于布图索夫而言,它创造了扩充文本的剧场真实——它表达了外在环境对特里波列夫这个年轻敏感的前卫艺术家最深切的嘲讽。
同时,角色的混淆与介入更进一步加剧了舞台与文本之间的对立感。在第三场特里波列夫与母亲阿尔卡基娜的对话结束之后,波琳娜上场,特里波列夫重复了他对阿尔卡基娜一开始说的话:“妈妈,请你把我的绷带换换好吗?你是个熟手呀”(26)契诃夫:《伊凡诺夫·海鸥》,第152页。,随后波琳娜用阿尔卡基娜的词回复:“医生到晚了”(27)契诃夫:《伊凡诺夫·海鸥》,第152-153页。。两人重复刚才阿尔卡基娜与特里波列夫之间发生的台词。但这次,这些台词已经不构成对话——他们各自歇斯底里地嘶吼,台词与台词之间交叠在一起,没有遵守任何对话的秩序。他们一开始拥抱、抚摸,接着波琳娜脱去特里波列夫的上衣和外裤,接着她开始推搡特里波列夫,特里波列夫挣扎着倒在地上,嘴里再次重复这句台词:“妈妈,请你把我的绷带换换好吗?你是个熟手呀……”波琳娜与阿尔卡基娜这两个角色的混淆给观众造成了直接的错乱的印象,这种错乱致使观众不得不积极地参与到剧场中,同时这种参与不仅仅是视觉性的——因为由角色外扮演所产生的意义断层不能够通过视觉被直接领会,所以观众必须主动探求超越文本之外的剧场表现,也就是说,观众需要通过对文本内容和舞台上重复语义的审视来感受特里波列夫对母亲的情感挣扎。
这些来自逻辑断层的“不确定感”自始至终贯穿着布图索夫的舞台,它们推动剧场中形成一种积极的观看机制:这种观看机制致使观赏内容成为不稳定的、非单一的,它们割弃了艺术家封闭的自足,勇敢地将观众囊括进创作中。而梅耶荷德的观点也在这种“不稳定”当中得到了实现,即观众是构成戏剧作品完整性的重要“第四维要素”(28)Robert Leach, Vsevolod Meyerhold: Directors in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30.(其他三维分别是编剧、导演、演员),艺术作品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他们需要在相互之间的作用下共同完成艺术创作。
从《海鸥》中的视觉创造与美学选择上看,这种具有“四维联系”的剧场氛围的实现有赖于布图索夫塑造的积极、现代性的艺术语言。而这种语言之所以是具有张力的,是因为舞台上下之间时刻有着多语境的“交流”产生。这同时让我们发现,笃定的导演剧场范式已经很难再建立与观众的对话机会,只有不断地尝试打破既定视觉语序,才有保持剧场“活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