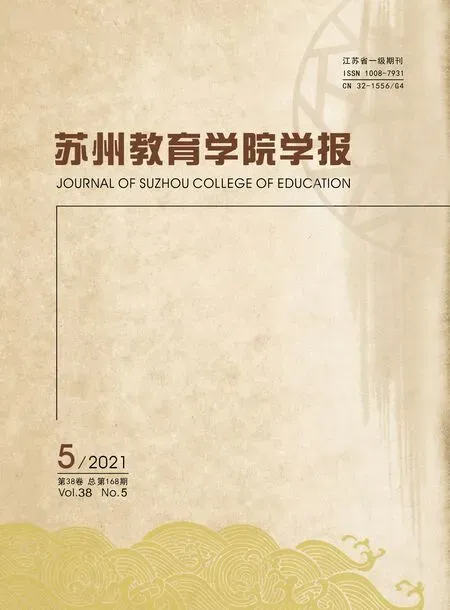栏目特邀主持人:龚 斌

主持人语:本期陶渊明研究栏目刊出四篇论文。
蔡彦峰《心无宗与陶渊明诗歌艺术考论》一文,论东晋佛学“心无宗”一派与陶诗的关系。所谓“心无宗”,僧肇《不真空论》的解释是:“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肇论疏》说:“但于物上不起执心,故言其空。然物是有,不曾无也。”简言之,谓心中无物,而承认万物有,是真实存在的。陶渊明及陶诗是否受佛教思想的影响的问题相当复杂。盖两晋(特别是东晋)佛教深受《老》《庄》及魏晋玄学的影响,乃是毫无疑义的。佛教初来中土,为弘法的便利,借中国传统学术以诠释佛经(所谓格义),乃是必然之事。故初期佛教的讲说与传播是依附玄学的。汤用彤等前辈对这个问题言之已详。因为佛教与玄学在解释宇宙本体上的相似,加上早期佛学依傍玄学,以至于有的陶学研究者就以为渊明及陶诗受佛教思想影响。对此,陈寅恪论渊明思想时否认渊明接受佛学,称渊明不归命释迦,以其新自然说之胜解,自可以安身立命,无须乞灵于西来佛教。陈先生的论断,我以为符合事实,始终赞同。判断渊明是否受佛教影响,应从大处着眼。譬如:1.渊明不信“神不灭论”,不信因果报应说,以为人受气而生,死为魂气的散扬。凡此,皆不合佛经。2.他不愿追随慧远,也是不信佛的证据。3.以《老》《庄》哲学以及玄学、儒家思想,足可以解释渊明其人其诗。4.慧远为当世高僧,学问渊博,尚且不解鸠摩罗什大乘中观说,可见东晋士人能理解佛经奥义者寥寥。明乎此,对于渊明是否受佛教影响的问题,可以思之过半矣。本文用相当篇幅论证心无义与郭象独化论的关系,有可取之处。论陶诗与大谢诗的写意与写景的不同,以及文笔畅达,都值得称赞。
李治中《从拟古九首见陶渊明在桓玄篡位前后》一文,探索《拟古》九首的系年及主旨。陶诗的系年,是陶渊明研究中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由于大多数诗没有作者的记录,很难推测它产生的确切年份,《拟古》九首也属这种情况。这组诗,历来的研究者多以为作于晋、宋易代之后。本文作者一反旧说,以为作于桓玄篡位前后。得出这种结论,是依据《晋书》《资治通鉴》等文献有关桓玄篡位前后的史料所作的新解读。例如《拟古》第九首“种桑长江边”,引《后汉书•张堪传》记载:“(张堪)拜渔阳太守……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文本中“种桑”指“天子命桑虞”,即天子任命负责种植桑树事务的官员,以之指称朝廷任用桓玄,让其治理长江上游的江州与荆州,如此等等。作者又据自己理解的各首诗的主旨,调正原诗的编次,以为“《拟古》九首的创作时间,以元兴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为上限,以次年四月刘敬宣任江州刺史为下限,浔阳、京口、建康等地均为创作地点”。总之,本文对《拟古》九首的主旨作出了与前人非常不同的解释,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勇气可嘉。当然,如此解释这段历史,以为在历史记录中有着渊明的行踪,真相究竟如何,尚需考辨并鉴定。
胡伟《再论东晋时期浔阳陶氏的阶层升降—以乡品考察为中心》一文,从乡品的视角,考察东晋浔阳陶氏代表人物陶侃从地方寒族变为权势显赫的势族的过程。从武到文,确实是东晋南朝的势族演变的大趋势。譬如东晋陶侃、刘宋皇室代表刘裕、齐梁皇族代表萧道成、萧衍,无不如此。陶侃本为家道中落的地方将领之子,依靠西晋末年南人代表的品评和推荐,才得以担任县吏的微职。以后凭藉累积的军功,军权步步上升,最后成为东晋早期重要的军事首领。本文立论正确,举证贴切。行文过程中,解释参军、长史等魏晋官职的官品及其职责,采用列表形式,令人一目了然,又说明何种官职具有“开府”的资格。凡此,皆有利于读者的了解。
杨高阳《试论曲牌【园林好】的渊薮与定型》一文,探索中国古代戏曲中常见的曲牌【园林好】的来源,以为它取自陶渊明名句“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时间大抵是宋末元初,是遗民感慨国破家亡而创调的。当然,推测【园林好】曲牌来源于陶诗,终究是推测。但这个推测,具有可能性。因为事实上宋末元初的遗民,创此调以寄托哀思,是有说服力的。在中国园林史上,陶渊明田园诗的自然朴素之风,后来成为园林艺术的典范。如果本文在这方面揭示和说明陶渊明的园林与【园林好】曲牌的渊源关系,文章可能更有说服力。而后面叙述这个曲牌的广泛流行与最后定型,似乎可以从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