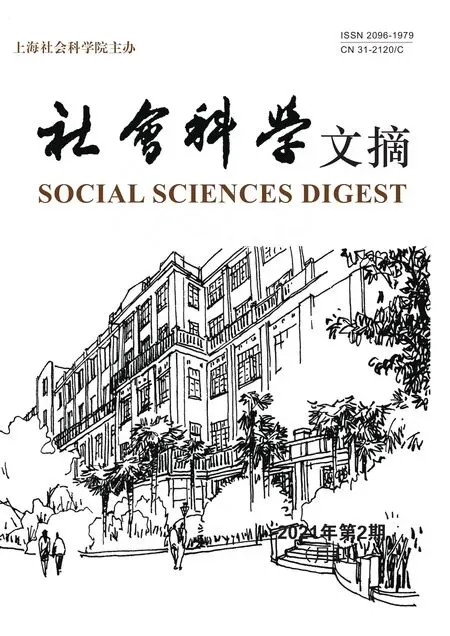禅让的变异:从传说、理想到制度设计
文/王士俊
远古传说的尧舜禅让,是先秦儒墨两家讴歌的理想。但这并不能消弭传说引发的争议。两千多年来,认传说为史实的除儒墨外,代有其人。及至近代郭沫若、范文澜等史家不仅肯定传说,而且将其释读为部落联盟时代的民主选举制度。与儒墨及后人对传说的肯定相反,先秦的荀子、韩非持质疑尧舜禅让说的立场。荀子认为,尧舜禅让“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唐刘知几在《史通》中持与荀韩相同的看法。清代崔述、康有为也不信尧舜禅让之说。及至20世纪上叶,疑古思潮滥觞,顾颉刚等人更是直斥传说是战国秦汉间的“造伪”。尧舜禅让的传说之争,至今尚未平息。本文不置喙传说的真伪之争,仅着重讨论尧舜禅让说提出的意义,以及由此展开的实际操作及制度设计,探讨一个美好的传说变为理想进入实践操作过程的变化。由此,观察变化的结果与原初传说、理想诉求的差距。
以传说表达的理想:禅让说的最初主旨及权力转换构想
尧舜禅让的真伪之争,对说明古史传说的尧舜时代的“历史”有重大意义。但是,即使传说有伪也不能表明这类材料无价值。本文就本着这种理念,检阅有关尧舜禅让传说的史籍、材料。
就历史上的禅让传说而言,争议很大的材料之一,要算《尚书》中被称为“虞夏书”的《尧典》。《尧典》记述了尧舜禅让之事。近人顾颉刚先生从《尧典》涉及的地名上分析指证“今本《尧典》为汉人作”。此论一出,引发众多学者反驳。竺可桢、唐兰、董作宾、胡厚宣等人分别从分析《尧典》涉及的天象、殷卜辞、祭名的角度发表了反对意见。
细观《尧典》论争中,各家对顾颉刚的驳难,虽能质疑顾先生的立论,但也不能证明《尧典》的纯真。如果撇开以《尧典》证夏商之前的历史,将它视为提出禅让问题、叙述禅让方式的材料,应该说是完全可以的。若如此,则需要弄明白,这份材料“作伪”或说形成的年代,这样才能明白它提出禅让问题的时代背景及目的,等等。顾颉刚先生认为,《尧典》“作伪”于西汉,至于《尧典》的禅让思想,他说最早是由墨家提出的:“……要知道禅让说是直接从尚贤主义里产生出来的;倘没有墨家的尚贤思想,就决不会有禅让的传说!”针对顾先生此说,刘起釪先生通过详细考辨,给予反驳。刘先生认为,《尧典》为孔子所编,成于春秋晚期。《尧典》是禅让思想的重要材料。若按此说,则禅让说源起春秋晚期。此问题,现今学界仍有争议。许景超研究《左传》《国语》有关古史记述,得出这样的看法:探讨春秋时期的一些有关古史传说,“可知尧舜禹时期之事迹已流传得比较广泛。尧以后的事迹,使我们清楚知道战国诸子所传的古史,是从春秋时期(或更早)便流传下来的”。
学界所做的这些推测并非空穴来风。要言之,流行于公元前五世纪的禅让说,有一个源起与形成的过程。《尚书·尧典》《论语·尧曰》应是出现较早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湖北郭店出土的竹简、上海博物馆购得的竹书,以及清华藏竹简中的《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保训》所论及的禅让传说,涉及年代久远、叙事之详、讨论之广都远超传世经典。出土文献记录的禅让文字,也从另一侧面显示出传说的更早源起。
关于禅让说兴起的原由,学界的主流看法是当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社会情势下,“士”阶层崛起,尚贤、尚德思潮的流行,进而衍生出德治、贤人政治的理想诉求。于是有“善善相授”、禅让贤人的王朝更迭、君权传承制度的构想。古代士人在春秋战国之际以传说倡禅让,在世袭、汤武革命这两种君权传承、转换方式之外,提出了第三种君权转换途径。
春秋晚期至战国,士人以禅让传说倡理想,勾画君权传承、转换的第三种方式,其用心良苦。他们勾画的禅让方式之要者有:(一)上德(君主)起意,主动禅贤;(二)与“四岳”(邦主、诸侯)商讨、选择贤人(禅位对象);(三)上德(君主)亲自面试被选择的贤人(与之交谈等);(四)将被选的对象举之高位,授职考验;(五)考核满意,确定禅位;(六)受禅贤者五让他者,“天下贤者莫之能受”;(七)上德禅位,贤者受禅,举行即位仪式。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先秦士人依据传说叙述的理想。在此之后的数百年中,它以一种思想、学说、思潮而存在,直至西汉中后期被政治家接受之前,其未登庙堂、难入密室。然而,世上所有的理想都有被实践的渴望,政治理想更是如此。
走向实践的理想:初行禅代的权力转换设计及其乱局
禅让由传说变成理想,是春秋战国士人思想的成果。但是,这种属性的理想,在思考、交流、争辩的过程中,很少考虑付诸实践的细节及诸多条件的要求。比如,禅让由上德(君主)禅让和受禅者(贤人)两方面构成。历史上,就曾有君主想禅让而被选为禅让的对象不愿受禅的传说。《庄子》载,“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逃尧”,不受禅。“舜以天下让”于善卷,竟遭到善卷的拒绝。理想的受禅者不接受禅让,这肯定不只令禅让者尴尬,也是事关权力转换成功度的大问题。此外,即使禅者与受者达成一致,禅让也可能出问题。《史记》说,禹受禅后,已“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更糟糕的情况是,禹另选了禅让对象益,而当禹驾崩时,禹的儿子和诸侯违背禹的意志,让禹子启取代了益登基即位。禹的禅让传说,其实早就严峻、现实地提出了禅让的实践问题。只是这方面的问题,未受到提倡禅让说的思想家们的重视。严格说,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是思想家的任务。禅让说兴起后,可作为较早的禅让事件来研究的,要算《战国策》记载的燕王哙禅位:
公元前320年,燕国的哙被立为王。哙用子之为相。鹿毛寿窥得燕王哙有图圣君之名,干大事的雄心,便设计劝燕王“以国让子之”。他说,子之肯定会像历史上的许由一样不接受让国,这样,燕王既得了尧舜的贤名,又不会失去王位。公元前218年,燕王让位予子之。不料,子之没拒绝。燕王丢了王位,结果引发燕国大乱。齐、魏、秦、韩、赵等国出兵伐燕平乱。哙、子之均被杀,太子平被立为燕国新君。自禅让说兴起,历史有记载且为史实的禅让之事,这可谓第一件。
燕国“禅让”之乱尖锐地提出了,禅让由理想到实践必须解决权力转换的正当性问题。自人类群居始就存在权力转换现象。无论以何种方式转换权力,都必须要让转换的权力获得正当性。世袭制权力转换的正当性是通过故君与新君的血缘一体来实现的;汤武革命为异姓之间的权力转换,周人以天命、德治及瑞应等理论阐释商周权力转换的正当性,也即以天命证明权力获得的正当性。当禅让说兴起,其提出贤人政治并欲实行贤贤相授的权力转换时,那么,权力的贤贤相授凭什么是正当的、为什么应该被认可等问题立即凸显出来。由此连带出许多问题,需要人们拿出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和可操作的方法、程序来解决。显然,当禅让说流行之初,这方面的理论说明、制度设计并没有被认真考虑。真正将禅让作为异姓权力转换的方式,并在制度上有所行动的,要到燕哙禅让失败三百年后的西汉末年——由西汉儒士围绕新莽代汉开创的权力转换机制。
西汉末的儒士们能做这件事,得益于西汉中期朝廷的政策转变。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先秦至汉初的儒学逐渐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学地位的这种转变,除了皇帝出于统治的需要外,也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改造儒学有关。汉儒强化儒学经世致用的因素,吸纳阴阳、五行、道术等思想资源,杂糅出一套思想、原则及可操作的规制、仪式。比如,董仲舒所说的“天人感应”“灾异”“天谴”等思想。“天人感应”将“灾异”与“天谴”、“祥瑞”与“盛德”“大治”相联系,使“天命”“天意”能够获得更为具体的解读。由此,可将国家的政治乃至社会的种种行为纳入可观察、验证、预测的体系,进而获得权威的支持。
汉儒的这套理论原本用于论证以汉代秦的正当性的。然而,西汉盛行的五行五德之说,在说明以汉代秦正当性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五行五德说将周人的“天命”观从胜利者的言说变为世人之识;“天命靡常”变为有规律的五行运转。五德像自然规律一样周而复始,那么,由此很自然地会生出“天命”非一姓所独有的观念。在西汉五行五德思潮正炽之时,自宣帝至哀帝的六七十年间,连年灾异频发,社会不安,人心惶惶。时人从五行观念看,汉家气数已尽。汉末王莽的禅代就是在这种氛围下酝酿、谋划、操作的。
客观地说,在中国历史上以“禅代”之名搞王朝更迭权力转换的,王莽是第一人。若论中国“禅代”历史上,最具儒术、儒味的“禅代”,恐怕也唯有王莽这一次。
王莽靠着家族背景,自身的“折节力行”“勤劳国家”,以及凭借权力翦除异己,达到权倾天下的地位。不过,他有代汉的野心,选择禅代之途,还有其内在的社会原因。一是,其时社会主流意识极度崇尚经义。赵翼《廿二史劄记》说,“汉时以经义断事”,可见一斑;又说“王莽引经义以文其奸”,则证明世有所好,行必盛矣。由经义举禅让,行禅代,顺理成章,难察其奸,取代成本最低。二是,在王莽取禅代之途夺汉位之前,西汉社会早已流行“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的说法,受禅者只需由此往下说,受者为舜之后,即可。王莽代汉,就选择了这个路子。三是,王莽虽与历朝取代君位的权臣一样,是在权倾天下时攫取权力的,但是他以受礼服儒的文臣身份问鼎帝座,既与此前汤武、汉高获得权力时的身份不同,也与此后汉魏以降操弄禅代的权臣有异。即使他效仿的周公,虽以文臣身份辅佐成王,但其出身却是武官。要言之,自三代以降,历代操弄王权更迭、禅代者,多为能统兵作战的将帅,鲜有受礼服儒的文臣。王莽禅代,是一个不多见的史例。
从《汉书·王莽传》的记述看,王莽虽以唐虞禅代为舆论,但其禅代行为多以周公、周礼为模本。这既是王莽代汉的路径特点,也是其禅代命运的规定。王莽如何阴谋策划取汉而代的过程,已有史书记载,本文不作赘言,只就其采行、建构的禅让仪规、制度作一些探讨,以窥其与禅让理想吻合的程度。依《汉书》看,王莽行禅代,未采用传说中的尧舜、舜禹禅让的方式,而是采周礼加以改造,效周公加以重塑。其设计了立公国、赐九锡、行居摄、伪揖让、进禅代的禅让程序:
(一)立公国。传说中的尧舜禅让,无立公国之说。王莽于元始元年被赐号“安汉公”,享公爵封邑。王莽以周公的封国为模本建公国,但又受限于汉制。首先,两者册立的主旨不同。西周分封诸侯出于“以藩屏周”;汉赐王莽立国,是为褒奖行殊礼,是一种礼遇。其次,由此设立的公国建置不同。西周的周公封国是一方的政治实体,有行政职能、官吏等;而王莽的公国封邑很大,但这只是食邑,非行政区域。再次,西周封国在官员任命等行政事务方面,自主权比较大;而西汉封国的重要官职均由中央委派。由此诸项观之,王莽的公国实在是以仿周制之名行汉制之实。总之,周制封国的意图是“以藩屏周”,王莽封国的意图是欲行禅代。王莽封国建制与立国意图的错位,一目了然。
(二)九锡礼。汉魏以降,行禅代前,例行九锡礼。此礼也不是尧舜禹禅让传说中的制度。《十三经注疏》说,何休注《公羊》对“九锡”有具体解释:“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鈇钺,九曰秬鬯。”汉之前,帝王为褒奖有功的诸侯,或赋予大臣某种权势而行九锡礼。《左传》就有周天子为春秋先后出现的五霸行九锡礼的记载。西汉以降,九锡礼成为历代受禅者先邀之殊礼。此制始于王莽。王莽所受九锡礼,是汉人按西周“九命上公”“九锡登等”的原则,择取古制拟作的。西周以礼赐周公封国,是“以藩屏周”;而汉末为王莽设计的九锡礼,除褒奖功能外,更具有对其权力僭越君臣之礼的承认。这是九锡礼成为后世禅代符号、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行居摄。中国历史上的居摄,指嗣君年幼不能亲政,由大臣代居其位理政。这种制度原本与尧舜禅让传说及先秦禅让说无关。王莽禅代前行居摄,实是不能一蹴代汉的无奈之举。元始五年,汉平帝14岁驾崩,此时的王莽已权倾天下。在立新君的过程中,他选了皇室后裔中最小的广戚侯子婴为嗣君,年仅2岁。太后同意王莽居摄,颁诏“令安汉公居摄践阼,如周公故事”。王莽居摄才4个月,安众侯刘崇率众反莽,兵败。朝中大臣以此为借口,说谋逆是因为王莽握权太轻,不足以镇叛。由是,让太后允准称王莽为“假皇帝”。王莽以“假皇帝”之名居摄3年,终行禅代。
(四)即真代汉。王莽居摄是效周公之制,居摄三年,即真代汉,计划以尧舜禅让的方式来操作。此时出了一桩“金匮神嬗”的符命之事。《汉书·王莽传》说:“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子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对此,王莽没有效仿先秦禅让说中许由、善卷等人的诸多揖让之举,而是当即下书说:“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
按王莽的说法,他是按照金匮中的汉高祖传国金策来受禅即真的。也就是说,王莽即真用的是禅让方式,但不是在位君主(孺子婴)的禅位,而是以在位君主的先祖刘邦之名禅让受禅的。虽然,汉末早有高祖为尧后之说、王莽为舜裔之论,但这种尧舜后人的禅让方式,还是与先秦禅让的传说和理想大相径庭。公元九年,王莽得金匮当日,便即位称帝(即真皇帝),宣布改正朔,易服色,定国号为“新”。公元20年(地黄四年),更始帝的汉兵攻入长安,杀王莽,西汉末的禅代,就此落幕。
对王莽禅代之败,论者多矣。笔者从禅让说进入实践的视角来观察:王莽在中国大一统王朝史上,第一个以禅让名义操弄君权转换。他从古制中摄取各种规章、礼仪,构建君权禅代制度,为新旧王朝更迭提供了汤武革命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但是,他以周公摄政作为权力转换方式的模本,这一路径选择自始就已陷自身于困局。须知,周公摄政的模式指向是归政,不是取代。以周公形象自居的王莽,从居摄走向代汉,等于让周公代周,何其荒谬!此荒谬加上他代汉后实行的种种改制错误,使其难以培育新朝代汉的正当性。正当性缺失,新权威难立,是刘氏复汉、王莽失败的重要原因。
先秦士人的禅让理想,在走入实践领域出现的乱象,是不是理想面对实践命中注定的遭际?但是,有一点清晰可见,禅让说是由御用汉儒帮扶权臣、政客纳入政治领域的。自此,禅让成为权臣操弄权力转换的工具。
成为鼎革主流选择的禅让制:由受禅者驱动蜕变的权力转换方式
王莽以禅代方式易汉为新,为后世权臣、野心家以禅让规避恶名、谋夺君位提供了先例。继王莽禅代即真后,曹魏代汉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个案。
曹氏以魏代汉,行于文帝丕,萌于武帝操。具体过程,史书记载颇详。此处仅就曹魏以禅代之名操弄君权转换,对禅让礼仪制度的增删、改变等作一讨论。
(一)改换禅代路径。建安二十五年春,曹操去世,曹丕袭位。曹氏代汉提上议事日程。据史载,汉魏禅代,汉群臣、魏公国臣僚劝禅代多达十余次。每次劝禅所引史上先例,多以尧舜禹的禅让事迹为说辞。可见东汉末的操弄禅代者,刻意避讳王莽的居摄—禅代模式。
(二)改仿西周公国制,建置预备禅代的政体。王莽代汉以周公为范本,建公国取西周上等公国之名,实际操作则按西汉的封国规制。史载,曹氏的封国不效仿王莽的公国做法,而是实质上采行西周裂土分封的方式。这可能与曹氏以武功崛起登顶权臣有关。曹操以武功“相天子”,不似王莽。其受汉封国,由公而王,是在汉献帝苟延残喘的局面下操作的。曹操的公国以魏郡为中心,重新划定九州,分置行政区划,还按公国礼制,建社稷宗庙。最重要的是曹操的魏国与汉朝一样,设有尚书、侍中与六卿,也设相国、郎中令等官职。因此,曹魏代汉前,在汉朝事实上存在两套行政机构,一个是朝廷的,一个是曹魏的。曹魏公国在东汉体内日益壮大,不断蚕食东汉母体,最终以禅代方式转换君权。
(三)揖让礼。古史中的禅让说,是以贤德为核心,礼让为准则的。禅让的要义,就是贤贤相授,不争。《汉书》载,王莽行揖让是在受封安汉公爵位和宰衡职位之际。前者封爵固让了两次,后者授职也固辞了两次。至于曹魏代汉时的劝禅、揖让,裴松之《三国志注》记录甚详。按此书的记录统计,曹丕辞禅、揖让达19次之多。
自曹魏代汉行如此揖让始,揖让成为后世禅代的一种礼仪制度。其后,司马昭受魏封爵、加九锡,也仿曹丕行揖让。据《晋书》所载统计,揖让达十三四次之多。魏晋以降直至隋唐,凡以禅让改朝换代的,均行揖让礼。只是,每代史书记载的揖让内容愈益简略,次数每况愈下。此种现象表明,原本作为禅让理想体现贤德礼让的原则,被转换设计成了一种君权易姓的礼仪。仪式化的揖让不再是贤德礼让。行之越久,仪式越固化,离其原则也越远。失去内涵的礼仪,同时也失去了令人敬畏的约束力。由此,汉魏以降,用禅让操作君权转换,所行的揖让礼多为血腥易代的伪饰,行之越久,双方心知肚明,强者夺权在手,揖让便成为走形式的虚礼。
(四)处置禅君。以禅让操作君权转换,实现的是君臣易位。由此便出现一个禅代后禅君(原君王)的处置问题。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禅让,均为前君衰老、亡故,受禅者即位,不存在旧君安置问题。当先秦盛行禅让说时,以禅让理想处理君臣易位的燕国,采取的是受禅者为君、禅君为臣的做法。及至王莽禅代即真,处置汉帝孺子婴时,明面上虽给予礼遇特权,但行为上要求孺子婴“北面称臣”。魏晋以降,曹魏、司马晋、北齐、刘宋、萧齐、杨隋的新君对旧主都规定“上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也就是说,新君不将旧主降格为臣,突显禅代中的不臣之礼。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曹魏代汉、司马晋代魏,虽将禅君封为王公,享不臣之礼,但其封地受监镇,行动受限制。及至刘裕代晋,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隋代北周,唐代隋,禅君均在禅位不久薨、崩。
以上古传说构建的禅让理想,自春秋战国倡行,至中国史上最后一次以禅代之名操弄赵宋代后周,蹇蹇而行千年。细察这一“理想”走向实践的历程,其在西汉末被践行之初,首先接纳它的不是在位的君王,而是欲取代君主的权臣、政客。由此,促成禅让的第一个变异:自此行禅代不再是上位禅君主动的推动,而是下位权臣谋夺的操弄。禅让主导角色的这个变化,导致第二个变异:禅让理想规定的贤贤相授、礼让易位的核心原则,被位极人臣的权臣所拥有的强力所阉代。禅君平庸不贤,受禅者被考量的不是贤否,而是实力如何。贤贤相授变为权力较量。第三个变异:谋夺者偷换了禅让理想的核心内容及礼让程序后,将禅让最初规定的贤贤相授的内在正当性证明,转移至以五行、谶纬、瑞徵等方术的外在正当性证明。原本禅让理想所说的尧舜禅让,是由禅君的让与行为使受禅获得正当性,其禅受双方内在关联的权威基础是天下公认的贤德。观察贤德的重要表现,是禅受双方对最高权力真正的敬畏和揖让。及至权臣用禅让操作权力转换,被迫让位的禅君,虽下一纸禅位诏书,但无内在的权威基础,由此不得不求助于神怪瑞应的外在证明。最后,在禅代走完封国、锡命、易位的程序后,手握君权的“受禅者”对不久前相揖、礼让的禅君加之幽闭、鸩杀,可怜的一点礼仪伪饰都被浸入宫廷喋血之中。
先秦士人以禅让传说构建禅让理想,以图实现贤贤相授的贤人政治,消弭人类在最高层面的权力恶争,可谓用心良苦。政治理想有拥抱政治的渴望,然而所有进入政治场域之人、事(思想、行为)必定要遵循政治的逻辑。政治逻辑本质上是权力逻辑。通行的不是士人所尊崇的贤德原则。中国自秦汉大一统之后,整个国家的吊诡之处在于,无处不称“礼”,却处处皆有争。在此背景下,禅让的旗帜高祭了千年。理想实现了?理想死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