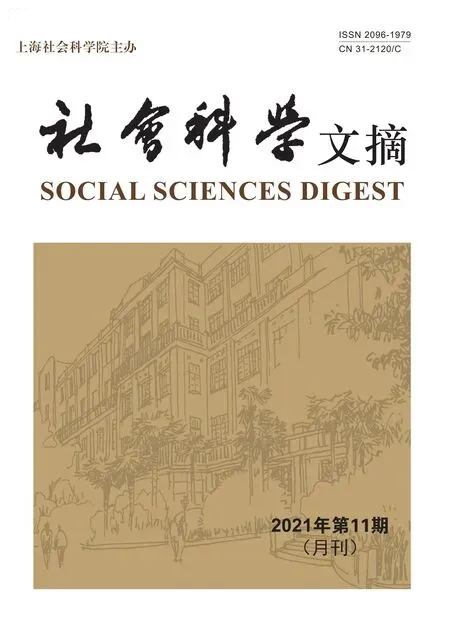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潮流化”问题
文/斯炎伟
(作者单位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摘自《文艺研究》2021年第10期)
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普遍的认知是线性而模块化的,即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现代派、先锋、新写实、新历史等文学潮流的更替,构成了线索清晰与逻辑井然的存在。这种“常识”的获得,一方面来自文学史的强大叙述,另一方面则与当时文学批评的“潮流化”有关。所谓文学批评的“潮流化”,是指批评家倾向于将一时的文学创作纳入某种特定的文学潮流中,致力于用某种“共名”的话题或理论来阐释作品和创作现象。这种批评使纷繁的文学创作获得某一话语的支持与开发,在凝结成“共同体”的同时,也迅速成为文坛热点,从而使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双双拥有了令人迷恋的前沿品格或革新光晕。“潮流化”的文学批评是80年代文学创作的强大驱力,同时也历史性地留下了某些问题。
作品的“被入潮”及其意义的嬗变
文学批评“潮流化”的一个结果,是一些作品在发表后,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某种文学思潮裹挟,原本不乏个人化的创作动机,极大程度地被该文学思潮的话语收编,而文本可能存在的别样意蕴,也经这种话语的特定阐释,实现了面向潮流的更替。
这种现象又分不同的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于强调“革命与非革命”“道德与非道德”的二元对立思维仍然流行,因此,文学批评对一位作家最大的压力,往往不是对其创作水准高低的评判,而是以“革命”或“道德”的名义,对这种创作的合法性提出根本性的质疑。在这种情形下,个人化的创作想要获得认可,其实并不容易。将作品与那个时代某种颇具感召力的集体话语发生关联,或索性将其定格为该话语的一个注脚,就成了文学批评帮助作品摆脱尴尬境遇的有效方式。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集体话语,无疑是依附于新启蒙思想之上的伤痕或反思文学。
以《爱,是不能忘记的》为例。这篇小说后来被文学史普遍置于伤痕、反思思潮中加以叙述,认为“它反映了对‘文革’灭绝人性的控诉”,或者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然而在没有历史创伤经验的后人看来,该小说似乎并没有多少“历史控诉”的成分,它更多的是在人道主义思潮复苏之际,一名青年知识女性对爱情与婚姻“割裂”问题的个人化思考,里面的“伤痕”与刚刚过去的十年动荡岁月并无直接联系,文本与《班主任》《伤痕》等更具标签意味的小说明显不同。“文学史常识”与作品内容之所以存在龃龉,当时的文学批评或许是问题的根源。小说发表后,随即引发文坛关于其中的“爱情”是否合理的争论。批判者认为,这种“爱情”的“合理性是很值得怀疑的”,“作者的许多优美抒情之笔恰恰是伤人的箭”,作家“不应把暧昧的、缺乏道德力量和不健康的情绪美化成诗”,评论家也不能“陪伴作家沉陷在‘悲剧人物’的感情里,共同‘呼唤’那不该呼唤的东西,迷失了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这种“道德质问”式的批评对当时作家的精神和文本价值的判定,无疑都构成了巨大的冲击。由此,顺应着当时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文学批评开始从“反思民族历史”和“批判封建意识”的维度中去求得作品的价值。批评家黄秋耘对作品的阐释作出引导,“我希望他们不要去责怪作者”,而是要去“认真思索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评论者禾子则指出,理解这部小说需要“联系到我们民族的历史”,“特别是最近十年的政治动乱”,认为作品正是“从这个角度,透视了社会的落后保守面,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生活理想”。在有意无意间,这些“入潮”的文学批评在当时形成了一种历史合力,把文本引向了伤痕、反思文学的轨道。当时《人到中年》《灵与肉》《绿化树》等作品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它们被反思文学“拯救”,同时又被反思文学“规限”。
如果说80年代初一些作品的“被入潮”带有某种形势所迫的意味,那么80年代中期一些小说被批评裹入寻根文学,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兼具民族现代化和文学现代性的双向关怀,寻根文学在80年代中期强势崛起,相关的批评话语也获得了巨大的感召力。在它的运作下,一些文本出现了意义转轨的现象。
以《小鲍庄》为例。王安忆说她写这篇小说“最明确的念头”,是“寻找一种与过去所看惯也写惯的截然不同的结构方法,寻找我们自己的叙述方法”,它源于一次采访时“沿途听到了许多故事”,引起了“我对插队生活的许多回忆”,并说对写作《小鲍庄》产生影响的是自己的“美国之行”,而不是当时已被视为寻根文学模本的《百年孤独》。可见《小鲍庄》的缘起没有明确的文化寻根意识,它是散落在民间的原生故事、作家的生活经验以及那一时期作家特有的艺术眼光共同发酵的结果。然而,在寻根文学无限风光的时节里,批评家似乎无暇去细细体悟“美国之行”以及那些原生形态的故事之于作品的意义。《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发表的4篇评论文章,或将作品纳入“向着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探求”的创作行列,或聚焦“小鲍庄人们的仁义”来阐释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或通过文本中“双重迭影”世界的分析来考察小鲍庄仁义文化逻辑的生成与衍变,或以“改造国民性”为尺度对小说的“光彩”与“缺憾”作出评析,这些批评都带有明确而浓烈的文化指向,都几乎搁置了作家本人的创作自述。类似的批评随即流行起来,“民族”“文化”“仁义”等一时间成了批评家阐释《小鲍庄》的必备符码,“捞渣”也从现实中的一个“小英雄”,变成了“仁义精神的符号”,一部寄寓着作家对小说形式进行艺术探索的作品,就这样获得了寻根文学经典的文学史定位。
“祛潮流”写作的尴尬及其历史化的难题
文学批评是文学历史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潮流化”的文学批评具有吸附与排斥的双重功能:既能通过批评的集体效应,汇聚某种文学潮流;也能以失语的方式,疏远乃至遮蔽那些“祛潮流”的写作。对于那些疏离潮流的个人化创作而言,它们多少遭到了这种批评的怠慢。
这种怠慢首先体现在对“祛潮流”写作意义或价值的低估上。因不够“时髦”,“祛潮流”写作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批评,其影响力、经典性及文学史价值的不足,也就在这种状态下变成了“共识”。这方面的典型个案,或许当属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从创作自述可知,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时是怀有强烈的经典诉求的。他不避以当时被众人视为“一辆旧车”的现实主义为方法,立志写一部向“十九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那样伟大的程度”看齐的作品。《平凡的世界》当然远非完美,但它似乎也具有某些经典现实主义的元素,是新时期以来各历史阶段读者“购买最多”“最喜欢”以及对读者“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之一。
然而,在新思潮席卷全国的背景下,《平凡的世界》遭到了“理所当然”的冷遇。出于对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等的偏爱,《当代》杂志和作家出版社的编辑直接将小说第一部退稿。第一部后来在《花城》上发表,但第二部和第三部在《花城》那里却没了下文,最终第三部发表在山西作协的《黄河》上,而第二部则从未在杂志上全文发表。198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在出版《平凡的世界》单行本时,公司领导则带着“深深的怀疑”。评论方面,除了蔡葵、朱寨和曾镇南这三位在京批评家给了路遥“永远难以忘怀”的“宝贵意见”,80年代其他对《平凡的世界》的批评极为零星与罕见。尽管这部小说拥有大量读者与听众,但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并不拥有书写文学史的资格。批评的缺席,让《平凡的世界》丧失了历史化的重要资本,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文学史叙述对其“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有人曾做过统计,在1986—2010年间的76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对路遥有记载的仅为16种,占总出版数的1/5,其中在21世纪之前提及路遥的文学史仅为5种,这里面还包括了只提《人生》而不提《平凡的世界》的文学史。这自然要被后来钟爱路遥的批评家视为“遗憾”。
对80年代“祛潮流”写作的怠慢,也体现在因话语准备不足而导致的批评的飘忽与游移上。80年代的“祛潮流”写作也有让批评界“眼睛一亮”的时候,但同样因逸出了特定的话语场,“潮流化”批评难以对“亮点”作出必要、恰当的阐释,导致文本的意义一度被悬置,并为作品随后的历史化预设了难题。
《受戒》就曾遭遇这种尴尬。文本强烈的新奇感,让当时不少批评家看后“喜形于色”。但相较于80年代初特有的创作与批评格局,这种新奇又似乎过于超前,主流批评界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话语来谈论它。不能像《爱,是不能忘记的》那样被某种强势话语“拯救”,那么对《受戒》的批评,其实已经被预置了危机。一方面,小说中的“另类”生活惯性地遭到一些评论者的质问,轻者指责其“没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重者痛斥“爱情居然找到和尚头上来了,多么新鲜呀”;另一方面,看后“喜形于色”的批评家对作品的肯定也显得小心谨慎,往往只是感性地称赞,而对小说的新质缺乏深入探究的意愿。毕竟,小和尚与村姑恋爱的故事,实在难以与当时主流批评所强调的生活的“深度”或“高度”发生关联。这种闪烁其词的批评当然无法沉潜作品的意义,但它为被嗣后汹涌而来的寻根文学的“征用”创造了条件。由于具有乡俗、士大夫精神等文化元素,《受戒》在80年代中期被寻根文学思潮重新发现并大规模评论。随着批评界或是指认汪曾祺小说的“精神母体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是将汪曾祺定格为寻根文学“这一群体的先行者”,《受戒》的思想意蕴开始由人生况味的抒怀走向文化形态的探讨,这成为当时评论界的普遍认知。被寻根文学“召回”虽陡增了小说的热度,但作家本人似乎对此并不认可。面对“怀恋传统文化”的说法,汪曾祺“看后哑然”,他不愿看到自己小说中的“真人生”被批评家装进“传统文化”的模子里。因此,《受戒》的意义其实在当时并没有被稳定下来,就像黄子平在1989年所说的那样,“直到今天,这种‘异质性’也未得到很好的阐明”。
批评范式的趋同与批评品格的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潮流化”的文学批评极大释放了80年代中国文坛的生产力,它也有许多值得发扬光大的特质。因此这里谈论的所谓“问题”,不是对这种文学批评合法性、合理性或重要性的质疑,而是指出当这种批评构成为一个历史阶段“整体”的批评事实时,它可能会留下的一些历史后遗症。
如果以恩格斯所指认的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衡量,那么较之于“美学观点”的丰盛,80年代“潮流化”文学批评的“历史观点”则要黯淡许多。“潮流化”批评对文本和创作现象的全神贯注,让我们见识了一代批评家非凡的阐释能力,但就批评的整体而言,它似乎像曾长期统治美国文学研究界的“新批评”那样,有着“走向某一死胡同的倾向”,即“一部文学作品成为供人们观照的完整客体,唯我地存在于自己的领域之内”。这并不是说“潮流化”的文学批评不存在外部研究的成分,比如在评论伤痕、寻根文学时,批评家也会联系“十七年”或80年代中国社会的某些周边因素,但这些因素往往只是批评家分析作品的背景,而不是批评中的“历史意识”。陈思和在90年代的一次对话中曾明确指出,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最大的先天局限”,就是“历史意识的极度贫弱与极度匮乏”。当然,不能无视“告别过去”的时代诉求对批评家历史态度的潜在规约。另外,80年代的文学演进与社会变革也实在太快,快到了批评家或许只能忙于应对新的创作现象,还来不及将它们置于历史的维度中进行考察。这样说来,“潮流化”文学批评缺乏历史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历史的难题”。
除了历史意识的匮乏,“潮流化”文学批评还存在欠缺科学性的问题。由于强调“欣赏”和“理解”,“潮流化”文学批评存在艾略特所提示的“滑向单纯的解释的危险”以及“堕入主观和印象的陷阱”。当这种批评被定格为80年代文学的知识体系时,就有了“局部的主观”与“整体的事实”发生混淆的危险,即批评家在某一特定语境下对文本的症候式解读,不经意地构成了后人“永久”“完整”的知识。这种以局部替代整体的方式,也许有损于批评的科学品格。我们现在或许可以思考:“潮流化”的文学批评是否过于强调了当时流行的思想?被这种流行思想所塑造的公共经验有没有武断的成分?或者说是否被放大了?“批评的事实”是不是对象本身的“事实”?毕竟,批评的主体性与经验的公共性、思想的鲜活度与知识的可靠性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的问题,这是保障文学批评兼有人文性和科学性的重要前提。近年来,随着“重返80年代”学术实践的不断推进,“潮流化”文学批评的主观性、绝对化等问题开始受到关注。一方面,“目标预设”的征象日渐显现;另一方面,知识的“破绽”似乎也越来越多。我们或许应该承认,批评的历史有效性并不等同于永久的科学性,理论的盛宴也不意味着理论的成熟。
另外,相较于发达的内部研究,80年代的“潮流化”批评较少关注文本的外部事实。这些事实既包括作者的生平阅历、个性气质、家乡风俗与地理文化等,也包括文学体制、文本“本事”、流行文化等。依照韦勒克对文学的定义——文学不是“内容”与“形式”的二分,而是“美学要素”的“结构”(structure)和“与美学没有什么关系”的“材料(material)”的有机体,那么这些外部事实无疑构成了文学的“材料”。疏离了这些“材料”,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疏离了文学本身。弗莱始终认为,文学批评的“中心活动”就是“为被研究的文学作品建立起关联域”,除了“文学本身的总体结构”与“词语的秩序”,还要把“作家生平、时代、文学历史的来龙去脉”等联系起来,因为“来龙去脉的关系几乎说明了批评的全部事实基础”。“潮流化”的文学批评当然注重文本事实,但对文本之外的种种事实疏于考察,因而它难以呈现弗莱所说的“全部事实基础”。而有没有“事实基础”作铺垫,或者“事实基础”的底子厚薄问题,不仅事关批评的底气,还关乎其日后遭逢各种“重评”时的抗击打能力。这大概也是今天的研究者普遍倾心于“诗史互证”式批评的原因。
本文讨论20世纪80年代当代文学批评的“潮流化”问题,并非要去颠覆一个时代的批评神话,或去否认一代批评家辛勤的劳动与卓著的理论贡献;而是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我们拨开当年的历史迷雾,去寻找那些被“历史需要”遮蔽的文学史事实,并进而与“潮流化”批评的结论一道,构筑一个更多元、立体的80年代文学认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