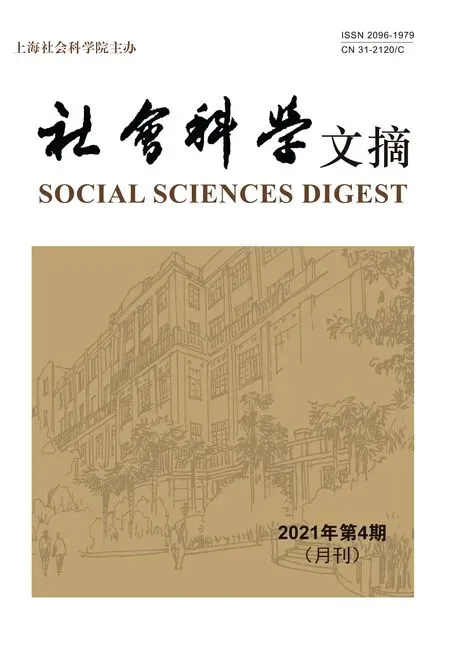社会基础变迁与部门法分立格局的现代发展
文/宋亚辉
改革开放后,中国致力于构建的以部门法为基本单元的法律体系开始遭遇结构性挑战,部门法的理论范式对实证法的解释力也日益捉襟见肘,由此上发诸多理论问题:第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法制建设,总体上是以大陆法系的部门法分立格局作为基本框架,但为何在既定目标尚未达成之时,立法者又区分不同行业领域,制定一系列拼盘式单行立法?第二,在法解释适用层面,能否继续套用部门法划分的理论范式,来解读当今中国大量涌现的拼盘式单行立法?解释论上能否将单行法中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切割并纳入各部门法的运行轨道?第三,在学科划分上,区分不同行业或空间领域的拼盘式单行立法,应被视为部门法的特别法还是独立的新法域?所谓的“行业法”“领域法”,能否独立于传统部门法体系而存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从根本上是对大陆法系部门法分立格局的深刻反思。
部门法分立格局在中西方的塑造原理
(一)社会结构与法律结构的交替演化规律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则,社会关系的存在状况与法律之间的塑造原理及其互动关系,经由20世纪后期法律社会学的论辩和全球性“法律与社会发展运动”之实践,已形成初步共识,亦即认为“法律既是社会发展演化的产物,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工具”,稳固的法律结构只能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基础之上。基于这一抽象共识,晚近的研究致力于用各种经验素材来测度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大陆法系漫长的法制史为此提供了大量可供相互印证的素材。若将大陆法系的法律发展史和社会进化史依时间顺序对应起来,则眼前将立刻呈现如下图景:随着社会关系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混沌一体”走向结构分化,法律结构也呈现出从简单到复杂、从“诸法合体”到部门法分化的演变过程。
(二)塑造中西方法律结构的共通规律
社会结构与法律结构不仅保持着交替演化的规律,而且前者对后者具有内在的塑造力。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在法律上的反映,本文将其简称为“法律结构决定论”。若以此观点来审视大陆法系的法律演化脉络,将会发现,当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从“混沌一体”走向“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二元结构时,法律结构也从“诸法合体”走向公私法二分以及部门法分立格局。因为随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日益多元化,相应的法律规范也愈加庞杂,面对浩如烟海且功能、手段各异的法律规范群,为避免冲突与紊乱,体系性必然成为立法重点。作为法的规范对象,社会关系的某种稳定结构自然会成为法律体系设计的参照系,否则将难以回应社会需要。于是就不难理解,法律结构与社会结构为何呈现出交替演化的规律,这是“法律结构决定论”之精髓。但这只是历史演化的方向,至于部门法分立格局为何诞生于欧洲启蒙时代,则是众多因素机缘巧合的结果。今昔对比,“当代中国的法学思潮与其社会之间的关系,与欧洲启蒙思潮及当时社会的关系具有某种相似性”,改革开放因此被誉为中国版的“启蒙运动”。
现代社会子系统分化带来的挑战
(一)现代社会子系统的多元划分与单行立法趋势
社会结构的演化具有历史的延续性,随着现代社会复杂性的陡增,社会结构呈现出从“块状分化”向“功能分化”的演变。前者是将社会分化成结构和功能近似的子系统,如家庭、村庄、部落等,除了规模差异外,它们彼此之间并无质的区别。而功能分化则不同,曾经同质化的市民社会,根据功能差异逐步分化出诸多相对独立且自成体系的社会子系统,如教育、医疗、环境、食品、交通、互联网等。曾经以意思自治来概括一切私主体之间社会关系的理论范式,如今已显得捉襟见肘。不管是功能还是运行逻辑,多元社会子系统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它们各自遵循“以我为中心的理性”法则。
面对现代社会子系统的多元分化,法律上已无法用单一的私法自治来概括不同社会子系统的规范特征,更无法用管制与自治的二分框架来统合多元分化社会的理性法则。曾经统摄所有社会关系并被视为构建部门法体系之基础的公私法二元结构,在现代社会已成为过于简单化的规范框架,它对于曾经同质化的市民社会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无法解释多元现代化趋势中的多个社会子系统各具特色的理性化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立法结构的调整在所难免。
中国当下的应对策略是调整立法技术,以多元社会子系统的区分为标准,进行分门别类的立法,立法内容大多是针对特定行业问题辨证施治。与部门法的普适性相比,行业单行法极具个性化特征。它们不仅坚持问题与对策相匹配,而且受到不同时期政策的影响,立法者致力于根据特定领域的问题为其量身定制最佳的规制方案,采取“一个领域一个立法”“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策略。
(二)拼盘式单行立法对部门法分立格局的冲击
随着现代社会子系统的分化,区分不同社会子系统的单行立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不管是其立法外观还是内部结构,行业单行法均呈现出与部门法不同的构造。
在内部构造上,行业单行法除了照搬或上用既有部门法规范之外,还习惯于根据特定行业的需要,在单行法中创设全新的法律制度。其中有些制度在性质上勉强可被部门法体系所吸纳,而有些制度则完全超出传统部门法的范畴。如《电子商务法》中的“平台责任”,《食品安全法》中的“加倍赔偿”,《电力法》中的“责令承担民事责任”等。这些全新的制度设计难以在部门法分立格局中得到妥当安置,即便勉强将其归入某个部门法,部门法分立格局的存在,又将限制不同性质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类似现象正在侵蚀公私法区分的根基,曾经以法律规范性质作为法典化和体系化整合基准的部门法分立格局,正面临“解构”的风险。
由民法、刑法、行政法等组合而成的部门法分立格局,被大量涌现的拼盘式单行立法所淡化甚至解构,法律结构的转型升级已成大势所趋。
法律结构转型中的路径依赖
法律结构的变迁在“法律结构决定论”中所展现的,似乎是一个自动演化的过程,仿佛社会关系的结构一经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结构也就会因之作出调整,但事实并非如此。倘若立足于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将会发现,任何超越既定格局的尝试,都注定是一个极端复杂且艰难的过程。因为既定格局的长期存在,必将塑造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体系、执法机制、权力结构、意识形态与公众认知习惯,而这将成为制度变迁的约束条件。这正是所谓的“制度转换成本”。由于制度转换成本的约束,包括法律结构转型在内的制度变迁才表现出对既定格局的“依赖”。
在崇尚理性构建思维的大陆法系中,根深蒂固的部门法分立格局为立法和法律适用提供了一个堪称“万能”的分析框架。根据法律调整对象的性质差异,法律体系被分为多个法律部门,它们相互之间分工明确,以不同的方法调整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由此决定了各部门法在调整对象、法律主体、权利、义务和责任等核心范畴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反过来又强化了部门法分立格局。理论和立法的互动,使部门法分立格局得到自我强化,逐步形成固化的法解释路径。经过上百年的适用,逐步塑造了部门法的理论范式。在法律适用中,部门法之间界限分明,各自秉承不同的行为评价体系、归责原理、责任方式和实施程序,若不严格加以区分,则极易产生法律适用错误。
在部门法理论范式的“惯性”作用下,当遇到特定行业的具体问题时,人们习惯于辨析其部门法归属或判断其属于哪个部门法的调整对象,而后才在部门法划分框架下运用部门法的逻辑展开分析。这是一种典型的“路径锁定效应”。部门法的理论范式塑造了法律适用上的思维定式,人们习惯于直接套用既定的分析范式,分门别类地以部门法的逻辑来应对各种社会问题。
在这样的理论范式中,现代社会子系统多元分化所催生的拼盘式单行立法,虽然在立法形式上超越了部门法分立格局,但因路径依赖,各领域的拼盘式立法在解释适用中仍被习惯性地切割处理,以各自部门法的逻辑独自运行。这种各自为政的应对策略,使整体上的规范效果可能因遭遇瓶颈而停滞不前。这种“内卷化”的倾向,使部门法内部变得日益复杂而无法向更高级的结构转型。
不过,路径依赖并不意味着制度变迁将就此停滞。一个与社会基础不匹配的法律结构将会处于低效率运行的状态。在社会结构与法律结构的互动关系中,一旦改变既定格局对于拥有充分谈判能力之人有利可图时,法律转型的进程便将就此启动。学者们的理论探索与立法者追求体系完美的动力,也将加速这一进程。
部门法理论范式的现代超越
(一)行业单行立法的两条体系化路径
面对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规范在行业单行法中的合流之势,体系上该如何重构日益碎片化的单行立法?它们不再是纯粹的私法自治原则或公法管制原则一以贯之的体系,反而呈现出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公私法相互工具化的融合趋势。未来应坚守部门法分立格局,还是超越既定格局进行体系重建?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的矛盾于此再次凸显,并表现为以下两条体系化思路:
第一,在部门法理论范式的惯性作用下,有学者习惯性地根据法律规范的性质,以部门法划分框架,对行业单行法作水平切割,视之为部门法的特别法,由多个部门法规范堆砌而成的拼盘式单行立法因此被视为“部门法分立格局在各行业领域的延伸”。
第二,依据拼盘式单行立法的行业属性或领域对其作垂直切割,形成“跨部门的行业法结构”。在宏观法律体系的构成上,如果说部门法分立格局区分了法律体系的“块”状结构,那么依据所属行业或领域所作的体系划分则形成纵向的“条”状结构。这样的垂直切割模式不再关注单个法律规范的性质与部门法归属,而是从功能主义角度,将各自领域的拼盘式单行立法作行业切分,只要有助于解决特定行业领域的实际问题,任何性质的法律规范都可整合到同一部单行立法。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在结构上并非松散的“水果拼盘”,它们以相互协作的方式致力于实现共同的行业规制目标。
(二)“跨部门的行业法结构”之理论根基
本文主张以垂直切割模式重构当今中国大量涌现的拼盘式单行立法,其法理基础在于,此举可以有效回应当今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一种与社会结构相匹配的法律构造。
法之“理”源于社会,面对现代社会子系统的分化和公私融合趋势,曾经坚守着私人自治的领域,如今已成为公私法协同共治的领地。“当代社会实践不再只能通过公/私的二元区分进行分析,不论是在社会科学中还是在法律之中;社会碎片化为多元社会领域这一事实也需要多元的自我描述视角。”行业单行立法中看似随意堆砌的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实际上均指向共同的行业规制目标。这一功能主义“共识”,为重构行业单行法的碎片化局面提供了统一的基准。
根据这一重构思路,未来的行业法体系将呈现出不同于部门法分立格局的双层构造:一是以多元社会子系统的区分取代传统的公私二分;二是在多元社会子系统内部重新上入公私两个维度的区分与融合视角。调整社会子系统的法律,由此呈现出一个个“五脏俱全”且自成体系的单行立法结构。理论上对法的认知,也将从“纯粹理性阶段”发展到“整体主义和多元主义阶段”,以此回应现代社会子系统的多元分化与公私融合趋势。法律结构与社会结构由此实现了结构耦合。
(三)“跨部门的行业法结构”之功能优势
以水平切割模式将各行业领域的拼盘式单行立法视为“部门法分立格局的行业延伸”,这种做法背离了各行业以自我为中心的理性化进程,阻碍了行业单行法的功能发挥。
相较之下,以纵向切割模式构建跨部门的行业法结构,有助于立法者系统性地围绕特定行业规制目标作综合性的立法设计,避免在同一行业内部进行人为的部门法分割所导致的制度壁垒与协调障碍。学界在以部门法的特别法视角研究具体行业的法律问题时,也已意识到水平切割的局限性,例如行政法学者虽将环境保护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消防法视为部门行政法,但也指出,部门行政法大都有其独特的理论和制度体系。再如,关于环境侵权、医疗侵权、交通侵权、网络侵权的法律,虽都被视为特别侵权法,但各自所属行业的价值取向、致害原理和行业规律差异造就了各不相同的归责原理、责任构成要件和举证责任,这源于不同行业以自我为中心的理性化进程。当部门法的内部构造越来越多地在具体行业领域发生变异时,理论上不宜简单套用部门法分立格局以部门法的特别法来对行业立法作水平切割。立足于特定行业领域的“特别法”,均承载着各自行业内部的独特规律,否则,立法者只需在行业单行法中直接上致部门法规范即可,而不必另起炉灶地创设新规则。行业法的体系化,须充分尊重其背后的行业规律,不宜强行以部门法的特别法来统合所有领域的拼盘式单行立法。恰当的思路是转向功能主义视角,根据单行法的所属行业与功能对其作垂直切割,以跨部门的行业法体系来重构拼盘式单行立法的制度结构。
“法律结构论”的范式转型意义
法律结构变迁不只是社会基础演化的结果,它同时也在推动着社会结构的持续分化与再次融合。这一法律演化理论,除了具有阐释历史之意义外,同时还具有规范构建之价值。这对于中国法的现代转型与法治实践而言意义重大。
第一,从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来看。“条”“块”结合的法律结构有助于实现社会基础与法律体系的良性互动,如果说部门法的“块”状分化回应了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功能分工的话,那么,行业法的“条”状分化则集中回应了现代社会子系统的多元分化与公私融合趋势。这样的体系构造,使得整个宏观法律体系能够保持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平衡。
第二,在立法论层面,行业法所强调的法律调整对象的行业属性与跨部门法结构,为行业单行法的内部制度设计提供了自由发挥的场域,便于立法者在特定行业领域,围绕具体规制目标进行实用主义的制度设计。
第三,在解释论层面,跨部门的行业法结构能为兼具公私法双重属性的制度创新提供恰当的解释基础。例如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借助私人力量来补充公共执法资源的不足。这完全是公私法融合的产物,而非部门法分立格局所能解释。
第四,既然行业法在立法论和解释论上均具有不可替代性,那么,法学学科的划分也应当重视以法律调整对象所在的行业或空间领域为标准来构建跨部门的行业法学科体系。这样的学科体系有助于缓解法学研究与法治实践的隔阂。这正是本文提倡“行业法”“领域法”“法域”等概念的深远意义,这种垂直整合的学科体系,将使法学研究更接近真实世界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