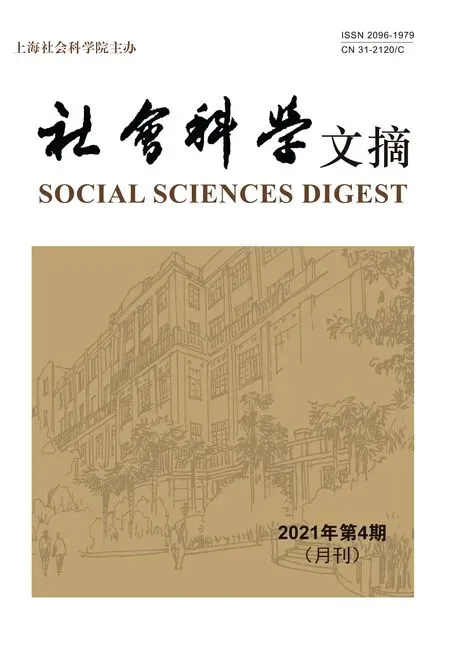脑哲学的可能性与问题域
文/肖峰
倡导脑哲学的背景
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大脑是我们在宇宙中发现的最复杂的物质,是科学研究最活跃的前沿,脑的奥秘成为科学需要攻克的最难堡垒和面临的最大挑战,各大国几乎都制定了“脑计划”,使得脑科学在近几十年内获得了蓬勃发展。
脑在成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同时,也正在成为技术模拟的对象。类脑设计的人工智能或人工神经网络及机器学习进路的人工智能,就是人工智能与脑科学结合的机器智能新技术,目前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喜人的进步。
当脑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模拟中呈现为最富价值和最具前景的科技前沿时,其理应得到哲学的关注和重视,建立“脑哲学”的可能性也就顺理成章,同时也刻不容缓。
维特根斯坦曾有过这样的感叹:令人奇怪的巧合是,每个人的头颅被打开后都有一个脑,这标志了哲学家对脑的一种惊奇感和对其沉思的冲动。脑哲学就是要将脑纳入自己的视野,使其成为哲学研究和反思的对象。
从脑科学走向脑哲学具有内在的必然性。脑科学与哲学世界观联系的紧密程度不亚于任何别的自然科学领域,脑科学家因此也不可避免会遇到哲学问题。因为脑是干什么的?脑就是思考的器官,这就必然涉及心脑关系这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当然还会涉及脑与人、脑与身体、脑与环境(的互动)等关系问题,从而牵涉到心智哲学、人学、身体哲学、实践哲学等部门哲学。不仅如此,哲学家思考大脑时也可能形成独特的角度,形成对脑科学富有启发性的问题。认知科学家保罗·萨伽德认为,脑科学对于有关知识、现实、道德和生命意义的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至关重要,可以使形而上学和伦理学问题得到更好的阐明。今天的脑科学提出的许多问题也需要从哲学上给予解释,由此产生的脑哲学可以与脑科学形成互补互惠的关系。
脑哲学的界定
美国哈佛大学神经学教授乔治·诺索夫(Georg Northoff)在2004年出版的Philosophy of the Brain:The brain problem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脑哲学”的说法。他将脑哲学界定为从三个维度对脑进行的研究:一是关于大脑的经验的、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含义;二是要开发一套经验、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的合适概念来作为研究大脑的合适的框架;三是要通过“大脑问题”与“精神问题”的联系来思考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向。我们可以从对哲学和脑的更广义的理解上将脑哲学尝试性地界定为“关于脑的哲学研究”,抑或是在人脑的科学研究中所产生出来的哲学问题及其探究,尤其是对脑的科学新发现进行哲学阐释,某种意义上也可视其为“脑科学哲学”。
其实,涉及脑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并非是有了脑哲学之后才开始的,在这之前,若干新兴的甚至经典的哲学学科或分支也不乏对脑的哲学问题感兴趣,以至开辟出专门的研究领域,“神经哲学”(Neurophilosophy)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领域。脑哲学虽然与神经哲学同样以大脑为研究对象,但两者之间也具有显著的不同:
第一,立场不同。神经哲学秉持了特定的立场,它是心脑问题上的“取消主义”这一流派的代名词,而脑哲学并不一定坚持这种立场,因为它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个领域。
第二,在对象上,两者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因为脑并不完全等于神经:神经只是物质;脑,尤其是脑状态,是神经活动及其心智状态的交织。
第三,基础不同。神经哲学的基础是神经科学,脑哲学的基础是脑科学。脑科学不等于神经科学,它研究的范围比神经科学更广,如它还包括脑电科学、脑信息学,广义地还应包括脑模拟技术——计算机科学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等。
脑哲学与身体哲学之间也具有独特的关系。当脑被视为身体的一部分时,脑哲学似乎也可视为身体哲学的一部分。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身体虽然包含脑,但由于脑的特殊性,尤其是作为身体的“司令部”,决不能简单地从隶属于身体哲学角度来定义脑哲学的学科属性。通过具身认知与具脑认知之间的关联可以揭示:心智是人脑的功能,但又不仅仅是神经系统的产物,身体及其与环境的互动对认知的开展乃至对脑功能的形成必不可少,在这个意义上身体哲学与脑哲学就具有一种互在互为的关系。
脑哲学的主要问题域
心脑关系问题无疑是脑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但脑哲学不能只研究心脑问题,否则它就和心智哲学没有区别,因此脑哲学还应关注更多的问题。
1.什么是哲学意义上的脑?
哲学意义上的脑,既来自作为脑科学对象的解剖学意义上的脑,又不同于解剖学意义上的脑,而是解剖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的集成,是由神经状态和心智状态共同造就的。脑科学从人脑与动物脑的物质关系上为我们界定了:人脑不是最大的脑,但是最好的脑,并从物质根源上解释了为什么人脑是最聪明的脑,衡量标准是脑中神经元的数目,且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大脑皮层的神经元数目。在这种特有的物质基础上,哲学视界中的人脑被界定为物质发展的最复杂形态,从而将人脑视为宇宙的缩影和精华,是联接两个世界的桥梁。当然,即使是从哲学的角度看人脑,在不同的哲学派别那里也会各不相同。在纳入技术(如脑机接口、人工智能)因素之后,人脑的功能被不断延展,于是脑的边界问题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哲学问题,这就是心灵的延展和脑的延展之间的相互纠缠,哲学中的脑由此也衍生出越来越多样的表述,从“孤立脑”到“嵌入脑”再到“动态脑”,体现了脑哲学对脑的理解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2.脑与人
一定意义上,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两者的脑不同。当我们说人是会思考的动物时,就是将人脑置于能规定人之为人的重要地位上,而人区别于动物的其他本体论特征(如语言、制造和使用工具等),也要归结于人有在智力上远高于其他动物的大脑;人在生物进化中从爬行到直立行走,其最重要的结果就是人脑的体积变大,从而为其智能的进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脑本身可以作为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之源,人类的神奇之处必须要从他所拥有的智慧大脑上去阐释,这就使脑具有了对于人的本体论地位之特殊的哲学意义。
脑哲学在考察人脑的独特性时,还必须基于哲学的视野,把人脑的形成置于更广阔的背景和系统中去考察,从基因与脑神经构造,从行为(劳动、实践等)和语言与人脑发育和进化中去揭示人脑功能的形成,进一步探讨何种因素对于建构人脑的作用更为重要或更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从而看到生物脑中联结着“社会脑”或“文化脑”的维度。不同的哲学派别还会强调不同的因素,并寻找不同的证据,由此还将导致脑哲学内部的争议。
3.脑与生命
作为脑科学和哲学的结盟,脑哲学可以用一种新的范式来研究生命,这就是借鉴脑科学的成就来考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在医学上,判断人是否死亡或生命是否终结的标准不再是以前的心脏是否停止跳动,而是将脑死亡视为更加科学的标准。因为脑是决定生命本质的器官,脑部死亡,病人即死亡。它同时也是更具哲学意义的标准,因为脑作为思维的载体,当其死亡后,人的感知、思维、意识和自我意识(作为人的本质特征)就已经丧失,生命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脑也具有了与生命等质的本体论地位,这也意味着脑与生命具有同一性。由此上发的哲学问题是:当脑可以在技术的支撑下存活时(如钵中之脑),是否就意味着生命的存在?或者说,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使脑存在?
在一定意义上,脑的存在不仅意味着生命的存在,而且脑的状况还深度地影响着生命的意义。保罗·萨伽德认为可以从人脑的视角探讨“生命为什么值得活下去”这类关于生命的本质和价值的最紧迫的问题。从脑状态的改善来丰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将生理的自然的因素转化为人文因素,是我们从哲学上理解这一问题的新视角。
4.脑与自我
“我是谁”的问题是经典而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在承接前面不断强化的关于脑与人、脑与生命之同一性的基础上,还继续延伸到脑与自我的同一性,这就是丘奇兰德的“我即我脑”的主张。这样的观点也可以表述为:人的自我意识使人有“自我认同”的感受,而人的自我意识存在于脑中,所以是脑决定了一个人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医学中的治疗实践似乎也印证了脑与自我的这种同一性,如在人体的器官移植或置换中,除了脑之外的无论哪一个器官被实施移植或置换手术后,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人还是他自己的身份认同。而一旦脑或脑中管自我意识的部分被实施移植或置换手术后(包括所谓的换头手术),则无疑会改变这个人的自我认同。
“我是谁”的自我认同或身份信息其实也是每个人对自己经历的记忆,于是负责记忆的海马体和前额叶或许才是“我是我”最重要的部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记忆的植入、增强或消除(如抹去痛苦的记忆、创建快乐的记忆)等“神经操作”已变得现实可行,从记忆的组装到记忆的篡改(如植入记忆假体)无疑会使人的自我意识发生混乱。可见,由脑哲学必然延伸出脑伦理学(或记忆伦理学)来对这类脑中的记忆或神经操作加以规范。
5.脑与心智
脑与心智的问题或心脑关系问题无疑是脑哲学中最主要、最复杂的问题,《脑哲学》一书主要探讨的就是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的直观表述就是:“颅内那一团布满皱褶的物质”或“黏糊糊的质料”是如何“上发主观状态的呢”?
心脑问题还可以从技术的维度加以拓展,如在技术介入的条件下从读脑到读心的问题。这一维度也是将脑与心智的问题转化为读脑与读心的关系问题,从心智的理论哲学转向心智的实践哲学,从心脑关系的本体论问题转向认识论问题。
读脑和读心是否就成为一回事?一种意见认为当心脑可以互译时,读脑就等同于读心,甚至认为表征心智的心理语言与表征脑状态的“物理语言”是同一种语言;另一种意见认为无论我们所读到的脑数据有多精准和详细,所看到的都不是心智本身,而是其物质载体,正如符号和语义不是一回事一样,这也被称为“心之不可化约性”。当然,从技术的视角或认识论的性质上看,没有必要将读脑和读心截然分开,而本体论上两者能不能互相归结,则是另一个问题。在谈论和追求读脑的技术效价时,可以暂时撇开这一问题,以便脑哲学可以和脑科学及其认知技术的发展形成更深度的融合,也正是在这点上,其和心智哲学具有一定的区别,即脑哲学侧重于从效果论而不是从因果论来探究心脑关系问题。
这样,与脑科学紧密联系的脑哲学,较之心智哲学就需要有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型,这就是从心智哲学侧重于本体论转型到脑哲学侧重于认识论,即在探究心与脑的关系时,更需关注通过脑是否能达到对心灵内容的“可知”。这里的“可知”绝非“等同”。从对人有意义来说,这样的“可知”比“是否等同”对于我们的生活世界来说更重要。
6.脑与机器
脑科学研究本身就包含对脑功能的技术模拟,人工智能就是脑模拟的重要领域。随着脑科学的新发现被越来越多地上入到人工智能的研究及其AI系统的构建之中,“脑科学启发的人工智能”成为一种强劲的趋向。这表明既然智能是在大脑中产生的,模拟智能的着眼点就应该投向人脑,而不是投向人脑之外的抽象地带;或者说大脑模拟的路径对于AI的进一步发展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其前景无限,而符号主义那种非具身化、没有“头脑”的智能研究方式,是走不远的。目前在人工智能界已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具有颠覆性的下一代人工智能(包括新一代算法)一定是基于脑结构、脑启发的。
人工智能所开辟的新领域,在人脑和机器之间建立了特定的联结。从脑哲学的视野看,脑研究和人工智能研究由此形成了互启互惠的关系,不仅存在脑启发的极富活力的人工智能研究,而且也可以有人工智能启发的脑研究,后者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新成就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加深对人脑的理解和认识,并且潜力极大。
虽然机器智能不完全等同于人的智能,但机器上涌现出智能的过程和机制,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人脑的类似活动,因此可以在某些方面为我们认识人脑产生智能的过程和机制提供借鉴。可以说,人工智能中联结主义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对脑的模拟,本身也是对脑的反向说明。机器所使用的算法本身,由于归根结底是来自人脑思考时所采用的方法,所以通过机器算法的开发及其在人工智能载体上运行效应的可观察性、可验证性,能够帮助我们部分地理解大脑运行的奥秘即活动的机理,甚至革新我们对大脑的认识。
人工智能和人脑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得脑哲学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AI研发的由人工器件构成的机器脑(或更广义的“人工大脑”)是真正的脑吗(即机器能思维吗)?它具有脑的本体论地位吗?抑或说它只是个“类脑”?机器脑与人脑的根本差别是什么?目前机器脑已有许多功能超过了人脑,如计算、记忆、模式识别等,那么我们研发更高水平的机器脑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将机器脑做得更像人脑,还是仅仅使机器脑的某些功能更强于人脑?在机器脑的功能增强时,人脑是否也可以借助机器脑来增强自己?假如延展脑与人脑的融合度极高,从而可以成为人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是否需要修改人脑的定义?这实际上也牵涉到脑的再进化问题:我们的脑究竟能做什么?我们还期望自己的脑可以做什么?我们是否对自己的脑感到满意?我们还希望自己的脑向什么方向进化?用基因工程、神经操作和脑机融合的手段来增强的大脑是否可以接受?人是否应该借助脑的延展(也是脑的再进化)而去追求拥有一颗“超强大脑”?如果人人都有一颗超强大脑,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如果只有少部分人有超强大脑,这个世界又会怎样?用技术手段增强大脑和用社会手段增强大脑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取得适度的平衡?这些都将是脑哲学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结语
与脑相关的哲学问题可以成为哲学的“富矿”和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的切入点。克里克说:“只有当我们最终真正地理解了脑的工作原理时,才可能对我们的感知、思维和行为作出近于高层次的解释。”从前述有限的问题域也可以看到,脑的哲学问题涉及哲学的各个层级和众多分支,而脑哲学将其整合集成起来,力求达到一种对脑的全景性的哲学把握;也即,将哲学智慧应用于洞察造就这种智慧的最神奇最复杂的生命器官,在最富挑战性的求索中提升我们的哲学智慧。无论从学科基础上,还是从理论必然性和实践的需要上,脑哲学的兴起都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