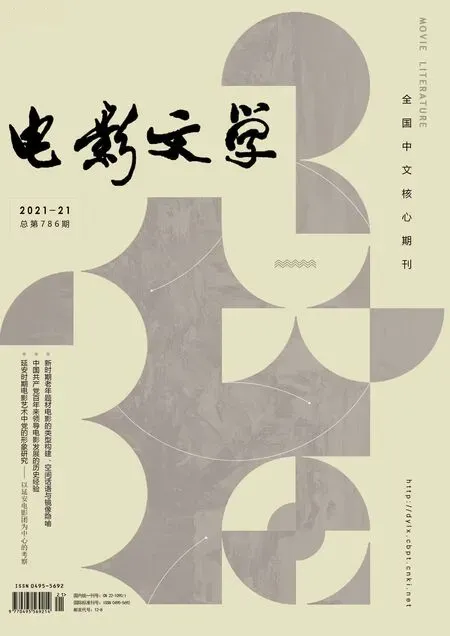成长与记忆:论电影《八月》时间的修辞
蒋诗洁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电影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八月》是中国青年导演张大磊的电影处女作,该影片获得第53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张大磊在采访中谈创作的冲动时说过,2008年他回姥姥家吃饭,80多岁的老人瘫痪在床,看着母亲用小勺给老人喂饭时突然感觉恍若隔世。张大磊回忆,1994年夏天,姥姥的母亲也同样卧床,姥姥也是这样扶着她的背,一勺一勺地将搅成糊状的饭喂到老人嘴里。那一刻他好像真的听到了1994年的音乐声和那时经常会听到的火车鸣笛声从远处传来。这样的直觉体验以及对过去时光的追忆让他有了一个拍一部呈现逝去情境和人的电影的决定。可以说张大磊的创作冲动来源于对时间的直觉。
20世纪初法国哲学家伯格森诗意地认为,现时就是人感觉的那一刻。所谓时间,就是人的感觉,只有人感觉才有所谓的时间。他提出哲学核心概念“绵延”,并指出“艺术不过是对于实在的更为直接的观看罢了……并且人们并不能直接感受到、认识到实在,因为在自然和我们之间,在我们自己和自己的意识之间,横隔着一层帷幕”,进而伯格森认为艺术的本质就在于拉开、冲破帷幕,让实在呈现于眼前。在文学叙事中,创作者对于时间、记忆以及遗忘等的思考从20世纪初到现在没有停止。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到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被掩埋的巨人》,从中国作家莫言到残雪,一个多世纪的国内外文学创作中不断构建叙事的时间。这里的时间更像是伯格森所说的一种“质的时间”,一种意识状态,聚合了过去、现代和未来,不断绵延下去的本质时间。如果说作为主体的人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的直觉把握叙事中的时间(绵延),那么电影中观者对时间的体验是从何而来?导演如何通过影像话语建构“实在”,创造不断流动的意识心理,以表现真正的时间:一种内心的、纯粹意识的绵延?
一、叙述者的无意识:时间与梦境
利用梦境中的隐喻将“质的时间”用影像外化为长大成人的欲念。《八月》以一个12岁男孩小雷的视角开始讲故事,小雷的第一个梦境出现在影片的第12分钟,从水中小雷的倒影开始。倒影中的小雷正缓缓走过一条隧道,从倒影中见到他走路的姿势:小心翼翼地仿佛怕惊醒旁人一般地沿着墙角通过淌满水的隧道,静止的积水路面像一面镜子。在拉康的立足语言学的“自我”理论中指出,从“想象态”(无语言)转入“象征性秩序”(学会了语言的)就是一个建立自我、意识确立的过程。淌水的路面与小雷的倒影象征着前语言期,表征着小雷即将在某一神秘的瞬间确立自我意识,也即将与“非我”相联系。梦境中小雷走过杂草茂盛的荒原,来到一个山谷,有人在埋头杀羊。小雷的父亲按住他的肩膀,和身旁的八个人一起津津有味地看着剥羊皮,并发出奇怪的声音。紧接着,小雷同样走过镜子般的河流旁,来到一个成熟女孩子身旁,等着她亲吻自己。
拉康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无意识就是非我的话语”。在拉康看来,语言是由意识控制的,超个人、超主体的语言和无意识便形成欲念,梦便是作为无意识的欲念呈现的一个方式。那么,时间与梦境的关系如何体现?在《八月》有关小雷的梦境中,时间对于叙述者来说就像一种意识状态,看似可以用语言(影像或文字)阐释但又无法说清甚至无法阐述(参照《追忆似水年华》),因此“时间”之于“我”包含有“他性”(无意识),就像是伯格森所说“我们自己和自己意识之间横隔着的一层帷幕”。因此,用电影语言的方式,用表现小雷梦境的影像语言、音乐音效语言呈现时间,更能说明伯格森的“实在”与“绵延”。如果把能言说的关于时间的意识看作是一个能指,当能指指向下一个新的能指的时候(下一个意识的时间),之间的能指链就是无意识,无意识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把我们包围在其中。简单地说,梦境可以作为无意识网络的一种呈现方式,来讲述叙述者对于时间无法阐述但又只能用起中介作用的语言进行说明的无意识的内容。小雷的第二个梦境出现在影片的第54分钟,从一片树林地开始,在梦境中只有小雷一人还在看杀羊,他突然发现杀羊人是现实生活中的厂区大院的“三哥”,杀羊人抬起了头。两个梦境如果用拉康的释梦理论来理解——这个理论的前提在于拉康吸收运用了雅各布森有关隐喻与转喻的修辞,雅各布森指出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是修辞性的,语言最基本的两种修辞方式就是隐喻和转喻;在小雷的梦境里,“三哥”这个能指代替“杀羊人”(一个能指代替另一个能指),类似于隐喻,表征心理症状——梦到三哥的起因;同时,这两个能指间的联系产生了空缺,空缺需要欲念来填补,无意识中小雷“想成为三哥那样孔武有力的人”——长大成人的欲念,类似雅各布森的转喻;相同的分析方式也可用于分析现实中拉小提琴的女孩与小雷梦境中的女孩。可以看到,这种“成长”的无意识又内涵着时间,在《八月》有关叙述者小雷的梦境中,时间就像小雷走过的山谷的小溪,既是发现自我的一面镜子,又如同流动的记忆;在能指与能指之间,无意识的网络遮蔽了叙述者的自我认识。
电影《八月》通过影像语言切开了一个口,让观者看到无意识的欲望是如何在成长中被察觉,这对于创作者来说需要透过时间的长河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聚集在一起,用艺术的方式呈现“实在”。
二、诗性联想:符号与象征
影像中有关生活的物象是通过“质的时间”聚合于现在与过去的时空中,利用象征的手法以表现人内心真实的感受。评论说,“《八月》是一部富有诗意的电影”。如何从语言、修辞、画面构图、摄影机运动、灯光效果等层面来看待这部影片的内涵是充满“诗的气质”?克里斯蒂安·梅茨认为,“电影的符号学可以看成诗内涵的符号学或是指示意义的符号学。内涵的研究将带领我们更为接近电影是一种艺术的观念……电影在美学上的运作及限制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内涵的要素,置于指示意义之上”。如果说电影内涵的所指是充满“象征的”“诗的气质”,那么按照梅茨的说法,能指要同时扮演指示意义的能指和所指的时候,上述电影内涵的所指才可能成立。举例来进行说明,比如小雷的双节棍,从影片一开始到片尾一直在他身边,挂在小雷的脖子上、他拿在手上练习、他拿着打老师、妈妈给他掰掉、在最后离开了他的身体被搁置在床上,这些都是指示意义的所指(物品),这样包含双节棍的叙述内容或者说含有双节棍的景观是指示意义的能指(利用道具双节棍进行情节安排);其最终目标则是内涵的能指:古典音乐响起,小雷背着书包推着爸爸的自行车走在家属大院的小路上,阳光洒在他的脸上,小雷从镜头前走过、越走越远,画面转换,静止镜头,双节棍放在了小雷的床上、枕头边。这些电影在美学上的运作,画面构图、摄影机运动、灯光效果、音乐音响效果等带有内涵的要素,置于指示意义之上,内涵的所指才可能成立:诗意地表达成长,小雷从外向内的转换,他不再通过外在的武力展示自己的男子气概,而是像父亲那样拥有强大的内心去适应社会的变化,成为社会的人而生活。
“昙花”在整部影片中具有象征意义。作为指示意义的符号学材料(内涵的能指):小雷的母亲把自己种的昙花从楼上搬到楼下细心地打理,固定好枝叶,从小雷手中拿过装着水的杯子,喝上一口又喷在昙花的叶子上,如此重复动作,小雷看着母亲的动作忍不住笑了。这里既有指示意义的所指又有能指。当这个场景依赖音乐音效的运用——小雷梦境中相似的背景音乐——的时候,内涵的能指,电影的效果就不只是“清理昙花”而已。同样,在夏末父亲离家的某个夜晚,母亲放在楼下的昙花开了,指示意义的所指昙花和指示意义的能指,关于昙花开了人们观看、拍照的景观,在一系列带有内涵的要素的运作下,镜头的运用、画外音的运用(朗诵诗歌)等,再从头到尾配合情节的需要的运作,可以看出内涵的所指的象征意味:美好的瞬间很快就过去了,时间如同河流般在作为主体的人的无意识中流走,想要抓住灿烂的一刻却又没有办法,时间的河流还在不停往前。
三、自传式影像:时间与回忆
曾经类似《关于青春成长的自传式影像》的论文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探求中国60后导演青春自传式影像的隐喻的建构。文中论述道,“中国电影‘后五代’导演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底90年代初的困境之后,现已初步浮出水面……对于他们早期的作品,虽然不断强调自己的个性,但是却显示出了极为相似的特点,这不仅是对‘第五代’导演创作的消解,更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一代人的艺术追求的显示与对现实生活的困惑、自我身份的定位”。但从近几年青年导演的创作中可以看出,这种影像创作的特征没有消失,一直延续到80后的导演。他们都是在创作社会变迁中探寻自我身份与自我意识的精神分析式的电影。《八月》的片尾打出了“献给我们的父辈”,类似的创作也包括80后女性导演贾玲的《你好,李焕英》,电影片尾中打出“谨以此片,献给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华莱士·马丁在讲到自传与精神分析中的叙事时说,“一个人从现在的视角来描写过去的经验对于个人的意义……自传是有关个人如何成长或自我如何演变的故事。回顾过去,作者发现一些事件具有当时不曾料到的后果,另一些事件则是在作者写作之际思考它们时才显示出意义……在某些情况下,自传作者并不打算描写一个他或她已经知道的自我,而是去探索另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尽管有所变化,却是从一开始就内在于作者自身,等待着一次自我发现,这一发现会在现在的我中把过去的一切汇聚起来”。从自身经验出发追溯过去特别是成长的经验,是当下中国导演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八月》的影像表达中,观者经常会跟着导演的摄影机的镜头“看”发生的事件,接着再是小雷作为一个旁观者观看,观者再跟着小雷的视角观察发生的一切。就好像是导演以现在的眼光去审视过去的自己,探索“另一个自我”。在媒体采访张大磊时他也有过类似的表达:“基本上这个孩子(小雷)的出现,或者孩子在凝视某一件事,并不是直接孩子的主观,而是先是我的主观,是我看着这些人的背影,而孩子出现在我的视野,是这样的感觉。我可以看到我自己,看到我参与的过去,把他呈现到画面上,目的就是这样。这部电影是以我的视角,孩子也是我的观察对象之一。”在这样的自传式影像中,过去的时光被重构,影片中小雷与父亲的形象都指向张大磊,其思考自我成长中转变的那一瞬:成为父亲或“我”就是父亲那样的人。因此导演张大磊也曾说过,他在电影中对父亲的描写不仅来自父亲,也有理想中自己的影子。
四、修辞建构:动态阐释与意义的产生
在后现代的语境中,电影修辞偏向于展现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电影文本更像是罗兰·巴特笔下的“复数的文本”,取消一切中心和统一,蕴含着多元异质的、不断“异延”的意义。电影《八月》中观者对时间的感知是一个动态阐释的过程,观者的观看读解是一个理解和解释的认知心理的、社会的活动,包含着从文本暗示生发出来的意义建构。这种建构又因导演“话语表述”手段的灵活多变以呈现修辞化的现实而成为一个让观者不断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于是,在这个由导演张大磊创造的充满动态符号的感知和解释的景观中,人们体验到情感的诗意流动,唤醒了人对自我存在的思考、对精神深处之意义的重新注目。
《八月》中多次出现“父亲看电视”的镜头和场景,例如影片一开始,一家三口围坐在电视机前吃饭,小雷的父亲和母亲一边评论着电视剧中的人物,一边夹菜吃饭;晚上,父亲守着电视边看边洗脚,母亲喊了“快关了吧”,他充耳不闻继续看,并拿起笔记本记录。这样的镜头和场景还包括:小雷父亲喝醉酒回家和小雷母亲起了争执,随后,镜头里是父亲拿着电视机遥控器睡着了,电视开着,不断传来声音,母亲想要拿走,父亲惊醒后说:“我看着呢。” 第四次“父亲看电视”是在厂子的剪辑机房里,父亲对着剪辑机工作,外面传来改制倡议的广播。第五次,小雷打了老师,回家后父亲看着电视,不痛不痒地表示“打了就打了”,惹火了母亲。第六次,父亲守着一摞录像带放进电视里看,而后又扯了带子。这样“重复”父亲看电视的场景和镜头,不是对事件时间性的意指,而是对一种特殊的“中心意象”的突出和强调,消解了“父亲看电视”这么一个平常的意义,强化人作为生活中的存在所面临的困境与艰难的反抗,这种反抗在个体的人的生命时间中都有可能会出现。导演张大磊通过修辞的特定手段制造有这样“特殊含义”的话语策略,是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强调;从接受角度看,观者通过电影表述和自我接受的动态过程,也将建构自己对于“时光”“困境”或者“往事”的理解。
需要提及的是,由于观者的动态阐释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导演电影修辞运用之上的,李显杰认为,“从接受角度看,电影文本其实并不能提供最终的意义,而是随着观众的不断阐释而不断产生新的意义,而观众的读解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继发性的修辞建构,他们结合着自己的生活阅历、文化水准、观影经验和审美好恶,建构着自己所理解、所偏爱的电影文本”。因此,这样的差异性使得每个人对于《八月》中时间、成长、记忆的体验都有可能是不同的,阐释和意义也由此保持一定的个体特征。
时间可以是具体物化的时间,也可以表征客体的人在成长中的无意识与欲念。因此,电影创作中的时间可以超越“质的时间”而成为一种修辞。中国青年导演在拍摄自传式风格电影的过程中对于时间的运用具有一种诗意的美学,影片在美学上运作的一系列带有内涵的要素让观者在影片虚与实的光影体验中,捕捉到有关时间与记忆的本质。虽然能从《八月》中感受到导演张大磊向伯格曼、侯孝贤、杨德昌等电影人在电影语言运用上的学习,但张大磊通过电影艺术呈现的有关时间、记忆、观看和思考是独一无二的,有自己美学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