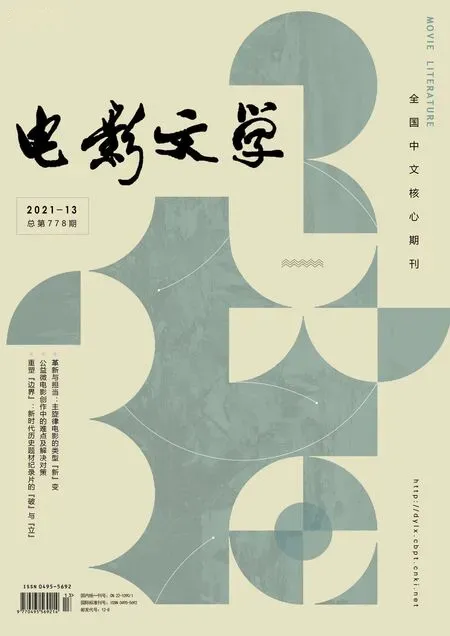虚拟情境与切真能指:《隐形人》的异化主题
田丽丽(唐山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0)
在《电影是什么》中,电影批评家安德烈·巴赞曾指出,电影在形式上富于革新和颠覆,“我们不能否认电影中的技术处理,但如若缺少了对内涵的传递和对人文的关怀,电影或许就失去了最初存在的意义”。单纯以技术构建出引人入胜的景观并非是电影艺术的终点,电影的价值在于,其在建立一个虚拟、夸张的情境时,有着切真处实的,关乎观众现实生活的内涵能指。对惊悚电影而言亦是如此。以雷·沃纳尔执导的《隐形人》为例,电影虚构了女主人公塞西莉亚惊悚怪诞,看似孤立的遭遇,而就叙事的外延来说,电影讨论的实际上是当代人尤其是女性遭受异化了的生存体验和精神状态。
一、技术理性与科技异化
电影《隐形人》改编自英国小说家赫伯特·威尔斯发表于1897年的长篇科幻小说。在原著中,利欲熏心的科学家格里芬发明了隐身药水后,以此来制造各种恐怖事件,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电影完全更改了原著的情节以及具体的隐身科幻设定,但是继承了原著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态度,隐形技术的发明者都是被科技异化了的作恶者。
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诞生的理性主义,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诸领域中,并与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相结合,在有着让人们摆脱蒙昧迷信的进步历史意义的同时,又逐渐暴露出其“副作用”。正如霍克海姆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的那样,在技术理性统治社会后,技术本身并没有如18世纪时启蒙者所期待的那样,是解放人,让人走向自由之物,反之,技术成了束缚人的自由,扼杀人的个性的禁锢力量。类似如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威尔斯的《隐形人》等文学作品,都饱含了对这种科技异化的忧思,当代惊悚电影中如《生化危机》等,也正是以这种异化来为观众制造恐惧心理,并影响着观众的价值判断。
在《隐形人》中,阿德里安·格里芬年少有为,被称为光学领域开拓者,在三十余岁时便已是科伯特光学公司的创始人。他在光学领域的突破主要在于他以折射投影以及光线追踪为基础,重新校准了多摄像机系统。从阿德里安“自杀”引起的轰动,以及他与女友塞西莉亚同居时海边的豪宅等不难看出,他的科研成就也让他名利双收。而当这一多摄像机系统被他用于隐形衣的制造,并且穿上隐形衣作恶时,阿德里安也就成了一个被自己创造的对象异化、扭曲的“非人”。随着情节的发展,隐形衣的精密之处越发显现,如不仅能从人们的肉眼视线中消失,还能保障穿者行动时的舒适、灵便和消音,甚至还能迅速洗掉液体等,这让阿德里安在与塞西莉亚、詹姆斯等人的斗智斗勇中占尽上风,而他利用隐形衣所作的恶也越发严重:从一开始的私闯民宅,骚扰塞西莉亚,盗窃她的作品,到最后与哥哥汤姆一而再再而三地杀人袭警,有恃无恐。
对于这种技术滥用,电影无疑是持否定态度的。最后,塞西莉亚穿上了隐形衣,在摄像头下抓着阿德里安持刀的手杀死了阿德里安。隐形衣包括遍布豪宅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原本是阿德里安创造、使用的“客体”,但它们此时完全与阿德里安对立。相对于小说中,格里芬被村民们打死的结局,电影的这一设定是更有深意的:正是阿德里安苦心孤诣实现的科技力量,如隐形衣能被迅速根据使用者的身形完成3D打造且柔软便携等,为塞西莉亚的复仇提供了便利,促成了他的死亡。
在电影中,阿德里安发明了隐形衣是一个虚拟情境,就目前的光学与材料技术而言,人们还无法实现如此神奇的“隐形”。但其背后的理性批判却显然是植根于现实的。如塞西莉亚在出逃之后,曾在浏览网页时看到了“有人正在监视你吗——揭秘如何通过摄像头窥探隐私”的内容,随即惊慌地想合上笔记本电脑,在镇定后她马上用指甲油将电脑的前置摄像头涂上。摄像头麦克风,智能家电以及互联网为不法分子利用,获取他人隐私的事在现实中早已屡见不鲜。在塞西莉亚被窥探的威胁所笼罩时,银幕之前的观众也足以产生警惕与深省。
二、视觉逻辑与身体异化
自柏拉图始,眼睛在感官中的霸权地位就已产生。柏拉图认为,人类唯一能洞彻理念的感觉是视觉,而其余感觉只会让人堕落放纵。尽管视觉在感知世界,获取信息上相较于其余官能感觉更为高效,但柏拉图这种拒斥其余感觉的观念显然是偏颇的。及至当代,视觉中心主义更是大行其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更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为视觉逻辑统治。“视觉跃居其他感官之上,所有源自于味觉、嗅觉、触觉,甚至听觉的感受,都丧失清晰性,然后消失……所有的社会生活成为眼睛待解的信息、待读的文本”。如包括电影在内的图像艺术成为人们热衷消费的对象,便是视觉逻辑主导当代社会实践的范例,最终,列斐伏尔认为视觉“摧毁”了人的身体。
而《隐形人》恰好从侧面佐证了列斐伏尔的理论。从阿德里安的角度来说,他的身体正是出于躲避视觉的需要而被自己异化,或曰被“摧毁”了。马克思否定了西方传统哲学认为人是精神性存在的观点,肯定人对象性的身体的存在,并且,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身体理应是具有社会性的。然而,阿德里安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伪造了自己的自杀,制造了与之相关的视觉信息和文本,如登有其死讯的新闻网页,留给律师哥哥汤姆的关于财产分配的遗书等,试图以此来让塞西莉亚放松警惕。但这实质上导致了,在阿德里安继续严格控制塞西莉亚之前,他已经控制了自己,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死人”,以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不再是社会存在物的沉重代价,换取肉体的消失。从塞西莉亚之后的查访不难发现,阿德里安离开了自己的海边豪宅,躲藏在詹姆斯家的阁楼上,他完全放弃了自己之前的正常生活。隐形并没能让他走向自由,而是让他走向处处受限。尽管阿德里安为自己安排了“死而复生”的后路,但这依然是以身体为代价的(阿德里安肉身被自虐与囚禁,汤姆肉身消亡)。
而从旁人的角度来看,人们的生活充斥着大量“眼睛待解的信息、待读的文本”,这也就导致了人们对视觉的盲信以及对其余感觉的麻木。除了塞西莉亚努力以其他感官来证实阿德里安的存在外,其余人都过于依赖视觉而被隐形衣所欺骗。如西德妮与父亲詹姆斯都一口咬定击打西德妮的人就是眼前的塞西莉亚,又如艾米莉相信自己收到的言辞刻薄的邮件来自塞西莉亚。而将塞西莉亚逼到绝境的则是,阿德里安在玉兰餐厅中割断艾米莉颈部动脉,随即将凶器放入塞西莉亚手中。视觉侵占了人们几乎所有的注意力,没有任何人能以嗅觉、听觉、触觉等发现到周围的异常。乃至最后在精神病院中隐形人的现身,其实都是阿德里安再次倚仗人们的视觉完成的一个骗局。
有意味的是,列斐伏尔提出,建筑是身体抵抗这种“摧毁”的方式,因为建筑并非只能凭借“看”来理解的,并且在建筑中,人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脚步,聆听到噪声和歌唱;呼吸着紧张的气息,跃入一个罪恶和救赎的世界;他们分享着思想,思考和译解着环绕他们的象征符号。他们以自己的整体身体,在整体空间中体验中体验着整体的存在”。而《隐形人》中塞西莉亚正是一名女建筑师,毕业于全美排名第一的加州理工大学建筑专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她始终思维敏锐,没有让视觉替代、置换其他感觉的原因之一。
诚然,在《隐形人》虚构的情境中,人物的所作所为是极端的,甚至与观众的生活经验有一定的割裂之处,但是在现实日常中,人们沉迷景观,迷信观看,为视觉所控制,将生活化为具有压迫性的视觉空间,从而丧失了身体的整体性,这却是不争的事实。类似地,如《消失的爱人》《看不见的客人》等惊悚电影,也有着同样的意指,在此不赘。
三、男权社会与女性异化
在《隐形人》中,最为触目惊心的异化非男性对女性的异化莫属。所谓女性异化,即在男性对女性的长期压迫与控制中,女性作为弱者几乎完全丧失能动性,在对方的物质与精神双重奴役下,成为“他者”,只能得到片面而畸形的发展,如变为男性价值体系下的“贤妻良母”或“魔女妖妇”等,而正常的诉求则被剥夺。在当下,这种性别二元对立秩序并未被完全推翻。为更好地阐发这一主题,沃纳尔多次探访了女性保护组织,研究了大量案例,从而完成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剧本。
在女性已经得到较大解放的当代,女性依然没有能全面从“他者”的困境中被解放出来。在电影中,塞西莉亚尽管在自己的建筑专业上十分优秀,但在与阿德里安成为恋人后,便不断为对方所控制。有着变态控制欲的阿德里安控制塞西莉亚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直至发展到控制她的言论和思想,对她施加性侵、监禁、殴打,以及精神羞辱等伤害,断绝塞西莉亚与亲朋联系和外出工作的可能,试图在她身上延续自己在哥哥汤姆家养的狗宙斯面前的权力中心地位。而作为一名拥有自主性别意识的当代女性,塞西莉亚选择了避孕与逃跑,但男性通过自己在现代技术、社会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继续对其进行迫害。
在塞西莉亚之外,强势、自信,对塞西莉亚伸出援手的艾米莉与西德妮代表了一种能帮助女性避免被异化的女性进步力量,警察詹姆斯则是背离男性霸权,理解女性绝望情绪的男性进步力量。这种力量自然不为男权所容,于是三个人都遭到了阿德里安的欺骗与攻击。
在男女主人公的尖锐对抗中,观众不难意识到,“隐形人”这一高概念能指,其含义正是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主要由女性承受的家庭暴力,亲密关系犯罪,以及女权主义批评家劳拉·穆尔维在《视觉愉悦与叙事电影》中提到的“观淫”,而支撑这一切的正是男权。当男性在家庭生活中对女性进行身体与精神摧残时,往往能够因为女性举证困难而逃脱惩罚;当女性忍受暴力后试图对亲朋诉说时,亲朋也难以提供信任与帮助,劝告受害者息事宁人。而在“观淫”中,女性是男性的观看与欲望投射对象,《眩晕》《沉默的羔羊》等惊悚电影都对此有所揭示。阿德里安肆无忌惮地窥视洗澡、睡觉的塞西莉亚,与男观众对经典好莱坞影片中的女性进行赏玩一样同属“观淫”。长此以往,男性以或合法(“观淫”),或非法(暴力犯罪)的方式,对女性造成无处不在的阴影,即使其不在场,女性依然备感不适,这便是现实社会中,有悖于性别平等旨趣的“隐形人”。当观众明晰“隐形人”的所指之后,电影虚构的情境便与现实生活体验一一印证,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积累日久的恐惧感受便被充分地调动与激发起来。
单纯讨论惊悚电影所设定的夸张符号或与现实存在一定距离的情境,而不关注到它们作为能指指涉的现实社会,并不足以使我们收获完整的审美体验。在《隐形人》中,隐形衣、隐形人的相关概念,是当代人精神危机,感官麻木与道德沦丧的能指。在电影虚拟的情境中,异化早已深入到科技、身体以及女性身份诸多方面,种种矛盾无不对应着现实症结,启迪着观众进行有益的延展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