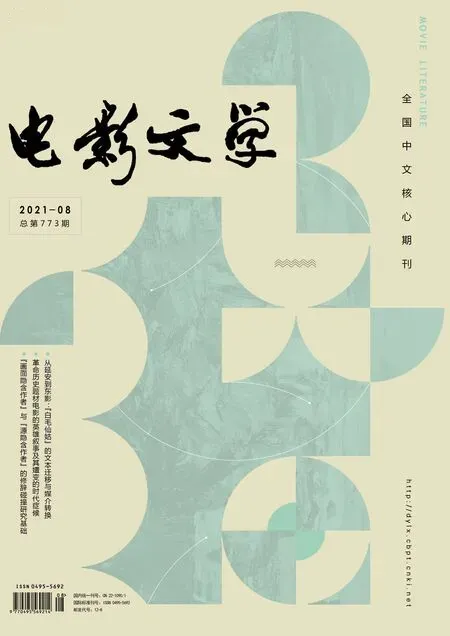理念、逻辑自洽与民族症候表达
——《误杀瞒天记》《误杀》比较研究
沈嘉达 沈思涵
(1.《黄冈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湖北 黄冈 438000;2.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电影翻拍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所选择的翻拍对象,作为优质的IP资源,可以给观众提供先验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翻拍”往往是超国界的艺术行为,这就决定,“翻拍”呈现的必然是不同族别、不同文化的社会表征。
《误杀》源自印度的《误杀瞒天记》。作为两个“成功”的文本已经具备比较的可能。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柯汶利执导的电影《误杀》累计票房突破12亿之后,已经于2020年7月20日在内地影院重映,再次成为我们的观照对象。
一、叙事理念有别源自不同的文化认知
《误杀瞒天记》(以下简称《瞒天》)原名《视觉》。影片中,当地警察局长梅拉和主人公维杰多次“解读”片名的显在含义:人们往往相信的是自己“眼之所见”,并将此看作是真正的“事实”。电影要凸显的正是某种“反讽”效果——维杰通过制造“事实”改变人们的视觉印象,从而“瞒天过海”。中文版《误杀》,英文名为Sheep
Without
a
Shepherd
,直译为“没有牧羊人的羊”,意译为“乌合之众”。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表层含义是主人公李维杰及普通民众,乃温顺而待宰割的绵羊,这一点可以从影片中多次出现绵羊镜头得到印证;深层意蕴是看似“乌合之众”的人们只要团结起来,就可以达成某种目的,形成社会力量。电影作为一门大众艺术,“讲好故事”是“应然之事”。“故事”的核心是人物,有人物就会产生冲突。我们注意到,《瞒天》与《误杀》虽然都是在讲男主人公为了保护家庭不惜利用智慧企图逃脱杀人罪责的故事,但是,立足点却迥然不同。《瞒天》中,回到家里,面对已经造成妻女“误杀”警察局长儿子萨姆的现实,男主人公维杰的本能反应是“我不认为我们做错了什么”,因而“我们要抗争到底”;他还进一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认为:如果是警察局长本人,也会为了儿女这样做。正是出于这样的理念,维杰利用所学到的电影知识,成功地偷梁换柱,涉险过关。在《瞒天》的结尾,当萨姆的父亲马赫什忏悔因为“溺爱儿子”而害了儿子之时,维杰虽然承认了是自己“将不速之客送上不归之路”的事实,却依然强调这是因为警察局长的儿子萨姆“想摧毁我们的整个世界”。在维杰看来,“我的家人是我最重视的,我会为他们在所不辞,用尽手段。在当下,(本人)看不清(这种行为)是对是错”。注意:即便是维杰已经承认误杀了萨姆,但也不确定这种行为是“错误的”——至少在维杰看来,看不出错在哪里。基于这样的认知,主人公维杰并没有选择自首从而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
何以维杰(也是《瞒天》的导演)会产生这样的“于理不合”“于法不容”的理念呢?显然,这与印度的法治现实攸关:只要梅拉、盖顿德这样的“坏警察”还存在,维杰们就只能“自救”,也就是利用智慧与作为强力部门的警察相抗衡。事实证明,自我救赎比幻想警察公正执法要现实得多。
内地版的《误杀》则全然不同。尽管依然讲述的是作为父亲的李维杰保护家庭不受伤害的故事,尽管影片“巧妙地”将背景设在泰国罗统地区,尽管沿用《瞒天》某些设置譬如桑坤被设置成“坏警察”(类似盖顿德),但我们发现许多电影“元素”已经悄悄位移:作为罗统警察局长的拉韫一出场并不具有“野蛮”色彩,相反却充满智慧:她轻而易举地破解了久拖不决的离奇杀人案件;她虽然也是“女强人”形象,也曾对李维杰的妻子阿玉进行过“威胁”,但母性色彩更浓更真实。特别是在影片结尾,对主人公李维杰进行忏悔的,并不是其丈夫而是拉韫局长本人。总起来看,拉韫的理性、智慧等,显然迥异于《瞒天》中梅拉的强悍、任性。更具有分水岭意味的是,李维杰一家能够暂时逃脱生天,不仅是因为男主人公巧设计谋,更在于警察局长的丈夫身份的转变——在《瞒天》中,梅拉的丈夫马赫什只是一介“生意人”;而在《误杀》中,都彭则被设置成了“市长候选人”。正是李维杰利用了其政治竞选对手达利,争取到了舆论宣传和鼓动,才迫使拉韫局长放弃了进一步的追寻。尤其具有现实意义的是,《误杀》中的李维杰选择自首,从而传达出“法治最终战胜亲情”的社会理念。在《误杀》中,“对”与“错”十分明了,“罪”与“罚”不容有误,“家庭亲情”与“社会正义”终于尘埃落定。
有记者问到《误杀》的结尾设置问题,导演柯汶利回答道:“其实不是(电影管理部门)审查的原因,我们整个团队都希望结局的走向是积极的,让人有个希望。”在接受另一个记者采访时,柯汶利说道:“我们希望电影发酵了,发现我们不只是悬疑惊悚片,里面讲的并不只是推理,讲的是一个很深沉的教育问题、社会问题。”显然,柯汶利导演有着清醒的社会认知,自觉承担起了电影的社会教化功能。在他看来,只有社会倡导公平正义,只有每位公民对法律充满敬畏并自觉遵守,这个社会才可能长治久安。而这,正是《误杀》和《瞒天》的根本区别所在。
二、逻辑自洽是“推理”电影的现实基垫
查阅资料发现,《瞒天》的故事设定灵感与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的作品《嫌疑人X的献身》攸关。《嫌疑人X的献身》所使用的“本格推理”,“强调的就是推理的逻辑性、公平性”。笔者以为,《瞒天》对《嫌疑人X的献身》的借鉴,就体现在推理的前置(“案底”一开始就认定)和逻辑的严密上。笔者想说明:一部成功的具有悬疑色彩的电影,其逻辑性——推理的逻辑性是多么重要!这不仅是揭开电影谜团的关键,同时也是吸引观众的不二法宝。
就一般意义上说,电影翻拍会将故事“横移”到翻拍国度里。显然,《误杀》不适宜将故事安置在当下的中国。导演无奈而“聪明地”将故事安放到泰国;为了迎合中国观众,故事中的主人公就只能是生存在泰国的华侨。
这就是《误杀》故事的逻辑起点。然而,在中国观众看来,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对本土公平正义诉求的有意无视,另一方面可能存在对他国制度、他国现实的前置想象。正是在这个维度上,专业影评人才会质疑导演和编剧的现实批判能力和专业态度。“《误杀》的唯一可取之处便是电影适度缩减了原片篇幅,使整个剧情在节奏上相比前作变得更为紧凑”。“《误杀》最为荒诞的所在,便是改编之后使《误杀瞒天记》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一个根据印度电影改编,中国人主演发生在泰国的家庭罪案,本来就尤为突兀。在呈现上时而中文,时而泰文,时而又英文的混乱,其实没有为电影带来丁点的国际格局,只是使电影失去了真实的奠基,胡编乱造的背景架空,对于一部原本影射社会现实问题,以家庭亲情为纽带的悬疑电影来说,荒谬至极”。
《误杀》与《瞒天》的对比,确实“印证”了“专业影评人”的批评。《瞒天》2小时40分钟的长度让电影略显臃肿,《误杀》则简化了许多,将故事长度控制在120分钟以内。然而,磨刀不误砍柴工,《瞒天》中的逻辑性(也就是维杰应对警察的每一步行动)都建立在从前到后的异常缜密的“伏笔”上。譬如,维杰之所以将萨姆的汽车推入废弃的工地水塘,是因为小舅子“无意”告知,而《误杀》就缺少这样的“暗笔”。人们不禁要问,李维杰怎么就知道有这样的大湖?他如何知晓湖水有多深?能淹没那辆汽车吗?再如,《瞒天》中,维杰之所以能成功误导警察,赢得应对时间,是因为他购买一部二手手机,并要求电源充足,消除铃声,擦除指纹,让长途货车带走后,成功将警方视线转移到他处。而《误杀》则直接让李维杰抛弃手机,显得不够精密。当然,《误杀》强化了李维杰“自学成才”的可能性,反复强调只要看了一千部侦破电影,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离奇的事。《误杀》甚至不惜开列《七宗罪》《肖申克的救赎》等多部影片,以此“证明”李维杰学有心得。这种过犹不及的强化,其实远不如《瞒天》中维杰守在公司观看悬疑电影而疏于回家引来妻子埋怨来得自然可信。所有这一切,就是想说明,《瞒天》表面看似“臃肿”,却重在“于无声处”做文章;《误杀》直奔主题,有逻辑疏漏和“理念先行”之嫌。
特别为人诟病的是,《误杀》“揭开”谜底也就是开棺之时,观众发现棺材板内侧上有明显的手抓血痕,结合影片中李维杰一家人吃饭时小女儿在桌上用叉子画下一道道印子,我们推测,受到李维杰大女儿锄头重击的素察只是昏迷并没有立即死亡(而《瞒天》中萨姆由维杰的妻子明确判定“没气了”),换言之,李维杰是将警察局长的儿子素察“活埋”的!这固然可以加重李维杰维护家庭不顾一切的决心,但也严重偏离了故事中“误杀”他人的原意,会让李维杰的行为变得格外残忍和血腥!而警察开棺验尸,明显看到棺材盖内侧有血手印抓痕,如何不进一步追问?怎么会视而不见?至于李维杰将桑坤开枪打死的山羊置于棺内,其实也完全经不起推敲。警察肯定感到奇怪,为何宋姓中国人的棺材内放的是一只山羊?这岂不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而《瞒天》则不然,维杰妻女只是将萨姆埋于树下,即便维杰置换成狗尸也可以“制造肥料”而敷衍之。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毋庸置疑,就故事的自洽性上说,《瞒天》胜过《误杀》多矣。
三、民族症候表达是建构民族电影的必由之路
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同其他门类的艺术一样,需要“特色”。换言之,具有民族特色的电影,更容易走向世界。相应地,一部电影如果缺失了独特的民族内蕴,必然不能行稳致远。
这里所说的“民族的”,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民族化的符号”,譬如稀有的风俗人情、独特的地理地貌等。“民族”的深层意蕴,指的是一个民族经历风雨已经形成的独特的民族精神、民族伦理、民族思维等。
从这个维度上说,《瞒天》并不是“符号化”的印度宝莱坞影片。我们很难从《瞒天》中获得印度电影“与生俱来”的民族歌舞、乐天风格之类的“他者”印象。那为什么我们又认可《瞒天》是一部印度电影呢?
就笔者看来,之所以认可《瞒天》是印度的,是因为《瞒天》如此深刻地反映了印度的当下社会现实(印度社会矛盾尖锐、法治紊乱等)。甚至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瞒天》所采用的维杰式的“自救”行为,体现的也是印度基层民众的社会想象。否则,我们如何能够理解,这样一部与现代法治伦理相悖的电影怎么能够在印度大获成功?它又是如何通过印度电影管理部门的行政审查和行业管理?笔者的意思是,《瞒天》的“印度性”不是体现在对印度的表象描述上,其深刻之处正在于对当下印度社会现实的内在把握。
就翻拍片《误杀》而言,显然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尽管《误杀》将《瞒天》中的布道会改成泰拳比赛,将印度符号化解为泰国风光,却面临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李维杰一家是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于泰国,还是作为移民华侨而呈现的个例?就其身份来讲,正如电影所言,李维杰一家是从暹罗移民过来,做过很多基层工作,然而,电影却没有突出李维杰的“华侨”身份以及由此而承担种种灾厄的必然性。我们尽管可以讲,《误杀》中的桑坤欺压的是所有底层百姓(诸如颂叔等人),李维杰一家所代表的是泰国的底层民众,但是我们依然要问,李维杰能代表泰国民众吗?如果能“代表”,其代表性又体现在何处?
我们还可以说开一点,来探讨一下翻拍电影由于未能准确把握民族症候而导致“失败”的案例。譬如,内地《大人物》翻拍了韩国电影《老手》。不客气地讲,《大人物》几乎完全复制了《老手》的故事,框架一样,甚至里面的次要人物形象都一致——《老手》中的崔泰勇是个龅牙,《大人物》中的崔京民也是个龅牙;《大人物》中警察孙大圣的表演也学着《老手》,油腔滑调,手舞足蹈。更可笑的是,《老手》中警察局长可以暗示徐道哲去查财阀集团,可以相互比着伤疤,可是这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怎么可能想象,中国的基层警察竟然可以跟局长比着自揭伤疤以此来推进故事情节?这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叙写吗?
众所周知,韩国电影走红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韩国电影善于抓住热点、敏感题材,敢于介入政治,批评政治人物。这是由韩国现实所决定的——“韩国财阀制度导致市场被这些庞然大物所笼罩,而且财阀得到了国家的支持”,“韩国财阀制度作为威权时代和儒家思想的产物,一直影响着韩国乃至亚洲”。即便“文在寅当上总统后,大力破除财阀制度,但是,因为财阀制度在韩国根深蒂固,要破除财阀制度绝非易事。一方面,文在寅倡导破除财阀制度;另一方面,文在寅又不知不觉陷入了财阀制度中”。《老手》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切中了韩国政治时弊,即财阀经济和政商勾结。就民众而言,十分痛恨财阀集团;而就电影而言,这成为反映民众呼声的“热点”。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老手》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国别意义。反观内地电影《大人物》,避开了政治问题这个“硬核”,而去设立房地产公司为对立面,这就注定了《大人物》的翻拍是吃力不讨好的行为。导演所能做的,就只能是风格上的依样画葫芦般的模仿了。
笔者再次强调,民族性是建立在社会性之上的。没有对社会现实的切身理解,就不可能准确表达民族症候。《大人物》对《老手》翻拍失败,反过来看,韩国人河正宇拍摄中国作家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同样难言成功(我们姑且也将这种跨国别拍摄看作是“翻拍”的一种)。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情节”其实非常简单,作者余华反复强调的许三观的卖血“惯性”,深刻映射出了历经磨难的中国人的灾难命运和民族韧性。然而,韩国电影《许三观》过于注重情感属性,反复渲染卖血以救助儿子许一乐,实在是避重就轻、买椟还珠。余华小说写到许三观儿子生病是在1959年前后,也就是中国20世纪五十年代末“大跃进”后,小孩患上肝炎是因为营养不良,中国观众能够感同身受,产生历史认同。然而,河正宇的《许三观》却将许一乐生病设置在1964年。韩国1964年发生了什么呢?中国观众实在没有什么印象,难以产生民族和历史认同。这就很容易理解,即便有河正宇、河智苑等明星主演,该片在中国必定要遭遇滑铁卢。我们怎么能够想象,没有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切身之痛的韩国人,他们能够深刻理解许三观的“卖血”惯性!
正如本文一开始所言,“翻拍”是把双刃剑。即便中日韩同属汉文化圈,也鲜有成功之作。更何况,作为非同宗非同源的印度文化电影艺术作品,翻拍之就更需要慎之又慎。《误杀》的票房成功,从内在机理上说,不能算是艺术的成功,最多只能算作面上的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