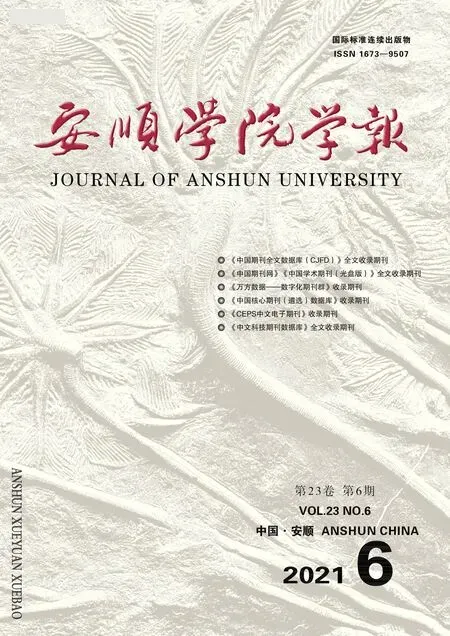以“驿”为媒:论明清时期驿道对贵州社会发展的影响
翁泽仁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在历史上,贵州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区位进入历代中央王朝的关注视野,即扮演的是通道角色,承担的是连接与中转的作用。尤其自元代起,进出云南的主要通道由湖广经贵州至云南以后,贵州的地理位置就更加突显。元代通过贵州有五条主要的驿道:湖广通滇道、滇南至广西道、川黔道、亦溪不薛道、乌撒入蜀入滇道。毋庸置疑,贵州在此成为连接湖广与川滇、边疆与内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及咽喉之地。其作用诚如明贵州布政司参政周瑛提及的:“吾藩财赋、人民视中州诸藩不及三之一,然而倚角形执,控制苗僚,以通西南朝贡道路,其地至要也。”由于地貌与气候等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黔地多顽山,黔天多瘴雨”,人烟稀少,长期是土司掌控的少数民族居住区。自然条件使得贵州成为封闭、边缘的政治区域,作为通道的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对于作为中央王朝经营云南、统一西南边疆道路上的重要中继站,拥有战略地位与作用的贵州,明太祖朱元璋有着极为清晰的整体性认识与谋略。“贵州四面皆夷,中路一线,实滇南出入门户也。黔之设,专为滇设,无黔则无滇矣。”因而,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就诏谕水西、乌撒、东川、芒部诸酋长修筑道路。后来逐渐形成了以贵阳为中心的驿道网络:以东的湘黔道、以西的滇黔道、以西北的龙场九驿、以北的川黔道及以南的黔桂道。也即是“黔省诸驿乃滇省所必由”。明太祖就此开创了在贵州大兴驿道的新纪元,极大地发挥了贵州的交通优势。洪武年间,贵州共设置驿34处,递运所、站、堡总计35处。诚如他在对兵部谕告中谈及的:“驿传所以传命而达四方之政,故虽殊方绝域不可无也。”毋庸置疑,明太祖对于驿道所拥有的政治、军事及社会意义了然于心。在他看来,驿道作为皇权、王权及军权的象征,在体现王朝统治意愿的同时,应该成为连接中央与地方、官兵与百姓、汉族与世居民族不可或缺的手段。驿道所在之处,也即是王朝势力所达之处。其目的显而易见,即加强权力中心对贵州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约束力与管控力,使之处于中央的有效统治范围之内。使得上情的下达、中央的集中与统一管理能够顺利地通达与实施,而不被地理环境阻隔、干扰。“置驿奠邮,榰桥架栈,划险为平,通夷达华,航鲸波而梯鸟道”、“朱旗邮兵走相报,绣衣使者来行边”,无一不在说明王朝势力的强大性、权威性及神圣性,以及其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能够得以真正地推广与执行,而无地域与民族之分。
清代在延续明代交通治理方略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与创新。“驿道干线不改,但在川黔驿道上‘裁驿设铺’,从四川边境至贵州省会贵阳设有26铺”,目的在于“以速军机,以苏驿困事”、“以速驿递,以便商民”、“庶道里均平,驿递商民均属便益”。清代修通了由省城至府州及由府州至州县的各条大道,全长7000余里,为驿道干线的3倍,共有大道36条、站铺500余处。这些线路长、数目多的大道与铺递、水驿与码头,把贵州连成一个点、线、面紧密结合与环环相扣的巨大交通网络,清晰地展现出清王朝加大与加快、加深和加紧对贵州全方位的统治之意。显而易见,这种有序、机构化的交通布局成为一种强大的融合及整合力量,不仅粉碎了崇山峻岭、险峡沟壑对贵州的政治与文化隔绝,而且塑造了贵州边民新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及认知系统。驿道的一体化作用无疑试图消除区域及民族间的鸿沟、弱化及淡化贵州与外界的界限、提升被边缘化的苗疆文化,以促成大规模、块状、统一文明的形成。驿道对内统一及约束、集中与凝聚作用,不仅将贵州内部、贵州与外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为重要的是,激发和唤起、加强和加固了贵州世居民族对中央王朝及中原文化的认同感与趋同感。毋庸置疑,在此,驿道更加发挥了作为政治认同符号和标志的作用。
一、促成城镇的出现
明初,朱元璋自平定云南后,即在湘黔至云南的“一线路”驿道上设立卫所,派重兵把守。如,洪武年间设置的普定、安庄、平坝、威清四卫及关岭守御千户所。卫所最初的功能是保障驿道的顺畅、通达。“开道路。则团聚哨兵”。在此之后,逐渐增修驿道及增设卫所系统。最终形成以驿站为点、驿道为中心线,沿途分布着大量卫、所、屯、堡的军事防御体系。如万历《贵州通志》记载:普定卫的兵防区域,东到杨家关哨;南有归华营,驻百户一员;西南到龙井铺;西北为十二营长官司。平坝卫“自南门官道,十里至沙作铺;十二里至寒坡哨,十五里至蛙山哨”。
“至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在今贵州境先后设有24个卫和26所”。卫所制度的建立无疑促成汉族军民的大量移入。“仅以屯军设置定额及万历民户统计,明末贵州汉族人口总量当为177800户,962972人。”数量庞大的官兵、军民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贵州这片边疆地区的生活气息。他们几乎围绕着交通沿线驻军、生产生活,很快把其开发为生机盎然的生活区域。作为交通站点的驿站与卫所交相辉映、互为补充。便利的交通及密集的人口,不仅使卫、所、屯、堡成为军事据点,也为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许多以驿站为中心的卫所与治所逐渐发展为城镇。如,洪武十四年(1381年)建成的普定卫城(今安顺城)。洪武十六年(1383年)因毕节驿改建的毕节卫。建于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原属龙里千户所城的隆里古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设置的桐梓县,即为以驿名为县名。该类型的城镇建设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益军益民,使得敌军不敢轻易深入。诚如明闪继迪在《创建十一城碑记》中谈及的:“诸城建则宿兵其中,出可攻,入可守,行李往来,收保足恃”。郭子章在其疏略中也提及了此意:“渐议筑城垣。首砌龙泉,次砌瓮安,又次砌余庆、湄潭,又次砌平越、水城、黄平州城、铜仁县城,又次修铜仁、平越府城、新添、龙里卫城,又次筑平越行府、铜仁营堡,而城垣举矣。即不敢谓金汤足恃,而五板安堵,千里联络,实空虚之地为扞蔽之资。脱有不虞,民亦可倚而守也”。成化年间,镇远知府周瑛的奏章同样持有相似的观点:“本府既立……一以递送,一以防守……修筑城堡,非惟居民之利,亦官军之利也。盖城隍立则居民自固,敌人不敢深入,军免于赴敌,而官亦得以自保,其利甚博”。
这种以军事为目的、开疆扩土及削弱土司的官方行为,在悄然间促成了贵州的城镇化发展。使得有明一代成为贵州城镇开发及城镇化建设最为重要的时期。“万历时期贵州全省共有43座城,除省会贵阳系在元代顺元土城的基础上扩建外, 其余各城皆为明代新建之城”。其中,“明代贵州处于交通线及卫所所在地的集镇有24个,占当时贵州集镇总数的68.6%”。
“清代贵州的城市化进程也基本保持了明朝时期的态势格局,即城市多是在卫所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城镇……清朝贵州共有75个区镇治所,其中38个治城所辖之地附近曾设有卫所。”乾隆九年(1744年),贵州按察使宋厚的奏章中就谈及了“黔省各处城垣,建自明季”的问题。“清代处于交通线及卫所所在地的集镇共有42个,占当时贵州集镇总数的52.7%”。显而易见,明清两代围绕驿道和卫所所在地建成的城镇(集镇)分别占据两个朝代集镇总数的一半以上,而明更胜一筹。
有清一代,加大、加强了对水驿的开发和利用力度。对于在贵州疏通河道的重要性诸多大臣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张广泗在奏章中对疏通赤水河的感悟甚深:“黔省威宁、大定等府,州、县崇山峻岭,不通舟楫,所产铜、铅,陆运维艰……查有大定府毕节先属之赤水河……若将此河开凿通舟,即可顺流直达四川、重庆水次……若开修赤水河,盐船亦可通行,盐价立见平减……川米可以运济,实为黔省无穷之后利”。
随着对赤水河、乌江及清水江等河流的进一步疏治与开通,许多水驿站点开始复苏或出现。它们大多因运送盐与粮食、木材及土特产品等经济原因发展为城镇的。如,川盐入黔仁岸赤水河中下游交界处的丙滩(今丙安)、赤水河盐运的终点港——茅台。乾隆以后,今岑巩县的“水路码头龙颈坳、罗家山,与江口、铜仁、玉屏接壤的羊桥、驾鳌,与石阡、施秉接界的客楼等地,很快发展成为集镇。特别是龙颈坳,成了思州的第二大镇。当时有人以‘日见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来形容此地商业兴盛的场景”。在开通都江以后,“商贾日众,南海百货亦捆载而至,古州遂为一都会”,以及“辰沅间人亦胥待于施秉争买(白蜡虫)归,遂成一閧之市”。
二、推动贵州经济的发展
因交通不便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人烟稀少,一直成为贵州经济难以发展的桎梏,纵使至清代该问题也依然存在。康熙十八年,学士佛伦就此进言,“黔民稀少,遭乱流亡者多,请敕将军督抚,招徕土民,互相贸易,庶于粮饷有裨”。随着驿道的开发,内地居民源源不断地前往贵州进行经济贸易。嘉靖年间,“思南府上接乌江,下通蜀楚,仡佬族采炼的朱砂、水银吸引内地‘商贾麟集’,‘舟楫往来不绝’”。嘉靖、万历两代由于采办“皇木”,黔东南苗、侗地区的木材被江淮商贾购销。铜仁府,“郡居辰常上游,舟楫往来,商贾互集”。他们当中有的是游商,有的为了方便商贸活动,举家定居下来成为坐商。如,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川商人在务川县城开设行号十余家,经营布匹、绸缎、盐、糖,并收购水银、朱砂、牛羊兽皮、药材、桐油、木籽油料等当地的土特产。光绪时期,陕西籍商人在仁岸开设了“协兴隆”及“义盛隆”盐号。清兴义县知县廖大闻在其《黎峨杂咏》中,就兴义县客民皆贸易而来,久而于此定居作了生动的描述:“天涯旅客至千千,岂不怀归务贸迁”。逐渐稳固与频繁起来的贸易交往不仅促成了贵州内部市场的极大发展,而且启迪了当地民族的经商意识:“只有黑苗生计少,沿街却喊卖山楂”。安顺府“白蜡虫树,四乡俱有,风雨调和之年,其虫更甚……乡民以立夏后摘取之,转售湖南辰沅间”。黎平府“为苗疆重地,通舟楫,民稍积聚,辄转售于外境,故其价昂,而储蓄亦寡。苗人皆食杂粮,其收获稻米,除纳赋外,皆运售楚省者也”。不容质疑的是,明清移民先进的经营理念、商品意识及经济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和影响着当地的世居民族,使得民间贸易逐渐昌盛、发达起来。
贵州的经济生活几乎获得了整体性的改观:“黎平之民富于木。遵义之民富于丝”,便是精准地告知人们,黎平与遵义地区民众富足的原因。乾隆时期,贵州按察使介锡周的奏章中同样提及了贵州经济的发展盛况:“自雍正五、六年以来……现今省会及各郡县,铺店稠密,货物堆积,商贾日集……且新疆大村小寨,暨各处僻乡,酿酒日多”。毋庸置疑,驿道改变了贵州境内与外地的交往格局。从而使得来自先进地区的汉族移民群体在不知不觉中,把许多的经济观念与认知传输给了贵州的少数民族。由驿道构筑的互动空间,打破了贵州与外部世界的藩篱、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激活了当地民众的经济意识、促成汉族与世居民族成为更加紧密的经济共同体。他们之间互通有无、互为补充、互惠互利,拥有高度的依存性和关联度。诚如方显在其《平苗纪略》中谈及的:“黔境苗疆……又所产名材百物,通津转鬻,皆吾民日用不可阙者”。意在说明苗疆出产的名贵木材和各种各样的土特产,通过渡口转卖到内地,成为内地百姓不可缺少的日用品。
尤为值得强调的是,由驿道提供、形成的稳固性与持久性的内外经济交往活动,对贵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革新意义:
首先,促成贵州农工商业的出现与进一步扩大。“19世纪50年代,遵义府绸的年贸易额达七八百万银元,成为当时贵州经济最富饶的地区”,“到了清代,全国产汞约1000吨,贵州产量为900吨,占全国产量的90%”。今赫章县的榨子黑铅银厂(于雍正五年开办,盛年产量达百余万斤)与莲花白铅厂(于雍正十三年开办,开采冶炼工人上万人,有“日以万马载砂”之说。年产量达五六百万斤,为全省之冠)所产之铅供京、楚之用。黑白铅作为该县的主要出口物资,也为清朝各级官府增加了收入。与此同时,各州县丰富的山货、农副土特产品远销外地,发挥着巨大的经济作用。如,务川的生漆:“漆树倍于他产,夏秋之间,商贾辐辏。务川县漆之利更广,四乡所出,岁不下数万斤,农民全赖以资生”。乾隆时期,思州贡物有桐油、铅、铁、金星石、朱砂、水银、蜡、葛、木瓜、竹鸡等。手工业与冶炼业相当兴盛。大有、水尾、羊桥、龙田等地出现了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的专业户。
其次,促成本地实业家的出现。如,乾嘉年间,怀阳丁里(今习水县三岔河)的袁锦道。他利用本地的竹木资源和附近江津四面山的矿产,兴办铁厂、锅厂、铧厂、纸厂、竹器厂及蓝靛厂,共建各种作坊48间。嘉庆年间,伴随着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发家致富的锦屏县人:姜仕朝和姜志远。姜仕朝,相传从卦治用六支苗船运银回家及其家族的显赫地位维持了五代(一百四十多年),因而被谓以“黄白冠千家”与 “富及五代”之称。被尊称为“官商一家”的姜志远,极其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他的两个儿子:姜吉兆和姜吉瑞皆为文举,并同在四川为官:姜吉兆任马边厅同知,姜吉瑞任什邡知县。咸丰初年,思州土家族解元田玉和文生周氏镐等集股于长溪河开采金矿,日产数百斤,有数百名矿工。这些依靠本地资源及优势发家致富的贵州富户,发迹后报恩家乡父老、积极兴办地方公益事业。因深知交通对本地的重要性,因而尤为关注对道路的修筑。如,袁锦道修通了两百多华里的各工场间及连接几处乡场以及至四川的道路,姜仕朝修路、建渡口等。三板溪电站水库在淹没前,文斗河边还存有立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的直径为30厘米、刻有“姜仕朝”名字的拴排石桩。清末,思州马鞍山菜夹沟的侗族富户姚复珍,自筹资金修建了乡村花格路293公里;思州羊桥贡生杨榜第等捐资千余金,雇人修建了羊桥街头的石拱桥。这些路或桥,有的至今仍然可以通车。
再次,促成规模较大的物资集散中心的出现。如,遵义及被称之为 “四大集镇”的打鼓镇(今金沙县城)、湄潭的永兴镇、仁怀的茅台镇及遵义的鸭溪镇。其中,永兴镇是棉纱棉纺织品集散地、茅台镇是食盐集散地、鸭溪镇为粮油土特产和食盐集散地。位于赫章县西南的妈姑镇,为赫章西南部经济贸易中心。妈姑为彝语“骂谷”的音译,“兵营”之意。古为乌撒部落君长的兵营,乌撒八大首目之一的妈姑首目驻地。乾隆以后,妈姑附近的铅锌矿远销上海及各省市,有“十家号”的街名。姑妈镇人生产的铁器用具,尤以马掌钉最享盛名,产品远销川滇及省内各地。畜产品以乌撒马为主,集中在此与各路马帮成交。兴义的黄草坝在道光年间(1821—1850年)为贵州西南部重要的棉布市场和百货交易地,鄂、川等地商人贩运棉花到此销售,又购回白铅。光绪后期,兴义和兴仁是仅次于安顺的贵州第二大洋纱洋布集散地。兴义则为滇黔桂三省交界处最繁盛的商品贸易中心。
毋庸置疑,这些物资集散、转运中心随着人们经济活动的展开,被赋予了多元的功能与色彩。一方面,它们激活了贵州地区诸多民族的经济意识、构建了贵州的贸易体系、带动了其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则打破了地域藩篱与民族藩篱,使得南来北往的人们在交换商品、信息的同时,也交换、交流了文化、习俗及思想观念等。驿道所构建的社会意义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回应了如下的理论观点:“交通……的改善导致了不同文明的人民之间更频繁、更强烈、更对称、更全面的相互作用,结果是他们的文明认同越来越显著”。
结 语
明清时期在贵州修筑的驿道,显然成为贵州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因素。四通八达的驿道干线在加强贵州交通优势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与提升了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官方的、政治性的驿道,作为一个隐性的统治手段及“冷媒介”,意义非凡:一方面,传播了王朝视贵州及其民众作为国家及民族共同体一分子的政治方略,加强了国家对边疆地区持续性的集中化管理意识。而另一方面,则促成边疆与内地新的社会交往方式的形成、扩大和加深了贵州世居民族与汉族的交往领域及其内容。最为重要的是,驿道刺激了贵州世居民族的政治感官、经济感官和文化感官,建构了他们新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及文化意识。其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规范及价值观念在悄然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