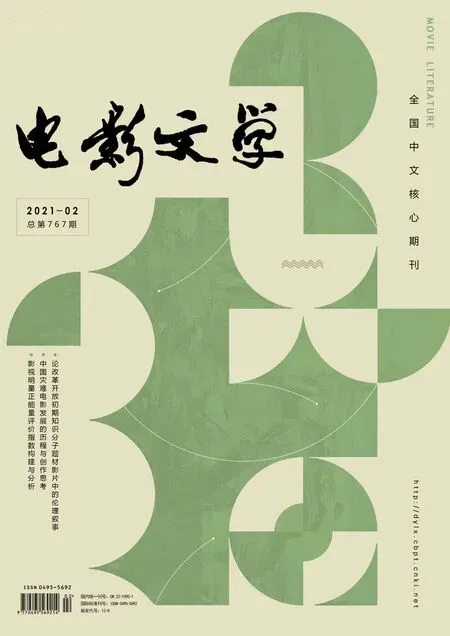“凝视”理论视阈下《八佰》的英雄主义书写
赵 群/Zhao Qun
作为后疫情时代影院复工后上映的首部国产影片,电影《八佰》自2020年8月21日上映截至8月31日,累计票房突破20亿元,成为2020年全球首部单地区票房超20亿元的电影。该片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管虎继《斗牛》《杀生》和2013年的《厨子戏子痞子》之后拍摄的第四部涉及抗战题材的类型电影。区别于前三部电影的黑色狂欢化喜剧风格,在电影《八佰》中,导演以严肃、内敛的拍摄手法,再现了抗战时期“八百壮士”誓死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英雄史诗故事。电影拍摄中高清ALEXA IMAX摄影机的使用,在确保画面高品质呈现的同时,向观影者传递出“看”与“被看”、“凝视”与“反凝视”作为电影表现手法的重要表意功能。通过电影内外双重维度的“凝视”视角建构实现了对英雄主义精神的书写和礼赞。
一、泛化的“凝视”主体与主客体意志变化
“凝视”理论最早源自古希腊的视觉至上原则,进入20世纪之后成为文化批评领域的一项重要分析工具。丹尼·卡拉瓦罗定义“凝视”为描述了一种与眼睛和视觉有关的权利形式。……它同时也是在探查和控制。福柯从“社会权利话语”的角度构建起新的“凝视”批评方法,将权力统治机制注入“凝视”的方法策略中,拓展了“凝视”理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淞沪会战临近尾声之际,为了在即将召开的布鲁塞尔国际会议上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当局对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战略定位为“为维持抵抗样态”,即向国际社会做出尚有中国军人在进行抵抗的姿态。88师524团第一营团附谢晋元率领420人依托四行仓库抵抗日寇,成为上海最后的国军军事力量。在留守指挥官眼中,这场战斗的目的与其说是最大限度地歼灭敌人,倒不如说是唤醒民众的抗战热情,因为“明天全上海的百姓将会看着我们”。自始至终,这是一场“被观看”“被凝视”的战斗。战士们的坚守接受来自权力当局的关注与“凝视”、成为权力当局谈判的筹码,也以获得西方国家的“凝视”为最终目的。河对岸法新社、美联社、时代杂志等众多外国记者的长枪短炮和飘浮在头顶上的外国媒体拍摄悬浮仓也确证了这是一场“被凝视”的媒体狂欢。
福柯曾使用“监督”“监视”等术语表征权利旁观者的观看行为。河对岸民众的观看与“监督”并没有在战士内部催生不安与恐惧,反而放大了战士们决战到底、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决战勇气。河对岸民众代表和记者带着慰问品进入四行仓库劳军采访时,摄像机的拍摄无异于直观地将对岸民众的“观看”与关注呈现在战士们眼前。对此,战士们非但没有表现出反感,反而企图依托这种注视希冀留下自己的英雄形象或给亲人留下遗言遗物。身绑炸弹慷慨赴死时,每位战士大声报出自己的出身、姓名,希冀在“被凝视”的狂欢中留下自己的身后名。“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四行仓库战士的一举一动接受来自河对岸民众和国内外媒体的“凝视”,而河对岸民众和各路媒体同时也在接受观影者的“凝视”。
20世纪中后期开始,雅克·拉康继承了萨特“注视”理论的衣钵,提出著名的 “镜像理论”。拉康认为“凝视”是充满欲望的,观看行为能对自身主体性的认同和构建产生影响。自我观看行为中掺杂了他者结构功能之后,观看行为将变得异常复杂而关键,左右自我建构的完成。除却来自外部的“凝视”外,“八百壮士”亦接受来自内部的彼此互相“凝视”。贪生怕死一心只想逃命的老算盘,圆滑世故明哲保身的老铁,典型化的小人物在结构内部的自我凝视中完成了自己的思想成长与蜕变,扛起了民族大义。
进入20世纪以后,萨特从其存在主义哲学分析中剥离出了“注视”的理论,指出在“注视”行为之下,主客体在相互构建中可能会发生异变,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存在“凝视”行为下的互为辩证、互相影响的关系。萨特的“注视”理论推动“凝视”理论作为一种文艺研究策略被广泛应用到文化人类学的批评当中。笛卡儿曾指出,“我思故我在”。萨特的“注视”理论则佐证了“你看故我在”的哲学命题。个体在被他人注视的过程中,完成自我认知和自我完善、自我建构的过程。个体的主体价值和自我观念生成依赖于外部的注视,外部的注视使“我”成为更完善的行为个体。四行仓库的守军将士不惧牺牲、前赴后继在仓库楼顶竖起国旗正是为了让河对岸的民众、西方媒体及其背后的西方政要、国内政府当局和各界爱国人士看到中国军队对国土的坚守和永不言弃的决心。“那里边就是西洋各国的观察员。在我身后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不只是在这里抵抗日本人,我们是在给他们看中国人还在。”此时,视觉注视已不再是自为与自在的当下联系,而是重新定义着看和被看的世界。
不仅如此,电影中人物的凝视行为同时会将观看者的主体欲望放大,诱发主客体意志发生变化。端午拿着望远镜看向对面窗台上风情万种的歌女不禁意乱情迷。观众在观影时意识到这种偷窥行为的不妥却享受这种偷窥视角带来的观影快感。偷窥式的“凝视”唤起剧中典型性人物甚至观影者正视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深渊。劳拉·穆尔维将电影观众的观看模式划分为“主动性窥视欲”与“自恋式窥视”。窥淫式观看包含着男性的控制性凝视,通过将女性物化成景物奇观以缓解男性的阉割焦虑。受父权文化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潜意识的影响,主流电影的拍摄往往更重视男性的视觉快感。银幕通过对女性肉体的直观展示或加入具有挑逗意味的性语言描述,使男性观众的力比多获得释放,激发并启动男性观众的视觉快感。女性观众亦可通过认同/误认完美镜像的快感,完成更为完美的影像的自恋式窥视欲,在自恋式窥视中获得观影中的心理满足。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女童军杨惠敏为送去鼓舞士气的国旗深夜泅水渡河。如此一位可敬可佩的女英雄,依然逃脱不了因自身女性身份被男性群体窥视的命运。杨惠敏在仓库内换下湿衣取出贴身藏匿的国旗时被老铁等大批士兵围观、窥视,“她香不香啊”更是将女性彻底物化为男性的性幻想对象。影片中另一段羊拐与老铁关于女性“啥滋味”的对话描写,同样赤裸裸表现了男权主义思想下女性被物化为景观对象、遭受品评与凝视的弱者身份定位。源于商业电影对票房的追求,导演在拍摄过程中始终没有摆脱屈服于观众窥视欲的窠臼,进一步印证了当代中国电影打破男性“凝视”、重塑女性权利平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凝视”背后的视听策略
隐喻和象征意象的引入,在一般经验性材料上添加了特殊的语义,延展了电影的叙事美学内涵。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红灯笼预示着封建阴翳笼罩下女性被支配、被禁锢的晦暗命运;贾樟柯《三峡好人》中赵红反复喝水的动作呈现出她在寻找丈夫过程中的焦躁与不安;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中的一幕幕旗袍秀表征了苏丽珍在遭遇丈夫背叛直至自己深陷婚外恋无法自拔的无奈与挣扎。电影《八佰》开场出现的老鼠躲进地洞的特写,预示了抗战初期人人自危、事不关己力求自保的心态。老鼠预感到危险仅须躲进自己的地洞中即可。宛如地鼠一样,成千上万的上海民众躲进租界区,租界区成为他们暂时性的安全“地洞”。电影中场出现的赵子龙横刀立马战千军的想象意象及虚实结合的白马意象,均具有典型的象征隐意。梅洛-庞蒂指出我的身体作为我的知觉的导演,已经将我的知觉与事物本身相一致这样的幻觉显现出来。从此,事物与我之间有了一种隐匿的力量,一种只有在不确定的目光中才使人重视的不确定的梦幻之物。赵子龙的意象作为一种梦幻之物,正是湖北保安团成员小湖北的精神幻化物。在阴差阳错进入四行仓库之后,小湖北的堂兄端午一开始想到的是如何逃命。然而在看到战友舍生忘死的战斗之后,端午放弃了自己逃生的想法,决意投入守卫家国的战斗中。“凝视”行为坚定了其内心的斗争信念,并催发堂弟小湖北内心深处衍生出赵子龙披挂上阵、保家卫国的英雄形象。端午在“凝视”与“观看”中获得了力量,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决心和信念。小湖北在对堂兄端午英雄行为的“凝视”中,将赵子龙形象移植入对堂兄的形象想象与构建当中。电影中的白马在断壁残垣的战场间穿梭,白马既是小湖北相信生命美好的希望,也是团附谢晋元与日方军官谈判时的尊严。灰暗冷色调废墟上出现的白马不仅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色彩对比震撼,也预示着和平与希望,类似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一战题材电影《战马》中的叙事手法。
与意象一样,电影色彩因其丰富的文化美学内涵而成为导演实现电影讲述的有力工具。色彩的一词多义及不同民族、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化对色彩经验和感受的差异性认识使电影色彩成为辨识导演个人特色的重要标签和载体。阴翳下灯笼的暗红、长镜头下黄土地的明黄、玫瑰的艳红浓烈、全景草地的延展式绿色均成为电影叙述的象征性美学要素。管虎电影的色彩使用多以晦暗的冷色调为主,根据剧情变化或人物性格表达需要辅助以与背景对比度高的色彩。红色和白色在管虎导演的作品中较为常见,成为承载其电影隐喻功能的重要色系。《杀生》中飘扬在祠堂屋顶上的红风筝和《斗牛》中九儿的红色夹袄,均在灰暗的底色中撕开一道裂口,成为隐射人物性格、推进故事情节的象征物。《八佰》中的血色喷溅、红旗招展,在展现独特的暴力色彩美学之外,寓意了战争的惨烈和军民内心的坚定。白色象征着高贵优雅、纯洁无辜。废墟上奔跑的白色战马与周围阴沉的断壁残垣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将战争的残酷和人们对和平的向往表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叙述者引导观众对电影的感知,它是电影创造者的实际工具。电影的画外音或开头部分的叙述者视角取决于导演想让观众看到什么。“同故事”叙述者可以出现在电影的初始部分,也可以以中部插入画外音、解释音的方式展开叙述。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以童稚视角展开故事叙述:“我跟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同样,《八佰》以老妪沧桑且极富感染力的上海方言展开故事的叙述,引导观众开启“凝视”程序。观众在老妇人的“大倒叙”式介绍中,如同翻开一张发黄的旧相册,走进尘封的历史。“我七岁那年跟着大人看对面楼里打仗,整个岸边挤满了人都在看那座楼”。而“酒酿圆子特别好吃”的记忆重复意在增加叙述的可信度和真实感,凸显叙述者幼时所见所闻的儿童视角。另外,电影中的多处画面以“镜中镜”的形式拍摄,借助对岸民众及西方媒体凝视仓库战斗的望远镜或摄像机视角,通过变换“凝视”的视听媒介,实现画面的多维度呈现和故事的多角度讲述。长镜头语态下移动的卖报者与静态的“凝视”群体的动静对比折射出动与静、生与死、焦虑与平和的思辨美学特征。
三、“凝视”镜像中的自我身份认同:英雄与平民的共生
战争题材电影的主题呈现往往围绕英雄叙事母题展开,鲜明、生动的英雄形象塑造成为决定战争题材电影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英雄叙事无疑是最清晰可辨的主线之一。英雄崇拜亦是贯穿各个民族衍生发展过程的一种具有普泛性的文化心理意识。英雄之为英雄,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经历某些特别的磨砺由普通个体逐步成长、发展而来。蜘蛛侠、钢铁侠等漫威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均成长于芸芸众生之间。英雄具有超越一般普通民众的能力、眼界、毅力和决心,能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脱颖而出,对周围民众产生引领和感召效应。英雄不是因为其为常胜将军而被供奉上神坛,而是因其具有唤醒民众内心麻木及对危险反应迟滞的能力,因其可以成为唤醒“铁屋子”里万千沉睡民众之人。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忠君报国、“马革裹尸”成为评价战争年代英雄的重要标准。于军人而言,抗击胡奴、战死沙场成为人们对英雄最直观的价值评价标尺。抗击匈奴的霍去病、抵抗金兵的岳飞、痛击倭寇的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等均为华夏民族耳熟能详的典型英雄形象。如果说《八佰》中的团附谢晋元与副官上官志标一出场就因其领袖身份自带英雄光环,怀着不成功便成仁、“丈夫许国,实为幸事”的决心指挥战斗,那么端午、羊拐、老铁、老算盘的英雄之路则是小人物的英雄蜕变之路。拉康认为婴儿的自我意识确立发生于前语言时期的某个神秘瞬间。当婴儿在镜像中确立区别于他者的自我的存在之时,预示着镜像阶段的开始。“他者”的目光成为婴儿确认自我主体的另一面镜子。我们通过对他者的“观看”与“凝视”构建本体的自我。镜像常常会内化为主体从而成为个体的心像。端午在进四行仓库之前是湖北农民,本以为来上海只是为了打扫战场顺带见识一下大上海的繁华,进仓库后一心只想出逃保命。凝视对面租界的繁华与美好,使他下定决心通过水道逃离仓库。出逃过程中意外遭遇日军偷袭后向仓库守军发出预警,在心仪歌女凝视英雄般的崇拜眼神中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毅然选择放弃出逃坚守仓库。在对周围英雄事迹的不断“凝视”中,端午最终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和怯懦,成长为小湖北心中如赵子龙一般的英雄存在。
“凝视”民众的英雄化倾向也成为管虎导演完成英雄主义书写的关键一步。英雄的个体性、平民性的意义赋能彰显了当代战争题材英雄形象塑造的普遍价值诉求。从英雄视角转向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视角,弱化英雄人物的阶级性、神圣性,强化他的个体性、日常性,就成为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当然选择。《秋之白华》《我和我的祖国》等一系列主旋律影片舍弃了宏大的政治性叙事,围绕英雄的日常性与普通人的英雄性展开对英雄主义的重构。在对对岸战局的反复凝视中,租界区民众从最初“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麻木中苏醒,沉睡的民族自尊心在日军炮火的蹂躏下集体爆发。精致利己主义心态逐渐为浓烈的爱国民族情绪所代替。在对面将士英勇行为的感召下,募集物资时慷慨捐赠的中俄混血妓女,冒着炮火将电话线送过桥的黑道人士和赌馆打手刀子,在租界开赌馆的老板娘蓉姐,为经济利益向日本军方和西方媒体出卖情报的方记者,手无缚鸡之力的教授,这些普通民众在看与被看、凝视与被凝视中,内心沉睡的民族正义与激情被激发,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对抗侵略的战斗中。在民族大义面前,这些普通平民绽放出无畏的人性之光。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意义绝不在于一场战斗的胜负,其对民众的启智意义以及其间迸发的舍生忘死、为保卫家国抗争到底的英雄主义精神才是导演极力表现和讴歌的主题。“凝视”与“被凝视”、英雄视角与普通民众视角的有机结合在实现民族集体创伤记忆的书写中隐去了意识形态表达的厚重感,更易于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和认知共鸣。英雄战士与平民英雄在“凝视”的镜像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象征界的他者功能,成就了自我理想,构筑了理想自我。
区别于以往导演对抗战题材电影的低角度叙述、背景化处理、聚焦小人物命运的荒诞表现手法,管虎在《八佰》的拍摄过程中,以高光手法展开宏大战争叙事和英雄形象符号的构建,真实再现了战争的残酷、血腥以及置身战争洪流中的平凡人的人性挣扎,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铺陈英雄人物的壮烈史诗。在中国电影国际化与本土化、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角力中如何实现中国故事讲述和中国英雄情怀的意向性表达,唤醒民众的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自豪感,将电影的商业价值追求、民族文化传播、价值理念引导统合在电影的叙事伦理中,实现电影的教化传播功能,成为当今抗战题材电影必须正视的责任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