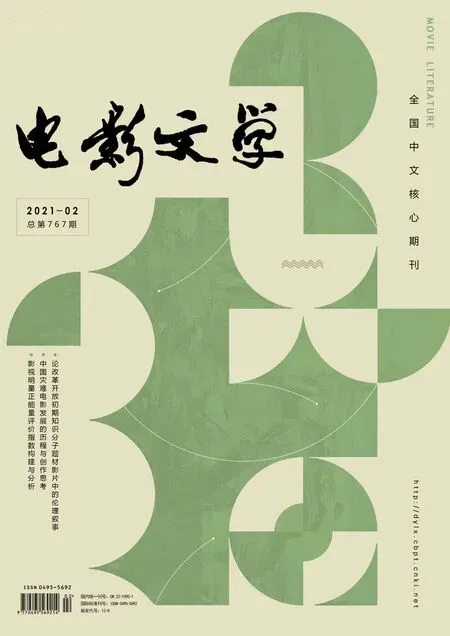“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创伤呈现
王 霞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弗洛伊德指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朱迪斯·赫尔曼认为,正常情况下,人在面对危险和刺激的时候,身体会处于警戒状态,集中注意力去面对眼前的危机。为了应对危机,人会忽略饥饿、劳累和疼痛。备受威胁的感觉还会使受创者产生强烈的愤怒和恐惧。这些反应最终都会促使受创者的身体和心智处于应战状态,武装自己。一旦上述的这些反应没有效果,武装、抵抗或者逃脱都不再有用,绝望降临,那么,人的自我防御系统就会被彻底击垮,处于混乱状态,产生受创反应。“创伤事件对生理激发反应、情绪、认知和记忆都造成严重而长期的改变。”所谓的创伤事件,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它往往会威胁到人的身体、生命,甚至使人直接处于暴力和死亡的处境下,心理上产生一种极度无助、恐惧、失控、被毁灭的感觉。创伤事件最主要的是能够正如赵冬梅所指出的:“医学和精神病学将心理创伤定义为某种非同寻常的威胁或灾难性事件所引发的精神紧张状态,包括无能为力感、无助感、无法抵抗甚至麻痹感;有些人在应激之后会进一步发展成为创伤后应激障碍。”造成心理创伤的事件是不寻常的、意料之外的事件,超过了受创者的应对能力,激起受创者的无助感与恐怖感。可以看出,上述对于创伤的界定都强调人在自然或人为灾难面前所产生的无助、绝望、恐惧,进而造成创伤性应激障碍,使受创者的自我认同遭到破坏。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其带来的创伤是持久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类型是多元化的,而无论何种类型的电影叙事,都是一种创伤性叙事。这些影像作品以不同的叙事视角、情节类型向我们描绘南京大屠杀的行为及其后果,呈现了历史创伤与民族记忆。
一、无辜百姓、战俘的创伤
国际法有对战时平民的保护条款,不能侵害平民的生命安全,不能抢劫失陷地区的城镇和村子。但是,日军却在攻占南京以后,违反国际法,抢劫财产,残害平民的生命。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大肆地抢劫公有财产和难民的私有财产等。“在南京沦陷后,他们毫不踌躇地侵入了普通住宅、商店、银行、政府建筑物,掠夺文物、高价物品、家具等,连难民们的寝具、衣服或者是戴着的手表、装饰品都抢走。”日军还进行文化破坏,抢走大量的书籍、古籍。“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日军的抢劫行为有所表现。在“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中,日军抢夺百姓的财物,霸占有价值的文物。在电影《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将领默认甚至鼓励日本士兵去抢夺中国人的财物。一个日本士兵为了抢中国妇女手上戴的玉镯,直接用刀将她的手砍下来。
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日军大规模地屠杀中国军民。日军十六师团在12月13日一天的屠杀数字就很庞大。一个日军士兵在接受松冈环女士采访时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叫我们收拾尸体扔到扬子江里。杀的尽是普通老百姓。总之,男人全杀了,这些尸体我们每天从早到晚大概花了一个星期才收拾完。”日军对战争中的中国俘虏采取的是杀光政策,日军的各个师团都不能接受俘虏。由此,日军屠杀中国俘虏的规模十分巨大,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表现了日军以残忍的方式杀害无辜百姓、战俘,有活埋、火烧、练刺刀的活靶子、砍头、枪杀等方式。在电影《屠城血证》中,日军将人装进袋子里,活活烧死。日军还枪杀战俘、普通难民,以活人为靶练习刺刀,场面残忍。日军只是在教堂里发现一个头盔,就杀死十几个无辜的中国人。日本报纸上对日军在南京的百人斩杀人比赛有报道,日军担心在南京的暴行被世界所知,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禁止西方人士拍摄相关的日军屠杀照片,掩饰罪行。在电影《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用机枪射杀中国人,战俘、伤兵一个不留。日军还进行杀人比赛,杀的中国人越多越光荣,有一个日本士兵杀了300多个中国人而被称为英雄。电影《南京1937》也有对日军杀人比赛的表现。在《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将领中岛今朝吾用百姓、俘虏来试他的镰仓宝刀,亲手杀死7名无辜的中国人。谷寿夫集体枪杀2000多战俘。日军在寺庙里枪杀和尚,将寺庙的和尚全部杀光,尸体堆积如山。由于日军的疯狂杀戮,到处都是尸体。日军为了清理尸体,用火烧尸体,将尸体投入江中或者埋掉。江边密密的一排排尸体,被浇上汽油,火势熏天,黑烟滚滚。在《南京1937》中,既有日军分散枪杀无辜百姓、战俘的场景,也有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场景。相比来说,电影《栖霞寺1937》对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残杀、虐杀的血腥场景的直接表现不多。但是寂然大师写了一封公开信登报,控诉日军的罪行:抢粮食、强奸、枪杀,几乎每天都有上述事情发生。日军不仅杀害中国人,还杀害国际友人。美国摄影师马丁拍摄了日军罪行的照片,想把照片送回美国,让世界知道日军的暴行。因此,日军全城搜查,追杀马丁,并将之杀害。《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与其他几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相比,不仅表现了普通的日本士兵的屠杀行为,还表现了日军高级将领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所言所行。电影通过日军将领之口解释了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国人口多、土地广,要尽快结束战争,只能采取威慑手段,将男女老少全部杀光,奉行三光政策,才能够震慑中国人。《南京1937》中的日军将领也说,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市民有几十万,军人有十万多人。如果日军采用极端的严酷的政策来对待南京的市民和军人,将会给中国的抗日运动以重大打击。因此,日军采取了对中国人进行全部消灭的政策。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屠杀的时间很长,整个南京城都弥漫着血腥、恐怖的气氛,到处都是悲惨的哀号和堆积的尸体。而且,日军经常故意强迫南京市民在旁边观看其罪行。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市民往往由于极度惊恐而处于畏缩、麻木状态。“恐怖的环境,及其决定的南京居民的身心状况,使得PTSD成为当时南京的一种‘常态’。”有些中国的士兵因为恐惧而精神失常。“有研究表明,在战争所导致的创伤中,最显著的症状就是情感麻木以及暴躁不安,而出现这些症状的主要原因是士兵对战争环境的适应不良。”军人和退伍军人都是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高危人群。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往往会出现明显的注意力与学习能力的下降、瞬时记忆能力的缺失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研究者对大屠杀和集中营的幸存者进行研究,发现幸存者最为核心的创伤就是“放弃、接受死亡和毁灭时产生的无助”。张生在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创伤性应激障碍研究中,指出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由于身处极端的恐怖环境中,又无力改变环境与事实,会出现惊恐无措、失去反应能力、冷漠、精神疲劳、失忆、歇斯底里、精神失常、自杀等症状。“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PTSD是广泛存在的。从受害对象来说,不仅有那些直接承受日军暴力的人,也有那些目睹暴行的人;从受害对象来说,不仅有南京人、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从受害时间来说,不仅是经历南京大屠杀的当时,也延续到今天。在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屠杀是当今世界必须正视的、属于全人类的历史。”
二、女性的创伤
在南京大屠杀中,有两万起强奸事件。一个日本士兵在接受松冈环女士的采访时说:“不管进南京之前,还是进南京之后,强奸妇女可以说是任你随便干,干多少都无所谓……即使设立了慰安所,也没有减少强奸事件。”程兆奇在对侵华日军军风军纪的研究中指出,当时的日军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操守,悖逆人伦。“日志和日记所记日军犯罪,最频繁的是强奸。这些强奸不仅‘全天候’,不受拘束,而且伴之以暴虐和血腥,与深刻在我民族心中的记忆完全一致。”日军所过之处,性暴力无所不在,给中国女性带来了深重的创伤。日军强奸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不分老幼,从八岁的幼女到五十六岁的老妇,都不放过;日军经常成群结队地进行强奸,轮奸的情况非常普遍;日军的强奸往往伴随着血腥、暴力,非常残忍。日本官兵在强奸之后,担心招来麻烦、留下罪证,就导致了对于被强奸女性的再次伤害和杀戮。“以强奸为目的去中国人家中,若遇见人反抗就把他们全部杀害,还有一些妇女是在逃避时被枪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程兆奇指出:“就强奸中对不从者杀伤、杀死全无顾忌而言,在近代以后确实极其罕见。”金一虹也指出,在南京大屠杀的性暴力中,最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在强奸中国女性之后的“超强奸”,即对受害的女性进行凌辱与虐杀,“如强迫受害妇女当众裸露奔跑,强迫其亲属与其乱伦,强迫中国人奸中国人,乃至对被强奸妇女进行剖腹、割乳、在阴道插入异物等极其残忍的杀戮”。
“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性暴力有所呈现,表现了中国女性被强奸、虐杀、强迫中国人奸中国人等场景。在《屠城血证》中,日本士兵在国际安全区的图书馆强奸少女,在强奸了护士白燕之后,将其杀害。在《栖霞寺1937》中,日本士兵在寺庙里强奸妇女。图书馆、寺庙原本是神圣之地,但是日军却在这样的地方施展其兽性与淫欲,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在《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将领说,日军占领南京以后,南京城里家家都是慰安所,每个中国妇女都是慰安妇。由此,日军军纪败坏,肆意强奸、杀害中国妇女的现象比比皆是。兽性大发的日本士兵不仅强奸孕妇、乳母,连老人、幼儿也不肯放过。即使在国际安全区,日军也丝毫没有收敛。他们到安全区抓中国妇女做慰安妇。在慰安所中的女性更是生不如死,一批批被蹂躏至死的流着鲜血的女人尸体被抬走。在《南京1937》中,日本士兵到处抓中国妇女,将她们装满卡车,拉去慰安所。大量的被日军强奸至死的妇女尸体被抬到坑里掩埋。在电影《金陵十三钗》中,豆蔻和香兰为了拿回琴弦、耳环,冒着危险回到妓院,却遇到了一队日本士兵。日本士兵残忍地将豆蔻绑在椅子上,供他们轮奸。豆蔻由于反抗,被一个日本士兵刺死,满身是血。香兰也是死状极惨。约翰在去妓院找豆蔻、香兰的路上,看见到处都是尸体,有些是女人的裸体。而女性的屈辱、死亡又往往和孩子联系在一起。在《屠城血证》中,一名妇女抱着婴儿哺乳,被日本士兵枪杀。在安全区的图书馆,日本士兵用刺刀杀死婴儿,强奸婴儿的母亲。《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对于日本强奸暴行的表现最为直接、逼真。日本士兵踢一名中国孕妇的肚子,她的丈夫去阻拦、保护妻子而被殴打。一名日本士兵直接用刺刀将这名孕妇的肚子剖开,从里面挑出血淋淋的胎儿。这一场景伴随着孕妇声嘶力竭的惨叫。一个日本士兵在强奸妇女时,将她的正在啼哭的幼儿活生生地放进开水中煮。日军所到之处,处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这些尸体里有一些是女人、母亲。死去了母亲,幼儿孤苦无助的啼哭声萦绕在南京城。
在南京大屠杀中,许多女性被强奸、杀害,即使有些女性幸存下来,也一生都饱受身心的创伤困扰。“被强奸仅仅是这些妇女苦难的开头,除了肉体的创痛还有深重久远的精神伤害。”有研究者对“强奸创伤综合征”进行探究,指出被强奸的女性会做噩梦,脑海中不停地闪回当时的恐惧场景。即使受创者处于安全的环境中,其头脑中还是会重新浮现创伤性事件,因而,创伤经历就成为一个永远都无法摆脱的梦魇,使受创者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强奸的女性除了身体上的创伤、死亡,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伤痛,许多被日军强奸的女性有睡眠障碍、哭泣、歇斯底里、精神失常、自杀。“受害者因没有保住身子而感到没了做人的尊严,当时没死,日后因羞耻感郁郁而终的妇女也不在少数。”弗洛伊德指出,创伤性神经病不同于通常的神经病,受创者执着于创伤发生时的经历。受创者经常会在梦里重新召唤和体验创伤性经历。“一个人如果不能应付一个强烈的情绪经验,结果便造成了神经病,所以神经病的成因约略类似于创伤病。”创伤性经历可以改变受创者的整个生活,使其混乱无序,丧失生命力,对所有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一直沉迷于过去的创伤性回忆里。因此金一虹提出:“歇斯底里、失语、精神失常乃至自杀等都是即时的创痛反应,长远的创痛到底有多深,有多长,这些创痛如何伴随她们度过今生?”
朱迪斯·赫尔曼将受创者对于创伤性经历的执着与固守行为称作记忆侵扰。受创者不论是清醒还是沉睡,都无法摆脱过去的创伤性记忆,一件不怎么相关的小事也可能引起受创者的创伤性记忆。“因此再平常、再安全的环境,对受创者而言都充满危机,因为谁也无法确保他的伤痛记忆不会被唤起。”此外,受创者还会出现禁闭畏缩,即受创者感到无助、绝望,所有的反抗都无济于事时,会进行一种放弃、麻木的状态。受创者会避免回忆起过去的创伤性经历,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限定,将自己的意识与生活封闭起来。张连红在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中指出,有一个叫杜秀英的幸存者,在12岁时被日军强奸,但是在接受采访之前她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尽管她将这件事封存起来,还是会做噩梦,在梦里重新经历过去的创伤事件,以致她听到门外的脚步声都会感到很害怕。可以看出,一方面杜秀英忍受着记忆侵扰,即使在睡梦中也要继续受到创伤性经历的折磨;另一方面,杜秀英又试图封存过去的创伤性经历,她的亲人也不知道她的悲惨故事。“在经历过极端危险之后,记忆侵扰和禁闭畏缩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反应,会形成一种摆荡于两端的律动。这两个相反心理状态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许就是创伤后症候群的最大特征。”记忆侵扰与禁闭畏缩的交替,反映了受创者想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到一种平衡的努力,但这种交替所产生的不稳定,又进一步使受创者的无助感进一步恶化。因此,这一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症状,可能永远都无法摆脱。
三、孩童的创伤
孩童在亲身经历或听到、看到创伤事件之后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的症状,称之为孩童创伤。经历创伤事件的孩童会出现害怕、无助、哭泣、愤怒、麻木等情绪,还会出现自我破坏行为、创伤的闪回、睡眠障碍、高警觉等行为。张生认为:“儿童期遭遇震撼性恐怖事件,更易形成PTSD,成年后的漫长岁月里,如再次被唤醒记忆,会反复遭受冲击。”朱迪斯·赫尔曼也指出:“在成人阶段发生的持续性创伤,会侵蚀已经定型的性格结构;而在儿童期发生的持续性创伤,则会扭曲尚未成形的性格,使他朝不正常的方向发展。”在战争中,孩童是最为脆弱的一个群体,身心尚幼。因此,孩童所面临的暴力与死亡的威胁对其心灵的影响更大。“有时孩子在暴行或杀害的威胁下,会吓得噤若寒蝉。”在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力事件中,孩童或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同胞被杀害、被侮辱,或直接立于死亡的阴影下,感受死神降临的恐怖。即使有的孩童成为幸存者,也会终生都饱受创伤之苦。“除对暴力的恐惧之外,创伤患者一致地报告他们有极大的无助感。”这种亲临暴力的恐惧、无助、绝望是伴随一生的。赵冬梅认为,受创者遭遇创伤性事件时的年龄很重要。受创者的年龄越小,以后形成心理创伤的可能性就越大,创伤体验也会越深刻。“幼年期是形成无意识的关键时期,还没有形成足够的整合能力,还不能对创伤事件进行正确的加工,也不能用语言清晰地表达出创伤体验、创伤过程等,所以,创伤事件就留在了当事人的无意识当中,对其日后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影响。”
在电影《南京1937》中,日军将一家中国人全部杀死,只剩下一个男童。一个日本士兵将一枚手榴弹放在男童手上,将其炸死。在国际安全区,孩子们问小陵,日本人杀不杀老爷爷?连孩子也杀吗?电影以孩子们天真的语言表达出日军不仅杀战俘、百姓,连最为弱势的老人和孩子也不放过的邪恶暴行。日本士兵还在孩子们面前强奸了他们的老师。这些创伤会永远地铭刻在孩子们的心上。在《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中,一个中国人主动给日本人当翻译,最后却被日本人当作练刀的活靶子。他的儿子在旁边看着父亲的脑袋被砍下,滚落在地的脑袋上还睁着眼睛。尽管电影的结尾表现了这个男孩并没有死,走在漆黑的夜色里。但是,在当时国家破碎的情况下,男孩想要活下去是很艰难的,即使能够活下去,也要经受身心的创伤之苦。《五月八月》是一部以儿童视角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五月、八月的爸爸出去找粮食,一去不回,只有小狗阿宝叼回来他的一只胳膊。接着阿宝被送走,奶奶被杀死,妈妈被强奸。在表现妈妈被强奸的场景时,隔了一层白纱,但是孩子们可以听到妈妈痛苦的喊叫与挣扎声。对于五月来说,爸爸、奶奶、妈妈的受难与死亡,让她迅速地成长,也让她的内心饱含伤痛。她要独自照顾年幼的妹妹八月,带她去寻找食物。五月给八月在河里洗澡时,看到八月的后面漂过来一具尸体,她一边挡住妹妹的眼睛,一边冷静地用脚踢开尸体。
根据创伤心理学对PTSD诊断的标准,诊断PTSD的最为核心的点是个体在经历创伤事件的恐惧感与无力感之后,具有三类症状。其一,创伤个体会反复地再度体验与创伤事件有关的经历与刺激;其二,创伤个体会反复回避与创伤事件有关的经历与刺激以及麻木症状;其三,创伤个体的警觉性会持续增高。孩童由于认知与情感的发育还不成熟,其创伤后反应也与成人有所不同。在电影中,五月的爸爸、奶奶的死亡,以及亲眼看到妈妈被日军强奸,对她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她回想起以前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后来踢开河里的尸体,都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符合的冷静,以及对于过去亲人死去的创伤事件的回避、麻木。喜欢画画的少年方毅,是一个孤儿,家人都死于南京大屠杀。他画的画色彩灰暗,画面上都是死人。他的爸妈为了救他而死,尽管他幸存下来,却充满内疚感,觉得自己很没用。有研究者指出,孩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个独特体现是他们会通过创伤性游戏、绘画或讲故事的方式来重现创伤。即孩童经常通过对于创伤的非文字表达来重现创伤。电影中的方毅只是一个少年,却经历了父母的死亡,因此他创伤后应激症状就是对死亡的绘画。通过绘画,重新体验了死亡带来的创伤。“创伤经历的不断重复再体验,一定是代表一种身体自发、想要痊愈却徒劳无功的企图。”也就是说,受创者通过重复过往的创伤性经历,重新去感受创伤,并试图去掌控、修复创伤。通过对于创伤性经历的再度体验,受创者能够重新去掌控创伤产生时的无助感、挫败感、恐怖感,从而修复创伤。但是,这个过程也往往伴随着再次经历创伤的无助与恐惧,所以受创者并不会主动寻求这样的再度体验创伤的机会。朱迪斯·赫尔曼指出,受创者对于创伤性事件的再度体验,会引起强烈的情绪折磨。“创伤经历的再体验,无论被侵扰的是记忆、梦境还是行动,伴随的情绪强度都正如创伤事件当时一般。受创者也会持续受到恐怖与愤怒的折磨。”
经历过童年创伤的孩童,身体上会出现慢性睡眠干扰、肠胃问题等生理症状,心理上会经历愤怒、悲伤、自我责备、自我认同的扭曲等。不仅如此,经过童年创伤的孩童,其性格很难适应长大以后的成人生活。“她仍旧是自己童年的囚犯,试图创造新生活时,她再度与精神创伤正面交锋。”在电影《五月八月》中,这些经历南京大屠杀的孤儿即使幸免于难,也永远都不会忘记家国之痛,那种无助、恐惧会如幽灵般伴随一生。创伤记忆会萦绕在心灵深处,无法排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迪斯·赫尔曼指出:“长大成人后的儿童受害者,似乎注定要再度体验她的创伤经历,不仅是在记忆里,而且是在真实人生中。”有研究者在对南京大屠杀中的39位孩童幸存者进行调查时发现,尽管这些幸存者已经进入老年,但是他们对当年的记忆仍然很深刻,无法忘记那段创伤性经历。南京大屠杀的经历让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恐惧、敏感、退缩之中。
四、历史创伤与民族记忆
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认为,对人的谋杀有两种,一种是谋杀人的生命,另一种是从记忆上抹去这个人的所有痕迹。因此,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对于这一历史事件中30多万的受害者来说,忘记就等于二次屠杀。阿维夏伊·玛格利特指出,记忆与关爱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记忆是关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遗忘了某个人某件事,则表明我们已经停止了对其的关爱。所有遗忘的核心,都是一种漠不关心。而关爱又和道德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们不仅需要道德反对邪恶,更需要道德反对冷漠。……一旦邪恶与冷漠结合起来,将更具有杀伤力,正如毒药融入水中。在某种意义上,关于平庸的恶的观点就指的是这种意义上的结合。”因此,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中30多万的受害者来说,记住南京大屠杀,记住他们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受难,就是对于他们最好的纪念和关爱。否则,就是一种道德冷漠。
那么,我们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逝去的历史事件,应该记住什么?张纯如曾呼吁世人,我们不仅要记住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亡的受害者人数,更要记住日军残忍地折磨受害者的极端手段。张纯如指出:“人类残忍对待同胞的编年史讲述着漫长而令人痛心的故事,但是如果说这类恐怖故事中人类的残暴程度确实存在差别,那么世界历史上极少有什么暴行可以在强度和规模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行的南京大屠杀相比。”高兴祖也指出,日军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行为,是无数暴行中的典型,其规模之大、受害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屠杀手段之残酷,在人类文明史中是罕见的。无疑,我们不能忘记30多万的受害者,也不能忘记这一历史事件带给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与创痛。
李仰智指出,历史已然逝去,不可回归,历史的文本化却能够通过对于历史的书写与解读来使历史死而复生。如果对于历史的书写仅仅停留于事件的外在层面,就会遮蔽历史中的个体生命。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数字的考证不能够以忽视其背后的受害者的创伤程度、屠杀记忆的否定为代价。“那种把灾难数字化抽象化的简约方式背后必然是对苦难历史的一种超然姿态。”过于强调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屠杀、奸淫、施虐的残忍性与兽性。正如孙歌所提出的:“从日军进行细菌战时在普通中国农民身上进行活体实验,到强奸中国妇女之后再杀掉她吃她的肉;这些兽性如何能够被统计学的数字说明?这些无法数据化和实证化的‘历史记忆’,是否应该在历史研究中获得应有的位置?它们是否也构成历史的‘真实’?”就此来说,“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能够以独特的视听艺术方式将这一创伤事件还原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记忆及其挣扎、屈辱、死亡,引导人们进入深层的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思考与表达。
南京大屠杀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记忆,然而,经历过这段记忆的幸存者面临的是一辈子都难以愈合的身心创伤。南京大屠杀不仅是亲历者的个体记忆,也是战后所有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成为一种民族集体记忆。对于参与这一集体记忆的人来说,就等于确认了自己成为集体中的一员,能产生自我身份的认同感。由此,“拥有某种共同记忆的‘我们’和不拥有这一记忆的‘他们’之间因此区别出亲疏不同的关系。”张生指出:“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抽象为民族共同记忆,化为促进中国国家整合的社会资源,对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由此,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创伤与民族记忆,能够增强国家的凝聚力。正如葛兆光所指出的,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会存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当大家去挖掘这份共同的记忆,就是在寻找共同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