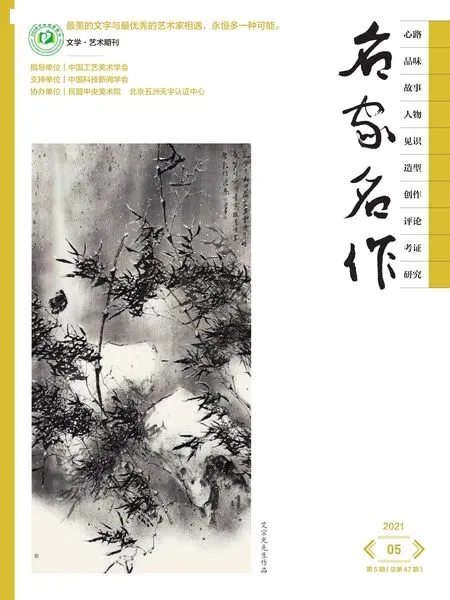基于认知的汉语名量词起源再探
徐淑颖
一、引言
名量词是现代汉语量词系统的两个部类之一。在近百年的汉语语法学史上,量词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从静态的对量词定名、分类,到把量词与相关词类、句法结构联系起来的动态研究过程。但从认知角度对汉语名量词的产生机制、认知功能和认知特性的研究还只零星见载,且基本着眼于一个或两个量词的认知研究,缺乏从全局着眼对名量词的认知基础的研究,以及对其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之间关系的研究。因此,本文选取现代汉语名量词的认知研究这一课题,探讨了名量词,特别是个体量词的产生机制。
二、汉语名量词的起源和发展
(一)名量词的萌芽
王力指出,汉语单位词起源很早,在殷墟卜辞中就存在“丙”(“马五十丙”)、“朋”(“贝十朋”)、“卣”(“鬯三卣”)、“升”(“鬯二升”)等。虽然目前对“丙”和“朋”具体表示的数量还存在争议,但都认为这两者是集体单位。“卣”是容器单位,“升”可认为是度量衡单位,也可认为是容器单位。因此王力认为,商代还没有天然单位如“匹”“张”等。另外一些学者,如黄载君,认为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天然单位”的量词,因为“俘人十又六人”“羌百羌”和“玉十玉”中的后一个“人”“羌”“玉”已经与前面的名词的性质不同,而成了量词。后来的日本学者Hashimoto研究发现汉藏语系的其他语言也存在这种用法,并称其为“回响型量词”(echo-classifier)。而在黄载君之前,管燮初认为这些词介于名词与量词之间,而王力认为这些词还是名词,并且指出“关于人的天然单位就用‘人’为单位词,数词前面不一定也是‘人’字”,如殷墟卜辞中的“羌十人”“羌十人又五”等。
甲骨文中对天然单位的数量表达法是“名词+数词”,如“鹿百六十二……豕十,兔一”。或“数词+名词”如“九羌”“九牛”等。因此,学界普遍认为甲骨文中的量词还很少,且是否出现个体量词还无法定论。
Wang Lianqing根据管燮初对金文的考察,认为西周时期新增了五个集合量词如“乘”(四驾马车为一乘)、“束”(指一束稻)、“旅”(五百人为一旅)等,十几个度量衡量词如“寸”“镒”“里”等。对于天然单位的计量,除了仍旧存在回响结构如“田七田”外,还出现了约六七个个体量词,如“匹”(指马)、“人/品”(指人)、“白”(指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夫”(指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两”(指车)。且所列举的名词短语格式均为“名+数+量”。
(二)名量词的确立和发展
到了先秦时代,王力认为:“度量衡制度建立以后,出现了很多度量衡单位词……但是天然单位的单位词还是很少见……只有‘匹’指马、‘乘’、‘两’(指车)、‘张’(指幄幕)、‘个’(指矢)等极少数的几个字。”Wang Lianqing对王力的观点进行了补充,认为在先秦时期,“衣衾三领”中的“领”,“枪二十枚”中的“枚”,“一埒肉”中的“埒”,以及另外几个量词已经明显用于指称天然单位了。但是先秦时期量词的使用还没有成熟,因为当时在表达数量概念的时候,除了甲骨文已经存在的用于计量天然单位的“数词+名词”和“名词+数词”,还存在两种少见的方式:“名词+数词+量词”和“数词+量词+名词”。其中“数词+名词”最常见,其他几种比较少见。另外,“名词+数词+量词”中的量词既可以是度量衡量词、个体量词,也可以是集体量词,而“数词+量词+名词”中的量词只能是容器量词。
两汉及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名量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且“数词+量词+名词”的出现频率也有所增加。刘世儒在《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提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名量词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进入成熟时期了。但是俞光中和植田均对唐代文献《敦煌变文集》里量词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按现代的眼光看,“该用量词的地方,还是不用的时候比用的时候多”。因此笔者同意郭先珍和Wang Lianqing等人的假设,认为个体量词成为必须使用的一种语法规范是在宋朝。
三、名量词的产生机制
(一)名量词的分类
汉语名量词的产生机制是量词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学界对量词产生的原因还存在很多争议,根据叶桂郴的研究,目前主要有功能派和语法派两个角度、五种说法,叶桂郴对这几种说法进行了详细的评论和辩驳,在此不再一一赘述。然而,这几种说法不能一概而论,主要是因为它们对“量词”这一概念包括的内容理解不同:其中有些是把量词作为一个大类来研究,包括度量衡量词、群体量词和个体量词,而有些是针对个体量词这一小类。研究的出发点不同,放在同一平面进行比较似乎欠妥。因此,有必要对量词进行分类并区别对待。
由于名量词是依附于名词的,因此对量词分类时应该从其所结合的名词入手。对此,吕叔湘有过精辟的论述:“世界上的物质,有可以计数的,有不能计数的。可以计数的,可以直接用数字来表示数量,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不能计数的,如各种物质,必须凭依种种度量衡单位或方便借用的容器,才能计数,如: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史记·淮南厉王传》)……”吕叔湘所指的“可以计数的物质”和“不能计数的物质”即李明宇所称的“离散事物”和“非离散事物”。在一些屈折语如英语中,前者用可数名词表示,后者用不可数名词表示。
可用来计量单个离散事物的量词我们一般称为个体量词。量词体系中还有度量衡量词、容器量词和集体量词,本文中将它们统称为非个体量词。
(二)非个体量词的产生机制
既然非离散事物必须依靠度量衡单位或容器单位才能计数,那么度量衡量词和容器量词的出现就是我们认知、把握世界的客观需要。因此,Erbaugh认为这两种量词是所有语言共有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当需要计量离散事物的集合时,也需要依靠一个量词,如“马五十丙”“贝十朋”等。去掉这些集合量词以后,名词短语所表达的量就不准确了,因此集合量词和度量衡量词和容器量词一样,是由于客观需要才出现的。叶桂郴把这几者的出现归结于计数的需要:“表数要求成为人类的共同要求,任何民族、任何文化背景下的语言都有复杂数目相搭配的语法范畴。如果事物本身表示不精确的模糊数量时,更加需要模糊的称量……”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可取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存在度量衡单位、容器单位和集合单位,而且在早期的汉语文献中这些量词在所有量词中的百分比占绝对优势,这也证明了这几种量词是社会交往、信息交流中计数的需要。另外,英语作为一种富于词性变化的屈折语,也有大量的度量衡单位、容器单位和集合单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这几种量词是各个民族为了明确表达计数要求而普遍使用的。
(二)个体量词的产生机制
离散事物本身具有明确的边界,在认知上有凸显性,因此实际上不需要量词就能表达量的概念。英语中可数名词可以通过加后缀-s直接与数词结合,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个体量词并没有认知上的必然需要。那么为什么汉语中会需要使用个体量词呢?原因有两方面。
首先来探讨个体量词产生的格式。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甲骨文中表示离散事物有两种结构:“数词+名词”和“名词+数词”。在前一种结构中,名词处于中心地位,凸显的是事物本身而不是事物的量,而后一种结构出现的语境一般是“清单”类话语环境,在这种环境里,数量通常是一种焦点信息。如“丁卯□□□兽正□□毕获鹿百六十二,□百十四,豕十,兔一”。而由于量词是黏附于数词的,所以个体量词会最先出现在“名词+数词”结构之后。
由于非个体量词是表量所必需的,所以“名词+数词+非个体量词”的结构对“名词+数词”结构产生了一定的类推作用,因此会有“羌百羌”“玉十玉”等结构的产生。李宇明对汉藏语系和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的研究也发现,许多语言中至今还存在这种重复中心名词的回响结构。这个重复的名词是量词的原始形式。但这种回响结构在表达上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名词和回响型量词语音和词形相同,可能不利于人们的理解,其次,脱离了这种结构,回响型量词就容易和名词混淆。因此在西周和先秦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用其他词来充当量词。
不过由于这些词不表量,缺少它们不会影响信息的准确传递,因此并没有成为一种语法必须。先秦时期,离散事物的量绝大多数还是数词和名词直接结合来表达的。但随着度量衡量词和集体量词的增加,“名词+数词+非个体量词”的结构的类推作用日益强大,个体量词也由西周的六七个增加到了先秦的15个左右。
王力认为,个体量词的真正发达还在汉代以后,刘世儒在《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列举了123个个体量词(刘先生称为“陪伴词”)。 根据肖从礼的研究,非个体量词在先秦已经基本成熟了,在两汉时这类量词数量相对稳定。那么语法格式类推的说法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时期个体量词大量增加的现象。笔者认为,还有另一个促动因素,即汉语的双音节化。
汉语的双音节化是指由于语音的简化导致同音字增多,为了确保信息的准确表达,汉语词汇出现了双音节化的趋势。除了语音的简化,还有其他原因也促进了双音节化过程,如外语的吸收和汉语自身的发展规律。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在甲骨文中就已经有少量双音词,但目前普遍认为,甲骨文和金文时期的汉语词汇系统还处在单音节词占优势的阶段,先秦两汉时期双音词的数量有所增加,而魏晋时期是汉语词汇双音节化比较成熟的时期。
汉语词汇中双音节化最明显的是名词,大量双音节名词的出现直接影响了名词短语的音律,导致了个体量词的增加。也就是说,当名词是单音节词时,数词和名词构成双音节化韵律,如“三人”“五事”。当名词是双音词时,由于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数词大多是单音节的基数词,在数词之后需要一个量词来构成双音节化的韵律,然后再与双音节的名词构成双音节化韵律,如“紫芝一株”“石穴二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量词绝大多数是单音节词。
蒋颖对汉藏语系其他语言中量词使用情况的研究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双音节化对量词产生的影响。如景颇语十以内的基数词大多是双音节的,可以和双音节的名词组合成双音节韵律,因此景颇语在计量离散事物时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不使用量词,而且景颇语中的双音节名量词在整个名量词体系中所占比例较大,占到49%,这与汉语中只有少数几个双音节量词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而哈尼语的数词都是单音节的,所以数词在句法中不能单独使用,必须与单音节的量词组合成双音节结构后才能使用。
因此,个体量词是由于“名词+数词+非个体量词”的类推作用而产生,并由于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促动而大量增加。魏晋南北朝双音节名词的大量出现和量词在这一时期的空前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不是像叶桂郴假设的那样,是两个平行发展的结果。另外,叶桂郴认为魏晋个体量词大量产生是由于表形的需要,这种观点与本文观点相左。如果真是出于表形的需要,那么通用量词“枚”的广泛使用就无法解释了。因为“枚”原指树干,量词原用于指称树木,汉代时量词用法扩展到“木器”,魏晋时“枚”的抽象度更高,原有的表形功能消失,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展,可以用于夜明珠、剑、澡盆、金钗等物,也可以用于鸟、鱼等生物,可以说,除了抽象名词和个别事物,“枚”的量词作用对离散事物而言几乎是无所不能了。如果个体量词的出现真是出于表形的需要,那么为什么最不表形的“枚”反而成了最通用的量词呢?只有像本文认为的那样,由于语法结构的类推和双音化的需要,“名词+数词+个体量词”中原本可有可无的个体量词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填补这个空缺,“枚”被广泛应用于那些暂时还没有获得量词的事物,或应用于那些事物外形特征明确,不会产生歧义的语境中。
四、结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回顾了汉语名量词的起源与发展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名量词产生的机制。通过与其他语言的比较分析,认为汉语非个体量词的产生是出于计数的需要,有认知上的必然性。而个体量词是汉藏语言中特有的一类量词,其出现是“名词+数词+非个体量词”结构的类推作用,且汉语双音节化的趋势也是个体量词大量产生的促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