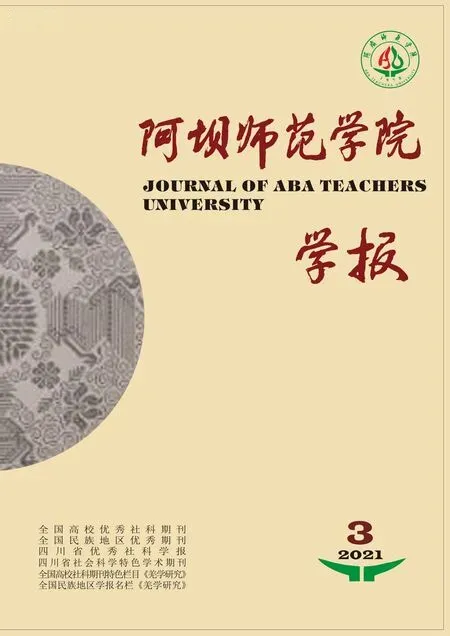唐传奇叙梦文本叙事空间的结构形态与审美特征探析
吴玲玲,杨 宏
叙事作为时间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叙事空间之中进行。在小说叙事中,叙事的空间性决定了叙事时间延展的范围与长度,并由此决定小说叙事的风格与审美特征。叙梦文本从史传记载开始,经六朝志人志怪小说发展,至唐传奇趋于成熟。梦在唐传奇叙事中,不仅是重要的文学意象,更是重要的叙事空间创设的叙述技巧。在叙事空间的建构上,唐传奇叙梦文本通过梦与现实的结合,在虚实变幻间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尝试多维度多层次的空间创作,形成了多种形态的梦境叙事空间结构,且梦境叙事空间在空间的主体性、细节化、生活化上都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
一、唐传奇叙梦文本叙事研究回顾与文本梳理
(一)研究回顾
唐传奇的文体特征与叙事特征,一直都是研究者的关注点之一。1990年、1991年,董乃斌分别发表了《从史的政事纪要式到小说的生活细节化——论唐传奇与小说文体的独立》《叙事方式和结构的新变——二论唐传奇与小说文体的独立》,这两篇论文可视为有意使用叙事学方法对唐传奇文体特征进行研究的始端,也大体上奠定了从经典叙事学对唐传奇叙事进行研究的路径,包括对叙事模式、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逻辑,叙事话语等的研究。此外,还有大量从后经典叙事学视野对唐传奇叙事的意识形态、历史文化语境、叙事意象、人物形象等进行专门讨论的论著。唐传奇叙梦文本是唐传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叙事研究基本上是遵循唐传奇叙事研究的经典与后经典叙事学研究路径。如高飞燕《唐代写梦小说叙事研究》从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三个角度分析了唐代写梦小说的叙事模式;《试论唐传奇梦幻小说的叙事视角》对唐传奇梦幻小说中的四种叙事视野进行了分析;卢笑涵《唐代涉梦小说研究》分析了唐代涉梦小说的内容、梦的叙事功能、主旨变化,并对唐代涉梦小说在创作态度、艺术体现、诗意等方面出现的新特征进行了探讨。
总体而言,当前叙梦文本叙事研究主要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唐传奇叙梦文本的叙事研究是唐传奇叙事研究发展到2000年左右对研究对象开始细分后的产物。在唐传奇整体叙事研究框架的遮蔽下,针对叙梦文本叙事特征的研究不够深入,未能突显其作为一个独特叙事主题类型的叙事特性。第二,无论是对唐传奇总体的研究,还是对叙梦文本的研究,都缺乏对叙事空间的关照。在部分论作中,如《裴刑<传奇>叙事研究》对叙事空间有所涉及,但不过数语概之。第三,研究对象不明确,对梦境文本未作涉梦、梦幻、叙梦之别,往往统指所有涉及到梦境的文本。因此,廓清研究对象,从空间叙事学的角度对唐代叙梦文本的叙事空间结构与审美特征进行探讨,可以使我们通过主题类型研究的方式,更深入地了解唐传奇叙事形态的多样性及其对后世叙事文学的多维度影响。
(二)研究对象:叙梦文本
依据梦境叙事在文本叙事中所占地位,涉及到梦境的唐传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以梦境为情节的涉梦文本。唐传奇叙梦文本中的梦境情节,或为设置悬念,或为下文埋下伏笔,或为推进情节转化等。此类文本如《郭仁表》《侯生》《娄师德》《五明道士》等,文本形态短小,情节简单、叙事直白,主要为宗教设梦或是为预言因果设梦。优秀的文本如《谢小娥》《尼妙寂》《霍小玉》《灵应传》等,梦境叙事在情节表现的曲折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表现出了较为成熟的技巧。以《离魂记》《崔护》《韦隐》《东洛张生》《徵异》等为代表的梦游文本,其入梦情节主要是为了营造梦魂牵萦、凄美含蓄的故事氛围。在这一类文本中,梦境是情节序列的组成部分,是故事的构成部分,但不是文本的主要表现对象。
第二类是以梦境为故事的叙梦文本。梦境是文本的主要叙事对象。故事是一系列情节有头有尾的组合,叙梦文本通过创设一个或多个梦境空间,在梦境空间中推动系列情节的展开与人物塑造。此类文本是本文主要的考查对象。这一类较为优秀的文本包括《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樱桃青衣》《张佑》《薛伟》《周秦行纪》《异梦录》《秦梦记》《齐推女》《独孤遐叔》《三梦记》《徐玄之》等。
二、唐传奇叙梦文本叙事空间的结构形态
史纪与志人志怪的叙事,偏于从线性时间对事件发生序列进行平辅直叙。至唐传奇,小说作者开始着意建构叙事空间,并借助空间结构技巧,为情节的曲折丰富创造足够的文本容量。唐传奇叙梦文本以“梦境”为主要叙事空间,通过梦与现实的结合,大体形成了三类叙事空间结构。
(一)环状式空间结构
环状式空间结构是唐传奇叙梦文本中最为常见的空间结构形态,直接沿袭自史传纪梦和志人志怪小说叙梦的线性叙事结构;以从醒到入梦到梦醒为基本叙事线索,文本结构呈现为现实空间——梦境空间——现实空间。其梦境空间类似于莱辛所说的“天才的世界”,即“把现实世界的各部分加以改变、替换、缩小、扩大,由此造成一个自己的整体,以表达他自己的意图。”以《枕中纪》《南柯太守传》《秦梦记》《樱桃青衣》等为代表,主要人物因机缘入梦,在刹那间的梦境空间中完成漫长的人生经历,再梦醒。梦境空间与现实空间既边界分明,又相互联结成一个结构完整的故事。
环状式梦境空间叙事既是整个文本故事的主要情节构成部分,也可以自成整体,以一系列的梦境情节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枕中记》中卢生因吕翁的瓷枕入梦,在梦境中经历的一系列情节:娶清河崔氏女——举进士——连迁升至陕州牧——兴修水利,百姓刻石纪其德——迁京兆尹——边境立功,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被流言中伤,贬做端州刺史——升任宰相,被誉为贤相——被诬下放,流放?州——复召为中书令,封为燕国公——一生政绩品德获皇帝的认可,八十因病而故,五子皆为高官。整个梦境叙述以时间顺序为主进行,辅之以卢生入狱后对入仕之前生活的追述,以及在去世前上表皇帝时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叙梦空间中发生的一系列情节组成了一个完整自足的故事。
梦境空间在保持自我完整性的同时,也与现实时空保持着结构上的紧密联结。联结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梦境空间独立梦境时间,使梦境时间暂时脱离现实时间序列,完成叙事后再与现实空间的叙事时间契合,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卢生梦中八十年,梦外黄梁米饭未熟;淳于棼梦中沉浮荣辱一生,梦外友人尚在濯足;卢子梦中二十年,梦外不过一上午。在时间的独立体验中,“士子”们由此感悟功利荣华不过一场梦。二是通过验梦,把梦境空间与现实空间结为一体。身为游侠之士的淳于棼,在梦醒后与友人验梦,梦中的“槐安国”和“檀萝国”竟都是槐树下的蚁穴,梦中情境历历如现。这种目之所触的震撼更甚于单纯的梦境体验,其感悟也随着叙事空间的转化与交错逐渐加深,由刚出梦时“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的感念嗟叹,上升至人生理念的改弦更张。梦境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交错,既增加了文本叙事的真实感,拓展了叙事情节展开的空间,也保证了整个文本结构上的完整性。
(二)“幻中生幻”式空间结构
“幻中生幻”式叙事空间结构指通过虚幻的叙事空间依次再幻创空间,直到完成一个具有多层性的复杂幻化空间,其情形类似于“中国套盒”叙事结构。“中国套盒”指一种故事里套故事,大故事中套一个中故事,中故事中套一个小故事的小说结构方式。最早使用“中国套盒”结构进行分层叙事创作的文本,为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所载的“阳羡书生”。阳羡许彦遇一书生以脚痛求寄鹅笼,至一树下休息时,书生吐出器皿饭食、女人;书生醉卧,女人吐出男人共饮;书生欲觉时,女人吐出锦行障遮书生,并与书生同睡;男人再另吐一女人。“阳羡书生”口中依次吞吐创设的是一个奇异的多次分层叙述,在许彦作为参与者与旁观者的限知视角下,叙述者依次出现:书生——女人——男人。“中国套盒”叙述结构会产生叙述分层,文本在不同的叙述层次上有不同的叙述者,“上一个叙述层次的任务是为下一个层次提供叙述者或叙述框架”。但作为空间结构形式,不一定产生叙述分层,同一个叙述者穿行于不同的叙事空间完成同一层次的叙事。为避免概念使用上的分歧与混淆,因梦境本就是幻构的空间,所以本文采用“幻中生幻”进行命名。
阿什河是松花江的一级支流。近年来,由于东北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工业废水、沿岸村镇生活污水处理率低下及农业面源污染强度大等因素的影响,已使得阿什河沿岸面目全非,流域水质长期处于Ⅴ类或劣Ⅴ类状态。人类活动导致阿什河流域天然的岸边缓冲带受到严重破坏,缓冲带断带严重、面积减少、净化功能减弱或丧失,引发流域生境多样性退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流域的生态安全。因此,针对阿什河流域岸边缓冲带现状,对流域缓冲带分布格局和特征进行分析,以提高缓冲带污染物截留能力为目标,进行缓冲带宽度的合理优化,对于阿什河流域缓冲带的综合规划管理、流域岸边污染阻断及流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幻中生幻”的空间结构形态,以《张佐》《徐玄之》《薛伟》为代表。《张佐》中,张佐少年居于雩杜时,认识了一位生于宇文周时的扶风人申宗,申宗向张佐讲述了他的前身梓潼薛君胄的梦境际遇。薛君胄的梦境幻中生幻,虚实相交,共创设有四个叙事空间层次。第一层:酒酣处闻两耳中有车马,进入梦境;第二层:两位二三寸长的童子驾车从薛君胄耳中出来,进入第一层梦境,与其交谈,并邀请其前往兜玄国;第三层:从童子耳中进入兜玄国,并在兜玄国中完成主体叙事;第四层:虚实相接,薛君胄因思乡而驰逐,从童子耳中掉落回现实空间。在层层相套的叙事空间中,不同的梦境空间层次间以及梦境空间及现实空间之间,可以相互穿越。
《徐玄之》中则是幻中生境,境中生梦,梦中生梦的结构。徐玄之未入梦之前,现实空间幻化成梦境,入梦之后,又梦中生梦,并通过占梦得以脱罪出梦,回到现实空间。《薛伟》中,把叙梦与人畜变相结合,创设了另一种“幻中生幻”的叙事空间。薛伟因病入梦为第一层;梦中因被美景所吸引变幻为红鲤鱼,进入水中世界为第二层;红鲤鱼被钓,薛伟以鱼身所历之空间为第三层;鱼被杀之际,薛伟梦醒,为第四层。薛伟梦中变幻为鱼之经历,在现实叙事空间中真实存在,且与被钓之鱼的经历完全重合。整个梦境叙事的进行,与现实空间叙事平行进行并相互影响。
(三)连缀式空间结构
连缀式空间结构指创设两个及以上的平行梦境叙事空间,各梦境呈现为相对独立的空间结构,又通过一个内在的叙事理念,把平行的空间连缀为一个叙事整体。在各自独立的平行梦境中,人物可以从现实空间进入他人梦境,也可以相互进入他人的梦境,并干预梦境的叙事发展。此类叙事空间结构源于史纪同梦记载,如《左传》中晋侯公与侍从同梦,行献子与梗阳之巫皋同梦。六朝志梦沿袭了这一构思,如《搜神记》(卷十)之“谢郭同梦”。直至六朝,同梦结构叙事都情节简单,以表现梦之灵验为主题,缺乏为叙事而设境的叙事冲动。
至唐传奇,同梦结构在叙事上开始变得相对复杂,不仅同梦,还可以进入他人梦境。《独孤遐叔》中,书生独孤遐叔在归途中宿于佛堂,“遇到”妻子形容憔悴被人调笑,被迫为人弹乐。遐叔惊愤不已,“扪一大砖,向坐飞击。砖才落地,悄然一无所有。”回家后才知道自己进入的是妻子的梦境,妻子在梦中与姑妹夜间郊游赏月,被凶恶之辈所挟持饮酒,有大砖飞来才从梦魇中醒来。独孤遐叔进入妻子的梦境,妻子进入她自己的梦境,两者在时间上并行,在事件上相互影响;从叙事空间结构而言,虽然在叙述上偏于前者,但依旧是同梦结构。
至沈亚之的《异梦录》和白行简的《三梦记》,同梦结构发展为连缀式空间结构。《异梦录》中叙述了两个互相不干涉的梦境。在陇西公幕府的宴会上,陇西公讲述了第一个梦:将帅子邢凤在一处古宅入梦,梦中与一曼妙古装美人相遇,并抄录美人诗集中诗作,醒后诗作尤在襟袖之中;第二个梦:宴会第二天姚合讲述了其友王炎梦游吴国,并在梦中作诗悼念西施。单就此两个梦境叙述而言,叙述技巧与叙述艺术都没有特别之处。但组合成一文之后,文本在叙事空间的建构上便表现出了其创设性。一是用同一个大叙事的场景——宴会,把两个独立的叙梦空间组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空间中创设空间的立体感;二是用宴会宾客述梦、沈亚之记梦这一线索,把两个独立的叙事连缀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连缀式空间结构形态。
《三梦记》记载了三个同梦结构的故事。第一梦:刘幽求奉命出使,夜归途中进入并干预了妻子的梦境;第二梦:白居易、白行简等游曲江,元稹在梁州梦见其事并寄诗纪梦,日期与游寺题诗一样;第三梦:窦质与赵姓女巫在华岩祠同梦并在梦中相会,后在华岩祠两人相互验求,两个梦境自始自终相互契合。全文以“异梦记载”为线索,把三个独立的叙事空间连缀成一个叙事整体。文本首句总起,点出全文统一的叙事宗旨,“人之梦,异于常者有之:或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或两相通梦者。”在每个梦境叙事之后,再以“盖所谓”重复首句相应的内容,并对故事作出评价。最后以“行简曰”呼应首句,说明了“存录”三梦的原因。在连缀式空间结构中,梦境叙事时间与现实时间平行,梦境叙事空间与现实空间深度互嵌,甚至边界全消。
三、唐传奇叙梦文本叙事空间的审美特征
小说的叙事空间建构处理的是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马振方认为,小说在“关乎它与现实世界的艺术关系”中具有三个特点:第一,“用语言创造世界,即以抽象的人为符号创造既非直观又充分具象的人生楼阁”;第二,“能摹写任何形态的人生幻象,从而得以广泛、细致地表现人与人生;第三,“内容高度生活化”。这既是小说应具有的三个特点,也是我们在考察某一类型小说文本的叙事空间所具有的独特性时应考虑的三个方面。相较于史传的实录、志人志怪的简单记载,以及其它非叙梦的唐传奇文本,唐传奇叙梦文本的叙事空间,在空间的主体性表达、空间描写的细节化、空间内容的生活化上,都表现出独特的审美特征。
(一)叙事空间的主体性
“小说结构说到底是作者心目中现实世界存在与运动方式的文学显现,它体现的是带有作者个人特征的人类对世界构造的一般理解。”唐代宗教文化繁荣,尤其是佛道两家。唐传奇作者对复杂时空的把握和对叙梦文本在空间结构形态上的创设,深受佛道融合思维的影响。一是空间创设思维深受佛道两教影响,依据叙事表述的需要,文本作者可以创设大小、数量随需变幻的梦境叙事空间;二是依据叙事时空架构需要而采用大量佛道的空间意象与事件。但通过梦与现实之间张驰有道的联结,叙梦文本对创作者主体性的表达,已远远超越佛道小说的宗教劝诫冲动与物鬼神怪的神秘主义。
《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樱桃青衣》这三个情节高度相似的叙事文本中,梦境空间中所叙之意象与事件,既是士人阶层的欲望体现,也是其对社会现实的体认,尽管在文本结束时都从佛道的角度表达了功名利禄终为空的感慨,但这只能视为士人对现实的不满与无奈,是一种的心理慰藉。《三梦记》中,第一梦描述刘幽求与妻子的夫妻之情,第二梦讲述元稹与白居易、白行简之间的深厚友谊,第三梦指向一段新的人际交往当始于心灵的相通。《秦梦记》中沈亚之梦回秦朝,体现的是士人遭遇穷困时对爱情艳遇与驰骋才华的向往。《异梦录》描述的士人在宴会上觥筹交错之时的风雅趣味,每个梦中都能看到真实的日常的人和人的活动。到晚唐时期的《徐玄之》,则彻底放弃了对佛道宗教意象的使用,直接把入梦前所见之幻境、入梦之后所见之梦境与社会现实一一对应,表现出了创作者对晚唐社会现实的隐喻与批判。
唐传奇的叙梦文本多由士人创作,文本中的人物也以士人为主,其叙事空间创设的“人生楼阁”表现的是士人阶层所想象的世界与人生,反映的是他们的追求、欲望以及他们忧患得失的情感体验,表达的是士人阶层的主体性。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主体性倾向,使得叙梦文本在后世叙事文学作品中被反复改编。
(二)叙梦空间描写的细节化与个性化
叙事空间的主体性需要通过空间细节描写来表达。唐传奇叙梦文本通过空间的细节描写,赋予不同的梦境空间以个性,进而通过个性化的空间展示曲折的情节和立体的人物性格。叙梦文本空间的结构形态,也为描写的细节化提供了必要的文本空间。
《三梦记》中,刘幽求“闻寺中歌笑欢洽。寺垣短缺,尽得睹其中。刘俯身窥之,见十数人,儿女杂坐,罗列盘馔,环绕之而共食。见其妻在坐中语笑。”虽然还只是白描,但与魏晋“郭谢同梦”的概述相较而言,空间描写已能承担起一定的叙事环境的功能,为刘幽求因为忌妒忿恨而“愕然”的心理变化和以瓦击之的行为提供了合理解释。《独孤遐叔》的写作时间略晚于《三梦记》,篇幅更长,空间细节描写也更丰富。在独孤遐叔进入佛堂之前,通过“斜径疾行”“人畜既殆”“天已暝”营造出远行失意之人归家心急、悲伤焦虑的空间氛围。及进入佛堂,“月色如昼”,佛堂中“有桃杏十余株”,由室外进入室内,荒郊之外的悲伤焦虑稍减,可安卧于西窗之下在思乡中等待天明。这些空间细节上的描写,再加上开篇对独孤遐叔落第与出游的交待,与刘幽求梦相比,叙事空间更为具体形象,活动于其间的人物形象也更为鲜明。进入妻子梦中之后,进一步通过独孤遐叔的位移,于窗窥视,于梁上府视,于暗处近观,从不同的角度展示梦境空间细节。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独孤遐叔妻。其妻的形象随着独孤遐叔的位移,由“忧伤摧悴”,到“冤抑悲愁”,到“收泣而歌”以致“诸女郎转面挥涕”。相比刘幽求妻,独孤遐叔妻更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个性有情感的小说人物。把刘幽求入梦单篇与独孤遐叔入梦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到传奇文体从奇事记载向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发展。
以《酉阳杂俎》中篇幅相对较长的“柳瞡知举年”(《酉阳杂俎·续集·卷一·支诺皋·上》)一条为例。《酉阳杂俎》在记载此事时,篇幅主要用于按时间序列记载事件的发生过程。为增加记载的真实感,甚至叙述了店里猜测客人不吃毕罗是因为不喜欢蒜味的细节。但其对梦境空间的描写,仅“相其榻器,皆如梦中”一语。与传奇二文相比较,其空间叙事,既没有整体空间的介绍描述,也没有局部空间的细节刻画,叙事空间缺乏小说必要的个性化,无法展现情节的曲折、人物心理的变化和人物性格的特征。《酉阳杂俎》与二文的成文时间接近,作者的才情亦大体相当,其在空间细节描述上的差距,主要原因当是作者因传奇与志异写作目标的差异而刻意为之。叙梦文本对空间的细节化与个性化的刻画,也为后世文学的反复改写叙梦文本提供了素材与想象空间。
(三)叙事空间中场景选择与人物心理塑造的生活化
叙梦文本的叙事空间,与仙界、冥界、妖界、鬼界等同为幻境的叙事空间相比,尽管情节设定一样具有奇幻性,但在场景选择与人物心理塑造上则更生活化,符合文本人物的身份、性格与经历。刘幽求与独孤遐叔归家途中的荒寺、黄梁一梦卢生的邸舍、樱桃青衣卢生的精舍等,是唐代士人游历在外常用的借宿空间;淳于棼与群豪醉饮的槐树下,醉卧的客堂东面廊檐,彰显的是其游侠嗜酒使气的性格特征;《异梦录》中宾客宴乐的庭院,是对唐人日常宴饮场景的再现。《徐玄之》中,在徐玄之进入梦境之前,提供了两个叙事空间:徐玄之从浙江东部迁到了吴地所居的宅院,宅院虽有不吉利的记载,但有珍奇花草且价格便宜;徐玄之在书房所见的幻境,幻境与他的书房空间完全重合。宅院和书房是士人的居家生活空间,在这样生活化空间的渲染下,徐玄之清贫、不惧鬼神的宦游文人形象就得以体现,梦境与现实政治社会的映证有了合理的联系。
浦安迪在论述中西古典小说家对空间选择的偏爱时说:“庄园领地、狩猎公园、荒野、大战场,还有田园凉亭,是欧洲小说虚构世界中现实活质地,古典中国小说则流连于客栈酒店林立的通途、隐蔽的寺庙、僧道的静修所、外省的衙门,这些处所同样具备再现真实生活的功能……就更加私密范围的生活空间而言……中国则更多借助一个带有封闭性的花园或书斋的四合家庭,这些场所往往用来提喻主要人物所生存的‘世界’”。尽管浦安迪论述的对象是以明清章回小说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但不难看出,对空间物象选择的生活化偏爱,在小说文体成熟之初便已确立了。几乎所有叙梦文本,无论其以何种奇幻的方式进入梦中,人物在梦境中所历之空间,于空间中所历之事件,都是对当时唐代士人生活的表现。也正因为如此,人物在梦境中的经历,才能真实地带给他们慰藉、补偿,并由而产生对现实的反思。
叙事空间的生活化,不仅在于空间物象选择与空间事件选择的生活化,还在于活动于空间中的人物心理塑造的生活化。叙事空间,尤其是近于幻境的梦境空间能否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人物的一系列行动,是否有其合理的心理动因,是否符合读者的日常逻辑与情感体验。《枕中记》故事原型出于《搜神记》中的《杨林》。《杨林》重在叙述人物的行动,以及行动序列之间的时间先后关系。《枕中记》在《杨林》简单的事件序列上,进行了生动而曲折的情节描写,卢生的心理变化也获得了一定的表现。卢生从梦中追悔“何苦求禄”,到梦醒后人生不过“黄粱一梦”的认知,再到窒欲、破我执的感悟,是一个渐变的心理变化过程,其中有着合理的叙事心理机制。《独孤遐叔》开篇的归家约期,是人物心理变化产生的根本原因。独孤遐叔出游之前与其妻约定“迟可周岁归”,因出行不利两年有余后才归家。在古代交通不便、远行充满风险的情形下,逾期一年余未归,夫妻双方都有可能发生各种变故。所以孤独遐叔不仅思乡也“近家心转切,不敢问来人”,见妻列于宴会之初的“大惊”之中,有意料相遇之惊亦有对情感可能变故之惊。正因为这一细节在心理塑造与情节推动上具有的强大的叙事动力,冯梦龙《喻世明言》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便直接借用这个“约期未归”的情节。
《薛伟》中,以第一人称视角,对薛伟幻化为鱼后的心理有适量且合理的描写。薛伟因病恶热求凉而离家。最初,“既出郭,其心欣欣然”;接着因景而“忽有思浴意”,“遇此纵适,实契宿心”;幻化为鱼后,随心所欲从容游玩,但每晚仍谨守规则;饥饿的驱使下,几番犹豫,心想自己是官人,纵使吞了饵料,钓鱼人赵干也一定会送自己回县里;之后历经“张弼之提、县吏之弈、三君之临阶、王士良之将杀”,薛伟也由跟张弼讲理,对县吏大叫,变为对三君大叫而泣,对王士良大叫,薛伟在生死之际的心理紧张程度逐层推进,其见同僚时的悲泣,更有一层物不能伤其类的深刻悲哀在其中。当鱼头适落,薛伟梦醒之际,情节的紧张得到释放,薛伟人物形象也在动态的心理刻画中完成塑造。卢生、独孤遐叔、薛伟等的形象虽还不够丰满,但其心理的发展变化、人物的认知变化,及由此而体现出的人物性格上的个性化,一定程度上已具备了现代小说中“圆形人物”的特征。
唐传奇叙梦文本的叙事空间,既源自于史纪与六朝小说已有的空间叙事结构,又深受唐人包括宗教观念在内的“所体验到的人间经验和人间哲学”的影响,加之梦境叙述本身所具有空间性与幻化性,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叙事空间结构形态。唐传奇叙梦文本作者在叙事空间结构与叙述技巧上的探索,也让本近于幻境的梦境空间超越了宗教意识与神秘主义,表达了唐代士人阶层的主体性。在具有细节刻画的叙事空间中,通过生活化的空间设置和对人物符合生活逻辑的心理刻画,小说人物从情节推动的行动者成为具有一定个性的人。当然,作为小说文体成熟初期的作品,唐传奇叙梦文本的叙事空间还存在着不成熟的方面,但通过对唐传奇叙梦文本叙事空间结构形态与审美特征的探析,不仅能进一步了解中国小说文体在发展过程中叙事空间的演化发展,而且能进一步把握唐传奇叙梦文本对后世叙事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