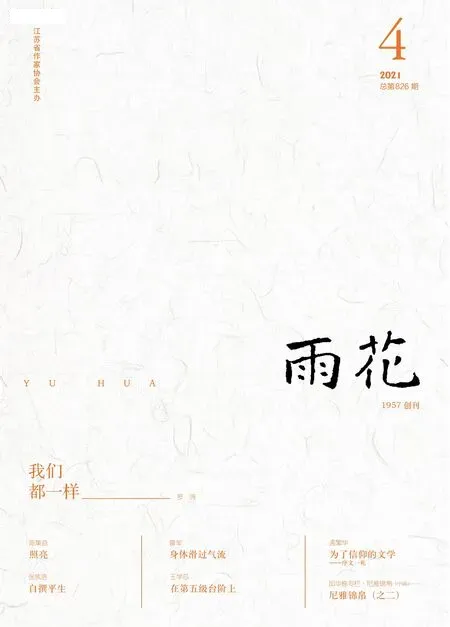危险的证据
1
我看谁都像个凶手。
我最近感觉很不好,每一个毛孔都像装上了警报器,哪怕是风吹草动,都会拉响警报。事情都过去一周了,我吃不香,睡不好,只要一闭上眼睛,脑子就如一台停不下来的放影机,反复地播放同一个画面,尽管那个画面在我脑子里已经播放了不下一百次。原本不过几分钟的画面,被我一次又一次地拉长,长成了慢动作,无休止地循环播放。我一次又一次地钻进去,只为寻找任何可能存在的蛛丝马迹。我研究了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有作案工具,这些在我无数次绞尽脑汁的回想中仿佛都有迹可寻。唯一令我头疼的是,我看不清作案之人,甚至不知道他是怎样的身材体型。他是那么的清晰,又是那么的模糊。我仿佛是被影子给捅了一刀,但撕心裂肺的痛感甚至比我以往受到的任何伤害都要真切。我无数次竭尽全力去回想那个影子,然而我只能判断出他是个男的。他的动作干净利落,熟练而果断。我能感受到他强悍的气息,那是一个人在邪恶之时散发出来的特殊气场,一如我在宰杀家禽时的决绝与毫不退缩。当然,不可否认,我还有一点点的自我厌恶,这种厌恶不是来自死亡与血腥,而是我隐隐产生的一种痛快感,一种莫名其妙的可耻的痛快感。
其实,关于这一刀,我实在是有点儿难以启齿。我甚至不能对任何人说起,因为它还没有成为现实,所有的谋杀不过是在梦中进行罢了。荒唐!的确是荒唐。我敢打赌听的人一定会嗤之以鼻,或者取笑我是个神经病。但我想为自己争辩一下,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即将变成现实,对此我深信不疑。我一直坚信自己有着某种特殊本领,就是我梦见了一些人或事,不久的将来,这些人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或这些事情会发生。但到底是先有了梦才有了现实,还是先有了现实才出现了梦,我一直想不明白。
对于这个现象我无法解释,而对于自己这个奇怪的能力我也颇感惊讶。为此,我咨询过一个奇人异士。他的回答有点儿玄,他说我前世中的某一世是有灵识之人,所以潜意识里保留了某种直觉,那属于第六识的范畴。他说可以把它理解为执念,一开始就像一个孔,放得开只是微澜,放不开就会变成心尖上的刺,心头上的大山。我现在就感觉被刺刺着,被大山压着。虽然朋友说的话我听不太懂,但我一直觉得我与别人有点儿不一样。有时,我盯着计算机,觉得人的每一世就像里面的合成效果,累世的因果像碎片,在合适的机缘下,匹配的碎片就组成了这辈子的人生。我承认自己属于敏感体质之人,“梦想成真”是绝对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梦想成真”?是谁发明的这词!我恨不能把我所有的“梦想”都他妈的摁死在摇篮里。
不管怎样,我想我该行动起来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首先,我必须得找出“凶手”。我把认识的人都在脑子里拉出来遛了一圈,从小学同学到只握过一次手叫不上名字的人,细细地撸了一遍。我在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下了认识他们的时间、地点,一起做过的事情,与他们关系的好坏。包括我前女友的现任男友,一些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我都一一地罗列了出来。看着被我写得满满当当的本子,我哭笑不得,难以置信在我短短的二十九年的生命里,竟然认识了这么多人。最后,在分析了各种可能性后,我把目标缩小到自己所生活的城市,且是三个月内接触过的人,特别是和我有利益关系的人。这么一推算,名单就呼之欲出了——徐浩,林小汉,孙万磊。
为了更好地找出凶手,我想安排一次聚会,除了徐浩、林小汉和孙万磊外,还有两个女的——铃子和小舞,都是俱乐部会员,大家彼此熟悉,熟悉到我不确定她俩是否和这仨男的有过亲密关系。当然了,她俩和我曾经有过超友谊关系。我特地叫上她俩,一是因为她俩能调节气氛,二是更能激发出某些微妙的东西来。
2
我把聚会时间定在晚上十一点,地点就在我的俱乐部里。那会儿,俱乐部刚打烊,徐浩在整理各种器具绳索。他近来有点儿沉默,偶尔会长时间发愣,有一次我喊他几声他也没听见,实在是有点儿反常。徐浩是我的合伙人,最近因为店里的事,我和他意见不合,发生过一些争执。
半年来,附近陆续开了三家攀岩俱乐部,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我们的客人被抢走了不少,这几个月几乎是负赢利。之前投入的几十万装修费还没赚回来,现在还要面临窟窿越捅越大的局面。徐浩想把店给盘出去,说有一位女买家对攀岩特别热爱,想买下一家自己玩儿,还愿意出个让我们不亏本的价钱。这听着挺不错,现在愿意出大钱接手的冤大头实在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但我仍极力反对。我反对的理由是目前的状况只是暂时的,我们是老招牌了,待客人对新店的新鲜感一过,肯定会回来。其实我一点儿底气也没有,不过是为自己找了个勉强的理由罢了。
我无法想象,没有了俱乐部我还能干点儿什么。虽然以前我也在一家贸易公司干过,但当了几年老板后,再让我回到之前那种看别人眼色过活的日子,是绝对不可能了。俱乐部规模不大,客人总喊我一声“李总”,那多少让我感到酸爽。不像在公司打工的时候,就连比我年龄小的人,都“小李小李”地喊,然后不知从哪天开始,就变成了“小李子”,这让我有一种屈辱感。
开了攀岩俱乐部后,我腰板挺直了,走路都比以往拉风。再说了,我打骨子里喜爱这份工作。攀岩时,我经常不系保险带,我喜欢徒手与死神过招的感觉。我每一天都活在险境中,逐渐习惯了面对挑战,觉得自己因此变得异常地强大。我越来越能控制恐惧,恐惧有时不是坏事,它能令我在重要事情上保持清醒,清醒是我的一种人生态度。
在倶乐部里,只有我和徐浩敢挑战无保护攀岩,而徐浩似乎比我更能玩命,有些我不敢过的绳段,他敢。这难免让我感到沮丧。
珠帘隔断啪啪作响,林小汉和俩女的从洗浴间里走了出来。他们相处得极为愉快,有说有笑的。林小汉皮肤白净,留了个披肩中发,特柔顺那种,爱走猫步,如果不认真看,还以为走过来的是三个花枝招展的女人。林小汉最近老针对我,只要我说这样,他必反对我说那样,从不掩饰对我的讨厌。果然,才刚走近,他就下巴一抬,眼白一翻,鼻孔朝天地瞪了我一眼。如果说是个女人那样瞪我,倒还好,可偏是个男的。我的胳膊上起了一层细细的鸡皮疙瘩,有轻微的呕吐感,像去年在海上遭遇了风浪的不适。但这个节骨眼上我不能表现出来,我现在的处境和以往不同了,我有敌人了,一个想干掉我的敌人。不管林小汉是不是凶手,我必须得拉拢他。于是,我忍住排山倒海的呕吐感,对他讨好地笑了笑。他明显地怔了一下,有点儿意外我的突然转性。看起来,他愿意接受我的“浪子回头”,于是,对我回报了一个羞涩的笑容。
林小汉是我俱乐部的一个客人,从四年前开店那会儿到现在,许多客人来了又走,就他一直不离不弃。林小汉长了一双丹凤眼,喜欢斜眼看人,显得特别妩媚。以前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有一次,我前脚刚进了厕所,他后脚就跟了进来。那么多的尿兜,他偏选了我右边的那一个,丹凤眼还上上下下认真地瞟了我许多眼,我一哆嗦,尿就吓了回去。他却掩嘴扑哧一笑。靠,那种感觉,像吞了一只苍蝇,还是绿头的。那次后,他开始明目张胆地跟着我,在离我三米远的地方,明里暗里地瞟我。这都还能忍受,谁让顾客是咱上帝来着,而且还是铁杆顾客。用徐浩的话来说,就是得罪了俺老娘也不能得罪这位上帝。所以,我不但要忍,还要憋。他在俱乐部的时候我就憋着不上厕所,真憋不住了就偷偷摸摸地上,进了厕所就鬼鬼祟祟地关门。后来有一次,我在尿尿的时候,他在外面噼里啪啦地敲门,我突然就爆发了,管他娘的上不上帝。我“哗”地拉开门,冲他发了火。他一副受气媳妇的模样,用幽怨的眼神看着我,一声不吭。那次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哑巴,外加一个幽灵,时常冷不丁地从哪里冒出来,站在离我三米远的地方冷冷地盯着我。这让我觉得毛骨悚然。
凭我这些年冲锋情场的经验,要一个爱慕你的人不再仇恨你,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予他爱的希望。现在的林小汉,显然被我重新点燃了希望,他那热切兼羞涩的丹凤眼毫无疑问地出卖了他。我暗地里松了口气。
此时,大门处的铃铛一阵巨响,一个人推门而进。此人正是孙万磊。他穿身笔挺的白衬衫,西裤,衬衣领里塞着一块咖啡色丝巾。头发打了蜡,根根竖起。他一手揣兜里,一米八的挺拔个子向我们有型有款地走来。俩女人和他热烈地嗨了一声,他矜持地笑笑。坐下。袖子往上撸了一下,一块金灿灿的手表探了出来。
斗鸡!我脑子里猛地蹦出这俩字。当然了,这并非我首创,是徐浩说的。他说孙万磊自从来到俱乐部,就如一斗鸡,时刻把自己保持在最佳的作战状态。当然,他要斗的人是我,而他的武器就是他的一身名牌,还有他引以为傲的英俊脸孔和大长腿。
孙万磊是我前女友的现任男友,按道理他和我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可我偏被他赖上了。我和前女友因性格不合分了手,分手后近一年没联系过。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问我有空不,说想见个面。她说话的声音小且急,像做了什么亏心事。然后飞快地说了见面的时间地点就挂了电话,生怕被我拒绝似的。我当时还一阵乐,不会是她放归森林后仍然惦记着我这棵小树,想和我重温旧梦吧?虽然我对她不再像以前那么热乎,但我是一个能吃回头草的人,决不让前女友失望也是我的人生宗旨之一。
我于是屁癫屁癫地赴了约。到了一看,靠,这演的是哪出戏呀?她的现任男友和男友的老娘竟然也在。她的现任男友,对,就那个孙万磊,穿得十分考究,连我此等俗人都看出了他穿着一身名牌。但裹在一堆名牌货里的那个男人,此刻正像只缩头乌龟一样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脸朝地面,双手肘支在膝盖上,十根手指插进头发里,每一次揉搓,腕上的手表就晃出一道亮光。我盯着他的手表看,猜想着是什么牌子。
忽然,那张脸抬了起来,那绝对是一张痛苦到扭曲泛青的脸。他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夹杂着浓重的鼻音,艰难地开了口。他说,我女朋友的第一次是不是你干的?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我看一眼他左边坐着的同样铁青着脸的老娘,再看一眼坐在他右边快要哭出来的前女友,使劲儿咽了一口口水,突然就深刻地领悟了他的意思。我有一种大义凛然的悲壮感,老子干了就干了,承认了又咋样?我鼻腔里喷出一股热浪,浑浊地“唔”了一声。他刚伸长的脖子旋即又缩了回去,脑袋耷拉得更低了,十个手指开始胡乱地抓起头皮来。我能听见“沙沙”的摩擦声,好几片白色的头皮屑从他的指缝里弹跳出来,落在了深蓝色的裤腿上。就在我默默地数着他裤腿上越来越多的头皮屑时,他又嗡声嗡气地开了口——
几分钟?
啥?我没听明白,下意识地反问了下。
我问你做了几分钟!他停止了抓头皮,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在心里“靠”了几声,想立马起身问侯他祖宗十八代,然后拍拍屁股走人。但我瞥见了前女友那哀求的眼神,她的泪水一触即发。我这人有个优点,就是看不得女人哭,一哭我就没了原则与骨气,于是胡乱编了个数字——四十分钟。孙万磊像被电击中了一样,猛地一哆嗦,然后飞快地向右转,瞪大眼睛看着我可怜的前女友,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质问她,你说才不到一分钟,你骗我,你说你压根没印象,你说你俩只做过一次,才一下就没了,就像是没做过一样,你说在你的记忆里你就像没和任何男人睡过一样清白。你说你说你说啊,是不是真的?
我看着眼前这个快要发疯的男人,极想哈哈大笑。但我还是没敢笑出声来,因为他老娘正把冷冰冰的眼神瞄准了我。我生怕笑出声来她会做出可怕的事情,比如拿个杯子向我砸来,因为我看见她一下握紧了杯子。我赶紧重重地咳嗽两声,转移了一下不合时宜的快活心情。然后我听见了她严肃而又沉重的拷问——到底是几分钟?她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从小没了爸,是我辛辛苦苦地把他拉扯大,他又乖又孝顺又优秀,他还没谈过女朋友,必须要一个清白的女孩才配得上他……
我突然就开了窍,立马脱口而出说可能是我记错了,可能也就三两分钟吧,第一次嘛,紧张,嘿嘿,嘿嘿……
我看见老太太和她儿子同时松了一口气,我前女友也松了一口气。我觉得自己给别人带来了快乐与希望,也跟着松了口气。接下来,气氛缓和了一点儿,他娘俩又陆续向我提了好几个细节问题,以证实我和前女友真的只是轻轻地接触了一下而己。说到后头,连我自己也觉得我和她好像什么都没干过一样。对,一定是这样的。我终于看见了孙万磊慢慢地露出了比较满意的表情。
我诅咒那几分钟,因为之后我发现,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只要和女友做那事就会想起孙万磊质问我做了几分钟,然后真的只有几分钟就结束了,像被诅咒了一样。这也就算了,从那天开始,他也来到了我的俱乐部。我不知他为何而来,但他每次出现都神气得不行。用徐浩的话来说,活像一只斗鸡,随时准备着向我展翅扑来与我一决胜负。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他有置我于死地的想法。
但我现在却不那样认为了。看见他一副精心打扮神气活现的样子,我反倒莫名地高兴起来。我知道他是来开屏的,怎能没有观众?他越作我就越觉得放心舒心,那一刻,我相信他一定希望我好好地活着,只有活着才能继续看他的精彩演出。我甚至想,如果没有了我这个观众,他将会是怎样失落啊。
3
人都到齐了,围着桌子坐了一溜圈。我的两边分别是铃子和小舞,铃子穿着紧身低胸露脐装,不时往我身上蹭。每次她贴过来,林小汉就使劲儿地咳嗽。铃子也不理睬,照蹭她的。徐浩自顾自地喝着啤酒,这小子最近总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林小汉一个晚上就忙着监视铃子与我,不时翻一个白眼儿。孙万磊双手抱胸,下巴微微抬高,与周围划清界线的样子。
关于聚会,我是有备而来的。为了谈论的话题更接近主题,我提前在俱乐部门口偷偷做了点儿手脚。果然,两杯啤酒下肚,小舞就把话题切入了我想要的方向。她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只看见两排毛绒绒的眼睫毛,脖子缩短,背部弓起,双手作爪子状,神神秘秘地说,看见了吗,门口有一只死猫。
铃子抢着说,我也看见了,就挂在树上,脑袋都扁了,估计是被车轮给碾死的。
林小汉说,呸!要我说,不定是哪个变态把它给活活砸死的,不然那身体好好的偏就脑袋扁了?
铃子揶揄他,你倒是观察得仔细。
林小汉翻了个白眼儿,哥的智商哪与你同一水平。
得,还哥——铃子掩嘴窃笑。
林小汉一跺脚,伸手去扭铃子的嘴。
孙万磊慢悠悠地开了口,他说,谋杀,绝对是谋杀。
小舞说,谁那么狠呀,下得了手?
你要恨一个人,就下得了手。孙万磊嘴里漫不经心地说着,眼睛却瞟向了我。
我当没看见,转身盯着铃子的胸。
小舞说,讲猫呢,怎么说到人去了。
这人与动物,其实一个理,要爱就有多爱,要恨,也就手起刀落的事儿。孙万磊一仰脖子喝完一杯啤酒,“啪”地把杯子搁在桌子上。
铃子说,那人的心和我们的心是不是不大一样?
林小汉尖声说,绝对是黑的,还用说。
那倒不一定,要我说,那人看着也就一普通人,扎人堆里谁也拎不出来,你看那电视里的变态杀手,通常都有三个特征。我故意卖起了关子,装作毫不在意地扫了大家一眼。
哪三个特征?林小汉和两个女人同时发问。
沉默寡言,感情受创,人模狗样。我搜肠刮肚地数了三点。
林小汉把身体微微地往前倾,挑了挑眉毛,压低了嗓门说,哎,你说,我们这里边,谁看着最有杀手范儿?
孙万磊咳嗽一声,把腰直了直,一只手揣兜里,摆了个死酷的姿势。可我在心里早看扁了他,真正的杀手是不会作秀的,就如武侠小说里的高手,不轻易出手,不多言一语,不动则已,一动致命。像孙万磊这种货色,雷声大雨点小。瞧第一次见面那怂样,我偏还怀疑他,真是抬举了他。
铃子把脸凑到徐浩鼻子跟前,装模作样地看了几下,“啧啧”几声,说,像!我觉得徐浩特像,那三个特征他都有。
小舞不以为然,人家感情受创你看见了呀?
铃子说,就凭我女人的直觉,他是我们这么些人里用情最深的一个,情嘛这玩意儿,一认真就害人。
徐浩耸耸肩,笑了一下,不置可否。
小舞看了我一眼,伸出食指指着我说,我觉得李庭才像。小舞是偏向徐浩的,俱乐部的人都知道她喜欢他。可她并不是徐浩喜欢的类型,而至于徐浩喜欢的是哪种类型的女人,我也说不准,因为从没人看见过他交女朋友。
铃子反驳,何以见得?
小舞说,因为他看着最不像,这才是杀手最高明的地方。
铃子拍着她的胸脯保证,李庭绝对当不了杀手,因为他多情,多情的男人大多心肠软,没原则,你看猪八戒打死过哪个妖怪?就只有被妖精整的份儿。
孙万磊像被谁狠狠地踩了一脚尾巴,一仰脖子倒入一杯啤酒,杯子重重地甩在桌面上。
大家当没看见,话题继续。
小舞说,徐浩,你别老装深沉,你倒来说说看。铃子也跟着起哄,让徐浩发表发表高见。
徐浩手里转动着空杯子,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下,说,优秀的杀手应该是代表正义的,不为利益,不为私人恩怨,不为泄愤。
小舞说,那为什么?
徐浩说,救人。
铃子率先哈哈大笑了起来,徐浩也笑了笑,但我发现他的笑有点儿意味深长。接下来,他做了一个动作,他的左手食指弓起,有一下没一下地用指甲弹着杯沿,杯子发出轻微的撞击声。我猛地一激灵,某个记忆被突然唤醒。我记得在梦里,听过这个声音。凶手把刀子刺向我之后,又拔了出来,我在倒地前,听见了某种特别的金属声,像是指甲弹击刀身发出的。
我一抬眼,徐浩也正看着我。
4
凌晨一点二十五分了,按以往的习惯,聚会将在凌晨两点前结束。我有点儿不甘心,虽然事情略有进展,但我想要更多的证据。于是,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我偷偷地打开铃子的背包,把镜子给藏了起来。铃子有个习惯,她每隔半个时辰,会照一下镜子。对于铃子来说,镜子就如她的另一张脸皮,不见了,那可是件大事。果然,铃子很快就发现镜子不见了。她大呼小叫了起来,说明明刚刚还在的,明明一直都在的,是我亲手放进去的,就在第二层的隔层里。小舞——小舞——,你也看见我照镜子了,对不对?小舞把头点得像鸡啄米一样。
为了把丢镜子事件上升到另一个高度,我假装喝高了,拍着脑袋分析起了案情。我说好好找,能去哪呢这是?这里又没小偷小摸的,再说了,不就一镜子嘛,谁会对那玩意儿感兴趣?如果说真有人给藏起来了,不是暗恋铃子就是个恋物狂。平白无故地不翼而飞,其中必有蹊跷。
大伙儿被我说得娱乐精神都上来了,一时间各种猜测。话题说到后头,就变成了这镜子肯定是我们中的一人给拿走了,而且是出于某种见不得人的动机。我极力附和,猛然一拍大腿,假装突如其来的兴致,提议玩一局杀人游戏,让杀手来决定谁是小偷。闭眼时,杀手把他认为最有可能藏起镜子的小偷给干掉,并在小偷面前放一枝红玫瑰。
一呼百应,游戏开始。
我选出六张牌,一张K 代表杀手,一张J 代表小偷,四张Q 代表平民,当众洗了,派给大家。我作了弊,不管我怎么洗牌,那张K 牌都在一个不变的序位,我故意把它发给了徐浩。反正也是玩儿,大家并没有过于留意我的一举一动。各自拿到牌后,笑嘻嘻地看了,倒扣在桌面上。游戏没有设置法官,只让铃子代法官依次宣布。
铃子大力咳嗽两声,缓缓说道——各位玩家,天黑请闭眼——
随着黑暗的到来,紧张也偷偷袭来。为了防止我的手颤抖露馅儿,我把它们揣进了衣兜,背轻轻地靠在了椅子上。
铃子接着念道——杀手请睁眼——
我感觉到了杀手锋利的眼光正看向我,他一定是在研究我。我的手在衣兜里拽得紧紧的,脚趾也使劲儿地弯曲卷缩起来。
铃子故作神秘的声音再次响起——杀手请杀人——
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画面猝不及防地再次出现——杀手拿起了桌面上的水果刀,慢慢地向我走来,他把刀子快速地捅进了我的身体。我想睁开眼睛,可怎么也睁不开。我的睫毛颤动了一下,一下,又一下,眼眶里储满泪水。我想我快要流下眼泪了,便更高地仰起头,装作犯困的样子,这样有助于眼泪回到安全的地方。天气凉薄,而我手里生生地渗出了汗水,腿也开始发抖。我只有拼命地夹紧双腿,不停地伸缩脚趾,以控制颤抖,不让其传遍全身。不过是几十秒的时间,我仿佛熬过了一个世纪。
就在我忍不住要爆发的时候,终于听见了铃子仿佛来自天堂的甜腻声音——天亮请睁眼——一阵妙不可言的兴奋感传来,只要我一睁眼,几乎就可以确定谁是凶手了。但我反倒不急了,我故意拖延了睁眼的时间,慢慢地揉了揉眼睛,像刚睡醒的样子,让自己恢复到了无辜的状态。但是,我很快便听见了铃子的一声尖叫,肩膀被重重一击,一阵浓郁的香水味闯入我的鼻腔,一具酥软的身体向我倾压了过来。
铃子撒娇的声音传来——我就知道是你,想我直说不就好了嘛,还偷偷藏了人家的东西,讨厌——
大家都看见了我眼前的红玫瑰,那意味着我被杀手干掉了。只有我知道事情的真相,那就是我被徐浩干掉了。我知道他是杀手,但他不知道我知道他是杀手,所以他肆无忌惮地干掉了我。他怎会知道我拿了铃子的镜子呢,难不成他一直在监视我?他为何要监视我?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对我另有所图。一定是那样。
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荤话中,我装作不胜酒力的样子,一把搂过铃子,当着他们的面,把脸埋在铃子的胸前。林小汉和小舞旋即发出了夸张的尖叫声,椅子被谁狠踢了一脚,然后有人朝门口走去,门被大力地关上。我的脑袋埋在铃子的胸脯里,呼吸有点儿困难,但并不妨碍我的听觉。铃子成了我一个很好的掩护,我慢慢地放松下来,尽情地释放了刚才的颤栗感,没人会怀疑一个淹没在女人胸脯里的男人的颤抖。我狠狠地磨蹭着铃子巍峨的胸脯,嘴里念叨着只有自己能听懂的话语——是徐浩是徐浩,要杀我的就是徐浩。不知是因为找到“真凶”而兴奋,还是铃子身体引起的反应,我飞快地把铃子拉到了里面的房间,尽管我觉得此举实在是混蛋之极。
5
我开始跟踪徐浩。
我跟了他两周,并把他的行踪详细地记录到了本子上。他喜欢晚上在俱乐部关门后,独自转悠到附近的瘦五宵夜店,点两瓶啤酒,一碟炒花甲,几串烤鱿鱼,一边喝一边玩手机,大约四十分钟后离开。有一次,他见了一个人,不得不引起我的重视。那人看着像电视里的黑老大,手臂和脖子都纹满了图案,还剃个光头,油光闪亮的,屋子里无端多了一盏低瓦灯泡似的。两个人聊了十几分钟,徐浩递给他一个信封,他捏了捏信封,也不说话,起身就走。出门后,两人一前一后朝西走,海关博物馆的方向。走了百把米,拐进一幢骑楼。门“哐”的一声被大力关上。我蹲在斜对面一幢骑楼阴暗的门槛上等,还抽了两根烟。约莫二十分钟后,徐浩出来了,手里多了一样东西——约一尺长,用报纸包着。烟灰落在我的手背上,也不觉得疼。
我猜想那一定是一把刀。
我还发现了徐浩一个秘密。他每周会去同一个地方两次,一般在上午,九点进门,十一点出来,非常准时。那是一幢独栋别墅,在我们小城最贵的一个楼盘里。那里的别墅至少也要卖五百多万一幢,但多是清水房,还没有人住。别墅三层半高,窗户通通拉上了窗帘,看不见里面的光景。院子里种着各种姿态的罗汉松,高的比我高,矮的也有一米。地面很干净,几乎看不到落叶和泥巴,想必是有专人打理。除开种树的地方,都种满了绿绿的草。中间有一条半米宽由鹅卵石铺成的小径,一直延伸向角落里的鱼池。有一次,我在外面瞎转悠时,觉得特无聊,就想溜进院子里看鱼。我翻开池面的水草,想看看这种富贵人家养的是什么品种的鱼。可鱼没找着,倒是看见了两只鳄鱼龟,正伸长脖子,冲我的手掌张大了嘴巴。我猛一缩手,差点儿没吼出声来。奶奶的,富人家连乌龟王八蛋都能欺负人!慢慢的,我和它混了个脸熟,其实也不算太熟,就是我用棍子去捅它的嘴,然后它很有默契地一次又一次张大了嘴巴。
在我第五次光顾别墅的时候,终于看见了一个女人。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上午十一点刚过,徐浩出来时,一个女人也跟着追了出来。女人穿件奶油色吊带睡裙,外面罩一件同色丝质披衫,能看见姣好的身材。女人的年龄接近三十,留着短发,很干练的样子。他们像是为什么事儿起了争执,徐浩紧锁眉头,想要离开。女人拦住他,不停地说着什么,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两人把嗓门压得极低,我听不清他们争论的内容,只见徐浩很警惕地左顾右盼,一个劲儿地把女人往屋里撵。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徐浩的女人,我不得不佩服那小子的眼光。女人与铃子小舞明显属于两种人,也不是说她有多漂亮,我甚至没看清她的五官。但她身上有一种高贵的气质,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哪怕你长得比她高,她仍然可以高高在上地俯视你。
徐浩离开后,女人并没有马上回屋,而是朝着我的方向,双手抱胸,下巴微微抬高,站了大约有一分钟,然后若有所思地一笑,转身离开。
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但我确定她没有看见我。
我听见大门被“砰”的一声关上后,才从假山后面走了出来。我抬头看一眼拉得严实的窗帘,猜测着女人与徐浩的关系。我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儿了解徐浩了,又好像不太了解。我仿佛找到了一个可攻击他的弱点,又不确定那是不是他的一个致命破绽。
事情发展到现在,我发现自己已处于两难的境地,我像故事里那个神经衰弱的老头儿,执着而又胆颤心惊地等待着另一只靴子的落地。我在主动防备与部署中等待那一刀的到来,多么荒唐。我也嘲笑过自己,或是说服自己放弃,但渐渐地,这变成了一个我不想放弃的游戏,我准备得越充分就越不想放弃。它逐渐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长成了我身体上的一个瘤,我甚至觉得生活因此多出了另一层含义与趣味。就仿佛在一场杀人游戏里,我是一个警察,聪明而充满了正义感。我知道谁是杀手,我不但要避免被杀手干掉,还要找出证据,让其他玩家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杀手。
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吓了我一跳,但我旋即开始为之而兴奋。我沿着小区的道路奔跑起来。也不知跑了多久,当我气喘吁吁地停下时,竟然又回到了女人的别墅跟前。我再一次想起那个女人,女人高不可攀的姿态,掩藏在丝质睡裙后面的高贵肉体,不知那个对徐浩屈服的肉体会不会对我傲慢?我身体的某个地方开始微微地膨胀起来。我在楼下来回徘徊,迫切地想干点儿什么。我几步窜到别墅的大门前,几乎是不经思索地按响了门铃。我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扑通扑通扑通”。在大门开启之前,我飞快地转身,撒腿奔跑。
6
又是一周。
上午九点整,徐浩再次走进了女人的别墅。我决定沿着外墙爬进去。对于一个攀岩者来说,那简直易如反掌。
我开始往上爬。
能踩的脚点很大很安全,但我爬得很慢。一个脚点我看了又看才敢踏上去,似乎它只有指甲一般大。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不像以往那么清醒,手脚像钝掉的机械,如初学者那么笨拙。我觉得现在的处境和无保护攀岩极为相似,仿佛自己选了一段并无多大把握的绳段,一个脚点就能决定生死,还有许多无法预计的情况随时可能出现,容不得半点儿闪失。因为性命攸关,我必须要做到绝对的专注。
终于到达了第三层。
我跳进了阳台。
门没锁,我轻轻地转动把手,走了进去。
屋里很黑,拉着厚重的窗帘,没有亮灯,没有人声。细听,我听见了微弱的呼吸声——不止一个人的。声音就在我的脚底不远处,正朝着我的方向蠕动。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像爬近的虫子。我使劲揉了两下眼睛,慢慢地适应了黑暗,顺着声音往下看去。底下的四壁皆是岩石,岩壁每隔几秒闪烁出点点蓝光。看不到地面,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深不可测的洞穴。借助闪烁的蓝光,我看见有两个人正挂在岩壁上,并排着一起往上攀。女的明显体力不支,呼吸声越来越重,男的动作很娴熟,不时拉女人一把。女的险情不断,每一次脚点踏空后,都会发出一声尖叫,男的瞬间把她拉住。她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笑声撞击着我的耳膜,特别地刺耳。待离得更近一点,我发现他俩并没有系保险绳。
我的眉心像被针猛扎了几下,肌肉不受控制地跳动起来,我伸手摁住了它。
他们就在我的下面,大概还有两米就爬上来了,此时哪怕是一个意外的惊吓,都有可能会造成他们的摔落。我颤抖地伸出手,往下胡乱地捞了一把,尽管什么也没抓到,但我确定,很快便能抓住一点儿什么了。
他们还在认真地往上攀爬,偶尔说一两句玩笑话,全然不觉上面猎豹一样守着的我。
为了不让他们发现我,我极力平缓着呼吸,几乎是紧贴地面趴着。声音离我越来越近,我判断着他们也快上来了。我一动不动,觉得自己该做点儿什么,可也不确定我要做点儿什么。我使劲地想啊想,想啊想,就是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在我的脑子乱成一团麻的时候,方才底下十分明显的喘息声突然消失了。我屏住呼吸又听了听,周围安静得难以置信。我往里挪了挪身体,底下漆黑一片,什么人也没有。我用手试探性地拍了拍岩壁,朝底下虚弱地“哎”了一声。没人响应我。我又大声地“哎”了几声。还是没有回应。我有点儿急了,我无法忍受他们的凭空消失,他们刚才分明离我只有一步之遥。我想下去,我一定要下去。我的身体慢慢地往下滑去,分别找到了两个脚点,两只手依次松开岩壁,开始摸索着往下爬。也不知爬了多久,我发现底下再也没有了可踩的地方,我只能用脚往两旁试探着侧踢出去,终于在右边找到了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我一只脚刚踩上去,就发现了有点儿不对劲,落脚点竟然是软的。借着岩壁上闪烁的蓝光,一张面无表情的脸露了出来——是徐浩。而我,正踩在他的手掌上。他沉默地看着我,足足有五秒,然后他对我奇怪地笑了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便抓住我侧踢出去的那只脚,用力一拉。
我坠落了下去。
洞穴极深,在坠落的时间里我努力回想。我不知道事情到底在哪出了错,我感到万分的懊恼与不甘。
尖利的石片从背后插入了我的胸膛,我痛楚万分,吼叫出声。
我浑身酸痛,也不知睡了多久。我从俱乐部的沙发上慢慢地坐直了身体,胸口的疼痛依旧。有人推开门,一道强光从大门处挤了进来,时针指向了上午九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