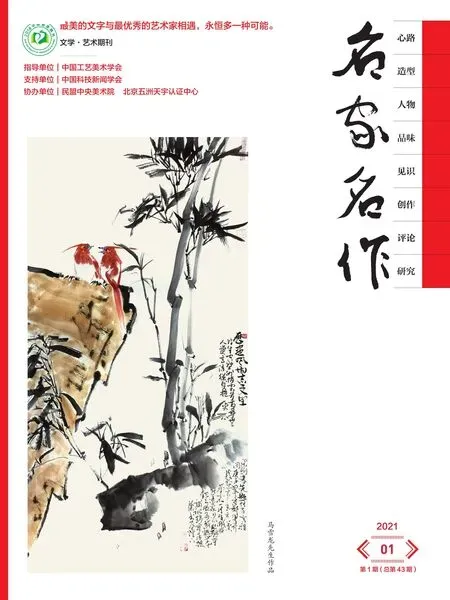钱钟书《围城》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林才钧
《围城》是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长篇小说,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殊社会群体——“知识分子”的特殊关照。知识女性作为特殊时期男权社会的特殊产物,在钱钟书笔下有冲动、有勇敢、有智慧,但也有心灵深处的墨守成规,她们有各自不同的矛盾,也有共有成长环境下的共性问题。
《围城》中的“头号演员”“男一号”是方鸿渐,“女一号”则是“方鸿渐的女人”,上帝视角下的“上帝”便是封建男权社会不可被打破的男权思想,这也是《围城》中女性悲剧的原罪。
一、方鸿渐的“女人们”
《围城》与方鸿渐产生关系的女子依次为欲求为先,搔首弄姿出卖身体的鲍小姐;工于心计,试图驾驭男人的精品女子苏文纨;明净聪慧,直言不讳,寻求纯洁男女关系的理想女孩唐晓芙;资质平庸,深谙男人需求,外弱内强的独立封建知识女性孙柔嘉。四个女子,四种性格,组合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方鸿渐的女人”,也是钱钟书先生所期盼的具有现代独立意识的“真实女人”——鲍小姐身上表现出不加道德规劝的原始欲求;苏文纨的万般优秀归于一身想拥有操控男人(权力)的力量;唐晓芙出淤泥而不染的天然明净理想;孙柔嘉对现实世界真实的解读。四种人生糅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全人的模型。当然,人无完人,他们也是独立的个体。
(一)“及时行乐”是一种生活方式——鲍小姐
鲍鱼之肆,恶臭满盈。“鲍小姐”无名有姓,姓却是恶臭之“鲍”。“局部的真理”是稍加掩饰肉欲与物欲的嘲笑之语,“熟肉铺子”是同船男人对鲍小姐的称呼,肉铺卖肉必然要有交换之物,两相付出,互为满足,此为“熟”。鲍小姐出身贫家,靠“夫”翻身(依附有能力的男人),是实现由“贫”到“富”阶层和身份转变最为简单和便捷的路径——鲍小姐靠“一个半秃顶、戴大眼镜”的黑胖子出钱出国留学,他靠未婚夫得以获得更好的生活。生活上得到满足,“夫丑且老”的现实让只对所谓梦幻泡影的美好生活渴望的鲍小姐不愿为夫守身,她凡事都想要“更好的”,她与方鸿渐在船上搭起的临时“围城”便是她尽情享受生活的态度。
鲍小姐是欲求的代表,满足欲求是她生活的真理。所以,船到达目的地之后,方鸿渐便成为陌生人。因为“欲求”不需要讲道德和感情,正常人有欲望,又有道德和感情,封建社会不会让女人操纵世界,所以“方鸿渐”们才痛苦,“鲍小姐”们才会被社会唾弃。
(二)“操纵”男人是精品女子的权力——苏文纨
苏文纨是高知、高颜,不易接近的精品女子。她是出身封建大家庭的“大家闺秀”,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所以会给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距离感。但随着年龄增长,高冷的“精品女子”有了危机感,所以她通过“洗手帕、补袜子、缝扣子”向方鸿渐示好,激发方鸿渐来追求自己的信念,但她高傲的性格又不容许其将这种情绪直接传达给方鸿渐,所以她只能以高压姿态逼方鸿渐就范。封建社会的男人是有“骨气”的,不大可能接受女人的胁迫,所以方鸿渐被“精品女子”的高压态势吓跑了。苏文纨发现不对,马上嫁给了看上去与自己门当户对的丈夫,并在“出嫁从夫”的封建伦理影响下,成为成功的投机商。
苏文纨的“拳(权)力”打在方鸿渐这朵棉花上,没有形成波浪,心中势必会有怨气要发泄。苏文纨对方鸿渐的“不通情达理”便因爱生恨,加之自身选择后的“成功”,当其再见到方鸿渐时,便将方鸿渐和他的夫人不留情面地奚落一番,告诉方鸿渐他当初的选择是“错误”。毕竟,权力就是要做给藐视权力的人看的,就像苏文纨觉得自己可以在男权社会操控男人一样,她最终回归男权,出嫁从夫,所以她也是悲剧。
(三)“出淤泥而不染”的理想女孩——唐晓芙
唐晓芙是钱钟书《围城》中最完美的女子,甚至批判词句都有“留情”,因为她是“理想女孩”,是男人甄选女子的完美标准,是女子羡慕和学习的楷模——出水芙蓉、坦率独立、热情活泼。男人喜欢她的明净姣好、涉世未深,女人喜欢她的敢爱、敢恨。“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以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待我——”这是唐晓芙对自己生命中男人的要求,也是其回绝方鸿渐的“尖刀”,但她却不知自己爱上了方鸿渐。有人说,唐晓芙之所以没有嫁给方鸿渐是钱钟书不想让“理想”破灭,但“理想”也就无法照进现实。所以,唐晓芙只是《围城》中男人们精神上的理想女性,是始终无法接受赤裸现实的“理想”,这是理想的现实“悲剧”。
(四)《围城》中唯一走进“围城”的女人——孙柔嘉
孙柔嘉是钱钟书《围城》中最为完整和接地气的女性形象,深谙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生存之道,所以她是唯一一个真正意义走进“围城”的女性。孙柔嘉与前三位“女主角”相比,并无明显的过人之处,长得不漂亮,甚至看上去有一些傻,但是她懂得要嫁给的男人需要什么——用柔弱,激起男人的保护欲。相较于鲍小姐的赤裸裸“贪财好色”,她把想法埋在心底,不动声色地让方鸿渐渐渐掉进自己的“温柔乡”;相较于苏文纨盛气凌人给方鸿渐施压却不表态,她“伸手拉方鸿渐的右臂,仿佛求他保护”。尽管未与方鸿渐提及婚事,却当着李梅亭、陆子萧的面“迟疑地”对方鸿渐说:“那么咱们告诉李先生——”。她的驾驭男人的智慧明显强过苏文纨,在于不动声色地主导推进;相较于唐晓芙爱而求“没有过去”的精神洁癖和探索,她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她知道不能给男人提过分的要求,懂得要隐藏自己的感情,所以方鸿渐选择了她,并筑起了“围城”。但是,男权社会下最靠得住的是男人,最靠不住的也是男人。进入“围城”便是久伴,就很难藏住内心、隐藏自己,进入“围城”前的自我“包装”便会不自觉地脱落。孙柔嘉也是知识女性,所以她心中也有理想主义,理想与现实如何融合,她还未参透,只是懂了一些皮毛,所以结婚后她给了方鸿渐巨大的压力,让方鸿渐有了逃离的想法,这决定了孙柔嘉在面对现实和理想围城时,无法真正调和其中的矛盾,所以只得悲剧收场。
二、《围城》中女性形象形成的动因
钱钟书以“围城”为喻,描述想逃离却无法逃离和想进入却无法进入的困局,这座“围城”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涉及现世文明的危机和现世人的生存困局。
钱钟书的“围城”虽然是具象的,却有很大的解读空间,放诸个人、社会和特定的环境都会出现不同的解读,强调了人出入其中的困难,也反映了人们冲入和冲出“围城”的渴望。
“围城”即矛盾。从社会层面看,《围城》中所描述的知识女性一面享受着男权社会下封建大家庭给其提供的优渥成长环境,一面又想挑战男权社会取得独立,两者的矛盾注定了其人生的悲剧色彩。苏文纨想掌控方鸿渐,却在围捕方鸿渐不得后,立马转投“新古典主义”诗人曹元朗的怀抱——“新古典主义”倡导“在社会和个人利益冲突面前,个人要克制自己的感情,服从理智和法律”,更直白点说曹元朗只是披着“新时代外衣”的“保皇派”。苏文纨在追求女性独立时转投曹元朗就是向男权社会“投降”,表明其从根本上并未逃脱男权社会的控制;从婚姻层面看,《围城》中只有孙柔嘉进入了“围城”,她作为受过“五四”新思想洗礼的知识女青年,看似愿意服从封建婚姻,但是从内心深处她又不满足“男人的附庸”“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她成婚后外出工作便是反抗男权的表现,而这也是埋下其悲剧命运的症结。
知识女性有冲脱现世的冲动,向往更加开化的社会和文化渴望,但因力量有限,生存的土壤不容许女性冲破角色限制。所以,钱钟书《围城》中的知识女性要么没有冲破男权的控制,要么在冲突中“理想”成了“悲剧”。因为封建社会的女性注定是悲剧的,所以苏文纨等知识女性只能在“围城”内外徘徊。
三、结论
对未知的领域寄托鬼神,以求希望——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也就注定人是矛盾的动物。所以,认知的界限会将人限制在“围城”之中,突破某个“围城”的封锁后,后面仍有无数个“围城”对你进行封锁,不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钱钟书以具象化的“围城”讲述人生存的困局,文字层面涉及的是婚姻、社会,其实有更为深层次的文学语境和社会意义。就本文论述的内容而言,钱钟书《围城》中女性的困局更多的是自身和社会的困局,对自身变革的不彻底,加之力量的薄弱,导致其在突“围”中要么失败,要么头破血流。苏文纨、孙柔嘉等女性虽然具有现代女性主体意识,但是其无法从根本上挣脱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枷锁,所以他们是矛盾的、迷茫的、不知所措的,只能在“围城”内外徘徊,而无法真正找到权衡“理想”和“现实”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