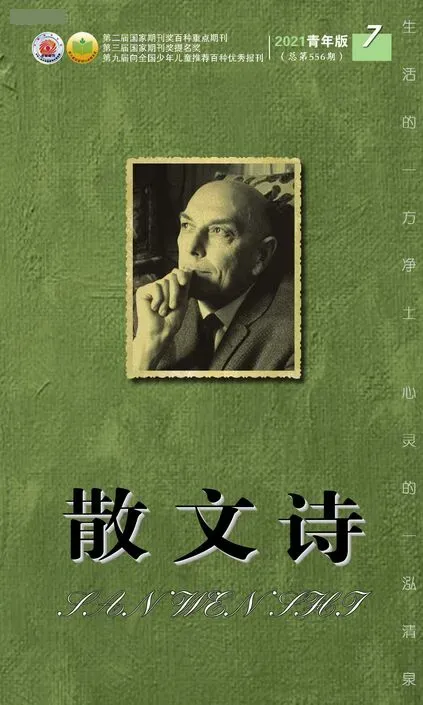一条飞鱼骑着白雪而至
刘 鹏
司空山
到了司空山,我就知道了什么是空
要用怎样的树木和石头才能填满,这无处不在的
思索,耗费了一千多年,有人依旧无法参透
树木越长越高,用稠密盛放湛蓝之空
石头相互退让,制造出无数裂痕,把空空如也
缝进去,要用怎样的空才能保守秘密?
月光依旧有足够的空间徜徉其中
飞鸟依旧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梳理羽毛
我们走入其中,像神仙和佛陀遁入
大千世界,用万籁俱寂讲经说法
明镜如水。水如明镜。从两手空空到一身赤裸
司空山上多出来的脚印和人声,迅速被青苔入住
多出来的烟岚,在高处徘徊与回望
我们走向暮年,从一只手掌的编年史里
放逐一匹白马,在真理的弧面轻舞,飞扬如雪
在惜字塔前
在惜字塔前
我翻出滚烫的文字
它们像干柴一样被我
投入幸运的火海,炉膛
包藏的祸心,在炉身里修行
那些有意无意写下的
错别字,轻薄,肤浅
秋风送走它们的背影,我感觉
远逝的烟尘又回到绿叶
接受雨水重重洗涤
许多凤凰拍打着金翅
涌动我凝重的血色
孤立的时光里,我终于看见
一条飞鱼骑着白雪而至
飞向沉默的幽蓝
木渎廊桥
一只乌面巨兽张开双翼
匍匐在两排开裂的木柱上
它安静的喉舌深不见底
吞咽白天的光、夜晚的灯火
一并耽视着
喧嚣的摊贩和行人
只有时间不可省略
冬天的风和夏日的雨不可省略
到此一游的记忆不可省略
灰瓦匆匆一瞥
光阴就凝固在檐头
桥下的河水
饱满得像水中游过的鸬鹚
帝王和宰相,榜眼与探花
这些锦鲤偶然点缀
对于古典的梦幻,廊桥选择沉默
江南是一碗泼出去的水
碧绿的香溪
清波摇曳,用一只手端平
去北极村
北方的月光被雪反复打磨
北方的大地被月光无限漂白
我在一辆开往北方的列车上
任由红色的衣服黄色的面庞
渐渐敷上洁白和安静的冷光
列车叩击着铁轨,微波荡漾
旅客打起的鼾声,连绵不绝
让我先一步听到北方沉郁的呼麦
此刻,我端坐卧铺,聆听这些
有如天籁的呼唤,北方的生灵
一路奔跑,向我诉说旅程的神秘
明天,我将一头扑入漠河站
飞雪与极光扑入我跳动的心房
覆盖南方的丘陵和体内的喧嚣
将我们雕塑成纯净透明的诗人
阜成门内大街171号
上香的人不争不吵
看风景的鸟不争不吵
没有人惊扰这座寺庙供奉的神佛
文字是多余的,经幡上有颜色足矣
与常驻和游历的神灵倾心交谈
我们只差一个信仰的姿势
在阜成门内大街171号
我看见一个枯瘦的老太太
一双小脚支撑起茫茫无边的愁绪
踉跄着倒下来,倒在众神足下
一定有很多想法将她摁倒
无法言说的生活等待引渡
摞在地上的重负轻声叹息
无数烟灰缓缓落入香炉
这老态龙钟的身体显得轻盈
和缭绕的烟火一样飘忽不定
沉重的灵魂随经幡雀跃
我看见她微微抬头
目光深处白塔洁净如洗
那些鸟儿得到了神谕
扇动翅膀,不带走一点尘埃
开往雪原的列车
一场雪粉碎另一场雪
在火车奔跑的时候,大风
卷走大地上富有生机的色彩
白色淹没白色,我们的火车头
唯一的绿,即将消失在
茫茫雪域。那是一个奇迹
被高楼大厦遣返
我们沉入多余的时光
像鸟蛋从树窝里滑落
架空翅膀的力量
液体渗入泥土深处,满怀虔诚
这算不算是一次回归
以文明的速度
在时空之漩涡里,钻木取火
发现原始的我
我们将消失,在迷宫深处
白雪铺张,寒流虚构语言
我们趴在水汽蒸腾的窗前擦拭,目光宁静
直到一座山,引领我们
投入到深邃的幽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