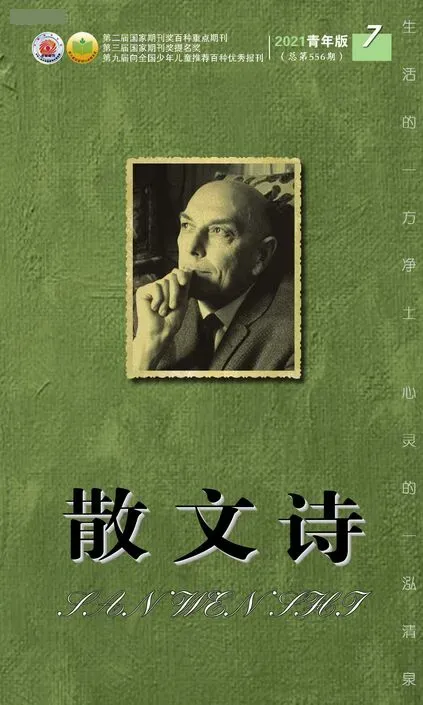归乡记
王向威
相似的故乡
车驶出郑州,我看到树林和麦田在枝枝杈杈和麦苗上,正呈现出冬天单色调的颜色,这颜色在风的作用下,以及在电线杆撑起的电线和蔓延的公路下,四处濡染。我在车上就已经想得到故乡村子的颜色,如此平常和随处可见,彼处和此处在外在上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冬夜晚归
你在路上,不敢往前走,又只能往前走。四周的房屋都熄了灯。白天还是泥泞不堪的路面,这时候被冻结,使得地面上一直凸起着坚硬的泥块。你又一次晚归,脚步声一路引得路边各家的土狗吠叫不止。你卧室墙外角落里堆积的玉米秆上,正落着霜,第二天早晨去看的话,一定是满满一层。
父亲的鼾声
地面上的雪,反射不远处汽车站的灯光到暗黑的夜里。他看到窗口处的夜看似混沌不明,始终给人一种天快要亮的感觉,却又长时间地没有什么变化。他听到一楼父亲睡觉时发出的有力的鼾声,时断时续。他一只手伸出来,触摸到了被子外面的凉,停一会,冷爬满了他的手臂。他想了想,乡居几日,时有枯燥的感觉,每天晚上摊开日记本,却不知道写些什么,有时候又为这觉得枯燥的心而心生难过,好像为了充实,日记可以改在早上写,内容是隐秘的夜晚里的梦境、冥想和发现。
回家
小中巴车迟缓地行驶着,拖起长长的忧愁,裹挟灰尘和太多送别的背影,在汽车尾气中,围绕着他读书的傍晚。他几乎要窒息了,俨然一尾鱼游到了海滩上等待着涨潮。于是,就看着写日记的硬皮本,直直的线拉着他写的字往下走,不至于旁逸出来。太阳落山了,那些黑漆漆的字,像水蒸气一样挥发,变成暮色弥漫在空气里,他合拢起来的书本,空空的,没有内容。他回家了,房门关着。
出发
一大早,从孤独的老家出发,去往孤独的工作地。是否因为你的来回往返,使得你感受到的这两个地方,都传染和到处蔓延着孤独?你呼吸着它,行走着它,早晨出门,听到铁皮信箱打开的声音,它又一次被邮寄过来了,你将要接收并阅读它。一位假装的目盲症患者,摸索着打开了一面油漆剥落的铁门。
林边草丛
早晨的草丛已不适合走入,秋季愈深,草间的潮气便愈来愈重,你穿了一双白鞋进去,出来时颜色已变得混合难辨,并沾染了草地泥土的黄。虽然上面落满了枯叶,可是,不管你怎么来回走动、摩擦,始终不能给它们一团火。即使它们渴望燃烧。
这些年的生活
一不小心,手中的书掉落在地面上,你忽然觉得:多年来,自己不是始终生活在书籍之软与地面之硬之间吗?
啄食的鹅
旧村庄荒废的宅院上,前几年手植的几排杨树,今已有碗口粗了,却仍显单薄。树干上分生着稀疏的几根枝杈,其间空地,被祖母种了些蚕豆和蒜苗。杨树、蚕豆和蒜苗,是此时颜色反差的三种意象。鹅,浮在初春的水面上,正努力啄食它们的倒影……
声音诗学
在加热的沸水里,有个生鸡蛋在煮熟的过程中发出一声炸裂声,这声音传到他耳边,催动着日常生活来到他的语言里……
嫩芽
也许有一天, “累”,终会变成一个动词,仅仅是一个动词,一左一右,拖住他的双脚,把他留在下雨的庭院内;不停地,他对自己翻土、耕种;他仿佛在重新生长。某一天,嫩芽顶破了他书写的稿纸,丢失的那几个字,它们凝聚的墨水四散开来,带来了他的生活所需要的夜晚和星辰。
遇见自己
到了夜晚,透明的玻璃变成了一扇镜子,嵌在窗口处。他看到白天隐藏的自己在镜子里显现出来了,或者他从远方赶来,在此时,来到窗前和他汇合,表情一致……
屋檐下的草丛
灯亮的瞬间,屋内的夜色退到窗玻璃的外面。一些晾晒的衣服已经不再滴水,在玻璃上显现出它们的影子来。布料里有剩余的水分,这夜晚带走的,能否充分打湿屋檐下那片草丛?天亮时分,你穿过它们,一部分水珠粘连泥土,被你的双脚带走……
广告和“绝交书”
村子墙壁上的广告和“绝交书”:一个也许来过此地打过井的外地人,用白色粉笔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有意思的是用红色粉笔写的几个“语法”一样的句子,写着王志慧、王熙文、王茹萍、王晨奕等几个小姑娘,都在跟一个叫“多多”的小姑娘的“绝交”声明……
夜晚里的钥匙
回到芦村,一把钥匙终于找到一扇可以打开的门。你进去后,等待父亲。他出门干活,总是晚归。他敲门,你打开门。在你回来的这几天里,他不用摸黑从裤兜里拿出钥匙串,并仔细辨识出开门的那一把。
白瓷碗
去庭院东面的“灶屋”取水,看到灶台一角摆放整齐的一摞干净的白瓷碗。忽然想起,以前在乡下,家里来了客人,主人迎接他们到堂屋坐下后,就会忙着从灶屋拿几个白瓷碗来,在桌子上放下,将开水从暖瓶中倒出来。他们一边说话,一边端着碗喝水。
自己和自己失散
在村子里一位邻居家,看到了一张1996年的照片。照片的人群中站立着1996年的我,现在来看,那么小,隔了这么多年之后,依然能够看到照片上自己当时的表情,也许是带着对未来的向往,可是,谁知道呢?现在连我自己都无法确认这个判断了。照片中的我,在村子里读书的小学校园内,站立在同龄的几位朋友之间,背后站立着教我们语文和数学的两位老师。我已经在过往的时间中弄丢了这张照片,邻居家的这位朋友却一直保存着。
站立在相框面前,突然就看到了这张照片。时间把这张照片染成了黄褐色, “却没有给里面的面孔和手增添一丝褶皱”(特德·休斯《六个年轻人》),于是,一个场景出现了,2020年的我站立着,看着1996年的我,像失散多年的兄弟一般相聚了,内心汹涌起伏。只是此时的我,是这个场景的一个组成部分,旁边没有一位及时拍摄的摄影师。
雪天所见
下雪天,在芦村里走着,看斜坡屋脊上的雪一层层变厚,坚硬的红瓦之上有了一层柔软;看麦田里,雪淹没了它们,而茂密的绿色依然让人感到没有冻僵的迹象;看父亲拿着扫帚和铁锨来到院内,把雪一锨锨铲到墙角,有一部分被他扔到了院子一边种植的菠菜上,而他会一直坚持到打扫完门外的小路;看家里的那只狗,终于安静下来,待在它的窝里,露出头看着外面,有意识地用前爪将露在外面的它用于取暖的麦秸,往里拢了拢;看黄昏降临了,而厨房里,动静越来越大,洗菜、舀水、炒菜,而那个逝去了八年的做饭的人似乎又回来了;看自己如何把自己送到卧室一张冷冰冰的床上,关上灯,看到自己见不到任何一粒雪,视觉的器官封闭了,而夜晚安静,竖起的双耳好像没有错过飘落屋子周围的每一粒雪。
重温自己
夜晚安静,一个人从睡梦中突然醒来,周围的一切模糊不清,一个人看到自己置身在巨大的黑暗中,整个村庄沉默不语。在故乡,他重新学习早睡早起,学习运用扫帚清扫每天傍晚时的庭院;他有时无所事事地走出去,但随着夜晚的来临,村子里每个家庭都关上了自家的大门。他回来,在熟悉的床上,每个夜晚,他都会如此醒来。
从记忆中抽身而来
他在湖边站着,湖很宽、很长,不远处的芦苇丛被风吹着,此起彼伏。这是夏天来临很久之后,他第一次如此亲近地接近这么多野外的自然之水,他想要跳下去,在湖水里游泳,像小时候那样,不仅仅为了避暑,更多地是为了一种游戏的乐趣,因此天天都要在水里待上一段时间。从湖边棚子下站立的地方往后退几步,就会看到张扬的炎热在地面和天空之间悬浮着,始终没有分散,且不断地沉在地面上。他感到阳光下的炎热在上升中,已提供了足够多的动力让他去亲近水,但是,他心里嘀咕着,又一次次削减甚至打消了这种动力。看湖面看得久了,他就仿佛真的看到一个有着自己模样的人从记忆中抽身而来,在水里游来游去。
晾衣绳上的日子
他看到凌晨的二楼阳台,是整个夜晚里这个家中唯一开放的地方;他看到阳台晾衣绳上挂着湿漉漉的衣服,好像它们一晾干,生活的痕迹就都消失了似的。汗水的气味以及灰垢和尘土都不见了,也再没什么能证明你曾经穿着它们体验过生活,一切都水洗过似的,模糊不清,连贯不起来。
河坡上的我
在河堤上走着,谈话有一句没一句地进行着;芦苇丛中的风连续不断地吹过来,草叶的气味如此依稀,抵不过一个人的呼吸和心跳声,似乎可以忽略;有一群人,在河对面靠近岸边的浅水里游泳,有那么一刻,他觉得自己已经闻到了河水的气息;在岸边的餐馆里,你们坐下来,这时候,店家推门走进来,送来啤酒和各种野菜,在你们的争嚷中,瓶盖子一个个掉了,瓶口儿冒着凉气。我看到游泳的孩子中,有一个不小心喝了口河水,站在河坡上,脸面通红,正呛得厉害。
在生者与死者之间
在一个老院子里,大家聚在一块,安静下来。逝者生前居住的老房子依然保存完好,灰色的瓦片和砖墙,显得低矮和陈旧,与周围新盖起的楼房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院里木兰花开得正好,二百多年的一棵老树,年年花开花落,荣枯更替。在木兰树下,大家沉默着,顺着一棵树的枝条,怀念还正在夜夜生长。我看到他们因难受而流泪的眼睛,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到底隔着什么?
冬天
从早晨一直到暮晚,冷,好像一种隐形物质,填满了空旷的天地和人世间;在路上走,挪动着缓慢的步伐,好像由于冷太密集了,使得一切变得太拥挤,并阻止着他。周围的冷变得不可移动似的,推迟了这一天暮色的降临。
雪野
雪,落在矮屋有着斜坡的屋顶上,原本就看不到的边界,因落满了雪而更看不清边际,这再次证明了雪在城市里是易逝的。只有这空旷无边的田野和错落有致的房屋,以及众多的事物,才使得落下的雪有了依附的地方,并能长时间地保存着,单一的雪因之有了多样的姿态。雪,才获得了可以从不同角度观看的存在。
离家即景
一场雨后,空气中的尘埃降落下来,回到地面上。
这是重新出发的早晨。
干净,碧绿,晦暗的远方若隐若现。
表达
书架、桌子、书本、水杯、钢笔、衣架和挂在上面的衣服。窗帘、墙上的照片、吊风扇、窗台上的仙人掌,陷入夜色中,都无法看清楚。借助手机荧幕微弱的光,他看到此时的心情,从心底通过文字慢慢描述出来。
雨天回家
雨中,我回到芦村。
雨水中的村庄,泥泞的路面。她开了门,从大门到堂屋的一段路,她打了一把伞,雨水顺着伞檐落在砖头铺就的地面上。第二天,她一早赶了趟乡村集市,买肉及各类蔬菜,溅起的泥巴,从出门开始就一路跟随。
一上午,她生火烧水,和面,包饺子,给我在家的假期一个温暖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