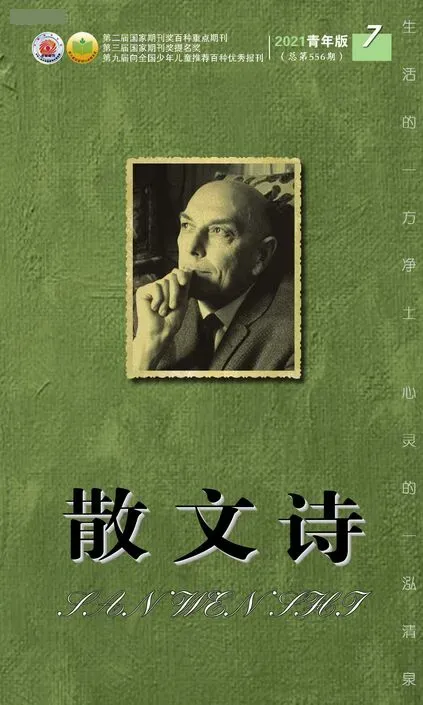紧箍咒
2021-11-12 23:40:51
散文诗 2021年14期
那家伙把风声吹入他的耳朵
他不想去听,卡波乔抓挠自己的鳞片
碎屑掉在地狱的第10个恶囊
像放射性的发光体
在很深的谷地,他双脚乱窜
影子在词语中越熬越咸
他的肉体像岩芯在压力下变质
笛孔张开
如阿耳弋斯的瞳孔
可以望到视网膜上闪电在发生
园艺师挥动黑色的剪刀
马匹、尘埃在他的髓骨间飞翔
时间逝去了,花果山的桃子成熟
腐烂的味道在空中漂浮
书中的蚕正在吃丝;酒精中的蛇已被分解
它的尾巴打成结,扑扑地拂弄着地板
那位不说话的石头父亲
(不知道现在已经多少岁)
在晚霞中守望着,和往常一样
羊群分娩,他的痛苦在白血球里聚集
正午的日光照在回归线上,没有阴影
有一瞬间,蚂蚁被包裹进琥珀
滚烫的夏日,把温度凝结在松脂里
他已经没有力气掏出耳蜗中的针
它沉淀、锈蚀在他的耳朵里
像一块陈年的钟乳石
蜡在融化
粘着发黑的耳屎
在他脑袋里的喀斯特山区
一枚被太阳挤烂的桃子,战栗着滴出水锈
他的毛发蜷曲如黑人
他不曾屈服,萎缩成蚂蚁
那戴着假牙的师傅,继续对鱼虾传道
水温骤升,他像一块石子
落入师傅所编织的网中
落入更深的没有底的海里
海水干涸,他被照射、被风化
越来越小,直至消失
猜你喜欢
大自然探索(2023年11期)2023-03-01 09:04:20
杂文选刊(2022年3期)2022-04-16 00:00:24
中国生殖健康(2020年7期)2021-01-18 03:02:34
小哥白尼(野生动物)(2020年4期)2020-07-27 01:54:38
小太阳画报(2019年8期)2019-09-11 07:01:50
娃娃画报(2019年6期)2019-07-04 17:59:14
阅读与作文(小学高年级版)(2019年5期)2019-05-27 09:56:46
祝您健康(2018年7期)2018-07-14 06:54:48
娃娃乐园·综合智能(2017年7期)2017-05-17 05:31:40
爆笑show(2015年1期)2015-03-26 17:5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