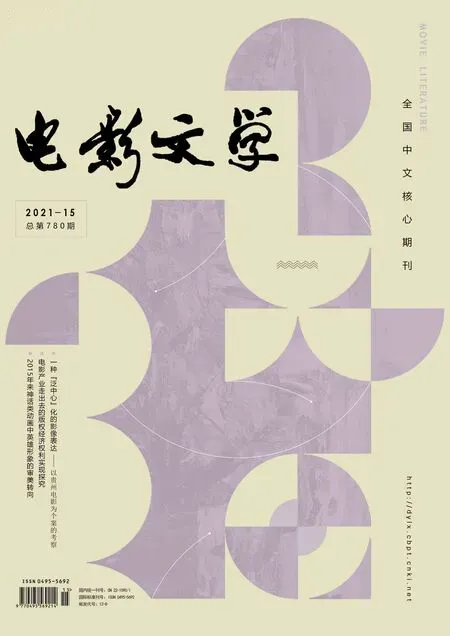诗意与超现实:慢镜头的观看美学
张 清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0)
慢镜头(slow motion,通常被缩写成slowmo)也叫升格镜头,是电影摄影的一种技术手段,它通过改变正常的拍摄速度,在银幕上呈现出动作变慢,时间延长的效果。早期这一技术的出现,仅仅只是吸引观众的“玩意儿”,但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慢镜头又不断带给观众富有诗意与超现实的审美震撼。
一、慢镜头的观看新体验
慢镜头呈现的动作如果以正常的速度展现,通常整个过程进行得很快,这样用慢的方式表现快,其观看性非常耐人寻味。苏联电影导演吉加·维尔托夫的《持摄影机的人》(Man
with
a
Movie
Camera
,1929)是一部集多种摄影技巧为一体的影片,其中慢镜头呈现的是掷铁饼、跳高、撑杆跳、链球、沙滩排球、跨栏跑这六项竞技体育运动,当这些动作以裸眼不能企及的速度投射到银幕上时,观众不仅能看到人物舒展、优美的动作,还能看到平时不易看到的人物肌肉线条的摆动、运动员灿烂的笑容等细节。吉加·维尔托夫之所以把这六项竞技运动用慢动作的方式呈现,和他的电影理念有着紧密联系。他认为电影的主要基本功能是“对世界进行感性探索。把电影摄影机当成比肉眼更完美的电影眼睛来使用,以探索充塞空间的那些混沌的视觉现象”。每一项运动的慢镜头结束后,下一个镜头是单个或者两个观众的近景镜头。这个镜头提示观者,看的主体是这些观众,同时摄影机视点既是观众视点,但又超越观众的肉眼存在于时空中,“以一种与肉眼完全不同的方式收集并记录各种印象”。眼睛作为造化的产物,天生是用来观看的。但“人的视觉不仅意味着看见,而且还包含了对所见之物的理解,还包含了对看的行为本身的理解”。这就是人的观看与动物的观看最本质的区别,即动物的观看是一种本能,目的是为了生存,人的观看是有意识、有选择的,人不仅能意识到自己在看,还能选择看的内容看的方式,并且为看寻求意义。约翰·伯格在他的著作《看》中也提到“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类具有以符号来思考的能力”。你可以训练一只狗开车,但是你不可能教会它们看懂交通警示牌的意义。观看需要一个过程,“‘看’这个动词从语义上很容易解释:‘使视线接触人或物’”。因此,观看过程的实现必须有一个可以看的对象,一旦视线投射到被观看的对象时,累积在个人身上的情感、文化、记忆被瞬间带动,观看的意义便产生于心中。人就是在这样的审美活动当中实现精神上的愉悦。
“美学”一词源于希腊语,其本意是“感性之学”(aesthetics),在西方理论界,一般都把这个词的现代用法追溯到18世纪德国唯理主义哲学家鲍姆加登。鲍姆加登用“aesthetics”这个词为其著作命名,从而创立了一门“研究情感和对‘美’的感知的‘科学’”即“美学”。“艺术哲学本来就是根据感性知觉(感知)和我们情感性的感性特点,双重意义上确定了感性的含义”。而人的感觉和动物的感觉又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在研究慢镜头时,一方面要体验视听画面的直观感受,另一方面,将感性的东西加以理性的思考,才能品味出呈现的美感。
二、慢镜头的视觉审美价值
苏联导演、电影理论家普多夫金在其文章中将慢镜头称为“时间的特写”。这是慢镜头给观者最直接的视觉印象。时间仿佛被拉伸、延长,观众的注意力全部集中于被拉长的慢动作,原本看不到的细节被放大。随着时代发展,慢镜头不再以炫技为目的,而是加入到叙事中成为影片组成部分,慢镜头的功效就不单是延长时间那么简单,其中渗透的影片主题、导演的情感表达等,都需要通过观看来体味。
法国导演让·维果的剧情片《操行零分》中,一群寄宿学校的孩子因不满学校非人性化的管制进而“反抗”。学生们撕破床垫,用枕头互相打闹,羽绒从床垫和枕头中飞出,像雪花一样纷纷飘落。一些学生手提自制的纸灯笼站在两旁,反抗小英雄达巴尔做了一个后空翻,稳稳地落在了一个孩子抬着的椅子上,孩子们抬着他们的英雄开心地“出画”。从达巴尔做后空翻开始,导演用一组慢镜头来渲染学生们“胜利”的氛围。如果以正常速度来拍摄,不仅这一时刻很快流逝,而且也达不到诗意、浪漫的效果。这一诗意效果也很符合影片当中青少年的年龄特征,让孩子们原本天真浪漫的个性通过镜头传递给观众。让·维果采用了一种抒情的方式发表自己对权威的反抗和对学生敢于反抗权威的肯定与赞扬。
美国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1980年推出的影片《愤怒的公牛》,有一段很精彩的慢镜头组合,成功地将拳击手的心理变化表现了出来。第一个镜头是杰西·拉莫塔(罗伯特·德尼罗)的对手,黑人拳击手罗宾森的中景镜头,罗宾森看着镜头做出拳的动作,其实是杰西·拉莫塔眼中罗宾森准备出击的主观镜头。第二个镜头是拉莫塔的正面中近景运动镜头,此时的他已大汗淋漓,身体倚靠着边绳,边喘气边凝视着对面的罗宾森。和第一个镜头做对比,二人的气势、心理有明显的变化,拉莫塔很明显占据下风,迎接他的是如暴风雨般的拳头。这两个镜头的速度是正常速度,剪辑节奏很慢,也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紧接着镜头切回罗宾森,罗宾森移动脚步,向镜头靠近,随着他一记出拳,拉莫塔被打的特写慢镜头和罗宾森出拳的正常速度镜头来回切换,这其中还穿插着正常速度的观众的反应镜头。疯狂拳击之后,罗宾森单人的慢镜头为这场比赛迎来结局,镜头从罗宾森的中景推到他高举的拳击手套上,其中还穿插着拉莫塔和拉莫塔妻子维姬的单人镜头(正常速度)。拳头落下,打在拉莫塔头上(慢镜头),大量鲜血缓慢地喷涌而出,落在台下观众脸上。导演将慢镜头和正常速度镜头交叉剪辑,同时让摄影机和被摄主体的距离以最合适的位置出现在银幕上,血腥暴力的瞬间被放大,银幕前的观众看到的远比电影中现场观众看到的更加暴力。
慢镜头常常被用来延长暴力的时间,因此它也成为“暴力美学”的代表性语言。山姆·佩金法的影片《日落黄沙》(1969)中,大屠杀场景的剪辑模式堪称暴力美学的经典,其中慢镜头观看性更是意味深长。佩金法的暴力美学风格对吴宇森、昆丁·塔伦迪诺等暴力美学大师的影片造成了深远影响。据统计,“最后厮杀的场面在短短4分30秒里集中了近乎270个镜头,平均每秒就是一个镜头。一些镜头持续了2到3秒”。慢镜头和正常速度镜头交替出现。通常镜头1是画面中角色射击正常速度镜头,镜头2是镜头1目标人物中弹倒地画面,大部分画面都是用慢动作呈现,也有一些是正常速度画面。镜头3再回到镜头1中的人物,或者是另外一个开枪的主要角色,接着再开始下一个慢镜头或者正常速度镜头。经过快速剪辑,将这些镜头组接在一起。这样一场长达4分多钟的大屠杀让人看得不免有些疲累,一个镜头接着一个镜头快速地出现,观者一方面要紧盯画面,避免错过,另一方面还要承受着大屠杀带来的视觉和心理的冲击。尽管如此,这样的剪辑模式已经被众多暴力影片运用和发扬。但是《日落黄沙》最为人称道的要数人物中枪流血的慢镜头,表现人物在中枪瞬间,子弹打中身体,鲜血瞬间喷出,随即便是中弹者快要倒地,痛苦哀号的表情。这个过程带来的效果,一是将血腥暴力扩大化,让观看者不得不看清楚整个过程,增加视觉冲击力,也满足了一些观众对血腥暴力场景的好奇;二是让死亡的瞬间增添一种庄严、浪漫的美感。试想,如果以正常速度拍摄中弹瞬间,这种美感会被死亡的恐惧给抹杀不少。这就是慢镜头的观看魅力。
吴宇森影片在风格上受到了山姆·佩金法的直接影响。这点从《喋血双雄》中周润发和一伙人在酒吧的枪战戏可以得到印证。比如:镜头1,周润发拿着两把枪指着左右双方对手,前景左下角是黑帮“老大”,中景是周润发,后景是打手,三人成一条斜线站立,其中周润发占银幕主要位置,左右两人被“逼”在角落,身体一半出画,强调当前形势是周润发占据着控制权。镜头2,黑帮老大被周润发的枪指着头,枪是虚焦,主人公的脸是实焦,黑帮老大的面部神情十分紧张和害怕。镜头3,周润发的反打镜头,周润发的脸先是实焦,枪是虚焦。然后是很明显的变焦,枪直指镜头,给人紧张、压迫之感。随着周润发开枪,这种感觉得到提升。镜头在开枪瞬间切换。镜头4,黑帮老大中枪的近景镜头。镜头5,周润发开枪射击黑帮老大的中景仰拍镜头。镜头6,黑帮老大被打中身体的中景反打镜头。镜头7,回到镜头5,周润发继续开枪射击。镜头8,黑帮老大被打中的中近景慢镜头。镜头9,黑帮老大倒在桌上的特写慢镜头。从镜头4到镜头9,慢镜头把死亡的瞬间放大,把中枪的过程完整、清楚地展示给观众,将血腥暴力放大给观众。这和《日落黄沙》中中枪的慢镜头作用相似。不同的是吴宇森还把主人公射击的慢镜头和对手中枪的正常速度镜头剪辑在一起。比如周润发双枪射击从吧台跳出的对手,镜头是以放慢的速度展示周润发的“英雄本色”,镜头回转是中弹者身体摆动、表情狰狞的正常速度镜头,导演用一慢一快两种速度,将双方的敌对状态和谁“赢”谁“输”的态势投放在观众眼前。
在科幻电影中,慢镜头似乎回到它最原始的“吸引力”意义。美国著名学者汤姆·甘宁把还没有建立起叙事意识的影片称为“吸引力电影”。这类影片着重展示细节、动作,让观众产生各种复杂的快感。科幻电影中一些慢镜头的动作毫无疑问是此类当代“吸引力电影”的例证。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黑客帝国》中的“子弹时间”。当子弹出枪时,电影中的时空被撕裂继而又重建。一系列的动作呈现几种不同的时间状态。尼奥开枪的瞬间,影片中的时间处于人类正常感知范围;子弹达到特工布朗时,影片中的时间被加速,继而布朗的动作呈现出快的形式,不在人类正常感知范围;尼奥面对子弹时,情形又与前者对立,影片中的时间被放慢,超出人类可感知的范围;从空间上来看,特工布朗躲避子弹时,因动作变化造成空间层堆积叠压在一起;尼奥躲避子弹时,摄影机围绕他进行360度拍摄,子弹从尼奥身边滑过,速度表现为慢速,摄影机的速度则相对快于子弹速度。时间的不统一性创造出了不同于现实可感知的空间形态。在传统的慢镜头效果里,时间和空间在同一场景中被凝固下来,“子弹时间”的出现,不仅把细节放大,更为观众呈现超现实的视觉奇观。此后众多科幻电影中,类似“子弹时间”的应用层出不穷,并且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在其他类型的影片中。
结 语
慢镜头的出现,最初只是电影创作者吸引观众的手段,在叙事电影还未成熟的阶段,这种奇观性的视觉效果,并不承担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功能。当电影的叙事越来越成熟后,电影创作者不只是看到它的奇观性,更多的是借助这种技术的奇观辅助叙事的连贯性,从而造成一种模糊的“艺术性”。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各种数字技术的进步,电影创作者又挖掘出更多潜在的可能性,慢镜头技术创造出的视觉效果的奇观性又被放大和发展,它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意义。但这绝不是故步自封,而是一次伟大的创新,它让我们看到电影的发展、进步,呈现给观众一次又一次的视觉震撼和心灵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