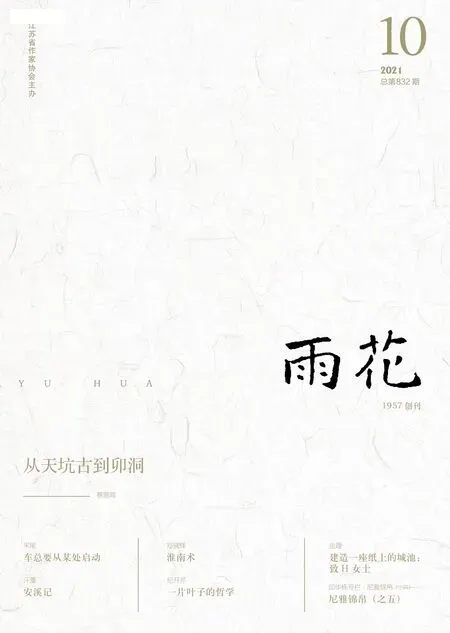建造一座纸上的城池:致H女士
金 理
题注:2020年,我参编的小说集The Book of Shanghai由英国出版社Comma Press出版。当年五月,翻译家H女士因写作该小说集书评的需要,发邮件给我,提出访谈要求。以下为访谈的回复稿。
H女士您好:
感谢您对The Book of Shanghai的关注以及诚挚的邀请,我也了解到您在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领域作出过重要贡献,我当然乐意与您交流。先简单介绍下这本小说集的来龙去脉。
2018年底,我的同事戴从容教授(她当时正好在曼彻斯特大学孔子学院担任中方院长)给我打电话,说英国的出版社Comma Press希望推出一本以上海为故事背景的小说集,邀请我一起参与编选。我向从事版权输出的朋友请教,得知Comma Press是一家非常权威的出版社,他们有一项长线出版计划——“阅读城市”,该系列丛书主题目前包括世界上十五座城市,如东京、伊斯坦堡、德黑兰、里约热内卢、哈瓦那……此前的《东京故事集》已形成较好的品牌效应。这些小说集多角度地展示一座城市的生活,其目标读者设定为英语读者及旅游者这两大类。一方面让英语读者了解上海、了解中国文学;另一方面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出现在上海的酒店、宾馆里,如手册导读一般让国外游客通过文学了解上海人与当地生活。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出版尝试,我当然应允参编。整个工作流程是这样的:英国出版方会给我非常详细的要求(他们想要什么、不要什么)以说明出版意图,然后根据我的阅读记忆与文学眼光提供一份十五篇左右的初选篇目,再由戴从容教授、我(我们两位署名联合主编)和出版社编辑及受邀请的外籍专家一起商讨,从初选篇目中择定十篇作为最终篇目,最后由出版社邀请译者翻译成英文出版。
出版方给我提供的具体要求如下:1.体裁是短篇小说,而且篇幅限制非常苛刻——8000字。我为极个别作品争取到了10000字(上限)。2.入选作者必须是健在的,而且涉及不同代际。3.故事以上海为舞台,时间从新中国成立延续至今。4.入选的短篇小说不完全是纯文学的概念,出版方希望里面包容科幻、悬疑等类型。我曾经向几位作家和学者朋友出示拟定的初选篇目,说实话,在经过上面四项编选条件筛选后,总难以给出完美的答案(光是篇幅一项就会剔除不少读者心目中有代表性的上海小说)。在此我倒是愿意与您交流遗珠之憾:在我心目当中,与王安忆这样作为上海城市标签性质的作家地位相同的,另外应该还有一到两位作家(抱歉我就不说具体名字了)。但是这些作家可能以长篇见长,或者他们在8000字范围内的作品无法代表其文学水准,所以尽管我将他们的作品放入了初选篇目(出于我上面提到的作家的代表性,在我心目中他们代表着上海文学),可是在多方商议后,还是被拿下来了。其中有一位作家在我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我初选了一篇他的小说,内容是关于一位上海小资女孩对于西方的幻想与梦魇的,但是出版方可能觉得这个故事对于该书的目标读者而言没太大吸引力,所以最终这个小说没有被保留。让我觉得最可惜的是一位“50后”作家的小说,这篇是我力荐的,出版方也同意,仅仅只是版权方面有些问题无法解决。这篇作品通过“我”与文学前辈亡灵的对话,来寻访生命的意义。上海这座城市总被理解为环绕着小资与物质浮华的气息,相比照之下,这篇小说是如此“沉重”,也涉及知识分子传统与人文精神的传承(我们不能忘了这座城市中有鲁迅、巴金等人的奋斗足迹)。本来有了这篇小说,完全可以为该书增添不一样的色彩,真是非常可惜。
虽然选录的是当代的上海小说,但在编选过程中,需要对照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学谱系与脉络,我是在既有的历史版图上建造一座纸上的城池。在序言中,我用最精简的文字这样向西方读者来介绍上海文学的传统:
鸦片战争后,1843年上海被开辟为商埠,1845年先后设立英、美、法租界,殖民者在上海引入了许多与西方接轨的文明设施。于是,既在丧权辱国的阴影笼罩下,又获得得天独厚的历史机缘,上海从一个位于长江口毫不起眼的小县城,一跃而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这里既有欧风美雨浸淫下的现代西方文明,又有老中国积淀而来的传统文化,交融碰撞,互相渗透。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和地理位置,容纳、试验各种思潮和文化观念,上海发展出了多元的文学传统,并奠定其在文学史上的重镇地位。
1933年,海派文学的代表人物、小说家、编辑家施蛰存在一篇文章中说:“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括着各式各样的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和前代的不同了。这种生活所给予我们的诗人的感情,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从他们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的吗?”(施蛰存:《又关于本刊的诗》,《现代》第4卷第1期)这段表述意味着,现代生活与过去生活发生了断裂,由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所带来的都市现代风景,以及一种由资本主义所构筑的现代生活方式终于浮现。这样一种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嬗变给文学带来了新变,于是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也发生了断裂。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有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的现象。由此形成了上海文学繁华与糜烂同体的现代性传统,该同体而矛盾的特征,形象地显示在穆时英的小说《上海的狐步舞》中的头一句话:“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这一传统早期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小说《海上花列传》(韩邦庆著)。而从郁达夫到丁玲、蒋光慈、巴金等,他们的创作则在另一派脉络中,其笔下的男女主人公既是现代物质生活的享受者与消费者,又是这种现代性的反抗者与审判者,希望尽可能地根除上海文化中糜烂与罪恶的因素。由此构成了海派文学的第二个传统,研究者称其为批判性的传统,这一传统中的代表性作品是茅盾的《子夜》,突出左翼立场和人道主义情怀(以上关于海派文学传统的分疏,参见陈思和:《海派文学的两个传统》)。
1949年,上海解放,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特别是1978年以来,上海不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也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上海的文学创作,在呼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的变革中,也承袭着上述文学传统。入选本书的作家中,既有素来坚持批判立场和人道主义的,也有以描绘旧上海的“风花雪月”见长,基本可以纳入海派文学的现代性传统。这一传统中有一支脉,表现身陷急速变动的生活而出现身份认同的危机,这是1930年代海派文学的重要主题(穆时英、刘呐鸥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本书中有不少作品延续了这方面的主题表现。上海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早期的移民大多来自浙江和江苏。开埠之后一度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据2018年统计,上海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8.33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占比为40%。身份认同往往与人类经验的延续性有密切关系,容不得剧烈而频繁的隔断、推倒重来,然而在城市化、工业化及人类生活方式移动性加速的情况下,身份的构成恰恰由本质、稳固转变为选择、流动。本书作家中就有“新上海人”,以“沪漂”经历为主题,围绕着高科技产品手机丢失这一情节,展开对城市人新境遇的思索。
上海这座城市的开放和包容,使其往往成为文学探索的策源地。从20世纪30年代以小说家施蛰存与诗人戴望舒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以小说家孙甘露与评论家吴亮等为代表的先锋文学,都汲汲于文学形式的创新。当然,形式创新也意味着叩访生存状态的多种可能性。特别有意味的是,在传统与主流的现实主义步履沉重的今天,反倒是科幻与悬疑这样的类型文学,在形式探索方面更具活力。
最终入选的作家中,年轻作家(“70后”“80后”“90后”)占了一半以上,这很吻合我的设想(近些年我个人在文学批评的领域,着力追踪的也是中国大陆当下的青年作家),因为上海本就是一座朝向未来、富有活力的城市。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本书出版后,英国出版方向我打听联系方式的唯一一位作家,就是入选本书的最年轻的那位作家。我想和您分享一段私人的成长经历,由此可能您会理解,为什么在我眼中这位“90后”作家如此特别。我是知青子女,父母都是地道的上海人,但是在特殊的年代里他们必须下乡插队。我出生在上海,但自小被父母带在身边,他们一遍遍地向我讲述:外滩的钟声和“世界建筑博览会”、豫园的九曲桥、凤凰牌自行车、王家沙的精美糕点……我是通过高考考回上海的,在回到上海之前,我生活在对上海无尽的想象中。坦率地说,我学习的最大动力就是我要回上海,回到那座城市!后来如愿以偿,有天在大学寝室里和亲戚通电话,旁边两位“上海土著”同学窃窃私语:“你听,他说上海话时有几个词咬不准音。”如同创伤经验,这件事让我纠结痛苦了半天。可想而知,我和城市的关系一度是多么紧张和焦虑(生怕被周围人辨识出“不是上海人”)。与我同龄的“80后”作家,其初期的创作也完全围绕个人与城市之间的紧张关系展开。那完全是司汤达、巴尔扎克式的写作:当庞大的都市在面前展开时,外省青年内心充满野心与狂想,既要拼命融入,又总是感觉到处处受排挤,出现累累伤痕。但我观察到,近些年来情况似乎有所变化,更年轻的一代写作者,能够以较为平和、冷静的态度去把握个人和城市的关系,紧张和焦虑已经得到了缓和。比如我选入的这位“90后”作家,借用她作品中的一句话来表达——她给了“我”一双眼睛去看上海,而透过这双眼睛所看到的上海,是我此前看不到的,准确地说,是我一度不想去看的,而从心理习惯而言,我们往往只会选择去看那些我们愿意看到的。请容许我再插入私人经历:当我回到上海读大学之后,每星期都会去奶奶家度过周末,但其实我很排斥这件事。奶奶家位于老式的工人小区,我总是在周五下午或黄昏的时候抵达,当双脚刚刚踏进那个小区,耳边传来的是搓麻将的声音,鼻子闻到的是煎咸带鱼(上海普通市民日常的“下饭菜”)的味道,眼睛看到的是树荫下老头老太在聊天……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到时间停滞了,衰败而缺乏活力,于是设想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去奶奶家。但是现在想来,其实这样的空间就是这位年轻作家着力表现的中心,她写出了像我这样的读者原本不愿意去关注的人和事。可见,文学选择何种地理空间,现实中的城市如何被写入文学,已不是简单的反映论问题,背后联系着深广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我们其实不能“透明地”看到城市,在实际看到城市之前,我们心中已经存有一张关于城市的“地图”,这张地图不仅是由感觉、经验绘成的,也交织着观点、价值和文化。而想象中的城市反过来也会对现实中的城市进行秩序化,它让我们选择去关注某些城市空间,遗忘另外一些空间。所以我们在观察、书写城市的同时,也应该不断地对自我心中那张关于城市的地图进行反省、清理(参见拙作《城市写作的两组关系命题》)。
该书出版后获得的关注出乎我意料。《亚洲书评》(Review of Asia)、英国电子文学杂志(Lunate)、《燕京书评》等刊发专题书评;“澎湃新闻”“新华网”“东方网”“上观新闻”“中国作家网”《文汇报》《上海日报》(Shanghai Daily)等作了专题报道。这次出版实践,也让我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讲述中国故事”有了崭新认识。首先,我们向国外呈现、传播的中国文化,一方面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应当注重当代中国文化,尤其是从鲜活的日常生活中提取出来的、体现中国人民生活智慧与丰富情感的文化。本书精选十位当代作家创作的上海故事,以此为窗口,见证普通人的生活记忆史。如果将它比作一张城市文学地图的话,我希望这张地图是完整的,既指示众所周知的城市地标,也引领读者深入城市隐秘的腹腔内部和边边角角,展示上海人潜藏在日常生活罅隙里的喜怒哀乐。来上海的外地游客,往往首先选择的观光地点是黄浦江两岸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外滩)和摩天高楼群(陆家嘴金融区)——这也是好莱坞大片经常选择的取景地。然而,单一的取景视角恰恰反证了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全世界各大都市的机场、星级宾馆、大型商厦、金融中心等现代设施可能是相同的,但是每个都市中居民的生活形态及其所呈现的精神面貌却丰富而独特,优秀的上海故事(中国故事同然)应该着力将城市生活的参差形态和不同个体的精神特征细腻地表达出来。从阅读接受而言,这样的文化输出也能自然地得到国外读者的认可。文化输出不应只是高端战略、顶层设计,也当入情入理地落实于日常生活、日常阅读的互动中。其次,“走出去”并不只是单方面、一厢情愿的输出。本书的出版建立在中方主编与英国出版方充分、平等沟通的基础上,前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有大体把握,后者对于读者市场有明确预估,最后直接以英文版在国外主流渠道发行,一改传统的“走出去”模式,代表着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新尝试与重要“突破”。其间得失,也甚盼得到您的反馈与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