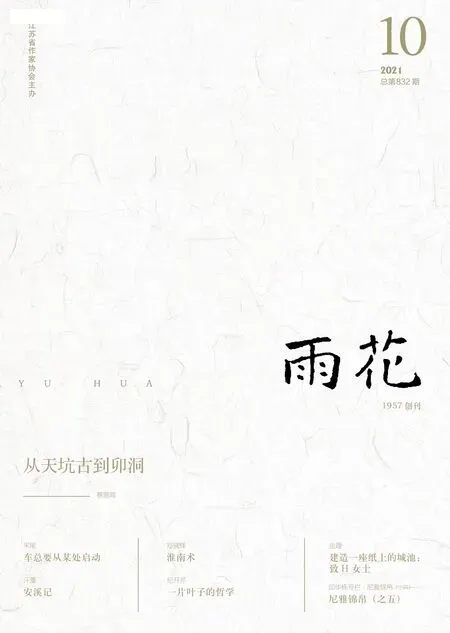船上的杜甫(外一篇)
徐海蛟
船在湘江上走着,青天在上,水在下。他越来越乏力了,寒气交织着湿气,江水漫漶啊;他越来越恍惚了,时日将尽,音书渐绝。他的世界小到只剩下一条船,他的惆怅漫过整个帝国的黄昏。冬天深了,时日将尽。
——题记
1
离开的想法早就萌生了,只是一拖再拖。去往何处?又开始困扰杜甫。到了五十五岁,他仍未洞悉天命,仍未将家安定下来,像不断迁徙的候鸟流离于异乡的天空下,焦虑和沮丧似必然降临的夜色,一再侵袭他。
他想过带家人去淮南定居,还托一位前往扬州的胡商打听当地米价。这一打听,令他望而却步了,便在夔州又挨过去两个年头。可这地方,并非外乡人的乐土。夔州居于长江瞿塘峡口,山高谷深,地气冷湿,风寒刀子般凛冽,不是一把中原带来的老骨头扛得下来的。病痛伴随衰老接踵而至,五十五岁的杜甫不可阻挡地进入了晚年。连年的颠沛用旧了身体,骨骼僵硬得生出锈迹。眼睛花了,看花看树,均模糊成一个梗概。牙齿脱落大半,咀嚼食物变得困难。糖尿病越来越严重,自行采集的草药,好比节节败退的小卒,挡不住压境的大军。
岂止蓬乱雪白的须发,岂止疏松的骨骼,岂止经年未愈的肺病,岂止如影随形的咳嗽……衰老是全方位的,铺天席地,它卸掉人的勇气与斗志,瓦解人的欲望,令梦境都变得反复。这一年,在偶尔可拾的梦的残片里,杜甫不断梦到儿时的自己在姑母家前院攀爬一棵枣树,树上的枣子累垂可爱。但每回爬上去,伸开胳膊要够到时,都会倏然失手,摔向一个深渊。有生之年还能回洛阳,看看儿时扑蝶于其间的姑母的小院,看看那棵枣树吗?念头一次次触及这件事,又消散在一个未知的空洞里。
秋天时,弟弟杜观的第三封信辗转捎到杜甫手中,他挪到草屋门前,借着下午的天光,想将字看清晰些。弟弟在信里再次提及让兄长出峡,由夔州顺江南下,或许日后可回长安洛阳。第三封信以及信里提及的地方,制造出一丁点温暖的期许,促使杜甫做了决定。
杜甫将位于夔州的瀼西草堂及四十亩果园赠给南卿兄,这位是前不久自忠州迁居来借住草堂的人。送出这片经营了近两年的果园,他的挂碍并不多,他期望果树林在自己离开后年年开出花,结出新果。他只郑重地和果园新主人聊到一件事:草堂西面有位老妇人,若来堂前打枣,由着她些。那是位无儿无女的妇人,儿子征了兵,生死未卜。她无人照料,实在找不到果腹的食物,才来打枣子。眼睛看不清楚了,小百姓的苦却历历在目。
公元768年正月中旬,择了一个宜出行的日子。天阴,灰云如铅,风自高崖间横切过来。在白帝城放船,那种木帆船,并不大。一根桅杆竖立船尾,用来升挂布帆,船身部分设舱体,可容纳五六人,恰好载得动一家子。这条船是杜甫在夔州置办的,毕竟这两年,很是受到夔州都督柏茂琳顾念,赠给他果树林,还让他租一些公田,用来维持生计。他一直想着以那点捉襟见肘的积蓄置办一条船。对于船,杜甫有着天然的感情。旅居蜀地的那几年,他在浣花溪畔也置办过一条船,可惜那条船残破到不能用了。他这一生,二十岁乘船离开洛阳,漫游于吴越间,坐着船穿过钱塘江,坐着船到达越州天姥山下。随后,又无数次乘船远行,江河与舟楫构成他生命里的另一片版图。船是远行者的白马,亦是漂泊者的陆地,是困厄里的人最后一丁点念想。杜甫喜欢船,船联结着出发与到达,联结着远方与故乡。
行李少得可怜。这些年,岁月像一个筛子,筛去了一切物质的念想,筛去了一切生活的积余,到头来空空如也。也不允许更多行头占用船上空间,毕竟那样小的一只船,空间得留给人。
一家人的日常衣物、一箱书、半麻袋草药、一点碎银子,差不多是全部行李,再加一张小几案,叫乌皮几——从故地河南随身带到成都,又从成都带到夔州,外面裹着一层乌羔皮的套子。平常坐榻上,横过来用作靠背;一旦竖放,就成了一张小桌子。这小几案上覆的羊皮已磨去光泽,他一直舍不得扔,经年的辗转,家乡带出的旧物寥寥无几,这张乌皮几算难得的旧物件了。实用,又令人遥想起洛阳的旧光景。
杜甫替艄公解开缆绳,回头望向云雾深处的白帝城,长长吁出一口气。
一段新旅途开始了,他不知道会有怎样一番命运等在前头。水路渺茫,别人或许能看到明天的事,或者看到下个月的事,他只能看到生活的这一刻,咫尺外都不敢预计。
2
船出瞿塘峡,布帆升起。一路风疾猿啸,小船穿过高耸欲倾的巫峡,穿过惨淡的浓云。出峡的水路,惊险无比。船儿有时被送上浪尖,顷刻又从浪尖跌下;有时眼看撞上险滩巨石,又陡然峰回路转。船上的人,在江水平静处还能端坐,在疾风恶浪里,只好趴在舱中。几箱书打湿了,一些家什也浸了水,一家子惊恐而失措。
这一程曲折的旅途上,杜甫就着舟中一点微弱的烛火,写就《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以四百二十字回望人生,那些羁旅与漂泊,那些苦难与挣扎,那些忧愤和慈悲,都重新回到纸上。风平水静的傍晚,他站在船头,望着北飞的大雁,心头的悲怆油然升起。他有时也幻想,如果成为鹭鸟,还乡的路途岂非便捷许多?
其时的江陵水陆交汇,通达四方。关内人民逃往西蜀,中原人民投奔江湘,都得经过此地。安史之乱后,江陵发展成为长江沿岸的一座重要城市,有南都之称。出峡后,杜甫的船到了江陵,就在江陵停留下来。杜甫和家人想着,先作一段休整,再启程北返长安,不行的话,就顺江东下去往青年时代漫游过的江东。
人生实在难以预计,杜甫抵达江陵不久,是年二月,商州兵马使刘洽兵变,六百里商於之地绵延起一片战火。八月,吐蕃进攻凤翔,长安再度告急。四起的烽烟阻隔了向北的回乡路。他本打算去江东,可既联系不上姑母,又未能等来兄弟的消息,先前写信给他的弟弟,也渺无音信了。
只好在江陵暂歇下来,凭藉着一点诗名,四处寻找活路。他想到担任荆南节度使的卫伯玉就在此地任职,他旅居夔州时,曾写诗颂扬过此人。他想到堂弟杜位也在节度使官署中担任行军司马。他还想到一个人,老友郑虔的弟弟郑审。他想他总归能找到些许倚傍,为了活下去,为了糊口,他并不怜惜一点可怜的面皮。时至今日,他的面皮早已被羞辱磨出了茧子。但这些人都没能给杜甫提供太多实质性的帮扶。生活总归是自己的,贫穷无法像诗句那样分送给别人。
他伛偻着腰,扶杖而行,步履蹒跚,走不了太远的路。想雇轿子,又供不起这笔花销。他一家一家去拜访脑海中竭力搜寻出的熟人和权贵,觍着老脸,敲开那些高墙下的红门。经常地,他并不能见到想拜访的人,不是门口守卫不放行,就是仆人出来回复主人不在家。第一天碰壁,第二日,又起身出门,生计系在发丝般细微的人情上,好比微弱的烛火,命运哈一口气就能吹灭它。他写下“饥籍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的诗句,这是生活最真切的写照。
左耳渐渐聋了,右胳膊偏瘫,僵硬得写不了字,只好试着以左手写,纸上的字东倒西歪,像拄着杖在雪地里蹒跚的老人。有时也让儿子宗武代笔,他大声说出一句想好的诗,盯住儿子的笔写下自己的诗句,恍然如梦。
江陵的日子难以为继了,他们一家再次登船,前往江陵以南的公安县。暮秋,小船在长江上行进。霜凋碧树,秋声萧瑟。他写诗给郑审,这大概是少数可以用来诉说自身境遇的朋友:“形骸元土木,舟楫复江湖。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即便这样艰难的时日,他的文字里依然遍布着别人的苦难。那些命如草芥的小人物,那些无声无息的卑微的生命,都来到他的诗里。渔民、农人、小贩,逃难的孤儿寡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写下万里悲秋的漂泊羁旅,也以无限热切与慈悲的诗行丈量人间苦难。
可在公安还未落下脚,兵变又起。数月间,他在公安受尽冷落,他的小船,他的家,只好再次漂泊起来。这一回,他们慌乱中逃到了洞庭湖边的岳阳。在岳阳过了不多时日,杜甫想起曾经的好友韦之晋正在衡州担任刺史,这是他搜肠刮肚想到的名字。
总算找到了方向,杜甫决定带家人投靠韦之晋。
船离开洞庭湖,继续沿江而下,去往衡州,他心里升腾着一线渺茫的希望。等船靠了岸,脚踏到地上,这点渺茫的希望似乎渐渐放大了些。找到韦之晋,至少可以让一家子有个落脚处吧?
船停在衡州江边,老妻、儿子去江边人家寻觅食物。杜甫拄着拐杖,一路询问,来到衡州官署。他向衙门前的卫兵打听刺史的去向。费了一番周折,问了几个人,才有个心肠和善的士兵告知这位破衣蔽体、满头白发的老者。
一路寻来的那点希望,被现实的风一气儿吹熄了。他没有料到,韦之晋已改任潭州刺史,到潭州不久,就于那年四月去世。他要寻的人,想依靠的人,竟在数月前生死远隔了。
他们刚下船,脚刚站到衡州的土地上,就又失了方向。在衡州勉强撑了数月,待到公元769年夏天,杜甫的船又开动了。衡州没有熟人,没有住下来的房子,他思量许久,还是决定离开,前往潭州。
此后,杜甫的余生只能依傍这条船了。
夏末,杜甫的船泊在潭州城外。天气稍好些的日子,他就到近郊江边的野地采些药草,放到渔市摆药摊,他想以卖药的收入维持生计。择一处背风的地儿,就在一溜鱼摊尽头,放下麻袋,支起一面小而破败的布旗,算作卖药行医的招牌。这也是他连年逃难中,所剩无几的自救方式。老迈的杜甫,满头白发的杜甫,斜倚在颓废的夕阳里,像江边一丛枯瘦的白菊。他偶尔会想起自己是大唐帝国拿过国家俸禄的官员,曾经有过一腔“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抱负。现在他跻身于一群引车卖浆者的行列,他们是渔民、打猎的、织布的、养蚕的……但他们又有一个与杜甫相同的命运:都是在艰难时世中挣命的人。
鱼腥弥漫着,人们来去仓促,至傍晚时分迅速散尽,只留江水不知疲倦地拍打堤岸。长日将尽,囊中依然羞涩,挣得几个零碎的铜子儿,还不够一家人晚上买粥喝。照例,他要扶着拐杖,在江边站一会儿,看江水浩荡,看江上的云聚拢又散开。他慢慢地踱回船上,船舱里已堆着一堆野菜,这是老妻的功劳。
有一回,一个叫苏涣的人来船上拜会杜甫,并拿出自己的诗作读给杜甫听。小小船舱中,响起了诗的声音,这是久违的声音。连年的漂泊里,已经很少有人特意拿着自己的诗呈给杜甫看。这是羁旅湖南的三年里,杜甫难得遇到的一位知音。他时常来鱼市的小摊前和杜甫聊诗,杜甫也常常到他的茅屋里畅谈。这是珍贵的时刻,诗歌就像困厄时日里的一点光亮,让生命的冷和暗退后了一尺。
由夏到冬,由冬而春。时间行进到公元770年3月,潭州城已鼓荡起春风的裙裾,枯树醒来,换上新衣,捧出明艳的花。年幼的、年轻的、年老的,每一种生命都获得了春天的感召,都醒来,抖擞起精神。杜甫在潭州城内重逢了一位故人——乐师李龟年。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受苏涣邀请,以幕僚身份参加某个显贵的晚宴。在那晚的席上,坐于末桌的杜甫,听到了李龟年的歌声。那是儿时的耳朵浸润过的歌声,是四十年间未能听闻的旧曲。歌声裹挟着滚滚往事而来,刹那间将他带回稻米流脂的开元盛世,带回“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少年时光……杜甫忍不住老泪纵横,他的周边,那些自中原流落此地的遗老,都在歌声里落下泪来。像世间所有好物般脆弱和令人感伤,李龟年的歌声,大约也是四十年前的盛世留下来的稀缺的馈赠。杜甫未能想见,暮年还有幸聆听来自故都的歌声。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老朽的生命已无法拥抱盛开的春天。在每一片明媚背面,他都想起破碎的河山,他的悲怆,连春天都无法稀释一二。
3
注定是不平静的春天,四月下旬的一个深夜,潭州城内喊杀声震天,一场兵变风暴席卷潭州。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死潭州刺史崔瓘,潭州大乱,杜甫与家人再次踏上逃难路。
“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这是杜甫写的《逃难》诗。
辗转无望中,杜甫收到舅父崔伟的信,崔伟在郴州担任录事参军,信中提及让他带上家人到郴州避兵灾。
去郴州的船经过衡州,进入耒阳境内,竟赶上连日暴雨,大水困住江上过往舟楫,困住来往商旅,杜甫的船躲到郴江岸边的方田驿中。老天爷像被谁触怒了,不断向人间撒气,古驿荒村,水势浩浩汤汤。无家可归的人,蜷缩在驿站深黑的角落,车马不闻,唯有雨声敲打瓦檐,敲打着不眠不休的荒凉和烦闷。
雨困住了船,困住了脚步,困住了流驶的时间。从白天挨到夜晚,从夜晚挨到白天,躲避于驿站中的灾民无处觅食,饥肠辘辘。无休无止的饥饿,撤退了又再次进攻,不断侵袭着诗人的胃,带来死亡的威胁。“这是生命末路的光景吗?老天要以这样一种方式置一家人于死地?”他扶着竹杖,立在驿站亭沼上,向着大雨如注的苍穹发问。水四处奔突,耒江在他脚下漫漶开去,横无际涯。整整五天四夜,除了水,一家人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供填饱饥肠的食物。饥饿的折磨,让时日变得漫长而残忍,杜甫不止一次想到了生命的末路。
第五天,耒阳的聂县令得到杜甫受困方田驿的消息,即刻派人送来牛肉酒食,外加一封慰问书信。聂县令的这一举动,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了不起的温情之举,是苍凉人世对绝境里的诗人的温暖一瞥。杜甫感念他的恩情,吃了酒食,当即于驿站写下一首向县令致谢的诗:《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他想着要当面将这首诗呈给聂县令,但他们终究未能见上面,谢意就这样长久地留在了纸上。
那场大水,改变了杜甫的行程,他们重新上船,依然无法南下郴州。杜甫心里再次生出一点期盼,想着何不干脆沿汉水北上呢?船就掉转了方向往北去。但他隐隐感觉到,或许走不出湖南了,他有还乡的心,却无力穿越迢遥的还乡路。
从夏到秋,从秋到冬,船啊,只是漂浮在湘江上。长期的水上生活,令杜甫的风痹病越来越严重。偏瘫、耳鸣、手颤、糖尿病、牙齿脱落……身体的痼疾和家国的愁绪交缠在一起,像海浪侵蚀泥沙堆积的堤岸,一次一次侵袭他。船在湘江上行着,青天在上,水在下。冬天深了,时日将尽。一家只剩下四口人,儿子宗武,老妻,还有他,另一个儿子流落异乡,女儿已饿死于逃难路上,小女儿的死,他只在最后的诗中道出来,当时锥心的痛,是无法进入文字的。米已越来越难见到了,终日以藜羮为食。那只蜀地带来的乌皮几皮开肉绽,只好用草绳层层缠起来。
船在湘江上走着,青天在上,水在下。他越来越乏力了,寒气交织着湿气,江水漫漶啊;他越来越恍惚了,时日将尽,音书渐绝。“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他的世界很小,小到连腿都伸不开了,小到只剩这立锥之地了。他的惆怅很大,漫过整个帝国的黄昏。
船在湘江上走着,青天在上,水在下。冬天深了,时日将尽。他以左手写下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杜甫的笔发出的最后一声叹息。一生的艰难和困厄重回他的诗里,他的心挂念着受难的人,挂念着干戈难平的中原,挂念着与他一样在大唐微弱的喘息里挣命的无望的生灵。
公元770年深冬,杜甫死在船上。
他一生的远行始于船,终于船。
清醒的酒话
若说饮酒也有基因,我们家族里的人恐怕没有多少天生的饮酒能力。记忆中,只有祖父好酒。祖父之好酒,并不出于对酒带来的醉意的迷恋。他只在每天午饭或晚饭时,热小半壶酒,悉数斟在一个小碗里,恰好平平一碗。不论大节还是平常日子,祖父只喝那么一小碗,不增不减,不追求酒的品类,一碗祖母酿的米酒,半浊不清的,他喝了大半辈子。祖父的酒,好比餐前开胃菜,简单实诚,是农家的喝法。
我印象中饮酒的情形就是那样的,我以为酒是一种特别质朴的玩意儿,想喝的人喝它,不想喝的人不会去碰它。好比有些人喜欢吃鱼,有些人爱蔬菜,有些人好甜食,有些人爱辣。年岁渐增,才发觉酒是不能和柴米油盐放一块儿的,有些路边小摊上写着“酒菜面饭”,这也着实属于不负责任的归纳法,草率了些。酒就是酒,菜、面、饭,或者柴、米、油、盐,你们可以归结到一处,酒是不能和这些东西混为一谈的。我这么说,是因了在芜杂世事里,我突然发觉酒并不全为身体的需要存在。很多时候,并不想喝酒的人也要拼命喝它,想喝酒的人不一定随时随地能举杯畅饮。喝或者不喝,真是一个问题。
酒是必需品吗?设若不是,为什么即便最偏僻最贫瘠的小山村,家家户户也会酿酒呢?当然,也可以理解为酒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后来,我隐隐悟到酒是一种生活的尺度,表明在解决基本温饱以外,人还有余力备下另一些物品,这大概是落后、原始又贫穷的人家也酿酒的缘故。酒当然也是一种待客之物,它是仪式感的重要部分,在好面子的国人这里,总要向来客表明有额外的礼遇,农家向来没有更多珍奇,此时就需要在碗里斟上酒,好比过年时贴上春联,元宵时挂起红灯笼。
酒怎么可能是必需品呢?刚才说了,它不能和居家日常填肚子的东西放一块,酒是另外的部分。它复杂多变,有时隐身于日常生活,常常跳脱出普遍形态。你可以说酒是情意的化身,哪一场重逢和离别缺得了酒呢?你可以说酒是得意的伴侣,哪一次成功和胜利缺得了酒呢?你可以说酒是沮丧和失望的替代品,哪一回爱情的失去生意的失败,不需要一场宿醉呢?一场不够,就再来一场。酒似乎能解决所有问题,醉酒之后,怂人都能成为帝王,土猪也能插翅飞翔。酒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宿醉醒来,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猪还是猪,狗还是狗,现实会给苍白羸弱的酒鬼一记更响亮的耳光。
大人嘴里有这样一句话:“你还小,不要碰酒,不要抽烟。”于是,少年成为男人的第一件事,就是躲在巷子里,偷偷拆开一包烟,或者在街角,买瓶酒独自喝掉,仿佛做成了这件事,便宣告长大了一般。第一次大醉,是师范二年级,一群十七岁的少年躲在寝室对饮。天气已是深秋,室友从实验室偷出三盏酒精灯一个铁架台。没有想到实验器具在那一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热黄酒。这大致也是我们学习生涯里少数几个富有创造力的时刻,以无限的求知欲积极拓展了实验器材的功用。
校园角落藏着一家小卖部,卖各种日用杂货,考虑到穷学生手头拮据,饭菜票通用。几个少年风一般穿过五楼长廊,沿水泥楼梯跑下去,买了十袋黄酒,那种塑料袋包装的黄酒,通常用来做料酒,一块五一袋,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叠皱巴巴的边角起了毛的菜票,拍在黑乎乎的玻璃柜台上,当然,还顺带拿了三袋“老奶奶花生米”。
酒和下酒小菜都有了,忽然觉得自家寝室五个人还缺点声势,就跑到隔壁班寝室招呼:“喝不喝?”那边周末还留在寝室里的三个人,呼啦一下,趿拉着拖鞋就来了。
长风吹过,秋意肃杀,窗外黄叶飞落。酒精灯点起来,酒倒进搪瓷杯中,搁在铁架台上。火苗刺刺响,蓝色的外焰像蛇的舌头舔着掉了瓷的搪瓷杯,酒气弥漫开来。八个少年或站或坐,一派青涩模样,有的唇角刚冒起淡淡的髭须,有的脸上遍布青春痘,有的头发乱作鸟窝状。热好的酒倒在搪瓷碗里,玻璃杯里,塑料杯里,五花八门,大伙儿一气儿喝下去,杯盏交错,大话连篇。说了什么话,谈到什么事,全忘了,只记得一杯接着一杯,一碗连着一碗的酒。十袋酒哪够,大伙儿便都掏出饭菜票,归拢在桌上,派另一个人下去,这回索性买了二十袋酒。不到一个小时,又喝完了,八个少年,大都有了醉意,酒兴却高涨着,像燃得正欢的柴火,仿佛不拼出个胜败高低,就不歇手。又下去,买了三十袋酒上来。从午后一点直喝到夜幕降临;从站着、坐着,直喝到悉数躺下;从高谈阔论直喝到全场哑然;从神采飞扬直喝到面目模糊,这场酒才告一段落。
后遗症很快显现出来。烂醉如泥的后果是,八个人在各自寝室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我们寝室几个都吐了,直接吐在床铺旁侧的地上,也没有人起来打扫,秽物一片,东一摊,西一摊,上面横七竖八铺了些毛边纸,馊而酸的臭气热烈汹涌。第二天,周日下午,两位事先回家去的同学返回寝室,立在门口,久久无法入内。
这是年少无知的醉,并不懂得酒的滋味。只懵懂地以为饮酒的姿态就是一腔豪情壮志。没有真正进入生活的人,都会从表象理解生活,以为生活只有清醒和喝醉这两个面。
喝酒远不是将自己灌醉那样简单,它内里丰富,有着多样的生命况味。起先只以为喝酒是张扬的,是豪迈的,就像少年的理想,烈焰高扬。时间长了,才会发现,单纯的一醉方休就好比天真的少年心气般奇缺得很。
十八岁那年除夕夜,餐桌上破天荒出现一瓶红酒。那差不多是我家出现的第一瓶红酒。父亲在时,是不饮酒的。偶尔亲戚朋友来,到小店里打半斤酒,也是有的,但都是黄酒。而夏天里来客,就去小店拎一瓶冰啤酒算作招待。那时,在乡下农村,红酒是另一种玩意儿,是一种西式的浪漫,它在电视中,在屏幕里的广告上出没。我大概是被电视广告蛊惑了,要么就是被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蛊惑了,特想在大年夜的餐桌上弄瓶红酒。
红酒是继父带来的,那是他到我家第二个年头。他的生活单调枯寂,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喝酒是唯一爱好。听到我和妹妹提及大年夜最好准备一瓶红酒,他就在某个空闲的日子,跑去买了一瓶红葡萄酒回来。这是父亲离世后,我们生活里一个难得的相对趋于完整的大年夜,如果家是一个房子,先前就好比缺了一堵墙,现在又重新竖起了一道墙。尽管,母亲依然会悄悄抹眼泪,但我们的大年夜已从前几年的凄清里挣脱出来了。母亲烧了她拿手的菜,红烧猪蹄、炸春卷、煎带鱼、青菜面结汤……这些再家常不过的菜,都是她认为节日里必须要有的。菜家常,母亲的手艺却是精湛的,春卷焦黄、青菜碧绿,猪蹄透着香气热烈的光泽。菜都上到那张从旧货市场买来的小圆桌上,桌面坑坑洼洼,圆桌上的白炽灯灯光黯淡。可这分明是一个不一样的夜晚,窗外鞭炮炸响,烟花的影子偶尔透进窗子来,一闪一闪的。我和妹妹都没有像以往那样,只要餐桌上出现一道菜,就拿筷子试吃一口,我们多么想要一顿体面的年夜饭!这份体面来自母亲心里燃起了一点过节的心绪,来自这个家一个空缺的位置被填补了,更来自……怎么可以忘记那瓶葡萄酒呢?这才是真正的体面呀。至少在十八岁那年,我心里是这么认定的。
我们当然没有忘记那瓶酒,这不是等母亲也坐到餐桌上来吗。喊了好几遍,她才围着围兜坐下来。我们期待,给母亲碗里也斟上一小碗葡萄酒。
我们没有想见那瓶葡萄酒会带来诸多难堪。当剥去瓶盖上的锡纸小帽,我们才惊觉里面是一个软木塞,也才想起,要喝葡萄酒得有个叫开瓶器的东西。我们家是断没有配备过这玩意儿的,那瓶零卖的葡萄酒自然也没有配备。
怎么办呢?首先想到了剪刀,用剪刀头翘,可没翘两下,软木的碎片就掉了出来,它是一点也绷不住力的。又想起螺丝刀来,那种扁嘴螺丝刀,直直往里插进去,再使劲往外翘,效果和剪刀相差无几,也只是掉下来几块软木碎片,一点没有破坏整个酒瓶的密封性。这下全家人都急了,我注视着酒瓶长长的脖颈,注视着里面深色的液体。生出一个念头:不可以把酒瓶头部那截敲下来吗?但这个想法被家人阻止了:“如果玻璃屑落进酒里呢?”再次拿来那把银色的剪刀,往软木塞里左右旋转,再使劲将筷子伸进去,抵,压,翘。噗一声。别以为是软木塞弹出来了,它进去了。
那深色的液体上,漂浮着一截不规则的软木塞。
倒酒,没有人表达异议。
我终于能喝到一口期待的红酒。酒注入白色小碗里,深红色的液体上浮着一些碎木屑,我就用筷子将其一点一点夹出来,还好不是很多。我想提议,端起碗来,碰一下“杯”,但随即这个想法又被心里的一股羞涩压制住了。只好自己默默端起碗,呷一小口,才明白红酒带着点苦味,但味觉不敢确认这是苦的,更不敢确认这是不好喝的,毕竟那一刻,我们的心都因这瓶酒的出现充满了某种不可言喻的神圣感。多年之后,回想起那个夜晚,那酒的滋味才泛起久远的心酸和苦涩来。
二十七岁那年,也是冬夜,在甬城战友饭店吃饭。吃饭的真正目的是分稿费。说来话长,文学圈里几个老人接了一个写传记的活儿,折腾着要给一个台商写本传记。那位台商八十高龄,住在城西四明山某个深山别墅中。由我跟青年小说家赵共同执笔创作,赵写初稿,我润色文字。我们俩折腾了大半年光景,每天花去一大把时间在这本传记上。二十岁不到的赵更是不辞烦杂,为了采访,乘着中巴车到四明山脚下,再打电话让对方开车下来接进山去。如此这般,颇牺牲了一些与夜晚的清风月色幽会的时光。终于整出洋洋洒洒一本二十五万字的传记。最终却落到“名分不保”的地步,传记作者署了台商的名,摇身一变成了自传,我和小赵则以“文字整理”的身份出现在那本书的旮旯里。这般地位,处在古代大户人家,就不是小妾之流可以比拟的了,差不多是婢女吧。不过好在我们也不在乎那劳什子的署名,只想着辛辛苦苦换来的劳务费,当然称为稿费也成。左等右等,等去半年,眼看新的一年又要来了,我和小赵才被一群“筹备组”的老油条约上吃顿饭。传记筹备组临时组成的“老板们”一一向我们敬酒,充分肯定了两个年轻人的工作。酒过三巡,终于谈及钱的事,总标的十万的写书酬劳,我和小赵分享五分之一——两万,他拿八千,我一万二。那时,心里说不上失落,觉得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将一个鼓鼓的黄皮信封塞进大衣衣襟内袋里。继续喝酒,这不是什么庆功酒,不是什么凯旋的酒,这是另一种滋味的酒,是打工者拿到辛劳的酬金的滋味。好在我和小赵都年轻,并不计较那么多,我们甚至为“老板们”的难处动了恻隐之心,他们说“十万元,刨去各项成本,真是分文未赚。”他们那么讲,仿佛只是给我们两个年轻人制造了创收的条件。
脚步踉跄着离开战友饭店,酒已上了头。走到门口,北风刮得紧,仰头一看,满空的雪花自路灯昏黄的光线中倾泻下来。我不禁掖了掖衣领,摸到大衣口袋里那一沓钱,身上涌起一点暖意。迈开步子,踏着被雪打湿的地面往公交车站走去。许多年后,我一直记得那晚的酒,记得酒后那一场纷扬的雪,记得背后那小饭店的名字。
喝酒,又是见性情的事。我个人狭隘地认为,一生中从未喝醉过一次的人,是不可交的。同样,喝酒中处处算计别人,鼓动别人,想着灌醉别人,自己却在酒里偷偷掺入白开水冒充豪迈的人更不可交。
有些人,喝酒根本跟酒无关,喝酒是他的一个幌子,他借酒装“醉”,借“醉”的掩饰道出内心不可告人的话,做成清醒白日里做不成的事。对于这类人,酒是他的盾牌,是他的烟幕弹,也是他的势,仗势欺人,顺势而为,依势而下。与这样的人喝酒,你要小心了。
初入机关那年,遇到过一个上司,此人平常内向闷骚,到了酒场,却颇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深信喝酒就是排兵布阵的游戏,得合力为之。下属中最低阶的先上,接着中层冲锋,第四第三第二把手断后,最后双方十死九伤之际,第一把手出场。以至于每次吃饭,喝酒都成为一种交战。我不善饮酒,吃饭就成了一种颇有压力的强迫。上司还有一个理论:一个人的职位要跟酒量成正比,现在你能喝一瓶啤酒,明年就要两瓶,后年三瓶。酒量上去了,职位也就跟着来了。你问我信不信这事?现在当然不信,但当初,我还愣是信了。一个智慧和经验都远远不够用的年轻人,最擅长的举动就是对上司的话言听计从。于是我端着酒杯,装作酒量还不错的样子,频频出击,随后在吃到中场的光景,躲进卫生间狂吐。那是我们人生中喝过的最无趣的酒,一个单位的人坐在一张桌子上,个个如临大敌,恐怕只有第一把手充分享受到了酒带来的快意,毕竟只有第一把手获得了喝酒的自由权。好比坐山观虎斗的猎人,心里暗自窃喜着。
年岁渐长,尽管智慧仍然短缺,但有了些许吃饭的经验。确实,在中国,吃饭也是需要一点点经验的。否则,文明悠久文化灿烂的中国人不会称吃饭为饭局,喝酒则为酒局。局是什么?局是一种陷阱和套路。年岁渐长,越来越喜欢和爽朗的人一起喝酒。喜欢喝就喝,不喜欢喝就不喝。能喝就多喝,不能喝就少喝。兴致来了喝它个酩酊大醉人仰马翻,兴致没了,就嘬一小口,润润喉咙罢了。我喜欢看老实人的醉态,仿佛酒就是一把钥匙,打开了那束缚他的镣铐,他心里深藏已久的欢快像春天枝头的红杏,试探着冲出墙外来。试想,从来古板的人发一次酒疯该是多么好玩的事。我也喜欢看真正的诗人喝酒,他们喝到七分醉,就能随口吟出不俗的诗句来,身体里孩童的真纯与好玩都跑了出来。有一回,酒过三巡,大伙儿从小饭店撤出,一道晃晃悠悠走在城市街头,走着走着,突然发觉少了一位。打他手机也不接,这倒让人心里有些发毛,就在原地等,左等右等,还是未见人影。大家只好继续踱步向前,复走出去几十米,有人眼尖,远远望见旁边人行天桥下的草地上躺着一个人。大家便走过去,走近了,才发觉那人跷着二郎腿,面朝夜空仰躺着。再近些,好家伙,不正是那个突然失踪的诗人吗?大家以为诗人喝到不省人事了,纷纷伸出援手。一只只手都被挡了回来,诗人说,这点酒根本醉不倒他,走到此地,他是突然想躺着看看月亮。抬起头,才惊觉中天一轮橙黄的满月,满盈盈地,一脸沉静地望着我们。就不好再打搅了,一行人撤出了绿草地,离开了天桥那一小片阴影,留诗人独享吧。
年岁渐长,越觉得喝酒是一件见性情的事。还没倒上酒,还没打开酒瓶盖,有些人就开始介绍自己的酒哪儿产哪儿来,多高级,他喝的自然不是酒,是酒的牌子与身份。现实中确实大有人活得无比虚幻,有人不炫耀灵魂的高贵,而是炫耀与之无关的皮囊的精致。有人连皮囊也不炫耀,而是炫耀衣服。有人不炫耀见识和智慧,而是炫耀学历证书。有人不炫耀生活本身的质量,而是炫耀房屋的套数和汽车的牌子。
我却觉得喝什么酒是说明不了事的,好比拎什么包,割哪种款式的双眼皮一样无法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谁一起喝,和谁一起喝醉,大概才是喝酒中最能见本心的事。
年岁渐长,发觉喝酒中最次的境界是一堆人,一大桌,甚或几十桌,觥筹交错,吆喝震天,种种喧嚣都与酒的本意格格不入。比较好的饮酒的境界肯定是小酌,三五故人,一二知己,于清秋小院。傍晚,屋内掌了暖色的灯,室外正铺开绚烂的晚霞。于桂花树下,置一小木桌,喝清淡的酒,聊浅浅的往日,馥郁的花香则一阵一阵地光顾,熏香了衣衫。
隆冬的雪天,一小家子人,拥火炉围坐,烫好绍兴炭雕,小白瓷杯,慢慢啜饮。
或者夏日,和心爱的人赤脚坐在沙滩旁的大阳伞下,迎着猎猎海风,来一杯冰镇的扎啤。
或者在旧木屋中,听雨落屋檐,和性情相投的兄弟们,喝家酿的浊酒,吹牛到深夜。
和意气相投的人,小酌,豪饮,谈笑忘机,这就引出了生命的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