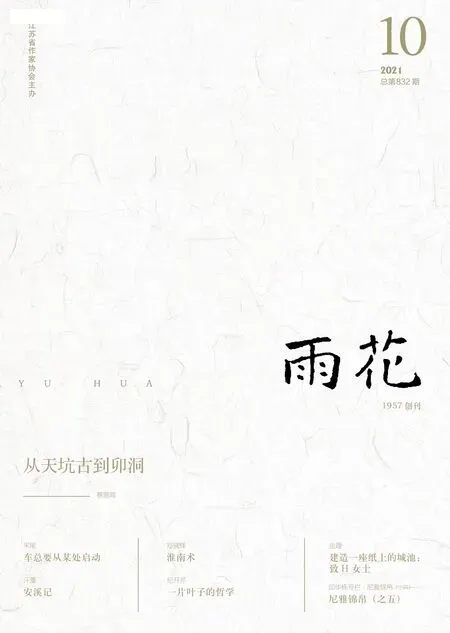纸上的故乡
周华诚
我现在要从这旧时光里,翻拣出一个故乡来。故乡不是一个空洞的大词,也不是一本生硬的古书。它是纤细幽深,是盘根错节,是一张又一张叫得出名字的面孔,是一个黎明接着一个黄昏;是山坡,田地,五谷与溪流;是羊群,鸡鸭,争吵,婚嫁,生育甚至死亡。
——题记
读清雍正《常山县志》。秋深,叶红,树下读高头讲章,颇有些枯燥,配瓜子一碟,清茶一杯,也就舒服了。由此可见,很多时候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配角。
闲有闲的读法。也好。譬如,闲的时候,就挑犄角旮旯的东西读。无关宏旨,鸡零狗碎。其实于乡间日子,鸡零狗碎也就是宏旨了。
方言
常山据浙上游,水陆交冲,土瘠赋重,疲敝甲海内。丙申秋,予适承乏。积驰之余,牍纷丝纠,弊丛峰房,村冷爨(读音[cuàn],烧火做饭)烟,野滋丰草,思得邑志一观,庶几暗室之炬,而镂板散失,怅然怀之……
(清嘉庆《常山县志》序,顺治十七年庚子夏五,邑令王明道题)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然而现在很多人,虽是从乡间出来,乡间的许多事却已是不知了。
我的故乡在浙江,祖先是从江西迁入,所以村人口上流传的是江西方言。而今,村中黄毛小儿都学习讲普通话,弄得从未正规上过学的老辈人,也得讲普通话才能与孙儿交流。无奈那普通话说得磕磕绊绊、别别扭扭,听来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其实方言并没有什么不好。
方言的流传里,有着多少文化的因子呀。
我现在久居城市,没有讲方言的环境了,但幼时许多方言的词汇,依然会在我写文章的时候冒出来,使我霎时一愣,觉得那个字真是传神。
我便有心用文字记录一些故乡的风物。
此次回乡过年,偶尔得到几册旧时《县志》,欣喜不已。随后两日,我徜徉于旧志书页间,在那些简练至极的文字里,读出许多亲切来。
略感遗憾的是,县志还是宏大了些。关于我一村之物,记载仍是不多。
不过,我现在要从这旧时光里,翻拣出一个故乡来。
万历年间,康熙年间,雍正年间,那时修志之人,怕正是要把他的故乡的样子呈给我。恍如对坐,闲说乡人旧事。
从这个意义来说,官方修的志,还是太端庄了些。
多希望有一个发须皆白的老头从旧志的书页间走出来,用乡音与我漫漫闲谈呀。
水稻
稻,分粳、糯,各有红白二色,又各有迟早不同。
麦,有大麦,有小麦,又有荞麦。
菽,即豆,有青豆、黄豆、紫豆、绿豆、赤豆、蚕豆、刀豆、豇豆。
黍,俗名芦粟,有粳、糯二种。
粟,粳者作饭,糯者炊粥。
芝麻,有黑白二色,膏可压油,故俗称油麻。
(清雍正《常山县志》之“物产·谷之属”)
风吹稻浪。我站在田间,手握一把镰刀。许多年了,我望望远方,也望望脚下。常山乡间的土产稻种,现在是愈来愈少了。不只是常山,全世界的水稻品种都愈来愈少。上次到中国水稻研究所去,沈博士带我们参观“种质库”(不是种子,是种质),或者叫“基因银行”。那是一个巨大的冰箱,收藏着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水稻种子资源——全部是常规稻种的资源,杂交水稻不作保存;而且,他们每年还会增加几千份收藏。
这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常以为,水稻嘛,不过就是那么几种,籼稻、粳稻、糯稻。其实都不一样。每个地方原先都有不同的水稻,也就是“土水稻”。云南出红米,江西井冈山也有红米,陕西洋县有黑米。这些土水稻有什么好?好就好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水稻(或者说,这世上有多少种人,也就有多少种水稻)。这土水稻,无论它繁殖多少代,长出的水稻产量和品质都不会有什么变化。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产量很低,所以农人种着种着,也就不愿意种了。于是,这些土水稻的品种也就不断地消亡。
我们现在日常能吃到的,大多是杂交稻。杂交稻,由不同水稻品种杂交而来,品质好,产量也高,缺点是只能生长一代。农人若把杂交稻的种子留下来,第二年种下去,将颗粒无收。因为杂交稻的染色体已经变化,不会繁殖了。
《县志》上说,常山的水稻各有红白二色——这是土水稻的样子,我是没有见过红色的。事实上,常山种植的“粳稻”并非粳稻,是籼稻。粳米短肥圆,东北米即是。南方的米,修长一些,都是籼米。口感上也不一样,籼米多干爽,粳米黏性强。沈博士这几年主要研究“长粒粳”,已经突破了重重障碍,各种各样的长粒粳在他的手上诞生。每年,他仍然会从那个巨大的、浩如烟海的种质库里,按自己需要的方向,取出十来份水稻资源,进行他的研究。
沈博士说,水稻的故事,就是坐下来说几天几夜也说不完。譬如,有一种海水稻,就是在海滩和盐碱地里也能生长。虽然产量低得可怜,但在科学家眼里,这几株海水稻可就是宝贝。有一次我在海南陵水县,到水稻科学家们的田间去看,各种各样的水稻长得形态各异。怪不得农民会开玩笑说:“还水稻专家呢,这水稻还不如我种得好!”
话说回来,我老家,现在只有糯米是自家留种的。糯米属于常规品种,每年秋天收割之后,父亲就挑最大的穗头,割一大把扎好,挂在墙头晒干。这一把穗子,就是来年的种子了。不知道这些稻谷的种子,代代相传,历经了多少年。江西万年县大源仙人洞,出土了距今约一万一千年的水稻;我们现在耕作的水稻,以及碗里的米饭,是不是跟那些先民有关?
有一次我在广东,参加一个散文创作研修班。一位社科院的老师说,中国的农民终将消失。这是从经济学的宏观角度来看的。但我以为,只要土地还在,水稻就一定会在——一个只有工厂没有田野的世界,将是多么可怕;只要还有土地,就一定还会有人种田,不管他的户籍本上写着“农业户口”还是“非农户口”,他依然是一个农民。种田的手段也许会变,可能是开着飞机种田,但那有什么区别呢?一万年以后,我相信故乡的土地上,依然还会有水稻生长。尽管,它们也许无法避免地,会很孤独。
麦子
麦,有大麦,有小麦,又有荞麦。
菽,即豆,有青豆、黄豆、紫豆、绿豆、赤豆、蚕豆、刀豆、豇豆。
(清雍正《常山县志》之“物产·谷之属”)
在稻之外,雍正《常山县志》还写到麦、菽、黍、粟、芝麻。
从前说的“五谷”,分别是稻、黍(黄米)、稷(高粱)、麦、菽(大豆)。另一说,则是把“稻”换作“麻”。这五种庄稼到底是什么样子,估计很难有人分得清了,现在的人真正实现了“五谷不分”,是不是也算一种进步?
荞麦,故乡并不多见。荞麦多被用来酿酒。有一年,我骑车越过山丘,见梯田里漫布一片白色碎花,也不认得那是什么。后来拿了照片回去问母亲,母亲说,那是荞麦。这倒让我吃了一惊,原来荞麦的花也是这样美好。
乡人用荞麦配比粮食谷物焐烧酒。荞麦烧比谷烧价钱要贵,因为大家觉得荞麦烧好。好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吃起来觉得,荞麦烧要烈一些,谷烧要柔一些。听说番薯烧、玉米烧、高粱烧性子都烈。谷烧即使是56度,我也觉得入口颇柔,大约是从小吃稻谷长大,比较适应此酒。吃惯了谷烧,也就不喜欢吃别的烧酒了。
焐酒是很好玩的:
放进去稻谷,焐出来是酒。
放进去荞麦,焐出来是酒。
放进去番薯和高粱,焐出来是酒。
放进去爱情,焐出来一个孩子。
放进去时间,焐出来苍老的农夫。
不说焐酒了,还是说荞麦。荞麦开花,比水稻开花好看。月明荞麦花如雪。
事实上,大麦、小麦,与荞麦相距甚远,连远房亲戚都算不上。麦是禾本科,荞麦是蓼科。
晚稻收割后,乡人多种冬小麦。
《县志》上有“农八条”,其中有云:
“农贵乎尽地力。常山与西安接壤,然西安田亩多,于四月栽秧,六月获稻。获稻之后,急种黄粟以乘其隙,谓之偷空。九月收粟,则又及时种麦。其地亩则二月初旬,即于麦陇中种豆,四月刈麦,六月刈菽。菽麦登,则种芝麻、黄粟等物,既收则又种麦,为来岁之计……”
这是说,农人要学会弹钢琴。要在有限的光阴里,让土地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不要无谓地荒废,无论是光阴、土地,还是人的力气。
《县志》上的“农八条”,几乎包括了精耕细作的所有要求——农贵乎力勤,农贵乎粪多,农贵乎开塘,农贵乎置具,农贵乎通沟,农贵乎尽地力,农贵乎乘天时,农贵乎齐人力。
农业是件大事。富兰克林在其所著的《四千年农夫》中写道:“中国南部一般都种双季稻,在冬季或者早春时节,田里可能还会种植其他谷物、卷心菜、油菜、豌豆、黄豆、韭菜和姜等农作物,不停地轮作以使农田全年食物总产量最大化。”他说,“由此,人们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用于思考、劳作和积肥,这些工作超过了美国人所能接受的极限。”
土地和人一样,需要休养生息。农人有很多好的方法,来让土壤保持肥沃,比如轮作。在晚稻收割前,人们会在田间播种紫云英的种子,在晚稻收割之后,紫云英可以一直生长到下一个插秧时节。紫云英是牲畜的青饲料,也是肥田的好植物。科学家用了三十年时间研究发现,紫云英这样的豆科植物,能把空气中的氮转入到泥土中。此外,农人几乎是下意识地,会在田埂上种满各种豆类,豌豆、黄豆、绿豆、豇豆等等。
中国人之所以“农贵乎尽地力”,一年四季排满了劳作的日程,几乎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我小时的记忆里,乡人在六月收获早稻之前,常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生活的窘境:青黄不接。许多人家不得不借粮,收获后归还。而在收获之后,这样困窘的状况并未得到多大的好转:绝大部分所得都要用于交“公粮”。上交“公粮”并归还借粮之后,粮仓里已所剩无几。
要有饭吃,农人不得不把所有的力气用于耕种。而即便如此,他们的生活依然无法过得优渥。
数千年来,农业一直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到了现代社会,工商业取代农业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农业税赋于2006年取消,农人再不用交“公粮”,肩上的压力一下子轻了许多。
美国人富兰克林在一百年前写下这样的句子:
“农民就是一个勤劳的生物学家,他们总是努力根据农时安排自己的时间。东方的农民最会利用时间,每分每秒都不浪费。”
直到今天,我故乡的农人们依然如此——他们不仅仅种水稻,还依据现在已经成为世界“非遗”的二十四节气,种植小麦、油菜、豌豆、黄豆、番薯以及其他各种蔬菜瓜果。一年到头,他们精打细算,统筹安排。他们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而更多的农人,早已离开土地。他们的麦田已经长出了工厂。
纸砚
纸,大小、厚薄、名色不同,其料不产于常山,惟球川人善为之,工经七十二到。
砚,有紫石,有黑石。原《志》云“山已刳尽”,今更百余年,存其名而已。
苎麻,江西、福建人垦山广种。常民多利其税,然刳山取土,培壅麻根,遂致抛弃棺骸,伤残龙脉。惟绩为女工之一,而常民弃不肯为,有害无利,识者忧之。
(清雍正《常山县志》之“物产·货之属”)
从四川夹江买了两包手工粗纸。打开,隐隐有竹料腌塘气息。
本来是想用来写毛笔字。写了几天没有长进,就丢下了。有一次给朋友寄书,怕快递莽撞磕坏了书,就找了几张黄纸包了寄去。朋友收到,说有雅气。
其实没有。不过是两张纸。有的,怕还是竹料腌塘之气吧。
以前在衢州,这样的竹料腌塘是很多的。腌的竹子,用来造纸。
2004年6月28日,我写的一篇通讯短文刊登在《浙江日报》上,题目是“衢江终结千年土法造纸”。文章不长,姑且摘录于此:
把青毛竹劈成片,用石灰或烧碱腌在塘里数月,再送进小造纸厂经过粉碎、捣浆、漂白等工序后制成一张张毛边土纸……随着最后一家土法造纸企业的关闭,这一沿袭千年的民间土法造纸工艺,6月中旬终于在衢州退出历史舞台。
衢州市衢江区盛产毛竹,自古有以竹造纸的传统,到去年仍有26家土法造纸企业,年产土纸约两万吨。因工艺原始,这些企业年排放废水数千万吨,全年排放污染物COD(化学需氧量)在3600吨以上,超过国家排放标准四至十倍。
去年以来,该区依法关停了这26家竹造纸企业,八千多个竹料腌塘被平毁,毛竹制纸转向竹制品深加工,昔日恶臭袭人的腌塘如今种上了蔬菜、绿树,溪流恢复清澈。
那是我做记者的第二年。这个职业,有一点好,可以见证一些事物的出现,也可以见证一些事物的消失。
然而余生也晚。老家常山县,据说在明清时期,造纸业还颇为兴盛。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述,“衢之常山、开化等县人以造纸为业。其造法采楮皮蒸过,擘去粗质,糁石灰,浸渍三宿,蹂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复蒸之。濯去泥沙。曝晒经旬,舂烂,水漂,入胡桃藤等药。以竹丝帘承之。俟其凝结,掀置白上,以火干之。白者以砖板制为案桌状,圬以石灰而厝火其下也。”把造纸的一道道工序,都记述得很明白。
球川系一古镇,旧时曾有一景,曰“球川晾雪”,说的就是其纸业繁盛时的景象,十里溪滩,皆晾满白纸,望之如雪。这景象,后来消失,我也无缘得见。
至于砚石,历史上也有。现在常山县与江山市交界之处,有一个地方名“砚瓦山”,据说明清时期曾出西砚,且是贡品。今已不存。旧时瓦当可以拿来当砚。
我在家乡的溪里玩,石头很多,菖蒲也多。我常捡石观赏而忘人之所在。溪石滑腻有之,粗拙有之,拾一块方正的做镇纸,拾一块粗陋的当假山——还没有拾到过合适做砚的。
十一月,与诗人志华兄同去安徽歙县,在古街一个小店里买得一方鳝鱼黄砚台。现在这方砚台与家乡的溪石一样,在我的书桌上摆着。偶尔从电脑屏幕上抬起眼来,看见这样的几块石头,一丛菖蒲,心就安静下来。
山泉
瀫泉,在县西十步。水味独胜,疑泉脉与瀫水通云。
孔家坞泉,在县后山之左。高峰环翠,隐士孔清植果园在焉。山泉盎溢,甃为石池,至今犹沾溉百家云。
詹家坑泉,在县前百步外。发源于白龙洞。山石壁峻耸,草木悬崖……后园詹西来因先世安乐窝,构金川书屋,贮图籍其中。诗载《艺文志》。
鲁家坞泉,在县后山之右。深源僻坞,内有涧水,甘冽殊常。
白露泉,在县北门外里许。康熙五十八年,岁大旱,僧天然感梦,从白露冈下探得泉源,遂名白露泉。剖竹接入奉恩寺中,甘冽出众泉上。知县孔毓玑有记,载《艺文志》。
严谷泉,龙山石壁嵌空,处处有泉沁溢。其清洌似白露,而泉味差薄。
(清雍正《常山县志》之“水利·泉”)
很欣喜在县志中读到这一节关于泉的文字。有一次,我与家人一起驱车几十公里至邻县开化,到龙潭公园坝上的智慧泉接取天然山泉水,运回泡茶。友人饮之,也赞不绝口。想到杭州有虎跑泉,济南有趵突泉,许多市民每天去泉边取水,成为城市一景。譬如杭州,早上六点多,虎跑公园半山腰的取水口就有四五十人排队,在一块岩石下面接水。除了虎跑这个最传统的接水点,杭州还有中天竺、梅家坞、黄龙洞、水乐洞等地,既有好景,兼有好泉。譬如济南,也有很多取水点,有些是市民长时间习惯、自发形成的,如琵琶泉、迎仙泉等,也有的是园林部门为满足市民需求而专门设置的,如趵突泉景区杜康泉取水点、黑虎泉取水点、五龙潭公园玉泉取水点等——总之,许多人早起,去取两桶水回家泡茶、熬粥,几乎是一种生活习惯与城市风物。
陆羽《茶经》上说:“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又说,“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陆羽的意思是,用山泉水泡茶是最好的,其次为江水和井水。
热爱饮茶之人,对水是很讲究的,水质好坏能影响茶汤滋味。古人钟爱山泉,因山泉多出于岩石重叠的山峦,山上植被繁茂,山岩断层细流汇出而成山泉,水质清澈甘甜。北宋皇帝赵佶不仅是艺术家,还是茶艺鉴赏家,他撰写了《大观茶论》,可谓宋代茶文化的重要著作。《茶论》中说到水的取舍,“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古人品水,虽曰中泠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常汲者为可用……”
这说明,有山泉水可取用,乃是爱茶人之福。
常山县城,怎么可以没有这样的一眼泉水,供爱茶人取用烹茗呢?也不知城里爱茶之人,是去何处取水的。好在现今物流业发达,网上径可购买桶装水来用。然而对于爱茶之人,若是自己从山上接水运回加以品饮,除了取水搬挪活动筋骨之外,又能增添自己动手的许多乐趣,茶益香,汤益美,一举两得,岂能废之?
县志上的这一节“泉论”,文字大美,所记之瀫泉、孔家坞泉、詹家坑泉、鲁家坞泉、白露泉、严谷泉,都在县城各处不远之地,徒步可至,读这些文字,仿佛可以感受到当时常山县城生态环境之美好,想那时小城遍地甘泉,若是称作“泉城”,似亦无不可。尤其是县令孔毓玑所写《白露泉记》一文,记北郊奉恩寺中白露泉事,读来令人欣喜不已。
前不久,县社科联曾举办茶文化圆桌派活动,数位专家学者、茶文化爱好者汇聚一堂,从常山茶叶的种植历史,聊到茶道、茶艺,我因事未能赴会。现在读到县志中的这一节,倘有茶人愿意推动,当可寻访城中诸泉旧迹,若旧泉还在,则疏浚清理,复其生机,亦可剖竹引泉,烹泉煎茶,不啻为小城一件雅事也。我则由此想到白居易的一首诗:
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
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
慕仙亭
慕仙亭,在县东南一里。万历初,邑人徐深为伊祖谦受家佣浮空立。
(清雍正《常山县志》之“亭台”)
浮空,不知何许人。洪武庚子,来佣里择徐益家。问姓名里居,不答,因以浮空呼之。尝为益董获,酣睡寝室,顾一日十余处俱有一浮空在焉。馈食上源姻族,计往返百余里,不数刻辄至。忽谓益曰:“君家有大难,请往营之。”益莫知所谓。乃徐氏有富户在京师得罪,将门诛。及行刑,会失富户名,遂得脱。盖浮空篡取私去其籍云。一日醉酒,朗吟曰:“人间功行满,天上梦魂高。”乃坐化。徐氏具棺殓,葬东明山。是夕,大雨雷电,以风启棺。尸蜕,遗一屦迹,深入石中。益孙深为作慕仙石亭以记其事。
(清雍正《常山县志》之“仙释”)
真是一个好故事,颇有《聊斋志异》的趣味,或《阅微草堂笔记》的感觉。《县志》“文部”说,“文章贵乎有用,是故风云月露多属可删。今其存者,大抵皆有关兴除之故,及人心、学术、民情、风物之宜,期于此邦多所裨益云尔。”的确如此,怪力乱神之类,一般不会收在这样的地方志书里,大抵还是以“有用”为标准。然而什么又是“有用”呢?除了人心、学术、民情、风物之宜,地方的故事传说,还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想到衢州有“三怪”,这也是蒲松龄记录在他的《聊斋志异》里的,也是衢州人老少皆知的传说。“衢州夜静时,人莫敢独行。钟楼上有鬼,头上一角,象貌狞恶,闻人行声即下。人驰而奔,鬼亦遂去。然见之辄病,且多死者。又城中一塘,夜出白布一匹,如匹练横地。过者拾之,即卷入水。又有鸭鬼,夜既静,塘边并寂无一物,若闻鸭声,人即病。”说是衢州城里有三个妖怪,独角怪、白布怪、鸭怪,一个躲在钟楼上,人深夜见了,就把人吓坏了;一个藏在县学塘,观音娘娘的白腰带变的,人若去捡拾,就会落水而亡;另一个是蛟池塘的鸭怪,夜深人静时也会出来害人。这几个怪物的传说流播甚广,人们也津津乐道,若有外地客人乍到衢州,本地人也会作为风物或地方文化,热心向客人普及,甚为有趣。
常山本地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应该也有不少,我小时候就听过一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故事渐渐被遗忘了。我想还能记起那些美妙或神奇的故事的人一定越来越少了。杭州有一本《西湖民间故事》,出版社的一位朋友跟我聊起过这本神奇的书,它畅销四十多年,一共卖了几百万册。不管对于新杭州人,还是对于杭州这座城市里刚刚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它都是一本必读书。如果你想了解杭州这座城市,就去读它吧。在断桥与西泠桥走一走,在雷峰塔边停一停,你会想起许仙和白娘子,想起可恶的法海,想起美丽可人的苏小小,这就是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传统文化;你吃着一块东坡肉,嚼着一根葱包桧,就会想起苏东坡、苏堤,想起奸臣秦桧,并把葱包桧嚼得“吱吱”响,这也是传统文化。如果没有这些,杭州这座城市将会黯然失色。
慕仙亭还能找得到吗?如果一座城市的传说与故事不可避免地会在时光里逐渐遗失的话,应该有人去做这件事,至少,仙是可以慕的,至少,在慕仙的时候,也会觉得这一个地方太好了,有仙气。
葛
菜,有白菜、青菜、芹菜、油菜、甜菜、冬菜、冻芥菜、苋菜。
莱菔,一名萝卜,小而赤者曰湖萝卜。
芋。薯。葱。蒜。韭。薤。芹。芫荽。莴苣。瓜。瓠(有大腹细颈者,老刳去其穰为瓢)。笋。姜。茄。蕨(根可作粉,贫民采以备荒)。
(清雍正《常山县志》之“物产·蔬之属”)
我走到菜场去看,摊上花色琳琅满目,不唯当季的蔬果,即便是反季节的蔬果,或是原产自热带的蔬果,现在也不罕见了。到底,农业技术在进步,物流条件更是今非昔比,蔬菜的品种,自然也比过去丰富多了。
我却只想到了葛——菜摊上并没有。葛是好东西。小时候上街,见有山里人蹲在街边卖葛,一根粗如手臂的长葛,已然煮熟,有人来买,就引刀横断,割下几片来。这是最朴素的卖葛之法——既不称重,也不议价,古风犹存。人家买了葛,就撕一小块下来,放进口中大嚼。这葛块甜津津、粉糯糯,嚼了一会儿,口中只余一些丝络渣渣。
我记得当年在县医院上班,偶尔也有同事带几片葛来,分馈众人,一人一片嚼而食之。
葛藤在山野极多,漫山遍野地攀爬,然而葛的生长又极慢,要许多年之后,那地下的葛根才长得粗壮结实,味道也尤甘美。挖葛是件非常辛苦的事。
有的山里人家,挖出粗壮的葛根来,敲打碾碎,磨出粉来,水洗,沉淀,晒干,制出葛粉。这葛粉与番薯粉、藕粉相似,但比番薯粉、藕粉都佳。西湖藕粉是好东西,天下闻名。上世纪20年代,影后胡蝶在拍《秋扇怨》时跟男主角林雪怀热恋,曾邀请郑正秋、秦瘦鸥等人游西湖。据秦瘦鸥讲,那天走到平湖秋月,他跟林雪怀发生了一点小争执,二人铁青着脸互不说话,气氛尴尬极了。后来,是胡蝶出面解围,请大家吃藕粉。
“亏得平湖秋月的藕粉,真不错,每人喝了一碗,不觉怒意全消,依旧说笑起来。”
好一碗西湖藕粉。
后来,胡蝶与林雪怀在上海闹离婚,秦瘦鸥听说了,忽生奇想:
“想到平湖秋月去买两盒藕粉来,各送他们一盒,使他们喝了,也能立即平下气来,言归于好;但我不该偷懒,始终没有去,于是就不曾调解成功。”
葛粉有这样曲折婉转的故事吗?也有的。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有一天,他邀请灵隐寺的韬光禅师进城赴宴,为此特意写了一首诗:
白屋炊香饭,荤膻不入家。
滤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
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
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瓯茶。
葛粉、藤花、青菜、红姜,都是又简单又美好的事物。白居易用心可谓良苦,然而韬光禅师这样的高僧,岂能为一顿斋饭动心,便也写了一首诗婉拒。
冯唐曾说,世间美好的事物都是半透明的。这话想来,还是很有意思的。
到朋友的民宿云湖仙境吃晚饭,饮的酒是自酿的葛根酒。这酒好,不觉就多饮了一两。朋友这几年从城市回到乡野,在山上引种了许多葛,夏天到来的时候,葛藤已然爬满山坡。朋友在山坡上搭了一个小小的篷屋,春夏秋冬,他都独自住在那里。
葛根们在土地里延伸生长,我想,它们也都是半透明的吧。
花红
梅。杏。桃。李。柰。莲子。梨。枇杷。橘。橙。柚。石榴。枣。栗(小者为榛,俗名茅栗)。菱(四角)。芡(俗名鸡豆)。林檎(一名花红)。柿。榧。荸荠。
(清雍正《常山县志》之“物产·果之属”)
我对林檎很感兴趣。
林檎也叫花红。我小时候吃过花红。苹果的品种很多,我到水果店里看到,苹果的品名各种各样,都记不住。有一次翻古罗马学者瓦罗的著作《论农业》,其中“储藏苹果”一节说道:“苹果中可供储藏的品种有小榅桲、大榅桲、斯坎提亚苹果、斯考迪亚苹果、‘小苹果’和那一般叫‘甜酒’如今通称‘蜜苹果’的一些品种……”
读《县志》,看到县里原先也是种花红的,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很多地方小品种都没有了,比如桃,本地品种的桃,有苋菜桃、毛桃、黑桃,现在这些都见不到了。李子也是,原来有一种本地品种的黄李子,也见不到了。
关于记忆里的那些蔬果,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收在散文集《草木滋味》里。这里姑且摘录一点:“我记忆中,乡下自家菜园子里的黄瓜,从架子上摘一根,胡乱地撸两把,把瓜刺儿弄干净了,就可以入口。一咬,嘎嘣脆!汁水丰富。滋味,是被阳光浓缩了的黄瓜的味道——真的是黄瓜,不像现在,黄瓜,都是青的瓜。”
是这样的。想想看,小时候的桔子,每一瓣都有浓重的桔子味。小时候的西瓜,那么多籽!可是没有天理,就是甜。水汪汪的呀,从田头抱回家,刚搁到桌子上呢,嘣!它自动就裂开了,西瓜的清香,在里头满了,绷不住,就飘了出来。现在的西瓜,你用拳头砸砸看。
是不是记忆里的事物,只是因为时光的阻隔,而给它加上了修饰的滤镜,变得一厢情愿地“美好”了呢?
也不是的。比如说番茄,我记得小时候的番茄,成熟之后果浆饱满,柔软生脆,轻轻一咬就果汁迸溅。可是我们现在从菜市场里买到的番茄,真是硬。有一次,我与农科院的科学家朋友聊天,说到这个事,他一语道破其中奥秘:一个原因是,菜市场里的瓜果,都是距离成熟尚早时采摘的,运输过程中才慢慢成熟;另一个原因,是品种改良使果皮变厚,这也是为了适应远距离运输的需要,不至于在路途上腐坏;还有一个原因,很多瓜果都是在温室大棚中生长,缺少阳光猛烈地照射,也缺少风雨温柔地抚慰,又能好吃到哪里去呢?
总之,现在的瓜果,都是为了跟得上这个时代的发展,才不得不跟着做了许多的改良。
当我翻开清代的《县志》时,看见梅、杏、桃、李、枇杷、石榴,下意识以为就是我们今天吃到的滋味,事实上,果已经不是那个果了,味道也不是那个味道了。
在漫长的时光里,一切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这且不说了吧。木心说,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来做什么?爱最可爱的、最好听的、最好看的、最好吃的。最好吃的水果是什么样的?我以为,就要到我们的乡下来,守着一棵或几棵果树,而且是那老品种的果树,静静地等候着成熟。千万不要在没有成熟时采摘。要有耐心,直到果实在枝头散发芬芳,直到鸟儿和昆虫都已闻到香味变得迫不及待,直到那些果实已抵达它自己的巅峰时刻——此时,请你摘取和品尝它。
此时,你才知道,那些瓜果的新鲜、清脆、丰富、浓烈、香醇、圆润、淋漓,都是什么样的;你才能领略,黄瓜之所以为黄瓜,花红之所以为花红,杨梅之所以为杨梅,毛桃之所以为毛桃——那些最原初、最本真的味道,就这样,在舌尖上缓缓爆裂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