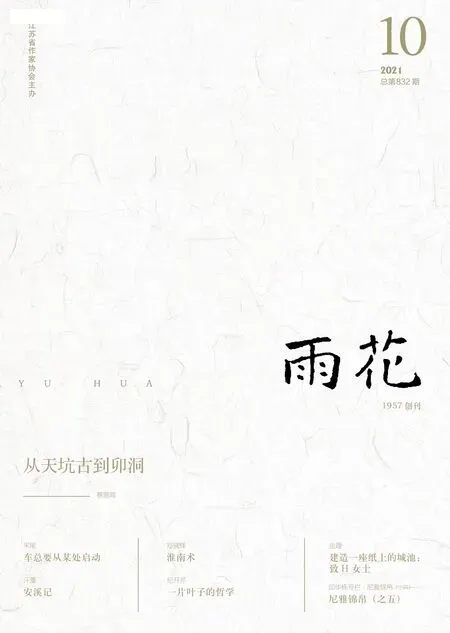淮南术
郑骁锋
“做灶豆腐”。
在我的家乡,这是一句相当恶毒的诅咒。因为赴丧葬人家的筵席,往往被邑人称为“吃豆腐饭”。
而换一个情境,“吃豆腐”又成了猥亵女性的隐喻。
没有任何其他食材,能够像豆腐一般,如此密切地融合世俗。在中国,豆腐早已突破食物的范畴,被赋予了多种深刻的文化寓意,诸如朴素、淡泊、日常、低调。而关于豆腐的衍生义,绝大多数都来自其柔软、易碎,可随意拿捏的特性。这种近乎逆来顺受的低姿态,与淮南在历史上的形象,却大不相同。
我一直以为,将淮南定为豆腐的发源地,正是中国文化的吊诡之处。
我是早上七点到淮南的,正好混在当地人中吃一顿最本土的早饭。
四下观望,食客最多的,是火车站广场斜对面,一家名为“北菜市老街牛肉汤店”的双开间小吃铺。汤锅有麻将桌大小,敞开盖,架在门口炖着,迎面就是一股香料与油膻混合的浑厚气浪。
牛肉汤七块钱一碗。比老婆饼厚道,真的有三四片薄切的黄牛肉。牛肉底下是红薯粉丝,还有一些千张丝和年糕片形状的豆饼,汤色金黄,滚烫,边缘浮着一圈红色的牛油,中间撒一把翠绿的葱花和香菜。浇上一勺剁椒,再搭配一块鞋底状的油酥烧饼,焦香薄脆——但我也看到有人是将饼掰碎浸入汤中,像西安的牛肉泡馍那样吃的。
说实话,对于浙江人,这碗汤偏油偏咸,口味有些重。不过我知道,牛肉汤是淮南最著名的民间吃食,在当地根基深厚,仅它的由来就挖掘出了很多说法,其中有一种便追到了淮南王身上。
而这位淮南王,同样被认为是豆腐的发明者。
今天的淮南市是一座三百多万人口的地区级城市,但在建国前,它还只是淮河岸边的一个老码头,淮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应该是今天淮南市下辖的寿县。
寿县,也就是春秋时做过楚国国都、三国时袁术也在此称过帝的寿春。历史上的淮南府城,指的通常都是这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
牛肉汤店门口有去寿县的公交车站点。6路车,四十分钟到蔡家岗;转29路车,再坐四十分钟便到了寿县。古城城北大约两公里处,有一座八公山。
淮南王就葬在八公山的山脚。
墓园很小。两层祭台,十几级石阶。墓冢覆斗状,榛莽杂乱,底部有一圈齐腰高的青石挡土墙。整体看起来比较新,应该是上世纪后期翻修的。墓碑倒是老物,“同治八年”的上款,书丹者为“吴坤修”,查了资料,是当时的安徽巡抚。
“汉淮南王墓”。说实话,第一眼,这块墓碑就让我想起了一条闹剧般的新闻:某地高调宣称,他们找到了齐天大圣的墓。
因为在传说中,这座墓的主人,淮南王刘安,也不是个凡人。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这个成语的出处便在淮南。据说,刘安痴迷修道,最终炼成仙丹,不仅自己服了得道成仙,连家里的鸡和狗,因为舔舐残留的丹药,也都飘飘然升了天。
《水经注》《太平寰宇记》等古籍言之凿凿,刘安炼丹和升天之处,就在这座八公山——所谓“八公”,即是刘安所供养的数千方士中,最出色的八位高人。淮南人还说,流转至今的牛肉汤,其实便是当年刘安宴请八公的一道菜;而豆腐,则是刘安与八公一起配炼丹药时,无意中取得的成果。
山顶流传白日飞升的神话,山脚却竖起一块冰冷的墓碑。
在同一座山上,淮南王的命运,被来回撕扯。
淮南王,其实是一个概称。
刘安并非唯一的淮南王。历朝历代,仅正史记载的淮南王便有二十名以上。所有淮南王中,无论权势还是影响,都属西汉时期的最大。
而在西汉,“淮南”二字,却相当不祥,历任以淮南封王者,都极少善终。
第一任淮南王,是刘邦时期的英布。他与韩信、彭越并称为汉初三大名将,在楚汉争霸时立下大功,却在天下安定后起兵反叛,兵败被杀。
英布被杀后,淮南王的封爵被刘邦转给最小的儿子刘长。二十多年后,刘长被控图谋叛乱。汉文帝将其废黜王号,流放蜀郡,途中绝食而死。
刘安就是刘长的儿子。刘长死后的第十年,文帝让刘安继承了父亲的王爵。汉武帝时期,刘安被人检举谋反,朝廷彻查,走投无路而自刎。
只是巧合吗?前后三任淮南王,居然全部因为谋反而死。
事实上,要到上世纪70年代,牛肉汤才开始在淮南出现。它最初其实是物资匮乏时期,某家回民饭店对边角料的一种弃物利用:他们将没人要的牛骨,配上本地特产的千张、粉丝,加足八角、茴香等香辛料炖煮,便宜发卖,不料居然大受欢迎,后来再加入牛杂升级,从此便有了这道老百姓的美食。
这完全符合历史常识:我国绝大多数朝代,对屠宰耕牛都有严格规定,牛肉向来是奢侈品,真正进入汉地民间的日常食谱,要到清中期以后;此外,牛肉汤真正的主角——粉丝,其原料红薯,也是在16世纪之后才由美洲传入中国。
很多事情经不起稍加严谨的推敲。
就像牛肉汤实际上与淮南王没有任何关系,那几起以“淮南王”名义兴起的大狱,与真正的叛乱,同样相距甚远。
三王之中,英布的造反,最为确凿。他的确起了兵,杀向长安,但察其叛因,却不过是恐惧:刘邦得天下后,诛戮功臣,“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眼看下一个就轮到了自己。左右都是死,干脆先下手为强,说不定还能图个侥幸。
至于刘长,仗着自己是文帝唯一在世的亲兄弟,骄横跋扈确是事实,但说他谋反却缺少证据,更没有过什么实质行动,以至于在他死后不久,长安城中便出现了为其鸣冤的民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说到刘安,其父亲蒙冤而死,想来免不了对朝廷心怀怨恨,但他的谋反同样充满疑问:史书长篇累牍记载了他对长安的种种阴谋,但几乎都是他与门客的口头商议,而且无论语气还是内容,都像事后精心罗织的供词。退一步,即便刘安有心叛乱,但自始至终都是纸上谈兵,不曾发过一兵一卒。
总而言之,从英布,到刘长刘安父子,所谓的谋反,要么被逼,要么牵强,甚至可疑,客观来说,都属于欲加之罪的被动性质。综观当时天下,如此接二连三地遭受朝廷猜忌甚至严厉打击的诸侯国,似乎只有淮南。
这片一再被反叛,也一再被镇压的土地,究竟背负了什么样的诅咒?
“大救驾”是我在寿县见到最多的街边小吃。
这是一种漩涡状扁圆形的糕点。由酥油面皮包裹核桃仁、金橘饼、青梅干、青红丝、糖桂花等馅料,入油炸制而成。色泽金黄,酥脆香甜,甚是可口。
寿县人说,“大救驾”有一千多年历史,而它救的,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驾。当年赵匡胤在这里打仗,积劳成疾,水米难进,随军大厨便做了这么一道点心。赵匡胤闻香开胃,几块下肚,又是生龙活虎。
虽然只是传说,但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大致不差。公元956年,后周世宗柴荣亲征南唐,作为前锋大将,赵匡胤攻打过寿县(当时叫寿州)。
后周的国力,原本就远远超过南唐,这次南征更是倾国而来,意欲摧枯拉朽,但谁也想不到,南唐的抵抗竟然会如此激烈,仅一座小小的寿州,就拖了赵匡胤将近九个月,几乎成了他毕生最艰苦的一战。
但在寿州历史上,赵匡胤这一战,只能说是寻常。至少,在此发生的淝水之战显然名气更大。淝水由东南向西北,在寿县城外过境。公元383年,就在寿县城下的淝水岸边,以八万对决八十万,东晋将十倍于己的前秦大军打得稀烂。
在寿县的北城墙上,隔着淝水,我能看到远处的八公山。这应该是对成语“草木皆兵”最标准的还原。当年,前秦的国主苻坚,就是以这个视角眺望着这座以刘安门客命名的小山,却错将山上的林木,看成了漫山遍野的敌兵;而仅这一眼,便泄了底气,为自己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淝水之战前,前秦的势力覆盖了整个中国的三分之二以上,触角一直伸到当今云南边界,从地图上看,就像一头巨兽大张了嘴,准备吞噬蜷缩于东南一隅的东晋。淝水,不过只是悬在这头巨兽獠牙间的一根蚕丝。
然而,很多时候,左右全局的,就是这根看似纤细的蚕丝。
能过去,就能开启一个大时代,就像后周与赵匡胤。
过不去,就逃不了身死国灭,就像前秦与苻坚。
滑铁卢或是凯旋门,都取决于寿州城的开阖方向。
现存的寿县县城,修建于南宋宁宗年间。城墙砖壁石基,很规矩,方方正正。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十字交叉。虽然规模不大,周长只有七千多米,走一圈也要不了太久,但城墙基本保持原貌,而且府衙、谯楼、文庙、佛寺、教堂、清真寺,一应俱全,在我去过的古城中,属于少有的完整。
寿县四面开门,北门,也就是面临淝水的那座,名为“靖淮”——过了寿县,淝水经城关北门港,过五里闸,在后赵台村注入淮河。这也是淮南地名的由来。
也就是说,淝水背后,站着一条淮河。
而淮河,是我国8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和一月份平均气温0℃等温线,以南属于亚热带湿润地区,以北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
古人自然不懂得现代地理带的划分,事实上,有关秦岭淮河线的最早论述,直到上世纪初才被提出。但他们很早就发现了淮河两岸水土民俗的明显差别,自古流传有“南米北面、南茶北酒、南舟北车、南蛮北侉”的说法,甚至春秋时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便已经成为俗谚。
正如兵家一再强调的天时地利,气候与地貌,往往能够构造某种军事力量的平衡点,或者说,障碍带。从卫星图上看,淮河两岸很不对称。北岸平坦,支流多而长;南岸支流少,而且都是丘陵山地,就像一把齿口朝上的梳子。对于南方,每一道梳齿,都是入侵的航道;而对于北方,每一片丘陵,都是抵抗的堡垒。
因此,自然属性之外,淮河同样是中国政局最重要的南北界线,欲饮马长江,必先突破淮河。有人统计过,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百次战役,发生在淮河流域的就要占去四分之一。这恐怕是几千年来除长城外战乱最频繁的地区了。
寿县,不仅濒临淮河,还处在中原与华南之间最迅捷的出兵路线上,既是“中州咽喉”,又是“江南屏障”,更是敏感之地,一旦南北对峙,如北魏与南齐、金与南宋,更是会被双方反复争夺。
应该说,这便是历代淮南王的原罪。他们在这条河畔的任何布置,都会被猜疑,被黑化,被放大无数倍。即便你已经软如豆腐,朝廷仍能挑出反骨来。
现在的淮河南岸,固然是淮南,但淮河北岸却不是淮北。淮南淮北两个地级市之间,隔着亳州与蚌埠,相距一百八十多公里。
两淮名实不符,根源可以追溯到元朝。元朝之前,划分政区,大致都会遵循“山川形便”的原则,但这也导致了不少割据。于是元人设置行省时,便将有可能凭险分裂的区域,全部打乱拆分,就像魏源所说:“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让各省无险可守。
这种建置模式被明清两朝沿袭下来,比如安徽、江苏两省区域,如若依据地理形势,应该沿着淮河与长江横向分区,却被朱元璋竖向一刀,切成了今天这样的格局。无论长江还是淮河,都被拦腰斩断。
类似的还有将太湖流域的嘉兴和湖州划给浙江。
这种将山河大地故意割裂的划区方式,号称“犬牙交错”。
对于风土人情,“山川形便”顺水推舟,“犬牙交错”,却是挑拨离间。
政区可以随意组合,每一地域的人文气质,却根深蒂固,极难移植。
而这往往又给了统治者更好的拆解理由。
诸多淮南王中,刘安最为人所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本《淮南子》。
与常人印象中的叛乱者正好相反,刘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文人。他的学术修养极其深厚,不仅皇室无人能敌,即便在当时文化界,也属于最顶层的大师级别。对这位学者型的叔父,汉武帝十分佩服,甚至有些忌惮,每次给他写信,都要请司马相如等大文豪修饰了才发出去。
而刘安最重要的著述,便是在他主持下,与门客集体编写的《淮南子》。
《淮南子》内容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多个领域,几乎无所不包,堪称一部公元前二世纪的大百科全书。
刘安非常重视这部书,将其定名为《淮南鸿烈》。“鸿”意为广大,“烈”意为光明,自诩此书出世有如红日升空,一扫千年暗夜。
某种角度上,这部书,才是刘安谋反的真正证据。
炮制中药时,豆腐也是一种重要的辅料。
通常用豆腐炮制的,大都是一些毒药和矿物类药。因为豆腐富含碱性蛋白,能与生物碱、鞣酸及重金属等结合产生沉淀。故而与豆腐同煮,能缓和这些虎狼之药的毒性或者燥烈之性。
豆腐的前身豆浆,也有类似的功效。而淮河流域,自古便是大豆的主产区。用此法炮制的药材中,最常见的便是珍珠与硫黄:一为服食上品,一为炼丹要料。
我想,这大概就是刘安能够创造出豆腐最现实的解释。
因为本质上,他是一位方士化了的道家信徒。
《淮南子》阴阳、墨、法、儒,几乎无所不包,显然,刘安试图借助此书对先秦诸子做一个总结。不过,《淮南子》学说虽杂,但理论基础却始终都是道家,体现在政治上便是无为而治;而自从汉武帝即位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刘安的著作影响越大,对他的治国理念的干扰也就越大。
武帝的铁腕之下,容不得任何杂音。骆驼背上又重重加了一捆草。
于是,又一任淮南王的叛乱,也被注定。
正如那丹鼎中炼药的豆汁,注定要被各种意外凝结成块。
汉武帝叔侄俩的这桩公案,使我想起了淮南另一位更加久远的王——西周时期徐国的徐偃王。
鼎盛时期,徐国的影响力覆盖今苏、鲁、豫、皖多部,淮南也在其内。但在中国的古籍中,对徐偃王的记载却很少。
我始终认为,这很可能是后世儒家信徒故意删减的结果。因为徐偃王的存在,对于儒家理论,是一个怎么也说不圆满的尴尬:
在中国历史上,徐偃王比孔子早四百多年提出了“仁义”的概念,并真正在治国中加以施行。然而,“仁政”带来的结果,竟然是亡国。
有限的文献中说,徐国在徐偃王的治理下,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前来归属的小国家越来越多,统治范围也越来越大,国力很快就强盛起来。但是,徐国的蒸蒸日上,引起了周王朝的警惕。当时周穆王在位,据说他本在西巡远游,得知消息后马上疾驰回朝,调动楚人出兵伐徐。徐偃王战败,国灭身死。
人类在三千年前进行的一次乌托邦试验,就此被强行终止。
偏离与扼杀,为何总是发生在淮南?
我想,这大概就是它地名中这条河的宿命。
两淮地区,有一种被称为“庄台”的奇特村落。它们四面环水,形状规整,地基很高,很像一口倒扣在水面的碗,屋舍都建在平坦的碗底上。
庄台本是当地的一种临时防洪工程。通过人工垒起台基,或者以天然高地为基座,发大水时,灾民可在上面暂时避难。后来人们嫌一次次携家带口上下庄台太折腾,便干脆在庄台上砌起正经房子,扎下根来,也就有了这种独特的民居模式。
在寿县古城靖淮门的外城墙上,我看到过一块嵌在墙砖上的石碑,正中刻有一道横线,边上有文字说明:公元1991年,最高水位线,海拔24.46米。石碑几乎够到了城门洞的弧顶,有当地老人甚至说,洪峰来时,坐在城墙上能洗脚。
很少有哪个地方能像寿县人这样爱惜古城的,寿县人还曾经倾城而出,赶跑过一支想挖几米墙基研究夯土的考古队。
淮河随时可能溃流。
淮河干流全长一千千米,总落差却只有二百米。淮南所在的中游,地势平坦,四百九十千米流程,落差更是只有十六米。这样的地势,使得一旦暴雨来袭,上游的洪水便会如猛虎般迅速落冲,在中下游平原上四处溢漫。故而“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两岸百姓苦不堪言。
淮河糜烂,祸根却在黄河。
“江淮河汉”。历史上,淮河曾经与长江黄河平起平坐,并称中华四渎。当时淮河流域不仅极少有洪涝灾害,而且风调雨顺,水土肥美——今天的淮南淮北,煤矿资源都极为丰富,这也印证了远古时期两淮植被之茂。
正如俗语有云:“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自古以来,淮河一直平波缓流,与世无争。但12世纪初,黄河却突然越界南下,强行夺了它的河床。而且,这种情况在之后的七百多年间,反复发生。
黄河夺淮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淮河原有的水系不仅被全盘打乱,甚至连入海口也被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淤塞了,于是,淮河只能自降身份,作为一条支流投靠长江,凄凄惨惨地借道出海。
一条被再三欺凌的大河,满腹屈恼,脾气自然越来越坏。
当然,黄河改道并不是天灾,而是宋金交战时人为决堤的莽撞后果。赋予淮河情绪的拟人化,只是为了说明,这块区域自古所受的压迫。
淮河流域,文明诞生其实非常早,考古发现也证明,这一带存在大量发达的史前文化。在先秦的典籍中,这片土地上的古民族,被统称为“淮夷”。而“夷”,是华夏族对被自己判定为蛮荒人群的鄙称,带有强烈的侮辱性质——徐偃王的徐国,也被他们归入东夷。他被消灭的真正原因,是把散居江河之间的诸多夷族聚拢在一起,隐然具备了挑衅正统的力量。
正如徐偃王,夷人是以被征服者的身份渐次融入华夏族的。从夏商周开始,淮夷不断遭到中原王朝的打击,后来吴楚等南方国家也加入了吞并他们的行列。
中原王朝发源于黄河,吴楚等国则发源于长江。
夹在两条如此强大的超级江河之间,淮河注定无法保持独立流淌,只能被绑架、被裹挟、被驱赶、被迁移,被强迫走别人的方向。
有学者认为,淮夷很可能以鸟为图腾。因为淮河的“淮”,来自“隹”,而“隹”的本意,是当地的一种水鸟,最大特征是尾巴很短。
联想到古淮河被堵死的出海口,我突然觉得这个名字充满了伤感。
大概是因为刘安,淮南,乃至于淮河,都经常会令我想起豆腐。
联想起了砧板上,厨师按自己的需求,对豆腐进行各种分切、各种加工。
来寿县总该吃点豆腐的。
据说寿县人已经开发出了豆腐豪华大宴,甚至还能让食客当桌亲自制作豆腐,美其名曰“刘安点丹”。但我还是更希望吃到街头巷尾,小摊小贩做的豆腐。只是一路走来,我见到最多的饮食店不是豆腐,而是牛肉面、牛肉汤、胡辣汤,甚至还有一种羊头肉。毕竟今天的淮南,也是华中一大回族聚居区。
这些游牧风格浓郁的吃食,使我记起了某种关于豆腐起源的争论。
自古以来,豆腐创自刘安,似乎已是定论,不仅朱熹将其称为“淮南术”,李时珍著《本草纲目》也沿用了这个说法。但上世纪开始,陆续有学者提出质疑,理由是五代之前,几乎所有文献都找不到豆腐的相关记载,因此豆腐应该要到北宋以后才出现。有人甚至认为,豆腐的发明,可能还受到了草原民族制作奶酪的启发:对于普通百姓,相比牛羊奶,看起来类似的豆汁显然更容易得到。
豆腐的谱系中,这也是一条被夺了河床的支流吧。
我是在通淝门,也就是古城南门附近的一家小店吃的豆腐脑。
寿县的南半城比北半城繁华得多,城门附近更是车马辐辏。明清以来,北富贵南世俗,是很多老城的特色,连北京和西安也大致如此。
方方正正一大块,洒了一撮切碎的榨菜,辣油椒盐自己加。除了量更足一些,我没吃出寿县的豆腐与别处有何不同。作为最大众的食材,豆腐的做法已经没有多少发挥余地。但令我有些意外的是,老板娘居然问我豆腐脑要吃甜的还是咸的。
有次在河北某县吃早饭,要一杯咸豆浆,老板奇怪地看着我,豆浆有咸的吗?而在我的家乡,虽然甜豆浆常见,却极少有人会在豆腐脑中加白糖。
北方眼中的南方,南方眼中的北方。
不南不北,亦南亦北。
刘安在淮河岸边测定的二十四节气,最终被当作定案,一直沿用到今天,或许是理所当然的。
人算毕竟大不过天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