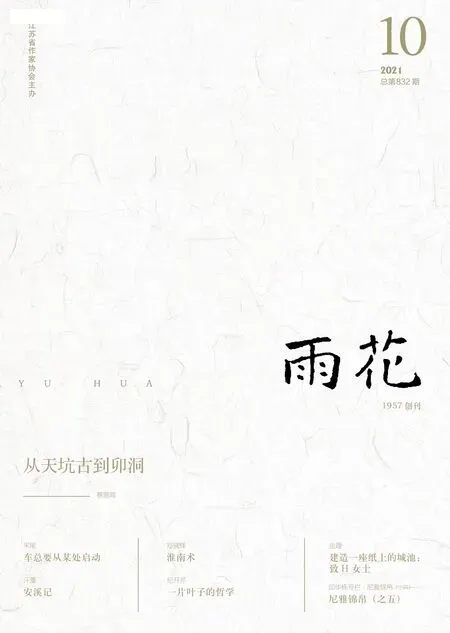信号灯
李敬宇
大雪下了两天,纷纷洒洒,不间断。我妈说:“这是下的什么雪?都下黏了!”
我妈坐在靠窗的床边上纳鞋底,一边拽出长长的线,一边自语:“不对吧,我的右眼怎么老是跳?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不会有什么事吧?”
我坐在小案板前,借着如豆的煤油灯,眼睛瞪视着侧边的四鬼——是一种警告,禁止他哭。四鬼一手端着空碗,一手拿筷子拨弄着案板上汤汁里的几颗米粒,小心翼翼地。他总是这样,一张苦脸,苦大仇深。
我妈扭过脸来,朝这边看看,说:“三鬼,你老是欺负四鬼!你欺负你弟弟,把他碗里的饭拨到你碗里。你以为我是瞎子,看不见呀?你把它拨回去!”
我漫不经心地把碗口斜向我妈,我是叫她看一看,我碗里早已空无一物。
我妈仿佛更加漫不经心,又开始自语:“你爸那边,不会……”
话只说出一半,就听得敲门的声音。虽急促,却小心控制着节奏。我妈仿佛打了个激灵,本能地站起身,握住鞋底,捏着针线,去开门。
踏进门的,是我爸单位的肖天义,后面还跟了一个高个子。肖天义一脚跨在门里,一脚丢在门外,有点慌急,却故作镇静。连喘几口气,他才说:“文嫂,老文那边……有点事情,我们是来——”
“出了什么事?”我妈伸出手,像要在半空里抓住什么,针线从手里脱落,挂在下面,晃荡。
“噢,也没啥大事,没啥大事。”肖天义急忙纠正。
“真的没出事?”
“……真的没出事。”
“……不可能。”我妈兀自说。
“老文他……可能是绊到铁轨了,绊重了。”肖天义尽量不去编词,可编词的意味反而更加浓厚,“这雪天!雪太大,他是看不清路了……三子你过来一下。你跟我们去一趟,去看一看。”
我其实已经有所警觉。如果问题不是很严重,他们干吗要跑到我家来,还跑得这么气喘吁吁?这在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呀!我放下空碗,“呼”的一下站起身,要跟他们走。
“你们都上门了,事情还不大?”我妈一语将话点破,“到底……怎么样?”
“没事文嫂,真没事……老文说,坐一坐就好,可就是……”
我妈狐疑地看着他们俩,却稍稍放松了点儿:“那让老二也跟着去。”
肖天义立刻伸出手,做出拦止的动作:“不用不用,女孩子出门,大雪天,不方便。让三子去就行了。”
“肖主任,”我妈看着肖天义缩回那只伸进门的脚,看着肖天义迅速转过身去,看着我从她身旁硬生生地挤过去,也跟着出了门,近乎绝望地说,“肖主任,我们这一家,可就指望他爸一个人过了!”
肖天义其实不是主任,是小组长;但他表现积极,别人就喊他“肖主任”。
肖天义和那高个子走在前面,步子迈得很大,走得也快,一会儿就走远了。地上雪厚,我努力追,也追不上他们。
走出小巷,拐上河西街,地上的雪就不如巷子里那么厚了,被人踩踏过,稀烂且湿滑。街上黑黢黢一片,风明显比巷子里大,我感到一阵寒冷,忍不住地直打寒战。穿两条单裤,在屋外,在晚上,就跟没穿裤子一样。出门前我应该跟五鬼换裤子的,但当时赶得急,根本就没想到。
我家兄弟姊妹五个,上面两个是女孩,从我往下,都是公鸡头。我十一岁了,上四年级。大姐在老家照顾爷爷奶奶,大姐不在家,我就是这个家的王——当然不算爸和妈。家里只有两条棉裤,我妈说了,给你爸和五儿穿。五鬼才七岁,穿个大裤子,浪费了。我不能多言;我要是多言了,我爸就会说我“讲废话”。
我爸总是这样,肚子里的墨水还没我多,一天讲不出几句话,脾气还犟,老会说我“讲废话”。我知道,他不烦别的,最烦我贪吃。
我总是吃不饱,不跟弟弟们动些脑筋,根本就不行。二姐我是不会动她点子的。我们刚刚学过一个词语,叫“做牛做马”;二姐在家,就是“做牛做马”。
肖天义在前面停了脚步。肖天义磕一磕鞋子上的脏泥,是在等我,却并不回头。我紧走十几步,跟上去了。可那个高个子,似乎等不及,径自在前面走。
“哦,雪下小了。”肖天义说。
我没有接话。
“你家大丫,在那边照顾老人,真的不回来啦?”肖天义又说。
我还是没有接话。
浑身冰冷,心也凉飕飕的,我没有一点儿说话的欲望。
那个高个子始终在前面走,像是丢失了记忆,把后面的人忘掉了。我和肖天义好歹走出河西街,上了河埂。河埂叫大坝头,大坝头上无遮无拦,风更大。
“你冷不冷?”肖天义问。
我还是不说话。
鞋子里早就进了水,雪水湿冷。先还如同无数小虫子叮咬着脚底和脚面,然后,那虫子就变成刀子,成了无数的小刀子,在脚上割肉。割一块,磨磨刀锋,再割一块。
“三子,你步子走大一点,再走快一点,身上走出汗,就不冷了。”
这话也是。我加快了步子。
终于走上了码头街。码头街是一条宽路,区政府在这条路上,铁路小学也在这条路上。白天的这条街可真是热闹,大家都在抓生产干革命,可是下了雪,下这么大,又下那么久,晚上可就出不了门了。路上几乎看不见人。铁路小学围墙上的标语还是前几年的,石灰水写上去的大字:“彻底消灭血吸虫病”。每回见到这个标语,我都会想到老师常常告诫我们的,不要去江边,不要被钉螺咬上了,那可是要得大肚子病的!
上学和放学,我天天要走这段路。过了学校大门,再往前,虽然也走,但走的次数就少多了。
雪像是停了。下了整整两天,真是难得。
我们一高一低,并排走在码头街上。我的两条腿,两条裤管,从上到下都已经湿透。肖天义说得对,走快一点就不冷了。等我们走到码头街尽头,走到天桥下面铁路挡道口的时候,我真的已经感觉到身上要冒汗了。
走到这里,我发现,除了天桥和挡道口这块区域,往左,往右,都一片透白。为什么呢?是因为啊,铁路沿线几乎没有人行走,雪下厚了,把沿线的一切都覆盖了。那众多的铁轨,本来还像银线一样露在外面,这一刻,和一片通白相比,反而不明显了。
当我们越过铁路挡道口,朝右拐,走上这片黑里透白的雪地时,路顿时就难行了。不是一般的困难,是很艰难。脚踩在雪上,深深浅浅,找不准下脚的枕木呀!
我爸上班,是在岔道口扳道。那扳道房,是一间很小很小的房子,解放前就有了,虽然解放好几年了,也没顾得上修整,连顶都罩不住。有一回,站上说是要派人来修呢,我爸说,别修了,有这钱,还不如拿去支援前线呢!我爸肯吃苦,他不在乎敞亮的天。
我爸是信号工,又叫扳道工,就是在岔道口负责扳道,给列车发信号。岔道口周围全是铁轨,有的轨道上停了货车,有的货车正在缓慢运行,也有客车经过,但客车从来不停,都开进了北门火车站。就是说,他扳道的地点实在是远,从天桥口沿着铁路线一直走下去,一直走到货车和进站客车交汇的地方。
扳道就不用说了,在岔道口信号标志的铁杆下方,有一个扳道的铁杆握把,扳过来,铁轨就岔到这一边,扳过去,铁轨又岔过去,到那一条线上去了。火车真是听话,你怎么扳,它就怎么走。如果火车从相反的方向过来,扳不好道,那可就要出大纰漏,车轮卡在铁轨中间,没法行驶,就会脱轨,就会翻车。
有几回,我跟我爸去上班,看他打信号。白天他用两面小旗子,红旗子和绿旗子。火车往这边行驶,一摇红旗子,就缓缓停下了;要是火车停着,摇一摇绿旗子,就启动了。那一回手上没旗子,他就伸开两臂,把人伸成一个十字型,火车也听话,也停。另一次也没旗子,我爸就远远地冲着火车头用手划弧线,拼命地划,火车便启动了。
我说:“这个工作不赖,好玩。”
我爸说:“这是随便玩的吗?这是革命工作,责任大得很呢!”
晚上或夜里,挥旗子打手势都不管用,看不见呀,只能用信号灯。我爸说,红灯停,绿灯行。
我爸下班,常常把信号灯拎回来,和饭盒一道。拎来家,放在大木箱上,不许人动。四鬼、五鬼都老实,动也不敢动;有一回我耐不住,动了,被两个鬼告了状,我爸当即扇了我的脸。
我是怎么动那信号灯的呢?我把它打开来看了。
打开来,里面有个圆形的小煤油锅,锅里面有一个粗粗的灯芯;灯的前后两边,分别是红色、绿色的圆玻璃,在玻璃的背后,各有一个活动挡板,可以把玻璃罩上,也可以打开。就是说,拿煤油点灯,本身是分不出颜色的,罩上一边玻璃挡板,打开另一边玻璃挡板,信号灯就成了绿灯或红灯了。
到十年以后,我已经二十多岁,全国上映一部电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其中的李玉和,手上拎着一盏灯,跟我爸用的信号灯,外观很相似。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看的,我就是好奇,打心里想看。
问题是,我并没有把信号灯搞坏,就是打开来看一看,偷偷研究了一下,我爸就动了火,扇了我两个大嘴巴。我爸说:“国家财产,能叫你随便乱动?!”
我妈说:“打一下就算了,你还扇两下,都要把他脖子打断了。”
“我要叫他长记性!”我爸说话的时候气壮如牛,并且指责我妈,“亏你还进了扫盲识字班呢,屁的道理都不懂!”
我们走在两股铁轨的中间。铁轨笔直,向远处延伸。来路已经够长了,可接下来,路虽然是直线,却一点儿也不短。是的,一直要绕到火车站的后面,走到火车站的尽头,还要再往前走呢!关键是,这“路”实在是不好走,大雪把枕木埋住了,埋得很深,脚步无法丈量距离。这就很麻烦,码不准步子,走几步就会踩在枕木的边沿上,不是脚尖就是脚跟,鞋子滑下去,引得脚尖或脚跟生疼。如此,脚步也跟着没了章法,乱七八糟,身体不断地趔趄。
前面那个高个子留下的脚印新鲜而清晰。起先我还踩着他的脚印走,可他步子太大,是隔一个踩一个,跳着枕木走的。我试着走他踩过的脚印,但不行。我脚小,鞋子也小,探不出他的脚印哪儿是实,哪儿是虚,根本踩不准。这样每走几步,我的脚就会往枕木下面滑一下,滑得很狼狈。
开始肖天义一直无动于衷,但接着,我每滑一次,他都会及时地拽我一把。当然,他的动作很机械,如同应付。
“三子,你爸在单位可老实了,是我们单位有名的‘闷头’。他在家打过你,我知道……三子,你恨不恨你爸?”刚才只顾着探路了,肖天义又拾回了他的嘴巴。
我不回答。
“三子,你是不是还欺负你两个弟弟?”他又问。
漫天都是一种说不清的颜色,是黑还是白?黑里隐藏着白,白里又透着黑,整个天空灰黑成压抑的一片;若不是前面有停着的货车,连天地都分不清。前面那个人的步子可真是大呀,这一刻,连人影都见不到了。
“三子,你不想说话,我知道……三子,我只问你一句,你现在是不是已经长大成人了?已经是……男子汉了?”
我的脚趾和脚跟都疼,两只脚都疼。我没有心思跟他讲话。
“三子,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是男子汉了,你怎么连话都不肯讲?”肖天义像是有点着急,其实是在酝酿,酝酿接下来的言语,“我们为什么叫你来,不叫你家小四小五,也不叫你二姐来,你想一想……三子,你别不说话,你好好想一想。”
“我爸到底出什么事了?不能动了吗?”我突兀地开口。
肖天义仿佛吓了一跳,我感觉到他身子激灵了一下。“你爸……”
“肖叔叔你别瞒我,你说我爸是不是残废了,不能动了?”我又硬生生地问。
“三子……你听我说……”肖天义言语迟疑。
我其实一直在听,但我忍不住,说:“我爸跌得很厉害,我知道。不厉害,你不会跑到我家去!”
“三子……又下雪了。”肖天义答非所问,“三子,我只问你一句,你现在,是不是一个……堂堂男子汉?”
我听他讲话的口气,都像带了哭腔了。这个家伙,我不想搭理他!
雪又下起来,先是松散地、不经意地飘,然后就下紧了,一阵紧似一阵。
这个夜晚使我对大雪的颜色记忆深刻。它的颜色此后影响了我一辈子。
飞落的大片的雪花,不是白色,是灰的,甚至是黑的,与黑夜融为一体;可当它们飘到地上,和白雪黏在一起的时候,又成白色了。它们怎么会变颜色呢?
我妈说得对,这雪,都下黏了。
我突然想哭。我突然感到不对头了。
“我爸是不是出大事了,肖叔叔?”我加重了问话的口气,也带了哭腔。
“你爸……”肖天义又迟疑了。肖天义总是在关键时候迟疑不定。
“我们班王港他爸被轧掉了一只脚。”我突然想到了那个整天拖着鼻涕的王港。
肖天义不讲话,只是闷声往前走,不时地拽我一把,又拽我一把。
黑,灰,白,整个天地,混杂不清。我忍不住,眼泪蓦地下来了。仿佛是无来由的,就像两股小溪的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淌。这一刻,我不仅担心我爸,还担心我妈。我妈老是对我说,三鬼你别不懂事,我们要给你爸多吃,他辛苦,要养活我们一大家子呢!
我吃得多,我妈就说我不懂事,有两次,竟从我手里抢过东西,原本是打算递给我爸的,但不知怎么的,在半空里变换了方向,递给四鬼五鬼了。
以前我是不懂,不懂事。不晓得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可是,此刻,被肖天义左一把右一把地拽,像是蓦然把我拽明白了。
“三子,你爸……”肖天义像是鼓足了勇气,但话未继续说出,又泄了气。
“我爸到底出了什么事?肖叔叔,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走了!我不走了!”我突然不予配合地停下脚步。说心里话,我也走不动了。
肖天义狠拽我一把,像是终于拾回了勇气。“三子,你爸他……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拽紧了我,如此,我们的脚步不仅没慢,反而加快了。
“犯错误……他犯了什么错误?”我喘息不定。
“该挂红灯的,他没挂。你知道的,应该挂红灯他不挂,司机看不到,火车开过来就会翻车。”
“火车……翻了吗?”我感到震惊,本能地意识到前面有一列已经倾覆的列车。
“那还没有。火车没见到灯,但司机有经验,停下了。火车虽然停下了,可它危险啊!这是一件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要是司机经验不足,没停下,那可就是一起非常重大的事故了!明天,就连北京,也会知道这个消息!”
“我爸被抓起来了?!”我像是立刻知晓了答案,飞快地问。肖天义一再瞒我,我感觉不到吗?我又不傻。
肖天义突然缓了步子,低头看我。几乎要停下了。
很明显,他是被我的话说愣了。
“要是被抓起来就好了!要是被抓起来……就好了!”肖天义终于控制不住,带着哭腔,然后把头扭向一边,不再看我,拽着我紧走起来。
他肯定是哭了,眼泪止不住,但憋住声音。是大男人的那种哭。
快了,不远了,就快到我爸上班的扳道房了。
可我走不动了,实在是走不动。
就在我准备绝望、却又找不到绝望的理由的时候,前方的天幕里,天与地之间,蓦然闯进了两个人。
一高一矮两个人,高的太高,矮的太矮,对比太明显了。他们闯进我视线,竟一点儿先兆也没有。这雪天,这倒霉的夜晚!
我们相对站住了。
“肖主任,赵主任来了,赵主任批评我们了!”开口讲话的高个子,正是刚才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一位。
我正想着,他怎么这么快,竟带了人又折返回来了,便听得旁边那个瘦精精的矮个子说:“走走走,都回去,回家去!肖天义,你还是组长呢,真不会办事!现场还没处理,一个小孩子,你就把他领过来,领来看,你就不怕他被吓着啊?!这又不是别人,是他爸!已经出这么大事情了,要是再闹出事来,咋办?!你真不会办事!”
“赵主任,赵主任我……”虽然高矮不一,但肖天义在矮矮的赵主任面前像是一下子就变矮了,矮了大半截。
“走走走,别说了!你呀,真不会办事!”赵主任重复着,带头往我们的来路、往天桥方向走。
我顿时明白了,像是一下子开悟了。我的明白和开悟,说到底,就是因了赵主任说出的“你就不怕他被吓着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出了天大的事,不是因为我爸遭遇了比不幸更加不幸的事,我一个“堂堂男子汉”,怎么还会被吓着?
我突然想发作,突然想歇斯底里。当然,“歇斯底里”这个词我是在许多年以后才听到的。总之,我就是甩开手,不管不顾了。我一把挣脱开肖天义的那只手,拼命地往前跑,往我爸所在的扳道房跑。铁轨中间的雪和枕木仿佛充满了阴险,是滞人脚步的,叫人跑不动。我索性跳出铁轨,从铁路的侧边跑。这也好不到哪儿去,同样跑不动。
虽然满是石子的斜坡上,高一脚低一脚难以行进,但是,但是对于一个已经不顾一切的堂堂男子汉,还有什么能够挡住他行进的脚步呢?
我跑呀跑,跑呀跑……
我听到身后的呼喊声,听到身后他们追赶而来发出的杂沓的脚步声;我还听到,听到来自世间和天外的所有声音。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阻挡我奔跑的脚步。我脚下已生了风,跑呀跑,越跑越带劲,越跑眼睛看得越清——是啊,我不敢不看清!我要好好地看一看,我爸究竟怎么了;待我看完了,还要赶回家去,去告诉我妈!
这一刻,我妈肯定在家等得正着急呢,纳鞋底的大针肯定戳到了手指头,淌了血,可她竟然不知道。她总是这样,平时好像很有主见,一旦遇到事情,就一点儿主见都没有。
我跑啊跑……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跑到终点,虽然终点已近在眼前。我眼前一片模糊,天地一色,却又清晰异常,仿佛连一根针都能透见。啊……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成功摆脱了身后的几个人,终于跑到了扳道房。
我看到一盏黑乎乎的信号灯端端正正地立在雪地上,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我爸使用的信号灯;在灯的旁边,有几根细小的洋火棍横横竖竖地躺在雪地上,虽然微小,但我仍然看清了,那都是没有点燃的洋火棍。是的,没有点燃的洋火棍。
然后,我走进了黑咕隆咚的扳道房。
虽然漆黑一片,但小房子太简陋,罩不住屋顶,地上还是落满了雪。我看见了地上躺着的那个人,并且,一眼就认出了他是谁!我蹲下身,伸手,试图去推动他,却徒然,他身子凉凉的,动也不动。
我急于要知道答案。我看到,雪地上,在他身边,横七竖八躺了更多的洋火棍。那细长的洋火棍,棍头上黑黑的洋火头,全都完好,竟然没有一根是被点燃的。而那只和我手心差不多大的洋火盒,也在雪地上,就在他的肩膀旁边,安静得很。打开了一半,里面空空荡荡。
我本能地抬头看天。天是黑的,有雪花稀松地飘进来,裸露的房梁清晰可见。我不仅看见了房梁,还见到,房梁上居然挂下来一截绳子。
我像是明白了什么,却又模糊,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梦吗?
这时,我的眼泪像潮水一样漫溢开来,眼眶内外都糊满了泪水。可不知为什么,我哭不出来,一声都哭不出来。
幻觉的力量真是强大,有时候比真实还显得真实。
我的记忆可能在哪个拐点出现了问题。我始终以为,那个夜晚,我跑到了我爸的尸身旁边,但其实,那个夜晚,我可能根本就没有看到我爸。因为后来别人都这么说。
许多年以后,我成了一个作家。我发表了很多小说;但是,我爸的故事是个特例,一直被我压在内心的最深处,像压在箱底的一枚蝴蝶标本,几十年了,不敢触碰。这个故事不仅令我感伤,似乎还有一点儿诡异的因子,让我始终找不到一个客观的、回归事实的答案。
我记得接下来,肖天义、赵主任、高个子等人都来我家,协助我妈处理我爸的后事。但那时候,我正发着四十度的高烧,一连几天都不见消退。所以,关于后事的处理,其实就跟我在事发当天去扳道房的经历一样,是否抵达了现场,真假实在是难辨。
在我昏睡时,他们议论纷纷。
一个说:“老文就是太固执,凡事老要追求个妥当。雪太大了,那洋火受潮,潮得很呢,他能怎么办?没点着火,干吗就想不开,要走这一步?”
一个说:“连公安到现场都说了,不能算犯罪,跟犯罪扯不到一块去。火车也停下了,也没撞到别的火车,也没出轨。”
一个说:“就是啊,开始大家还说,老文是畏罪。他畏的什么罪?连人家公安都下决断了,说既没有故意,也没有发生后果。”
我的高烧如同一场阴谋,甚或一场骗局。待高烧退去以后,一切都归于平静,仿如几片雪花落进水里,不起一点儿波澜。是的,对于我爸的死,后来,正面的、反面的说法都没有。就像我们北门镇上停在第十三股道上的火车,被远远地甩在十三股道上,无人问津,成了一个永久的标本。
现在,我从箱子底下小心地拣起这个标本。
噢,关于洋火,我要解释一下。洋火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火柴。那时候,我们中国的许多东西都带一个“洋”字,洋火、洋油、洋线、洋钉、洋灰、洋糖果、洋山芋,还有洋车子、洋楼。
为了省煤油,凡两列火车间隔时间长的,我爸都会将煤油灯吹灭。他总说,为国家省钱,省一分是一分嘛。我能想到,那个临近夜晚的黄昏,他在扳道房的门口拿洋火棍擦火的情景。他擦了几根,擦不着。他只好进屋,再擦。可是,洋火受潮实在是厉害,一根一根都试过了,仍旧擦不着。
真是急人呀,能急死人了!这受潮的洋火,一根也擦不着!再过一会儿,火车就要开来了,时间紧呀,紧得叫人喘不过气来!可是,没有信号灯,一列火车就会理直气壮、不顾一切地开过去,那将是什么后果?可是,洋火呢,洋火一根也没有了。
——怎么办?是啊,怎么办?怎么办呀?!
我爸在那个大雪天的傍晚,面对一地细长的、冷冰冰的洋火棍,突然绝望了。
绝望,使得他做出了一个更加绝望的选择。
……乌飞兔走,时间过得飞快。直到六十多年以后,我也快老了,连我儿子的岁数都比我爸那时候的岁数大上十几岁了,那压在箱底的蝴蝶标本,不能不拿出来看看了。细看,我终于有了刻骨铭心的疼痛。
借助于一根绳子,他将突兀而至的、漫无边际的绝望,以那样一种奇特的方式,戛然终止在那个雨雪霏霏的傍晚。那一年,他还不满四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