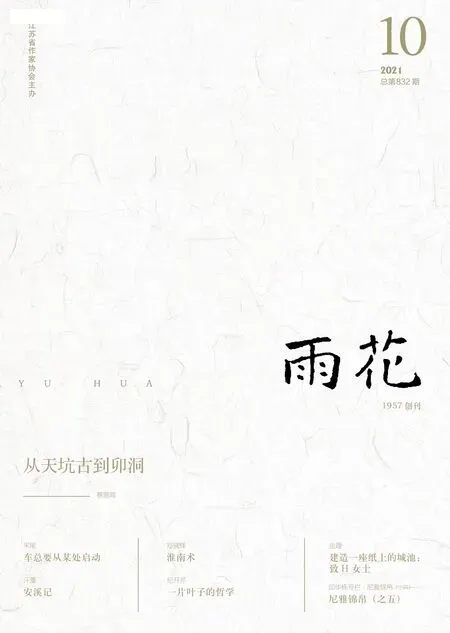昆士街市集
王晨蕾
市中心正在举办一场热闹的圣诞市集,直到平安夜。昆士街因此披上了节日盛装,人流络绎不绝。昨天新来的租客姑娘再次证实了这件事。
新租客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她在深夜雨下得最大时,和房东一起出现在门廊。我裹着毛衫给她开门,房东简单地嘱咐几句后,便撑伞离开了。他住在同一个社区。
当时已过午夜,她眼底布满血丝,手忙脚乱地翻找纸巾,擦拭挂满水珠的行李箱。我不禁问她为何这么晚才入住,她说自己一路辗转了近十五个小时,刚从伦敦希思罗机场乘大巴过来,再上一站则是北京首都机场。
上楼梯时,我没有帮她提行李,只是尽量步伐缓慢地走在前面,我不希望她因着急弄出太大的动静。到达狭窄的二楼后,我顺手打开走廊尽头卫生间的灯,简单给她看过后,便为她打开了卧室的门,这是一间位于我隔壁的次卧。据房东说,这个女孩目前只租了两周,合约也谈得比较着急,全程在微信上进行沟通,一切都很临时。她恳请房东提前为她准备一套被褥,甚至不惜为此加了50英镑的租金。
我问她是否还需要别的帮助,她环顾四周,说不用了,让我快些休息。
我回到房间时,女儿还是被吵醒了,翻了个身嘟囔道:她怎么这个点才来?
我关上台灯,房间重新陷入漆黑。雨滴敲打后院里那套塑料桌椅的声音清晰可闻。在这里——英格兰北部的一座城市,很少能够听到这样的雨声,它让我想起了家乡浙江的梅雨天。在英国,雨是虚无缥缈的幽灵,不是液态的“物”,而是一件流动着的“事”,它并不随着时节的变化来去,而是时时刻刻笼罩在城市上空,悬挂在人们头顶,黏在鞋底,顺着鼻孔钻进身体,既不具形状,也没有声音。
我已经同女儿在这里生活了小半年。其实对于时间,我多少是有知觉的。她每天上午出门上学后,我会先收拾早餐的残局,此时距离中饭还有一段时间,我会倒一杯热水,站在客厅的落地窗边,看窗外低沉的乌云和后院闲逛的海鸥。这段时间往往很慢,因此很真切。午饭我独自一人,通常都是简单解决,秘诀是提前烧好几天分量的葱油,每天中午只需煮一小把挂面和几片菜叶。饭后我会按计划出门,去超市采购,为晚餐做准备。
女儿的高一生活似乎还算顺利,她说外国同学和老师都很友善,她讲述课堂活动时的轻快语气令我安心。她的作业比从前在浙江读书时要少得多,见她每天回家后还能腾出好长一段时间练吉他,我更没什么可担心的。但最关键的一点我无从考量,那就是她的英语水准,因为她很不愿同我张口。每当我问她能不能讲几句时,得到的都是同一个答案:你又听不懂。
她说得完全在理,我无法反驳。
这天早上,我洗完碗回到客厅,便见新入住的女孩出现在楼梯拐角——瘦高个,穿一件墨绿色的连帽卫衣和深色牛仔裤;单眼皮,又或许是内双,那对突兀的肿眼泡妨碍了我的判断。然而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她微微下扯的嘴角,因为这导致她的笑容看上去有些勉强;与此同时,笑眼下面,饱满的颧骨高高隆起,因而又浮现出某种违和的亲切感。
她说自己是已经毕业的留学生,之所以又从国内飞回来,是为了一件“没处理完的小事”。接着她说与朋友有约,要马上出门。
“去商场啊?”我随口问道。
“去市中心的圣诞市集,有热红酒卖。”她说。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圣诞市集,房东对我说起过,我还曾在超市听见几个中国留学生议论它。不难理解,在一个无聊的小城市,这样的年度盛事是格外吸引人的,何况昆士街(Queen’ s Street)本就是市里最繁华的区域,女儿和同学们总在那里碰面,她习惯用英语讲这个名字,还告诉我它原本是“皇后街”的意思。
“热红酒?”我从没喝过,于是下意识地重复了一遍。窗外的云依旧压得很低,后院潮湿的地面上,我的老朋友——一只海鸥——正同我对视。这半年来,它几乎每天都造访。
新租客出门时把帽衫随手罩在了头上,于是我塞给她一把伞。那是女儿的伞,一直闲置在门口的鞋柜里,她不喜欢出门带伞,即便是来了英国,仍坚称随身带伞这种行为没有必要。但是租客女孩接受了我的伞,还感谢了我。她走后,我在门廊张望了一会儿,目送她到公交站台,她上车时,合伞的动作并不熟练,这让我有些担忧,不过在我即将冲出门帮她之际,她顺利关上了那把伞。公交车开走后,我回到客厅,从抽屉里拿出便签,列举下午的采购清单——今天的晚餐需要排骨和芦笋。
这里有很多连锁超市,如同扁平的积木散落在市郊地带,它们也许是英格兰给我的最大惊喜。如今我格外喜欢逛超市,享受在一排排充盈、整齐的货架间游走的感觉。那些市郊的超市都大得离谱,可供我打发掉漫长的时间。渐渐地,我总结出了不同超市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简单来说,它们有的主打低廉的价格,有的定位更高端,卖有机食品;有些以肉类食品见长,有些则因果蔬新鲜、种类齐全受到欢迎;还有一些超市擅长做漂亮的烘培食品。如今无论去哪家、买什么,我都轻车熟路,但仍会每次都循着“之”字形的路线,从距离入口最近的食品货架出发,一直行进至最底部。厨具货架上悬挂着亮闪闪的锅碗瓢盆,它们的陈设从无丝毫变化,像一群保持着阵型的士兵,一员不裁,坚定又孤单地守在阵地上,为我的超市之旅画上圆满句号。之后我便会斗志昂扬地离开,仿佛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我和女儿刚来时,英国正处于凉爽的夏季,晚上九点多钟天才会黑,日落之前,总有大片的、梦境般的紫色晚霞,它们漂浮在这座随处可见古老雕塑的城市上空,傍晚被浪漫地延伸了。那是段快乐时光,一切都新奇,我们经常逛超市,女儿沉迷于浩荡的零食区,她喜欢花时间辨别包装袋上的英文,而我更偏爱灯光明亮的甜品冷柜,各式糕点在透明包装下一览无余,精致、诱人。如今女儿已对那些甜得要命的东西失去了兴趣,她前阵子得了急性牙髓炎,差点因此回国治疗。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许是秋天变深时,落叶铺满公园小径,冰冷的夜幕下人们回家的步伐愈发急促——女儿不再接受我逛超市的邀约了。于是每天我一个人出门,就去离家最近的那家连锁超市,虽然小了些,但买点日常食材绰绰有余。通常在超市买完东西后,我不会马上回家,而是会往社区深处再走一走,转到一家华人超市,看看在那些英国超市买不到的食材,如豆芽、豆腐、冬瓜、整颗的大白菜等等,还有酱油、香油、花椒这些调味品。
这天我其实没什么需要在中国超市买的,但还是抬脚往那个方向走去。出乎意料——超市不起眼的小门敞开着,超市老板出现在柜台后。
“来了。”他用港味普通话和我打招呼。
“最近挺忙的?好几天没开门了。”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一个朋友来英国了。”
“哦,怪不得。”我脚步迟缓,假装在货架前搜寻,拿起瓶瓶罐罐又放下。
“找什么?”
我早已准备好答案:“有泰式辣酱吗?”
“小茹又要吃辣了?”他来到我身边,伸手够到货架最顶层,从深处掏出了一瓶虾粉色、漂浮着大红辣椒屑的半透明酱汁递给我。小茹是我女儿。
我说:“去哪玩了?伦敦?”
“还没来得及。不过去了市里的圣诞市集。”他也提到了这个神秘的圣诞市集。
“喝了热红酒吗?”我马上问道。
“哦,那天人太多了,没有喝上。”他显得有些吃惊,“你去过了?”
“还没有。”我掏出钱包,拒绝了他扯下塑料袋的动作。
“慢走哦。”他说。
我出门后径直朝家的方向走去,步速快了许多。
我回到家时,房东正在客厅里转悠,浑身散发着中餐馆后厨的油烟味。他来英国有些年头了,最初为一个香港人打工,在伦敦唐人街洗盘子,如今他已在本市拥有了几家中餐馆,还购置了几套房产,出租给学生。他孑然一身地来,现在已将全家——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都迁来这里。房东逢人便讲自己的这段英格兰奋斗史,但我揣测他来的原因和途径并不光鲜,他的作风总让我想起“投机分子”这个词,我一直对迅速发迹的人持有偏见,认为他们不过是善于追热潮、钻空子罢了。
他隔三岔五就会来这栋房子,不为别的,只是同我讲一些漫天闲话。但更深一层,我认为他是想夯实自己“房东”和“华人”的身份,这令他感觉良好。
这天,房东照常和我絮絮叨叨一些陈旧的琐事,说他最近招的一个前台小姑娘做事不认真,时常上错菜,账也记不好,又说最近后厨也不安宁,师傅国内家里出了点事,做菜总心不在焉,放太多盐和酱油。他说话时,我在厨房和客厅之间不停地来回穿梭,制造出“乒乒乓乓”的声响。我干脆地撕掉冷藏盒的塑封,把排骨倒进洗菜盆,然后将水龙头开到最大。粉色的排骨沉在盆底,粘连的白色脂肪如海草般漂浮着。
外头传来钥匙孔转动的声音,那女孩回来了,令人惊喜地闯进了这个永恒的场景——厨房、水流声、房东清喉痰的咳嗽和散漫的踱步声。她手里提着某连锁超市的购物袋——就是我和女儿之前最爱去的那家。她冲我与房东笑了一下,算是打过招呼,接着便拉开冰箱门,逐一掏出袋子里的东西,抱在怀里。那些盒子尺寸各异,几乎全是甜品:米布丁、提拉米苏蛋糕、柠檬挞、巧克力泡芙,除此之外就是几盒微波食品。
“你就吃这些啊?”我看着她把食物塞进了冰箱最上层的狭窄空间,井然有序。
“是啊,我喜欢吃这些。”她笑嘻嘻地答道。
房东插话进来:“昨晚住得舒服吗?”
“暖气温度好像有点低,可以调吗?”她简洁地回答。
是不可以的,一直都那样。我知道答案,但我没有说什么。房东动作迅速地上了楼,女孩也跟了上去,剩我一个人在厨房。我低头看着剧烈的水流淋在芦笋上,闪烁着晶莹的绿。我想到方才超市老板口中的那位朋友,我不清楚那是他的什么朋友,或许就是他上次提到的那位朋友。距离我们上次对话已经过去一周了。
我耳边再次响起男人的声音,房东已经下了楼,女孩似乎留在了卧室。我不晓得他用了什么策略将暖气的事不了了之,但此事显然打断了他同我废话下去的兴致,于是他说:“你忙吧,我回去了。”我决定把我们屋里的小油汀拿给新租客,如果她需要的话。
房东走后,我把芦笋刮皮,切成段,同时再次陷入回忆——关于那个同香港超市老板一起度过的下午。
我称呼香港人为林先生。大约一周前的某个下午,我结束了常规的超市采购,决定去林先生那里买几袋速冻水饺。我进店时,他正在忙于给货架上新,单薄的身躯被淹没在堆叠的箱子中间,堵住了我去往冷柜的路。他热络地同我问好,之后便继续拱起腰忙碌起来,没有意识到我的为难。
“我来得不巧了。”我将目光投向过道尽头的冰柜,暗示道。
“不好意思。”他手忙脚乱,试图重新摆放箱子,腾出一条更宽敞的通道。促狭的小超市里堆放了数十只纸箱,仅有的走廊深深凹陷下去,如同一条战壕。战壕中一位新入伍的小卒迎头遭遇了长官,林先生是不知所措的“新兵”,我则是那位威严的“长官”——不料从回忆视角出发,我脑海中竟生出这样荒诞的比喻。
“其实我只要几袋水饺,您帮我拿就好,三袋吧,猪肉两袋,一袋三鲜。”我提出了一个完美方案。
“这些东西要多久才能整理完?”我付钱给他时随口问道。
他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说:“或许要到晚上了。”
“我帮你吧。”
他礼貌且坚决地回绝了我:“不,不,这怎么可以——”
“离我女儿放学还早,回去也没事可做。”我打断他,“你上次帮我了大忙,就当是我表示感谢吧。”
他或许被我不由分说的态度吓住了,缓缓说道:“哦,那件事啊,哪里算什么帮忙……”
我没有答话,而是直接将手提包放在了一旁的箱子上。这个动作,表明我突如其来的坚定决心。他大概感知到了这种态度,难为情地解下自己身上的围裙递给我:“穿上这个吧,衣服弄脏就不好了。”
尽管被动接受了我的帮助,林先生还是坚持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让顾客帮忙整理货物实在荒谬,他对此感激不已等等,甚至提出为我提供永久折扣。整个下午,他时不时便要重复这些语句,为了缓解他的不自在,我搜肠刮肚,尽量说些宽慰的话,然而无论我说什么,林先生单方面的声明并未停止,我于是断定这是他自我疏解的方式,便由着他去了。
实际上,我认为那个下午令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林先生,而是我自己。前不久,我发觉自己时常精力涣散,还为此十分担忧、焦虑了一阵子,我毕竟是个医生,等将女儿送入大学,我希望自己回国后还可以穿回白大褂。但那天下午我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对照货物清单,将瓶瓶罐罐填满货架,将一切完成得有条不紊。弯腰、起身,弯腰、起身,这一机械的体力活动模式重塑了我,我感到久违的、难以言喻的快乐。这一过程中,除了林先生持续的“自我反省”,我心无旁骛,没有受到任何打扰,直到超市焕然一新,所有纸箱都被腾空,我脱下围裙交给他。
“你刚说你女儿,在这边读书吗?”他问道。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无意中透露了女儿的事。
我告诉他我女儿的名字,甚至给他看了她的照片,又讲了许多有关她的事。似乎除了她,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但说完我便后悔起来,觉得自己过于鲁莽了,如果被小茹知道,一定会就此狠狠地讨伐我。她从小就热衷于划定边界,经常把“侵犯”这个词挂在嘴边,似乎对此有着明确的定义。随着年龄增长,她的四面八方生长出弯曲、凌乱、密密麻麻的疆界,她笔直地站在疆土的中央自我捍卫。我很庆幸她没有遗传我的软弱、迟钝或者她父亲的圆滑、木然。
“那小茹适合在这里生活。英国人很懂得保持距离。”林先生总结道。他直接引用了我对女儿的昵称,这多少有些怪异,毕竟我很少听到除我丈夫以外的男性说出这两个字。
我对他的论断表示赞同后,瞄了一眼时钟,距离她放学还有半个小时左右。我开始走神,频繁地变换站姿,将重心从左脚挪到右脚,再切换回来。
听完我的“陪读”经历,林先生有些动容,逐渐打开了话匣子,说他五年前从香港搬来这里,“本来是打算和老婆一起的,但她走了。”他自嘲地笑了笑,“我就自己来了。”
我想我大致明白这句“走了”的意思。我向来不擅长应对别人的不幸,一方面,我认为淡漠的态度不可取,但又觉得赤裸裸的同情更不妥。这种情形下,我往往会使用一个面部表情:微微抬起眉头,再将嘴唇抿成一条直线。这很奏效,既透露出善意,又足以让谈话对象捕捉到我复杂的感情,并自行结束这个话题。林先生也不例外,看到我的面部表情,他立即切换到开朗的口吻:“这没什么,我们仍然是好朋友,保持联系的。”他说自己过于平淡无趣,所以不适合她。
看着案板上整齐码好的笋段,我直觉“她”就是这次光临英格兰、迫使林先生暂停营业的“朋友”。回想一周前,我本可以获取更多信息,但是当时已经太迟了,我仅剩二十分钟的时间,可以赶在小茹到家前回到那座房子里,将晚餐准备起来。于是我仓促告别,近乎不耐烦地接过那几盒最终免单的水饺,落荒而走。
那天晚上女儿说她不想吃速冻水饺,希望我下次能包一些,但我至今还没有实现她的这一愿望。实际上我很少聆听她关于衣食住行的提案,因为她总是突然迸出诸多想法,但转眼就忘记。尽管很少被认真对待,她仍然每顿都吃得很快乐,鲜有抱怨。她懒得就生活琐事提出批判,我觉得她的雷达悬浮在某个更靠近高空的地方,不像我,我的雷达被水泥牢固地封在地面上。
这天的排骨烧芦笋是她很久之前提过的愿望。晚饭进行到尾声时,小茹的手机开始在桌面振动,一个微信消息提示出现在屏幕上。我抬头看了眼时间,晚上七点半,国内已经是凌晨了。她迅速抓起手机划拉了一下,我扒拉着碗里的米饭,抬眼瞥见手机屏幕里那张模糊、粉红的脸,酷似泰国辣酱汁和生排骨的颜色。
“你又喝多了?”女儿的语气陡然冷下来。那头的杂音断断续续传来,她没能坚持多久,便称要上楼睡觉去了,将还未中断的通话丢在狼藉的餐桌上,迫使我来接管。
“最近怎么样,小茹学校都没什么事吧?”他似乎对女儿的冷眼并不在意,或者说是未能感知。
“她挺好的。”我说,“就是我想换个地方住。”
“怎么了?”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觉得这房子暖气不是很足,”我将手机平放在桌面上,摄像头朝着天花板,开始起身收拾餐桌。
“能找个中国房东不容易,再换租多麻烦啊,跟房东说一声不就行了?不行给他加钱,让他修修。”
“知道了,没什么事,你赶紧睡吧,我洗碗。”我将摞好的盘子放进水槽。看着盘子里凝固的褐色酱油渍,我决定将它们留到明天再处理。
回到卧室时,小茹正在练吉他。这首歌她已经练了近一个月,仍不成曲调,变形的音符从她的琴孔里笨拙地散落出来,源源不断。我本想提醒她隔壁住了人,或许应该暂停,但最终没有开口。我躺下后,反倒是她先开口说:“你今天去中超了?”
她总是将中国超市简称为“中超”,这让我联想到那群身背骂名的足球运动员,觉得很滑稽。
“我觉得那个老板看起来不像什么好人。”她拨弄着琴弦说。
“为什么?”我讶异道。
她停止拨弦,反问道:“你不觉得他长得很像以前港片里那种奸商吗?”
我被逗笑了,觉得她到底是个孩子。我从没和她讲过这位“奸商”的善举。我们刚到英国没几天时,我头一次独自采购,当时我还不知道如何使用超市的自助收银机,只得鼓足勇气到柜台结账。我反复温习过“谢谢”的发音,不料还是在收银员面前出现了意外,对方——一位皮肤雪白、身材丰满的年轻女孩,抢先一步开口对我说话了。她讲出一个长句,通过她征询的口吻,我意识到那绝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礼貌用语,而是有实质信息的,然而我无从得知。透过她美丽的浅色瞳孔,我看见了一个中年亚洲女人干瘪的轮廓。更糟的是,面对我的沉默,店员丝毫没有失去耐心,甚至缓慢地重复了一遍询问。我不得不做出最后一搏,我联想到在国内购物的场景,猜测她是问我有没有优惠券,或者只是在建议我办一张毫无意义的积分卡,于是摆手连声说“No”。
“OK”,店员耸了耸肩,扫完最后一盒酸奶的条形码,便停止了动作,任由那堆商品散在柜台上——如同一座大厦倾塌后的废墟。
“你确定不需要购物袋吗?”我回头看见一个亚洲男人,个头适中,偏瘦,头发有些自然卷。从他的口音,我几乎立即就猜出了他是香港人。“她刚才问你要不要购物袋。”他补充道。
“哦!要的。”我转向店员,脱口而出。
她瞪大眼睛,疑惑地看向香港人。
“Yes, yes! ”我意识到自己竟然对英国人讲了中国话。
接着香港人开口了,他流利地讲了一个不算长的句子,以“Thanks”为结尾。
“这个要一英镑的,要补给她。”他提醒我。
我忙掏出零钱包翻找起来,钱包里塞满了银色、铜色大小不一的各式硬币,它们如同无数闪烁的眼睛,高傲、漠然、调侃、鄙夷地凝视着我。
“那个金色边的,厚厚的多边形就是。”他小心翼翼地伸手指了指。
我把那枚硬币递给店员时,她向我投来和煦的微笑——我宁愿她没有。香港人选择了自助柜台结账,我踌躇片刻,并没有停下来,而是选择等在超市门口。
“谢谢你。”我说。
“没关系。下次记得带购物袋,这里购物袋很贵的。”他说。
“记得了。”我说,“您是香港人?”
他似乎并不吃惊,只说道:“是,香港来的。”
“香港人英文都蛮好的。”
“普通话不太好。”他笑了笑。
“很好了,很标准的。”我发自内心地鼓励道。他又笑了,但没再说什么,于是我稍稍加快脚步,走在他前面一点,他始终跟在我两三步之后,没有消失在某个中途的岔路口。经过我的住所时,我先道了别,他则继续往社区深处走去。
回到家,我将钱包里的硬币洒在桌上,一字排开,打开手机搜索“英国钱币”,对照着屏幕上的图片和标注逐一辨认起来。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每隔十几分钟就在脑海中温习一遍,总算成功背诵出这些硬币的面额。
几天后,我从房东那听说社区有家香港人开的华人超市,里面可以买到国内常用的调味品,我便立即去了,事实证明,这个社区没有太多香港人。结账时我几乎没有费什么工夫,便将准确面值的纸钞和硬币交到他手上。对于他当时似乎带着赞许意味的微笑,我装作毫不在意。
我独自回忆了一番,没有开口对小茹讲这件事。
“听说市中心有个圣诞市集?”我转而问道。
她肯定了市集的存在,但否定了它的分量。她说:“没什么可稀奇的。我和同学去过了,只不过就是一些摆摊的,卖的东西很寻常,价钱又贵。”
“你喝了热红酒吗?”我又问。
她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说:“你不会喝得惯的,红酒里加了橙子皮一起煮,还有你讨厌的肉桂。”
“而且,你知道吗,那里设了一个临时的游乐场,就在市政厅门口的花园上,设施又小又旧,还挤满了大人小孩。如果他们去过欢乐谷或者迪士尼什么的,一定会觉得这十几磅的门票是个笑话。”她描述得神采飞扬。我想到一部关于小熊在伦敦历险的动画片,在国内看的,当时我以为那些五彩缤纷的布置只是演绎,但或许圣诞市集的确如此呢。
小茹终于放下了琴。房间沉入软绵绵的安静,我隐约听到隔壁的女孩在用英语打电话,不久便睡着了。我做了个十分怪异的梦,在梦里我和租客姑娘、林先生一起在房东的中餐馆吃饭,我们用普通话交流,香港人谈了许多有关那位朋友的事,女孩也要揭开她重回英格兰的神秘原因。但是夜里小茹把腿压在我肚子上,打断了这次交谈。
第二天我没有起床给小茹煎鸡蛋,这还是头一回。我下楼时,一切如常,她早已去上学了,只是冰箱里少了两片吐司,水槽里倒着一只有牛奶渍的杯子。
租客女孩坐在客厅落地窗旁,正盯着后院我的海鸥老友看。
“今天不出门?”我并没吓到她,她大概已经听见我下楼的动静,只是没有回头。我开始沏茶,开水浇在立顿茶包上,一缕缕朱红色如烟般从杯子底部升上来。
“阿姨——”她仍旧没有回头,但显然是在对我说话,“你喜欢这里吗?”
“这里挺好的呀。”我的水杯倒满了。
“我不喜欢,”她说,“每天都这样阴沉沉的——一年四季。这儿的人很好,总对你笑。”
我没有说什么,而是在等待她的转折。
“但他们对你说着他们的语言,还那么自然,仿佛你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你的英语应该很好吧?”我感到诧异,没有提及我听见她用英语打电话的事。
她终于回过头来,冲我撇撇嘴说道:“所有人都说我的英语好,就连英国人也这么说,唉。”
我在餐桌旁坐下,将视线从海鸥拉回到她身上,她的红毛衣和外面灰白惨淡的天色形成扎眼的反差。我对着她浮肿的脸颊说:“你看,你一个人来这里,坐飞机、坐车、租房、交朋友,什么都搞定了,你妈妈肯定很为你骄傲。”
她将头转了回去,再次背对着我。我的目光也再次回到海鸥身上,它钻进了那片矮篱围住的花圃,慢悠悠地在泥地上挪动脚步,最终停留在颓败的小花园中央,但我并不清楚它来时的路途。女孩鲜红的后背稍稍移动了一下,将那条本就模糊的轨迹完全遮住了。“那你为什么回来?”我放弃辨别海鸥的路径,问女孩。
她犹豫片刻,说自己为一个重要的朋友而来,她必须为之奔波。她频繁地停顿,空泛又警惕地讲了很久。这位朋友的年龄、国籍、甚至性别都显得暧昧不明,我无法判断,但感觉到我们之间升起了一道篱墙,她站在篱院中央。总结她的“朋友”时,她用深沉的语调说“给了我一股奇怪的动力”,好像在宣读一则人生格言。我看到她鲜红色的后背一点点矮下去,海鸥面前的道路显现出来。
“我房间的暖气太冷啦。”她后来补充道,更像是自言自语。
我则在脑海中搜寻,试图找出一位这样值得我踏上遥远旅途的“朋友”。
“你知道这个社区里有家香港人开的中国超市吗?”或许是同样被赋予了某种“奇怪的动力”,我说出这句话。
“不知道。”
然后房东打开门,在门廊跺脚,结束了我们的谈话。
那天之后,女孩依旧每天出门,我也还是遵照时间表往返于家和连锁超市之间,偶尔会去附近的喷泉花园坐上一会儿,但我没有再去林先生那里。
平安夜如期而至,小茹接到了一位本地同学隆重的圣诞晚餐邀请,我受宠若惊,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套昂贵的银制餐具礼盒,让她带去同学家作为圣诞礼物,并立刻在微信上将这一消息分享给了她父亲。
尽管女儿不在家吃晚饭,下午我还是去了超市。我买了两块牛排和一瓶酒,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酒,但它漂亮的瓶子吸引了我。我想这是平安夜,不能再放任租客女孩吃塑料盒里黏糊糊的通心粉。
我回到家时,楼上传来一阵仓促的脚步声,随着行李箱轮子缓慢而有节奏地敲击台阶的声音,女孩出现在客厅。我吃惊地问她要去哪。“想回家去,不愿在这了。”她回答我时扯了扯嘴角,如同第一天早晨出现在客厅时那样。
目送女孩登上开往机场的大巴,我往社区深处走去。香港人的超市门旁站着一只海鸥,隔壁的马来小吃馆没有营业。
“林先生。”我郑重地打招呼。
“今天这么晚来?”他有些诧异地从柜台后抬起头,似乎已经在做关店前的收尾工作。
这时,通向二层仓库的小楼梯传来动静,我循声看去,一个女人正走下来,身上系着林先生归置货品时常系的围裙。她穿一条浅蓝色牛仔裤,裤脚微微堆叠在鞋面上,露在围裙外的米色毛衣是束袖设计。她与我想象中的模样竟然十分吻合。
林先生用粤语对她说话,随后转向我用普通话介绍道:“这位是我香港来的朋友。”
她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欢迎。”
“今天需要点什么?”林先生说,他脸上写满了节日的热情。
“我有点忘记了,再说吧。平安夜快乐。”我回答得干脆利落。然后我走出超市,轻轻关上了身后的门。
我并没有立即回家,而是绕着社区的外围兜圈子。此前每次去中国超市的路途中,我总是步履悠闲,但离开时却总带着急迫甚至慌乱的情绪,仿佛要赶回哪去。但今天不同——今天是平安夜。我带着急切的愿望而来,却漫无目的地离开,没有什么确切的目标值得我疾步。
我脑海中不断出现林先生同那个陌生女人讲话的场景,他说了一句简短的粤语,粤语是那么好听,懒散而不失亲昵,胜过他用普通话和我讲的任何一句话。他介绍我时,她脸上闪过一丝会意的笑,仿佛瞥见旧流水账里不经意的一笔,在片刻的惊喜后,便翻过这一页,永远束之高阁了。林先生一定和她提起过我这位顾客。而她则崭新地出现在我面前,毫无序言可循。我心烦意乱,故意踩在路沿的水坑里,但愿每一步都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不留下印记。
我没料到平安夜是如此安静,社区弯曲交错的小径上停满了车,但无人走过,甚至没有鸽子停留。我缓缓经过每一栋房屋,它们看似一致,实则家家户户都在门前做了富有巧思的装饰,以彰显自己别具一格。不过此刻,它们被如出一辙的金黄色灯光覆盖着,融进同一片温柔的夜色。我听不见任何喧闹的声音,但十分确信自己处在一个盛大、热烈、欢乐洋溢的夜晚。
家门外那盏路灯已经亮起,将潮湿的地面上那些散落的枯叶照得晶莹透亮,如同沉没在铅色雾气中的星星。
我把钥匙揣进口袋,掉头朝昆士街的方向走去。通往闹市的主干道上同样空无一人,海鸥的鸣叫此起彼伏。夜色还在不断下沉、蔓延,我平静地步入其中,偶尔有车子从我身边疾驰而过,搅动起冰凉的空气,也冲撞着厚重的夜幕,这时,我便把脖子缩紧,加快步伐。
我想象百米长的圣诞市集繁忙喧嚣,蜿蜒而去,从远处望去,泛着一层金色的光晕。光晕笼罩下,有调皮的人偶、忽高忽低的笑声、香甜的气味——我将手捧热红酒穿行其中。
无论如何,我都这么想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