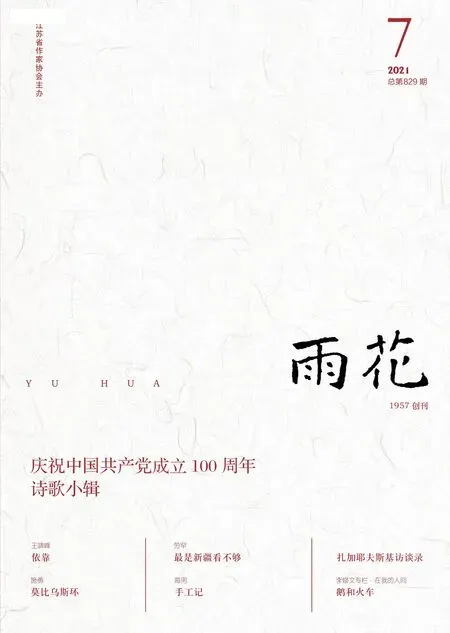鸽子
朱苑清
1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记得她好像姓孙。那是一个高挑、瘦削的年轻女人,跟我年岁相仿,长相一般,唯一给我留有印象的是,她左额处有一块隐藏的胎记,铜钱般大小,蓝灰色的,颜色分布还不太均匀,有浓有淡,有疏有密,疏淡的地方像小猪佩奇跳泥坑时溅出的一颗泥点子,浓密的地方像一团密集细小的虫卵。也许正是因为这块胎记的存在,才使得她用长长的刘海遮住左额。这是一种很古怪的发型,从我见她第一面起直到后来,只改变过一次,而且也是仅有的一次,这是后话。
秋后的一个早晨,我到菜场买鸽子。她的摊位就在菜场尽头出口处的一个拐角,与后面的一条窄窄的小街相连。她的鸽摊不像菜场里正规的门面那样宽敞明亮,伸出来的雨棚是私搭的,占用了原本就很窄的小街的空间。鸽摊大约有五六个平方,最前排是几个锈迹斑斑的铁笼,笼子后面堆满杂物,小小的空间显得凌乱而拥挤,给人一种窒息感。
还是三十五的吗?她问。
我点点头,说,你帮我挑一只吧。
只见她往一排铁笼后面一站,手腕带力向外一甩,说,往后站,不然喷你一身灰!
里里外外,肮肮脏脏。锈斑、青苔、灰尘、鸽毛、蛛网、鸽粪、血迹……五颜六色,铁笼子上糊得毛茸茸厚厚一层。掀开位于鸽笼上方的活动门,她将一只手伸进鸽笼里,一捞,拽住一只白麒麟花的,掐住它一对翅膀,拎起来掂了掂分量。不满意,手顺势一荡,往笼子角落里一扔,又重新捉了一只灰雨点过来。笼子里,密密匝匝的小生命,浅灰的、纯白的、灰白条的、蝴蝶花的、红宝石的、雨点花的……本来一只只都安安静静地待着,脑袋贴脑袋,身子挨身子,被她这么一撩,纷纷扑腾起来往角落里躲,躲不及的干脆骑在别的鸽子身上,又一阵咕咕乱叫。
就这只吧!她说,利索地把灰雨点从铁笼里拽出来。
灰雨点被她的粗鲁吓着了。小眼睛瞪得圆圆的,边扑棱翅膀,边蹬着小腿。霎时,灰尘、鸽毛伴着臭气一拥而上,充塞了狭小的空间。
站远点。她说,善意地笑笑。
我下意识向后退了几步。这时,只见她从血水交融、鸽毛遍布的操作台上,操起一把磨得锃亮的老式铁剪子,另一只手把灰雨点的脖子用两指掐住,反方向一折,刀尖直戳进喉咙,再一剪子下去,不等鲜血冒出来,便迅速往身旁半米高的黑塑料桶中一扔。黑桶微微摇晃几下,很快便停止了晃动。稍过片刻,她将手伸进黑桶里,灰雨点再被拎出来时,先前活蹦乱跳的小家伙已变得毫无生气,脑袋脱垂着,脖子、躯干看上去全都软塌塌的,覆羽周围沾满鲜红的血迹,唯独两条小细腿绷得直直的。她拎起它一只向里蜷缩的小爪子,往身旁的热水锅里一扔,随后用长长的木棍把它捣进热水的深处,随便搅动几下,便又将它拎出来。这时,灰雨点厚厚的一层鸽毛便很轻易地被撸干净了。然后是开膛破肚,清理内脏……她做这一切时,手法娴熟,动作准确而麻利,脸上毫无表情,俨然无情的杀手。
好了,拿去吧。她说,将光秃秃的小家伙塞进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递给我。
我接过来,随手拨开看了看,无意间发现鸽子的背脊处有一块麻麻点点、紫黑色的印迹。我先以为是没洗干净,用手搓了搓,没搓掉,又用力搓了几下,印迹仍异常触目地留在原处。
老板娘,你过来一下。我说,你看。我用手指了指鸽子的背脊。
哦,这是在笼子里撞的瘀斑,不碍事。她不以为然道。
我说,好像不是吧。突然想到最近市面上爆发的禽流感,内心不由一紧,认定这肯定不是瘀斑。
她见我不说话,便宽慰道,鸽子在笼子里打闹,皮肉上受点伤是常事,吃是一样的。
我说,不。断然摇了摇头。
那你说,不是瘀斑是什么?她反问。
我说,搞不好是体内有什么病毒,也有可能是一块胎记,总之小家伙肯定是有点毛病……我没说完便停住了。因为我突然发现她眼皮一垂,身子像遭了电击般地一颤。她慌乱地用手撸了几下前额的一片刘海,脸色先是微微一阵发白,继而又一点点涨成通红。她一声不吭,站了一小会儿,身板挺得僵僵的。而后,她从钱箱里拿了三十五元钱往我跟前一搁,夺过我手里的鸽子随手往操作台上一扔,意思是要我拿钱走人。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令我很吃惊。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她是一个蛮随和的人。就在我发愣时,排在我身后队伍里的一个老阿姨悄悄走到我跟前,用胳膊肘抵了抵我,伸手在自己的太阳穴处比划了几下,诡异地笑笑,挥挥手,又做了几遍嘘声的手势。事隔多日之后,我才知道那手势背后的含义。当时却浑然不知,认为老阿姨只是想缓和一下紧张尴尬的气氛。于是,我自找台阶向她赔了个笑脸。
老板娘,你别生气,那只算我买的,你再重新给我捞一只。说着,我便亮出一张百元大钞。
就你钱多,是吗?她不屑地睃了我一眼,语调冷冷的。
受了奚落,我的脸一阵发烫,心跳似乎也加快了,呼吸显得有点急促。但我没有发作,脸上仍挂着矜持的微笑。她还是冷着脸,一言不发,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旁边那个老阿姨有点看不下去,连劝带哄说,小孙,你再卖一只给人家吧,我看这个女同志,人蛮好的。
这跟你有关系吗?她反诘道,又冲着我身后喊,下一个。
由于是周末,生意好,不愁卖。不一会儿,我身后已经排了五六个人。
人家不卖给你就算了,你往旁边站站。我听见身后有人说。
我下意识地闪过身,让出自己的位置。这时,我感到背后有人对我指指点点,也听到有人在窃笑。十分钟,也许还不止,我窘迫地站在鸽摊旁边的暗处,像个被人欺负了的无助小孩。我记不清被晾了多久,也记不清什么时候回的家。
2
自那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视她为冤家。我到菜场买菜的时候,最多也就到她家附近的鱼摊或者肉摊,买点鱼或者肉。然后,就一定会绕道回头。有几次偶然与她相遇,我都是将头往反方向一偏,装作没看见的样子。
一个初冬的傍晚。天色很暗,到处灰蒙蒙一片。下班后,我顺便去菜场带点菜回家。菜场里,人不多,地上一如往常又脏又黏。我买了点蔬菜,还想买点肉。肉摊和她的鸽摊挨得很近,肉摊灯火通明,而落在巷口拐角处的鸽摊则灯光昏暗,显得冷清而孤单。我原本就没打算买鸽子,所以买完了肉,从她摊前绕了一下就准备回头,可也就是不经意间绕那一下,让我忽然闻到了一股异常刺鼻的怪味,这股怪味不同于以前我熟悉的那种单纯的鸽臊味,而是一种辣眼发齁,闻上去十分奇异的臭味,并且由于气味过于浓烈,嗅到鼻腔以后还会往喉头钻,以致鼻根连至喉头都跟着一并发苦。眼看天色迅速暗下来,想着要赶回家做饭,我也没想上前去探究竟,眉头一皱,捂住口鼻,迅速掉转头往反方向迈开了脚步。
可是,还没走两步,我又停下了。
我的脚步是被一种似唱似吟、低回深沉的乐声给拖住的。当我诧异地反应过来,从她家鸽摊里居然飘出了印象中只有在寺庙或者佛堂里才能听到的音乐时,好奇心开始迫使我一点点转身回头。
伫立。细听。
笛声、水声、古琴声、唱诵声,熨帖地轻轻一并揉捏……入耳虽轻,却低沉浑厚,深远绵长,听上去使人心神宁静。我回过头,望向乐声的出处,刺鼻的怪味又掀起新一波强劲的浪头向我盖过来。顿时令那妙哉妙哉的舒逸感一下子又荡然灰飞了。我强忍着不适走过去,这才发现她正在里面忙活,并没有注意到我。我的好奇心从来没有像此刻这般强烈,不禁暗暗打量起她的四周……
凑近了几步。狭小的空间,不难察觉异样。袅袅绕绕,轻轻曼曼,一缕细烟,在融融光晕下像是一片轻飞的绒毛,慢条斯理地从她身旁一道简易的木挡板后面飘了出来。烟气不疾不徐地向她头顶悬挂的小灯方向散去,与几只莽莽撞撞、萦绕在灯下的小飞虫纠缠在一起。
这道挡板,过去似乎是没有的。
我向着弥漫而来的烟气细细一嗅。这缕烟气里还藏着一丝隐隐幽香,闻上去好似木质香,有点像是檀……檀木香?心中顿生疑惑,又扫了几眼四周。墙角里,蛛网密结,灰尘遍布。正想着,散漫的目光不经意向挡板背后一觑。
刺眼的金黄!头戴天冠,左手持宝珠,上有幢幡,右手作施无畏印——挡板背后,居然供奉了一尊地藏王菩萨的铜坐像!
又见矮矮的供桌上,深棕色的佛龛前,三只供水杯里供着清水。香炉里,正燃着一支佛香。冉冉缠缠,缭缭绕绕。一星光点在丝丝余烟的环抱下,躲躲闪闪,时隐时现……收录机里,不间断地飘出一连串我听不懂的梵文唱词。
袅袅佛音从佛龛旁的红色小收音机里流淌出来,在一片串了味的污浊空气里继续漫行。黄昏散尽,夜色被一点点注满,铁笼里的鸽子们忽闪着一双双不谙世事的眼睛,望向黑夜,望向不久后注定要降临在它们身上的死亡,它们低沉地咕咕叫着,像是在对收音机里的经文唱诵者发出求救的请愿。而她呢,正站在操作台前宰杀一只鲜活的白色鸽子。好奇心紧紧攥着我,我迫不及待地将目光投到她身上,试图从她的一举一动中找出这番蹊跷的来由。我站到她看不到我的一处视线盲区,目光牢牢盯着她,这时我发现,她的神态和过去不大一样,杀鸽子的速度明显比过去慢了,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一剪子下去,将鸽子往黑桶里一放,还没出一分钟就将其拿出来,提着它的一只小爪子往热水桶里随便摆几下,木棍都还没来得及上场,就又急匆匆把鸽子提上来。鸽毛还没脱干净,纷纷黏在身上,她就拾起操作台上的铁剪子将其开膛剖肚。剪刀尖儿戳进皮肉后,她的目光没有像以前那样定在小家伙身上,而是一直紧紧地盯着操作台正前方的一块白瓷砖墙。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墙上除了有一点水迹和几块斑渍外,并没有什么异样。
光影晃动。佛音渗透。异味弥漫……
她的目光就这么凝在墙上,眉头紧皱,眼神里揣着一丝心不在焉的烦躁,两只手却没闲下来,清理鸽子内脏的动作依旧在继续。
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噔噔噔”一阵连贯而急促的脚步声。我不禁四处张望,寻找这声音的出处。好像是从贴着她操作台的墙根处的一道小门后面传出来的。这道小门过去有没有,之前也没什么印象。
脚步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急迫……
突然,小门上原先静止的门把“咔哒”一声,急速转动——
只听,“砰”的一声响。
门,被推开了。
是一个小男孩!
他嘶哑地喊道,妈妈!妈妈……我害怕……
那个声音,那张浮肿的小脸,暴露在我眼前的一刹那,我的心不禁“咯噔”了一下。
多年以后,如同后来我又在公园里偶遇她那次一样,回忆会把我带入一种难以言说,斑驳吊诡,琉璃般的梦境氛围里。菩萨、怪味、轻烟、鸽子;肮脏的铁笼、湿滑的路面、蜿蜒曲折的小巷、年久颓旧的菜场、面目浮肿的孩子,所有浮光掠影一一闪过后,在她那张像是被附上一层金色柔光的、瘦削的、散着长长刘海的侧脸上,她的眼睛里噙着泪。她安抚儿子时,那一只未被刘海遮住,可以被我看见的眼睛,一直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尖上。
幽幽暗灯下,我无意间听见了母子俩的一番对话。
孩子问,妈妈,你不是说烧香给菩萨认错,我的病就会好吗?怎么我还是觉得这么难受?
女人说,妈妈身上的罪很深,而且我们才开始烧香,世上求菩萨原谅的穷人这么多,菩萨还没看见妈妈呢!
孩子问,妈妈,你犯了很大的错吗?
女人说,是,很大的错。
孩子问,那是什么错?
女人说,你还小,说了你也听不懂。
可是,菩萨会原谅你吗?孩子问。
如果菩萨一直不原谅你,我会死吗?孩子又问。
妈妈,你说话,快说话呀……孩子急切地摇晃着女人的肩膀。
女人微抖地吐出“不会的”三个字时,一把将孩子瘦小的身子揽入怀中。她的嘴唇不停地嚅动着,像在对孩子说,又像在对自己说,你不会有事的。菩萨会原谅妈妈,一定会原谅的……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小,直到站在暗处角落里的我再也听不清,只看见她的眼眶微微变红,眼泪无声地流了出来。
妈妈,你帮我点香,我要给菩萨再烧一遍,多磕几个头,求求它早点原谅你。
寒意渐浓,月色淡黄。女人点了一炷香,递到了孩子手里。续上香。短的,依偎在长的那根旁边。微微弱弱,我看见两星光亮在狭小晦暗的空间里扑朔。暮秋的晚风,挟着仓促而来的细雨吹进了她的鸽摊,将这里的夜晚洒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沉郁的颜色……
3
之后,没几天又去买菜,隔壁肉摊老板悄悄告诉我,鸽摊家的孩子一天早上起来被发现浑身水肿,结果送去医院一查,没想到居然患上了慢性肾衰。她带着孩子到处求医,却老是看不好。然后她也不知道听谁说,可能是因为杀生杀多了,这种难治的业障病才会报应在她孩子身上,所以就开始烧香忏悔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她几年前就和丈夫离婚了,她的摊位背后的一间平房就是她家。
消费完对她的所有同情心以后,渐渐地,人们都不太愿意上门来买鸽子,她家的生意也就大不如前了。
转眼之间,又过了两个月。
离菜场半站路不到,有一个小公园。绿篱、假山、溪池、石桥、草坪、盆景园……该有的都有之外,在绵延的石子路深处的小山坡上还有一座小庙。小庙里,只有一个驼背的老头没事会拿着个鸡毛掸子忙里忙外,几乎见不到有正儿八经的僧人出入。所以,那小庙更像是一个空洞的景观。见菩萨就拜,上一炷香,再往功德箱里投几块钱,做一遍同样空洞的仪式,既不会显得对菩萨不敬,又能满足保佑自己的一厢情愿,反正像我这样肤浅的普通人,比比皆是。那段时间,我常到小公园里晨跑。一天清晨,天色微明,清冷的空气中透来阵阵寒意。我正跑得呼哧带喘的,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清脆的车铃声,我一回头,竟是那个卖鸽子的女人。只见坡路上,她正气喘吁吁地蹬着一辆小三轮车,肩上斜挎着一只款式陈旧的黑色皮纹包。也许是蹬车蹬热了,又或者是被冷风吹的,她的脸红扑扑的,显得气色特别好。我主动和她打招呼,问她去哪儿。谁知,她往三轮车后面的车斗里一瞥,微微一笑说,你猜。我看她一改往日的颓丧,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便更加好奇了。再定睛一看,车斗里,平放着三只鼓鼓囊囊的灰绿色大编织袋,袋口被绳子捆着,像是扎得很紧,每只袋子都装得满满当当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动来动去。我凑近一听,里面发出“咕咕”的声音。
我问,去哪儿?
她仰起头,朝坡顶方向一指。
寺庙?我问。
她点了点头。也许是猜到接下去我会问什么,不等我开口她便朗声说,我去那儿放生,做功德!
来到坡顶,太阳已在东边露了头,天空变得越来越清亮。寺庙的铜门严闭着。宽阔的石板路两旁,枯黄的草坪挂着昨夜的霜露,一派苍白。她把三轮车停在路边,卸下身上的黑包,她的一举一动像个活泼的孩子。走来的这一路她告诉我,昨天是她的鸽摊最后一天营业,她决定不干了,她要把摊位租出去,然后在附近重新找份工作,如果能同时兼职几份更好,像超市、家政、推销、保洁、送快递、送外卖……脏活累活她都愿意干。聊着聊着,她愈加放松,进而打开话匣子向我袒露心声称,自从孩子生病以后,她才知道佛经里“人死为羊,羊死为人”这句话。她告诉我,杀业是世间最重的恶业,果报也最苦。她想尽快消除自己身上的杀业。她还说,她把昨天没卖完的鸽子全都拖来了,这次放生的功德会抵消很多很多她身上的业障,加上以后又不再杀生,她儿子的病也许会慢慢好起来……她一路和我说个不停。山间的风,凛冽地吹着,她的脸颊依旧红红的。我时不时看看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庙门外,山顶上。她将黑包的拉链拉开,从里面掏出我眼熟的那台红色小收音机,她把它放在地上,随手按下开始键。然后,又从包里取出一个深棕色的小香炉和一盒佛香。她打开盒盖,拨开里面薄薄一层细软的灰白色裹纸,认真地数:一,二,三,四……从里面数出六根,又捻出三根来递给我。这时,我发现香炉里没有香灰,心想,这香没法插住。没想到,她悄悄把一只手伸进了黑包旁的侧袋,从里面掏出了一小把米来,手呈半握状小心翼翼地将米放进了香炉里。随后她看了看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掩饰不住的激动。接着,她左手捏着香,右手托着香炉底部,我跟在她的身后看着她一步步走向庙门,她的背影就像在隆重殊胜的忏摩仪式上一样庄严,一样令人生畏。
庙门上的铜环被她重重反复叩击后,依然静默。没有人来开门,一切都在岿然不动中持续。沉默,像是对她无声的、冷冰冰的拒绝。她没辙,只好将香炉放在庙门前高高立着的门槛上。
雄赳赳的火苗从打火机里蹿出,换来香上一星持久的光点之后,点燃了香。闭目思索片刻后,她双手持香高举,双眼紧闭。她的眉头微微皱起时,眉间“川”字形的皱纹深刻地显露了出来,就像镌刻在双眉间似的。深深揖拜后,她来到香炉前,蹲下,把三支香牢牢地插进香炉里,又重新折返到空阔的石板路中间——庙门的正前方。这时,她抬眸,用一种深邃的目光望了一眼疏朗的天空,又闭上了眼睛。她挺直身子,双手合十,屈膝跪下,双手翻转,摊开掌心,口中一番默念后,将身体深深地埋了下去,几乎与地面平行。她的衣角被风吹得高高掀起,几乎将她整个人都包裹了起来。她起身、跪下、磕头,然后再起身、再跪下、再磕头……就这样,她对着庙门东、南、西、北、每个方向,重复循环磕了一遍,再一遍,又一遍……
我站在不远处的石阶上,静静地望着她,等待她将这一神圣的仪式全部完成。天空,像一床巨大厚重的被衾,将她覆盖,将她掖藏,将她悄悄掩埋。
该你了。她终于走过来,对我说。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然后开始照着她的方式点香、揖拜、磕头。她则在一旁低着头,虔诚地诵起了经。
风吹香散,佛音飘荡……
末了,我和她一起把沉甸甸的编织袋从车斗里卸下来,抬到了空旷平缓的山坡上。天空,像是展开了它的怀抱。解开绳结,扑棱棱,扑棱棱,一只只鸽子从袋子里冲出来,飞向天际。盘旋在空中的鸟儿见到突然涌来的鸽群,纷纷让出自己的领地,任凭它们尽情飞翔。斑斑斓斓,像烟花齐放,像满天星飞,像彩蝶翩跹。它们就这样披着晨曦馈赠的外衣,一点点飞向了未知的远方……
忽然,她转过头,望向我。
你说,菩萨会原谅我吗?
会的。我说。
4
回去的路上,她把两只老鸽子和一只翅膀上受了轻伤、飞不高的鸽子,带到了山后的小树林里。找到一片草木繁茂的地带,她把它们一只只从编织袋里取出来,小心翼翼地。被她托在手心的鸽子胆怯地看着她,圆圆的小眼睛里尽是惊慌。她轻柔地抚着它们背上的覆羽,时不时给予一些安慰。走到深处,她把它们放在一片柔软的、黄绿斑驳的杂草丛里。去吧,去吧,别让人发现了,发现就把你们逮回家吃掉啰……她调笑着与它们道别。而后,她把黑皮纹包侧袋和香炉里的米全倒出来,撒向草丛,撒向它们。可小家伙们大概是不明白她的好意,反倒惊慌起来。看着它们一会儿低飞,一会儿连蹦带跳,她温柔的目光里浮现出了一丝母性的光辉。安顿好它们后,她如释重负,一路和我又说又笑。山风总是调皮地吹乱她的头发,走着走着,她忘情地把头发勾到耳后,显露出那块醒目的蓝灰色胎记,可她好像并不那么在意,直到我们在小公园门口分手,她也没有将刘海放下来。
后来,我再去菜场,发现她家的鸽摊果然关门了。摊位旁,青灰色的水泥墙上贴着一张皱巴巴的白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招租”两个字,下面一排是她的手机号码。后来有好几回我经过她的摊前,看到那张白纸被风吹得又干又脆,边角高高地翘了起来。再后来,纸便不见了。露往霜来,日子在平淡中周而复始。没过多久,我因为工作变动,随后便开始搬家。直到一年多后,有一天,我去搬剩下的一些零碎物件时,突然想起了她,便想去她的鸽摊看一看。我想,她的摊位也许早已租出去了,不知她现在做什么工作,还有,她儿子的病好一点了没有?
我再次看到了她的手,那是一双伤痕累累、触目惊心的手。手背上,全是大大小小,深深浅浅,各式各样的疤疤点点。深褐、浅褐、深红、浅红,乌青、紫黑……一点点,一条条,一片片,新伤叠着旧疤,疯狂地交织在一起,就像一张密织的罗网,它们无序密集地排列,看上去比她额前的那块胎记更加不可思议。
此时此刻,我浑身颤栗,心脏连同全身的肌肉都在剧烈颤动,我的目光定格在她手背上短短长长、密密麻麻的伤口上。而她就站在装满鸽子的铁笼后面,除了先前被额前长长的刘海遮住,而现在正大光明地露出的那块扎眼的胎记之外,她看上去和过去并无二致。我站在她摊位前,这里没有怪味,没有佛乐,没有菩萨。什么都没有。有的还是那扇小门,那盏小灯,那个操作台,那把老式的铁剪子,连同那块隔板……一切都是老样子,一切仿佛被格式化到了最初的状态。
是的,她就站在我的面前,难以置信地重新回到原先她所扮演的杀手的角色中。我的目光凝在她的手上,有几道显然是才受的新伤。伤口的样子像是针刺的,又像是划伤的,更像是戳破的。其中较深的一条细小的伤口上,还立着一颗微微突起的血珠,旁边蜿蜿蜒蜒地漫出两条树杈形的血色溪流。珠子正在变得越来越饱满,越来越圆润,直到突然破裂,将包藏其中的血水全部贡献给了溪流,而它的消失果然让溪流看上去增加了一分雄壮。
她胳膊向前一伸,把装有刚杀好鸽子的透明塑料袋递向客人时,站在一旁的我,正好看到了以上这一幕。
现在,我看见她的手腕处还戴着一串深棕色的檀木佛珠。
一旁的客人走开后,她这才注意到我。
怎么是你啊?她招呼我,语气一如既往地亲切。
你好。我的声音隐隐发抖。
好久不见你!
我搬家了。
哦,怪不得呢。她说。
冷场的沉默,在各自将一个短促的微笑抛给对方之后,才被打破。
还是三十五的吗?她突然开口问。
我的心跳顿时微微加快,赶忙回道,不不,我已经好久不吃鸽子了。
只听她低沉地“哦”了一声,仿佛突然回忆起了什么,神色瞬间变得不太自然。
你儿子的病,怎么样了?
她沉吟了一下。
还行吧,时好时坏的。她说。我找过几份工作,时间都不自由,照顾不了他,还有……说到这里,她摇了摇头,突然又停下了。
我感到她好像是特意在向我作解释。
还有,医生和我说,这个病往后说不定能看好,但也不排除恶化的可能,我想趁自己现在还年轻,能苦几年是几年,多攒点钱,万一以后不得已他需要换肾什么的……
她没再往下说,我的内心突然涌动起一阵莫名的酸楚,连连安慰她道,孩子还小,身体都在长,凡事还得多往好处想!
嗯嗯。她机械性地点了点头。
这时,她的摊前又来了一名顾客。我看见她很麻利地从铁笼里捞出了一只活蹦乱跳的灰鸽子,然后拎着小家伙径直走到操作台前。她的神情依旧淡定,只是没有像从前那样,立刻将锋利的剪刀尖直戳进小家伙的喉咙,而是用双手微微托着它的翅膀根部,轻轻举起了它。这个动作像极了她跪在庙门前,发露忏悔时的姿态。备受惊吓的小家伙眼睛鼓瞪着,慌乱地开始用尖利的喙对她的手发起有力的攻击。一下、两下、三下,连着又是几下……它啄得凶猛,啄得一点儿也不留情。她闭着眼睛,眉头微锁,从皮肉间渗出的那一丝丝掩饰不住的疼痛在她的眉宇间徘徊,打滚……轰轰烈烈,酣畅淋漓。她像是在享受这一刻疾风暴雨般的痛楚。可是,仅仅在片刻之后,她就又抄起了那把铁剪子,将寒光凛凛的刀尖对准小家伙柔软细长的脖子,然后用力地、深深地戳进了它喉咙的深处……
剪破。放血。脱毛。直到它终于变得无声无息。
离开鸽摊,我向蜿蜒的小巷深处走去。阴沉沉的天空中,飘起了一阵花絮般的雨丝。深远的小巷里,几个孩子拿着彩色的塑料棒子正互相追逐、打闹。远远地,我的耳边忽然传来了一个女人温柔的喊声,下雨了,快回来……只听,从我身边匆匆跑过,落在最后面的一个小男孩满脸通红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长长地“哦”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