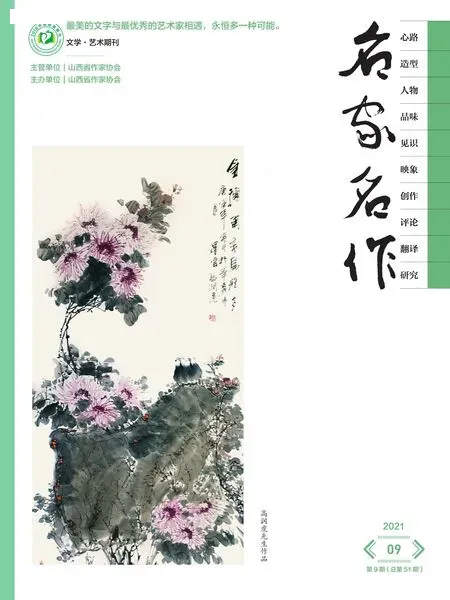壁 鬼
黄元标
还是集体化的时候,憨狗就是闻名村里的壁鬼。其实“壁鬼”这个名字,就是专门给躲在墙壁内叫号的人起的绰号。
这不,还有三天就过年了,村里放干了鱼塘。天寒地冻,生产队长带着五六个小伙子全都穿上雨靴连长裤的雨衣下塘捉鱼。
整整一个下午,大大小小的鱼全捉了上来,装进了岸上的篾箩,接着抬进了村头的大祠堂。
傍晚,村里人都拿着菜篮、脸盆、水桶什么的聚集在祠堂内。几个有声望的村民和队长在忙着分鱼。先挑出大鱼,一股一股堆放在地上。今天是按门户分鱼,每户一股,地上满满当当地堆了九十八股。没有秤,也不用称,凭众人眼光,多的匀出,少的补上。等待分鱼的村民靠墙围在四旁,眼睛骨溜溜地看着,不时有多嘴的—队长,这股好像少了一点;队长,这股大鱼好多。
谁多嘴,队长就拿眼瞪谁,斥责道,就你名堂多。便真的过去翻翻看,比较比较。
最后,大家看看匀得差不多了,队长拿出分鱼花名单,大声叫喊,壁鬼,分鱼啦!
壁鬼憨狗大声应着,来了来了。他忙挤出人群,从队长手里接过花名单,转身躲进祠堂左侧的小杂间里,等待队长叫名字。
村里有个规矩:队里分东西,一不抓阄,二不排队,三不论资排辈。喊一个忠厚心实的人做壁鬼,隔墙叫名,叫到谁的名字,谁就去拿,好省事。
村里好多人都不愿做壁鬼,怕挨骂。分到好的笑,分到差的叫,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谁愿得罪人呢?
队长为这事特伤脑筋,最后只能指派憨狗去做壁鬼。憨狗挺乐意的,逢人就说,是队长看得起。
憨狗爹娘死得早,姐妹全嫁了人,他脑子迟钝,说话大舌头,有点含糊不清。可他为人忠厚热心,不管谁家碰上为难事,他只要在家,随喊随到,尽心尽力。他都四十多岁了,还是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细婆也带他相过好几回亲,不是女人嫌他家里穷,就是他嫌女人不好,条件好一点的女人只要听到憨狗的名字,就躲得远远的。
后来,细婆岁数大了,再也没有精力去操这份心,只好让他顺其自然。
分鱼开始了。队长指着地上一股鱼大声说,这股是谁的?壁鬼在杂间内马上回答,强仔咯。外面马上有人接嘴,强仔咯!
强仔拿着脸盆马上过去装鱼。
队长又指着一股说,这股是谁的?壁鬼回答,二牛咯。外面又有人应,二牛咯,二牛快装鱼!
二牛妈拿着竹篮子慢慢腾腾地过去捡鱼。她没看中这一股,心里有气,脸色难看。
这股是谁的?三矮咯。
……
祠堂内喊一声应一声,此起彼伏,有条不紊。壁鬼在小杂间里每叫了一个名字,就拿圆珠笔在花名单上的名字后面打个勾,做个记号。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地上的鱼堆不见了,只留下满屋的鱼腥味。最后一堆是壁鬼的,也不用队长叫,已经有人帮他装好了。这留在最后的一股也可能是最差的,队长心中有数,壁鬼也不计较,乐呵呵地把鱼倒进自己的木盆,屁颠屁颠地回家了。
憨狗习惯了做壁鬼。每回分完东西,村里免不得有人咒三骂四,他知道自己心里无鬼,常说,让他骂吧,自己骂自己兜回去。他从不记仇,见面总是笑脸相迎。也就这样,壁鬼在村里倒成了憨狗的专行,时间一长,村里人也懒得叫他的真名,老老少少壁鬼壁鬼地叫,憨狗从不介意,倒觉得壁鬼这个名字比憨狗动听。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村里分了责任田,生产队也改成了村民小组。壁鬼在自己的责任田里真有股使不完的劲儿。他家的禾苗长势喜人,比别人的青,比别人的壮。他每天收工回家,总是一步三回头,田里的禾苗好像娇美的大姑娘,叫他恋恋不舍。
水稻在一天天灌浆、一天天抽穗、一天天泛黄,看来今年丰收在望。他想,待秋收后托人找个四川女人做老婆。壁鬼看到村上好多单身汉娶了四川女子。他心里乐得跟真的娶了老婆似的,蜜甜蜜甜。
好人命短,到了开镰割禾,壁鬼突然得病住院,不到一个礼拜就死了,是肝癌晚期。
出殡那天,全村人都头披白布,家家门前点香烧纸,燃放爆竹。送葬的队伍一里多路长,浩浩荡荡。
细婆坐在壁鬼坟前,一边烧纸钱,一边抹老泪,自言自语:“才四十几岁的人,怎能说走就走了呢?女人的滋味你都没尝过。唉,老天爷瞎了眼,好人总是不得寿长……”
壁鬼虽然没有传后,但每年的清明节,他的坟上倒是插满了香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