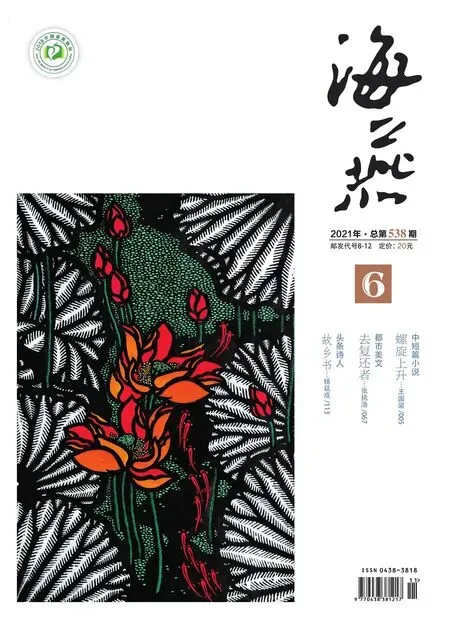西安雪
文 博
一
正月初三早晨,西安的天空,飘下雪花。还未完全醒来的地面上,已有了一层薄薄的积雪。那层积雪披在车辙以外的地方,轻轻柔柔的,如同一袭白纱。每片雪花之间,都留着空隙,松软地堆叠在一起,有种说不出的柔美和典雅。
我不忍心踩伤脚下的雪,也怕被雪滑倒,在长得像个假小子一样的年轻女导游的引领下,登上旅行社空荡荡的大巴车。女导游等我身后的车门关上后,语调活泼地跟我说:“您第一个登车,就是一号家庭。从现在开始,到今晚旅程结束,为了方便联系,一号家庭就是我称呼您的代号。您千万记住了。”
我一边点头,一边顺着过道走到最后一排,坐在靠右边车窗的座位上。这里既不会被其他游客打扰,又能随意观察到每一个人,感觉很不错。
大巴车启动了。只行驶了几分钟,就接到了二号家庭的三个人。其中一个是身穿浅棕色及膝羽绒服的男人,差不多有五十岁;另一个是三十多岁、皮肤白皙、腼腆羞涩,身穿黑色带白条纹及膝羽绒服的女人;还有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穿了一件跟那个女人一样的黑色羽绒服,一看就是亲子装。他们都穿着阿迪达斯黑色运动鞋,坐在过道左侧司机身后前两排的座位上。那个男孩靠窗、女人靠过道坐在第一排,男人靠窗坐在第二排。女导游把刚才跟我讲过的那番话,又对他们讲了一遍。他们一边听一边点头,男孩还回头看了我一眼。
在我观察二号家庭时,大巴车在一个地铁车站旁,接到了三号家庭。那是一对身高体壮、浓眉大眼的中年夫妻,带着两个六七岁左右的双胞胎小女孩。那个男人戴了一顶稍微嫌小的黑色鸭舌帽,跟两个小女孩穿着同样款式的黑色亲子冬装。而那个女人却穿了一件粉色羽绒服,略显凌乱的头发盘在脑后。他们在隔开二号家庭男人身后一排的座位上坐下,两个大人男人在前、女人在后,都靠着过道,一人横抱一个小女孩,很快就睡着了。真让人羡慕。
雪下得似乎比刚才大了些。架在空中的各种电线,让我想到了火。挂在树上的大红灯笼,都被雪花染白了头,疲惫不堪地在晨风中摇摆,仿佛是已经湮没在历史深处的那些古老朝代的缩影。公园里的晨练者,在飞舞的雪花里又蹦又跳,感觉像演戏。行驶在街道的车辆,行走在街道两旁的行人,都越来越多。
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后,接到了四号家庭一对疑似夫妇的中年男女。男人高大傲慢,穿一件棕色毛领的黑色大衣,站在车门口把车上的每个人,都拿眼睛挑剔一遍。女人肥白冷漠,穿一件大红羽绒服,漫不经心地听女导游重复那番话,连头都没点一下。他们径直走向后面,好像打算坐在我前排的座位上。我连忙装出感冒症状,非常剧烈地咳嗽一气,感觉大脑都缺氧了。那一男一女厌恶地看着我,躲瘟神一样毫不掩饰地倒退两步,选择了过道右侧隔我两排的座位,女人靠窗、男人靠过道坐下。女人还嘟哝了一声。应该是说我坏话。但这没什么。
那个肥白女人的漫不经心,根本没有影响到女导游。她又在打电话,不厌其烦地强调着一个地点,好像正在安排两个相距较近的家庭,都到同一个地方候车,那样会节省时间。在女导游打电话的过程中,司机熟练地拐了几个弯,又穿过两条街,接到了两个家庭。先上车的五号家庭,是两对神情严肃的成年男女和一个戴着白口罩、拿着手机的少女。他们根本没有向后看。两对成年男女,都女人靠窗、男人靠过道,占去过道右侧座位的头两排。而手机少女则靠窗坐在第三排,与四号家庭有一排之隔。跟在五号家庭身后上来的,是六号家庭的三个女孩,看上去像是在校大学生。她们都有一份清纯和朝气,背着双肩包、穿着牛仔裤和白色羽绒服。她们先往后走了几步,又犹豫不决地站下,看了四号家庭那对夫妇一眼,回头坐在二号家庭的男人身旁和身后的座位上。
飘落在车窗外的雪花,像蒲公英一样上下翻飞。大巴车正经过大雁塔广场。手持禅杖的唐玄奘,站在大慈恩寺山门前的广场上,肩头和脚下都覆盖着一层圣洁的白雪。我对唐玄奘充满敬意。他历尽艰辛求取真经的精神和所求取的真经本身,交相辉映地照亮了东土大唐,在人们的心灵暗处,布了一道柔和的佛光。
在我回望大雁塔的时候,又上来一对中年男女和一双八九岁的双胞胎小男孩。车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他们身上。那个身体强健、五十出头的男人,穿一件深灰佩红的户外冬装,表情庄严、目光慈善。女人比他小几岁,眼睛很大、气质动人,穿着藕荷色呢质短大衣,像一个热情的邻家大姐。两个英俊的小男孩,都穿着灰色呢料、斜拉索的翻毛领短大衣,戴着时尚活泼、有卡通图案的头套护脸帽,毫不拘谨、轻松调皮地走在女人身后、男人身前。他们来到三号家庭后面的两排座位,两个大人都挨着过道,女人在前、男人在后坐下来,把一双不老实的小男孩,分别挡在前后两个靠窗座位上,配合得非常默契。
大巴车又向前开去。车窗外的古城墙,绵延在飞雪中,被装饰上各色花灯,如同一支歇息在雪中的秧歌队。想象着这道古城墙内外,曾出现过的繁华与凋敝,悲欢与离合,战乱与平安……随着车身摇晃着,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传来一阵手机铃声,惊醒就看见一个年轻女人,坐在我前排的座位上。她优雅的气质和接听电话的声音,都柔美得使我怨气顿消。这时,年轻女人身旁,靠窗坐着的一个烫了一头卷发、像洋娃娃一样的小女孩,回身趴在椅背上,好奇地打量我。我冲她扮了个怪脸。她声音清脆地开心笑了。而那个年轻女人,面带歉意地冲我回眸一笑,搂住洋娃娃,让她重新坐回去。
灰暗的天空,仍然无动于衷地抛撒着雪花。每一个公交站点上,都有许多人等着上车。城市的喧哗声,开始像浪潮一样,一浪一浪地涌动起来。
大巴车在楼房之间转来转去,又接到九号家庭的一对母女,坐在四号家庭身后的座位上。那个母亲带着一顶黑白间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八角针织帽。她的女儿总是低头浏览手机,还常常压低声音接听电话,看上去很文静。
那对母女上车不久,十号家庭的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和我后来得知的他们的女儿、女婿,也上车了。他们不愿意分开坐,别无选择地走向我身旁的四个座位。我注意到那个年龄大的男人,穿着一身黑色耐克运动装,脚上那双黑色运动鞋上的白色耐克商标,特别引人注目。比这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跛脚和一脸羞怯的愧容。我向他递去友好的目光。他感激地笑了笑,挨着我坐下了,又朝我客气地点点头,说了一句:“谢谢大兄弟。”
最后上车的十一号家庭,是三个同样黑衣黑裤、活跃异常的年轻男子。他们分别坐在四号家庭前面和五号家庭的手机少女旁边,一落座就开始旁若无人地交谈,似乎想引起那三个女大学生的注意。
此时,前排的洋娃娃被年轻女人搂在怀里,睡得很香甜。
二
大巴车驶离城区,经过收费站,行驶上乡间的原野。公路两边都是空旷的黄土地。在黄土地的低洼处,沉积着一片片白雪。女导游向我们做了集体问候,同时要求:昨天只交了定金的游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需要补交费用,包括用手机完成支付的手续费,也要我们出;还有就是到达汉阳陵以后,需要租用讲解器,每个二十元,费用也是我们出;再有就是到达法门寺,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要坐电动观光车,每位三十元,费用还是我们出。
女导游说完便走到每个家庭跟前,用两只胖乎乎的手和一个黑着面孔的二维码,收取现金或手机转账。轮到我时,我用手机转了账,并表示不需要发票。
女导游回到前面,又举起一张夹在红色塑料书写板上的表格,要求每个家庭按照表格上的序号,填上经她命名的家庭号码和一个联系电话,以便在有人走散时,进行联络。她把表格递给五号家庭坐在第一排靠过道的男人。男人填好自己的内容,按照女导游交代的顺序,把表格递给了身后的十一号家庭。表格就这样从前到后传到我手中时,我发现在序号4那一栏里,没有填写任何文字。而序号4应该由九号家庭那个母亲填写。但她好像填写了序号5的那一栏,把八号家庭挤到了序号6,使我不得不在序号7和序号4之间来选择。
对数字的迷信和忌讳,在我看来是件可笑的事。我把我应填写的内容填进序号4的那一栏,感觉自己又与众不同了。但我并没有嘲笑九号家庭那个执笔填表的母亲。人生有多少悲苦,就有多少忌讳。趋吉避凶是人之常情。
表格经我身旁的跛脚男人,传给过道左侧的家庭,再传到女导游手中没多久,汉阳陵就到了。我最后一个走下车,看见女导游正给大家分发讲解器。她教我们如何使用并戴上讲解器,去看那些陪葬品。在进入从葬坑之前,女导游把二号家庭的男孩,三号家庭的两个双胞胎小女孩,七号家庭的两个双胞胎小男孩和八号家庭的洋娃娃,挨个叫到最前面,让大人们从现在开始,要把方便让给这些孩子们。三号家庭那个魁梧男人和十号家庭的跛脚男人,也被女导游让到前面。他们一个是军人,一个是残疾人,和孩子们一样享受优惠优先。
天空不再飘雪。阳光从云朵之间,照射到地面。积雪变得越来越软,在我们走进帝陵外葬坑展示厅之前,已经开始融化了。由于女导游不建议我们这些活人,跟陪葬品和帝陵合影,没人耽误时间,参观的时间并不太长。一路上也没什么令人惊异的东西。倒是那六个孩子,刚凑到一起,就嘻嘻哈哈地闹做一团,甚至把手机少女都带动过去,跟在他们身前身后,一面玩手机,一面看热闹。
准备向下一个景点出发时,几个孩子的家长们,在车门口和过道上,相互微笑着点头致意,也有了含蓄得体的互动。大巴车开动以后,我发现五号家庭的手机少女和她身后靠窗坐着的十一号家庭的年轻男子,跟二号家庭的男人身旁和身后,靠过道坐着的六号家庭的两个女大学生,相互调换了位置。六个分别坐在一起的青年男女,立刻就相见恨晚地交谈起来。这轮操作明目张胆,但不费解。
而那个年轻女人在上车以后,把不想和双胞胎男孩分开的洋娃娃,慢声细语地商量回座位,给她一粒一粒地剥石榴,哄她慢慢吃。洋娃娃看上去很懂事,不停地抬起小手,把剥好的石榴籽,送到她嘴边。每当这时,她有着淡淡忧伤和脱俗清纯的脸上,便流露出幸福和开心。洋娃娃吃过石榴,躺在她怀里,又睡着了。年轻女人将剩下的半个石榴包好,重新装进既可背在后面、又可挂在胸前的浅色双肩包里,把洋娃娃妥帖地托在臂弯,红润的面颊贴在洋娃娃脸上,便开始轻轻地摇晃身体。那份专注的柔情,能让世界安静、时间静止下来。
不知不觉间,大巴车开到了唐懿德太子墓博物馆。我一直等到十号家庭起身,才跟在他们身后走下大巴车。道路上覆盖着积雪。人们走过的地方,露出湿淋淋的地面。三号家庭那个军人、十号家庭的跛脚男人和孩子们,又被女导游集中在队列前面的入口处。二号、三号、七号、八号家庭的女人们和二号家庭的男人,自动组成一个小团体,紧跟在孩子们身后。五号家庭自成一体,不紧不慢地夹在队伍中间,窃窃私语地说着什么。十一号和六号家庭的六个青年男女,形影不离地交谈得越来越热乎。四号家庭那对夫妇,经常举着手机游离在队伍之外,表情僵硬地相互拍照。我和七号家庭的男人走得比较近,到了随时可以搭话的地步。九号家庭的母女和十号家庭的其他成员,不由自主地走到一处,不再感觉生分。
博物馆里的土阙、石狮、石小人和华表,无不散发着哀伤与凄凉。近七米长的《仪仗出行图》,无论画面如何宏大奢华、绚丽精巧,都难以承载一个帝王之父对于儿子的无限哀思,以及一个帝王尚未得势时的万般无奈。走在100.8米的斜坡墓道中,我感慨懿德太子即使生在帝王之家,其生命竟也脆弱如斯,其命运竟也不堪作弄,其结局竟也令人如此骇然。
想来人生不仅短暂,还有许多难以把握的转变,将命运变得吉凶无常。
孩子们的兴趣与大人不同,更多集中在墓道的回声和盗洞上。七号家庭的男人和我一样,也对盗洞产生了兴趣,感叹退隐在历史中的摸金校尉们,比鬼魅都难以捉摸。一直到女导游在讲解器里发出召唤,我们才相对一笑,被另一伙游客拥挤着,走出墓道,重新回到大巴车上,向乾陵开去。
天上的云层变得更加透明。但阳光还是被云层遮挡在天空,未能直射地面。而路上的积雪,却早已被过往车辆碾压得荡然无存,只剩下灰蒙蒙的沥青。远处的积雪,由于变得越来越薄,便不断有潮湿的土地,破坏了锦缎一样罩在田野上的白雪,一块块地裸露出来,在整个大地上制造出苍凉的残破感。
三
女导游怕大家无聊,开始介绍乾县的苹果和锅盔,让人感到饥饿。大巴车开到乾陵外的一片空地时,我们都饥肠辘辘地下了车。高低不平的水泥地上,到处都是白雪融化后的积水。在一排并不高大的房子前,几个缺少生气的小贩,无精打采地守在摊位后,没有一个人主动叫卖,只等游客自己上前。孩子们又高高兴兴地凑成一团。洋娃娃不知施了什么法术,竟让两个可爱的双胞胎小男孩,一人牵起她一只白嫩的小手,拿她当小公主宠着。七号家庭的大姐和八号家庭的年轻女人,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跟在孩子们身后,并肩走进用餐大厅。三号家庭那对夫妻,正趁机站在路边抽烟。在我经过时,恰好赶上他们都将烟蒂熄灭在脚下,共同朝我笑了笑,跟在我身后,说笑着走进餐厅。
按照女导游的事先安排,我们被分配在互相挨着的三张餐桌上。我只记得,我和三号、七号、八号家庭,应该同坐中间的那张餐桌。但当我们走到已经有八号、七号家庭和三号家庭的两个小女孩,围坐在一起的餐桌前,却发现有两个位置,被四号家庭那对夫妇给占去了。他们旁若无人地低着头,各自翻看着手机里的照片。站在一旁的女导游,发现了问题。她来到四号家庭跟前,请他们回到事先安排好的桌位上。那个肥白女人不耐烦地说:“坐哪不是吃饭呀?”女导游笑着说:“对呀姐!坐哪都是吃饭。您就按事先安排的坐吧。”她指着三号家庭的两个小女孩说:“小孩吃饭,需要大人照顾。”四号家庭的男人,脸色有些尴尬地起身说:“不好意思。咱们没想这么多。”他边说边拉起肥白女人,按照女导游的指引,走到旁边已经坐着五号和十号家庭的桌前,重新坐下。
这段插曲没有演变成争吵,有些出乎意料。我对四号家庭的男人,开始产生好感。坐下吃饭的时候,我们这桌人,虽然还没有说话,但却有了一种同盟般的亲近感。七号家庭那个爽快的大姐,啃了几口锅盔后,说了一句大家都想说的话:“这个女导游,真能忽悠!这锅盔又凉又硬,咬一口直掉渣,哪有她说得那么好!”三号家庭那个军人,声音洪亮地说:“旅游景点的伙食,都是糊弄人的。好锅盔我吃过,确实好吃。但这个不行。这不是锅盔,这是锅盖。”年轻女人很含蓄地低头笑了。两个双胞胎小男孩趁机起哄,跟他们的妈妈说:“妈妈,我们还想吃锅盖!再给我俩来一块!”两个双胞胎小女孩也叫了起来:“我俩也要吃锅盖!再给我俩来一块!”坐在我旁边的洋娃娃,唯恐大家注意不到她,用筷子敲着桌子连声说:“吃锅盖!吃锅盖!我要吃锅盖!”年轻女人连忙按住洋娃娃的筷子,趴在她耳边告诉她:“这样不礼貌。”我们左右的另外两桌,也被孩子们影响了,都开始对锅盔发表看法。三张桌子之间的气氛,变得融洽而活跃起来。
午饭后的天空,开始放晴了。天上的云朵,都朝着一个方向飘动。我们走在残雪化尽的乾陵神道上,觉得两边的石人、石兽和石碑,虽然看上去很沧桑,但不再是冷冰冰的了。在二号家庭的男孩带领下,孩子们都一窝蜂地跑起来,把神道当成了赛道。五号家庭的手机少女也受到感染,将口罩褪到下巴下面,拿着手机追过去,跟八号家庭的年轻女人一道,紧跟着照顾孩子们。追随在她们身后的,是二号家庭的女人、三号家庭的夫妇和七号家庭的大姐。七号家庭的男人,站在神道边上打电话,听上去像是布置工作。而二号家庭的男人,则买了一口袋削好皮的苹果,挨个递到我们面前。没人拒绝这份善意。苹果很甜、名不虚传,就是个头有点小。我有意放慢脚步,跟十号家庭的跛脚男人并肩走到一起。他感激地对我笑了,又无奈自嘲地摇摇头。十号家庭的其他成员,也都微笑着对我表达友好。六号家庭和十一号家庭的六个青年男女,无所忌讳地男女搭配着站成一排,让九号家庭的女儿给他们拍照。他们又把九号家庭的女儿拖进来,让她的母亲给他们七个年轻人,拍了一张洋溢着青春朝气的合影。赶在我们前面的,还是四号家庭那对夫妇。他们的手机始终没有闲下来,像是把能看见的东西都拍了下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肥白女人,居然对着乾陵主墓,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走在最后的,是五号家庭的其他成员。他们对眼前的一切并不关注,一直到离开乾陵时,还在什么话题上谈论不休。
由乾陵赶往法门寺的时候,车厢里的气氛更加轻松,除我以外的每个家庭,都在做着互不干扰的轻声交流。女导游趁机兜售起产自当地的石榴糕和狗头枣。她告诉我们不必为携带不便而担心,她会把石榴糕和狗头枣送到酒店,还可以帮我们邮寄回去,意思是大家尽管放心购买。
最先对女导游表示支持的,是二号家庭的男人,他买了四包狗头枣和六包石榴糕。五号家庭经过商量,只买了两包狗头枣。三号家庭很爽快,一样买了十包,说是要分给邻居和战友吃。女导游在六个青年男女面前,遭到了拒绝,他们说还要在外面走几天,家里也没人吃零食。七号家庭的大姐,在征求了两个小男孩的意见后,买了四包狗头枣和两包石榴糕。九号家庭的母女先是没想买,后来改了主意,买了四包石榴糕。到四号家庭的时候,肥白女人的意见占了上风,每样买了二十包,给女导游留下一个茶楼的地址。八号家庭的年轻女人,微红着脸说“不想让孩子吃太多零食”,一样只买了一包。十号家庭那个跛脚男人,对他的家人小声说:“这个女导游很辛苦。她刚才在乾陵跟我说,她的孩子已经两岁了,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咱们多少买几包吧。”他们一家人达成了共识,每样买了两包。我本来不想买,但怕给别人留下冷漠吝啬的印象,就用手机向女导游付了四包狗头枣的钱,并实话实说:“我不喜欢吃零食,特别是甜食。”女导游收完我的钱,才冲我笑一下,走回重新加速行驶的车前,指着前方对我们说:“法门寺到啦!”
我们在山门广场下车,又分乘两辆电动观光车,经过佛光大道,在合十舍利塔前开始步行,穿过一条商街,进入法门寺后,四号家庭那对夫妇和十号家庭的跛脚男人,急匆匆地在真身宝塔前,磕了许多头。当女导游招呼大家进入地宫时,八号家庭的年轻女人,把洋娃娃交给七号家庭的大姐,自己一个人垂首跪在大雄宝殿内,连地宫都没进去。我主动走在洋娃娃身后,示意七号家庭的大姐,可以帮她照看洋娃娃。大姐领会了我的热心,让我陪着洋娃娃走在她前面。我怕人群挤倒洋娃娃,便征得她同意,把她抱了起来。洋娃娃用手抚弄着我的头发,显得很高兴。当我们走出地宫时,年轻女人正在地宫出口处等候。我将洋娃娃交给她,顺便说:“孩子真可爱!”她感激的微笑和清澈的目光,让我心生欢喜。
四
踏上归程时,天空昏暗下来。大巴车单调枯燥地轰鸣着。女导游跟每个家庭核对下车地点时,有种难言的感受,开始在我心里弥漫。其他人准备在哪里下车,我都没记清,但却记住了八号家庭的下车地点:永兴坊。女导游走到我跟前,问我:“您在什么地方下车?”我问她:“除去大唐不夜城、钟鼓楼和回民街,晚上还有什么地方值得去?”女导游建议我去永兴坊,正好跟八号家庭一道。
奔波了一天的我们,都疲倦地随车摇晃,半梦半醒地过了好一会儿,在距离机场较近的路边,感觉大巴车停了下来。十号家庭都站起身,蹑手蹑脚地通过过道,相互搀扶着走下车门,钻进一辆等候在路边的别克商务车。那个跛脚男人在起身的时候,特意跟我握了手。通过过道时,还朝着每个人,都点了一下头。
过了收费站,城市的灯光,重现眼前。在一个树上挂满大红灯笼的路口,五号家庭下车了。手机少女在下车之前,还两手扶着过道两侧的椅背,专门走过来,分别摸了摸七号家庭两个双胞胎小男孩的脸蛋,对八号家庭熟睡的洋娃娃笑了笑,亲了亲三号家庭两个小女孩的额头,又和二号家庭的男孩,轻轻地挥了挥手。
我的鼻子有些酸,多愁善感的视线,也模糊了。
满街都是中国结造型的红灯笼。大巴车在车流中,缓缓地行驶了十几分钟,又停在一个宽敞的十字路口。三号家庭在下车之前,那个军人给大家敬了个军礼。他让两个双胞胎小女孩朝大家挥挥小手,那个女人留下了一个憨厚的微笑。
车窗外的天空,又飘起了雪花。灯火通明的街市被渐渐密集的雪花,装点出晶莹的斑斓。但我已没有心情欣赏这夜色雪景。已经袭来的离散之情,带着似曾相识的味道,让我感到无比惆怅,却又无法描述它的形状。
在一条繁华明亮的商业街上,大巴车再次停下来。二号家庭要下车了。那个男孩在他爸爸的示意下,从过道走过来,跟七号家庭的两个双胞胎小男孩,幼稚地握了握手,像长大以后的男子汉一样,郑重地道别。二号家庭的男人下车之前,冲大家抱了抱拳;女人腼腆羞涩地笑了笑,向我们点了点头。
又往前行驶没多远,六号家庭和十一号家庭的六个青年男女,都站起来跟我们摆摆手,转身便下了车,很快消失在阑珊的夜色中,给我留下了很多问号。
车窗外的雪,下得越来越大,模糊了街市灯光,加深了我的惆怅。我在这个飘雪的早晨,眼看着一车人,一站站地聚集在一起;又在这个飘雪的晚上,眼看着一车人,一站站地离散在路边;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浑身都不舒服。
大巴车开到钟鼓楼附近时,七号家庭也要下车了。那个男人微笑着跟我们每个人,点头告别。热情直爽的邻家大姐,没让八号家庭的年轻女人站起来,怕她惊醒洋娃娃。她让自己的两个漂亮小男孩,每人给洋娃娃留下一个手指大的彩色武士俑。我看见年轻女人咬住下嘴唇,眼里有了泪光。邻家大姐的眼睛也红了。她倒退着走了几步,又挥了挥手,才转身抹了一下眼睛,走下车去。
这一家人的善良和热情,深深打动了我。
大巴车重新启动不久,洋娃娃便醒了。她刚接过那两个彩色武士俑,就瞪着大大的眼睛,发现空荡荡的车厢里,少了许多人。她一手攥着一个手指大的武士俑,从过道后面跑到前面,把七号家庭、三号家庭和二号家庭坐过的地方,都看了一遍;又跑到七号家庭坐过的地方,趴在座位下面去寻找;而后扑向那个年轻女人,拉住她的手,突然哭喊起来。年轻女人一边哄着洋娃娃,一边抱起她,不知如何是好地走向车门口。大巴车刚好开到了大唐不夜城。九号家庭那对母女,要在这里下车了。女导游也要下车,早已收拾好东西。四号家庭那对夫妇,也都站了起来。洋娃娃拼命地向车门倾斜着身体,不依不饶地哭喊着,非要下车不可,去找双胞胎哥哥,双胞胎姐姐,还有那个小哥哥。
眼角挂着泪花的年轻女人和她的洋娃娃,跟随在其他人后面,走下车门。她在纷飞的雪花中,蹲在地上搂着洋娃娃,显得很孤单。女导游和九号家庭那对母女,还有四号家庭那对夫妇,分别在洋娃娃跟前弯了弯腰,便各自转身走远了。
漫天飞雪在灯火迷离的街市上,将洋娃娃和那个年轻女人,一重重地包裹在中间,离我贴在车窗上的脸,越来越远。人生如梦、过往成空的无助感,开始让我怀疑人生。我已无意再去永兴坊,便让司机把车停下,来到飞雪漫天的路边。
纷纷扬扬的雪花,瞬间便朦胧了我的双眼,让我倍感迷茫。它们覆盖了道路,包括每一条小巷,还有我们的足迹。我在风雪中行走,竟走到大雁塔广场。站在唐玄奘的塑像下,我看见大唐不夜城灯光迷幻的街市上,如潮水般涌动的茫茫人海,正汹涌澎湃地席卷而来。我茫然地站在风雪中,却不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