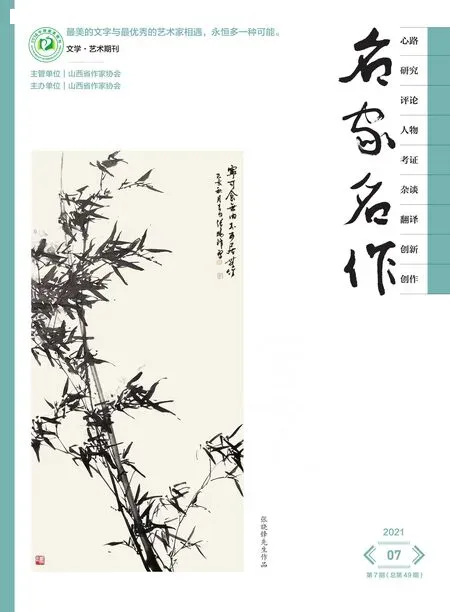不可译性视角下的意象翻译——以《红楼梦》第二十八回中的诗词为例
祁 宏
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在其1965年出版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提出不可译性,并将其分为语言和文化两方面。为了弥补不可译性造成的意义缺失,《红楼梦》的两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补偿措施。
一、语言不可译性及其补偿
语言的不可译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源语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汇或语法单位共用一个语言形式;第二,源语单位一词多义,在译语中却没有相对应形式。”
(一)修辞的不可译性及其补偿
由于发音、词汇的本质不同,中文的一些双关、比喻等修辞手法无法译出。
例子1 玉粒金莼噎满喉
霍译:chocked with tears
杨译:rice like jade and wine like gold
出自贾宝玉所作的《红豆词》,原文有隐喻的修辞,将饭菜比喻为金玉,意为由于思念,再美味的食物也难以下咽,烘托出主人公茶饭不思、思念成魔的形象。在霍克斯的译文中,译者并未保留修辞,通过增译的方法补充说明食不下咽的原因。杨宪益的译文将暗喻转化为明喻,但由于英文中没有“玉粒金莼”的说法,译语读者无法理解,甚至会造成歧义。相比较两个版本,杨宪益的译文虽然保留了修辞,但译文较为生硬,主人公的难过之情也未传达到位。
例子2 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霍译:blue as the mist blue as the water
杨译:like the shadow of peaks like the green stream
出自贾宝玉的《红豆曲》,原文运用隐喻,省略本体,只保留喻体,将思念比作青山和绿水,表现出宝黛之间绵长不断的情谊与思念。霍克斯与杨宪益的译文分别使用as,like将隐喻转化为明喻。但相较而言,霍克斯的译文更加精致,blue一词既表示颜色又表示抑郁之情,实现双关效果,而杨宪益的译文则平淡直白。
(二)发音的不可译性及其补偿
《红楼梦》中的诗词总是寓意深刻,作者将人物的姓名与命运巧妙编织于诗词中,但由于英文不具有完全对等的同音异义词,效果无法完全传达。
例子1 花气袭人知昼暖
霍译:flowers’aroma
杨译:fragrance of flowers assails
出自蒋玉菡的席上生风令,表面上是用木樨花作令,木樨开花说明春天来临,实则将袭人的名字包含其中,表明日后蒋玉菡与袭人成亲,生活幸福。这里的难点是如何将“袭人”的双重含义译出。在霍克斯的译文中,将贾宝玉的侍女袭人的名字译为“aroma”,意为“香气”,他巧妙地将“花气”译为flowers’aroma,正好也是袭人的名字。可见霍克斯到位的理解能力以及其翻译的良苦用心。杨宪益则将判词中的袭人直译为了assail,这个单词更倾向于“袭击”之意,非常生硬直白,也没有达到与人名的双关。
例子2 桃之夭夭
霍译:the peach-tree-o
杨译:the peach trees
出自云儿的席上生风令,原句“桃”通“逃”,意为“逃离”,云儿身世可怜,没有可以值得她托付一生的男人,还要忍受妓院老鸨的打骂,此令预示着她将极力逃出这痛苦之地。由于语音修辞的缺失,两位译者都只表达出“桃花”之意,但没有将其言外之意表现出来。
二、文化不可译性及其补偿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涵。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表现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民族信仰、宗教信仰等方面。下面从词汇空缺和历史典故空缺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词汇空缺造成的不可译性及其补偿
词汇空缺指由于特定历史环境及事件的空缺导致相关词汇的空白,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汇。
例子1 桂花油
霍译:crumb
杨译:pomade
出自蒋玉菡“无钱去打桂花油”,这是在说袭人在贾府败落后无可依靠,生计成为问题。桂花油是古代女子每日梳头时要用到的必需品,当时由于卫生条件差,基本上不洗头发,用它梳头,头发又亮又光,还有香气。霍克斯的译文运用归化法,将“桂花油”译为“面包屑”,对于西方人而言,面包是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食物,用“面包屑”来替换“桂花油”表达了袭人的基本生活都成问题这一层意思,易于读者理解袭人的窘境。杨宪益运用异化策略将“桂花油”译为“润发油”,由于文化上的空缺,会造成读者困惑,不能准确理解桂花油对当时女子的必要性及她当时的状况。
例子2 刁钻古怪鬼灵精
霍译:my Mary Contrary
杨译:an imp of mischief
出自冯紫英的唱曲“你是个刁钻古怪鬼灵精”一句中,这一意象暗示冯紫英的夫人是位调皮可爱的女子,宠溺的口吻中也表现出爱意。霍克斯的译文采用归化法,译为一首英文儿歌中的主人公的形象,歌词为译语读者熟知,表现出女子难以捉摸的性格及冯紫英对她的喜爱。而杨宪益的译文则更加直白,不易使读者产生共情,感情色彩较弱。
(二)历史典故空缺造成的不可译性及其补偿
在历史典故的反复引用中,某个意象具有某种约定俗成的意义,由于东西方较大的文化发展差异,中文典故在西方文化中空缺,此种意象的深意无法表达。
例子1 红豆
霍译:Little red love-beans of my desolation
杨译:省略
出自《红豆词》中的“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红豆”自古表相思,比如诗人王维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又如“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在这里红豆表现出宝黛间无尽的相思情。霍克斯的译文通过增译的方式为红豆赋予情感色彩,增加解释,帮助读者理解其中蕴含的情感。杨宪益的译文省略该意象,没有具体翻译,虽然结合上下文中“流不尽的相思泪”也能表现出相思之感,但未能让西方读者体会中华文化的“红豆”之意,略有遗憾,不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例子2 画楼
霍译:window
杨译:painted pavilion
出自《红豆词》中的“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原文中的“画楼”指雕饰华丽的楼房,在这里指女子的闺房,意为“窗外的春柳春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霍克斯的译文体味到了这一点,达到了动态对等,可见他查看了许多相关资料。而杨宪益的译文进行字对字的翻译,容易引起歧义,令读者感觉突兀。
例子3 乌龟
霍译:marmoset
杨译:queer
出自薛蟠酒令小曲“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这是对薛蟠的老婆夏金桂的判词,这个“男人”指的自然是薛蟠,他喜欢调戏年轻俊秀的男子,这里说的薛蟠是双性恋。霍克斯的译文直接译为“乌龟”,没有表达出深层含义。而杨宪益译为“同性恋”,进一步点明薛蟠的性取向。
例子4 结双蕊
霍译:a lucky crest
杨译:a double flower
出自蒋玉菡的酒令小曲儿“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这是对蒋玉菡的妻子袭人的判词,意为她最终嫁于蒋玉菡,也算是个不错的归宿。“结双蕊”是指灯芯之余烬结为双蕊花型,是婚事吉兆。霍克斯的译文通过“好运”一词将这种吉祥之意译出。而杨宪益的译文仍是字对字翻译,并未暗示出蒋玉菡与袭人的婚姻。
例子5 冤家
霍译:lovely boy
杨译:lover
出自云儿琵琶曲“两个冤家,都难丢下”,符合云儿多情、妩媚的人物设定。“冤家”是对情人的昵称,自古有“小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等说法,这里表现出女子对于这两个情人想摆脱却又不舍得的感情,但称不上是真正的爱。霍克斯的译文点明了两位男子的外表、年龄特点,及女子对他们的喜爱之情。杨宪益的译文用词过于正式,不符合年轻人之间玩笑逗趣的关系。
三、结语
本文基于卡特福德的不可译性理论,分别从语言和文化的不可译性这两个方面对《红楼梦》第二十八回中涉及的诗词意象做出分析,并对比霍克斯与杨宪益两位译者的翻译补偿措施。通过分析我们了解到翻译诗词不是生搬硬套,很大程度上要结合译语读者的用词习惯及文化背景进行再创作,其中不可避免语义流失。在形与意的选择中,两位译者有不同看法。霍克斯虽然是外国人,但对于《红楼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能够用地道英文表达;杨宪益也是饱读诗书,有极高造诣。两位译者在以文化沟通为目的的前提下,通过不同方式补偿意象的不可译程度,相较而言,在第二十八回的诗词译文中,霍克斯的表达更靠近译语读者,杨宪益更紧贴于原文,取得的翻译效果自然不同。希望通过本文分析,能使更多读者了解两本译著的风格特点,进一步探究不可译性的补偿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