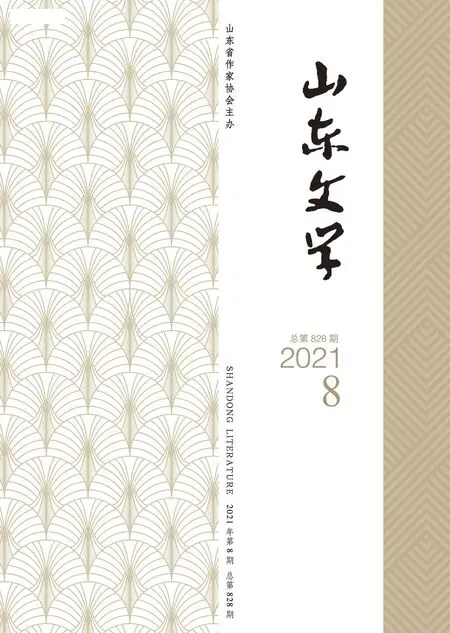生命:在受伤和痊愈之间挺立
——论尘石的长篇小说《生命深处》
邵子华
著名女作家尘石,本名杨彩云,她的长篇小说《生命深处》2020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此著上下两册,煌煌百万言,在她人生的山巅构筑起一座恢弘壮丽的艺术宫殿,其气象峥嵘,氤氲透骨,读来荡气回肠,令人扼腕、长叹、深思!这不啻是她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更是她几十年创作经验的展览馆。小说是一部高清晰的社会镜像,记叙了1949年前夕至当下七十余年的现实社会的变迁,还是一座描绘城乡民间风情的水粉画,而它的深邃、明了处更是探入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厚重的个性,同时又展现出时代精神的斑驳和进取。我们将会从这部巨著中深入了解当代历史和现实的真相,从中看到人生的凄凉、人性的温暖和倔强,从而在这些鲜活的事实中仔细寻找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能稍微用心,还可以在阅读中获得恰当的感知生命的方式和情绪类型,明白一种价值尺度进而深入地理解自己和发现自己。
在我自己的阅读过程中,一直伴随中抑制不住的强烈冲动,我不得不佩服作家缜密的观察力、深刻的感受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芜杂的社会现象的理解力,她把曲折离奇的人生过程和复杂诡谲的社会现象之间一团乱麻似的联系演绎得丝丝入扣。但要全面论述《生命深处》的价值是困难的,我们这里只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讨论它所采取的创作样式和所达到的精神高度。
一、家庭集群的结构方式
先来谈《生命深处》的结构。长篇小说的结构是它全部元素以及贯穿其中的题旨的总组装,有着最外显的小说生命体征。如同人的骨相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气质,长篇小说的结构最能展现它的艺术个性,最能反映作家思想的广阔和深邃。在古今中外的小说创作中,家族叙事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样式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曹雪芹的《红楼梦》、张炜的《家族》都是家族叙事的经典之作。尘石采用的不是家族叙事而是以家庭为组织单元的叙事,即家庭集群的结构样式。家族和家庭虽然都是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的亲属团体,但家庭比家族的结构要简单得多。家族一般要由多个有血缘关系的几代人的家庭组成,而家庭主要包括父母、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亲属。家庭是最细小的亲属团体和最基本的社会单元。用家庭而不用家族来表述可以更确切、明了地说明《生命深处》的结构要素。集群是一个数字信息术语,指的是一组相互独立的、通过高速网络互联的计算机。这类似小说中的一个个家庭。集群技术可以利用各档次的服务器作为节点来实现很高的运算速度从而完成大运算量的计算;集群系统造价虽低却具有较高的响应能力。我们用“集群”来描述《生命深处》中众多家庭的联结方式和表达功能。作家把一个个的家庭自然、巧妙地连接起来,组成了中国当代社会并展示了它的悲苦欢歌,进而揭示了社会进程的梗阻、决荡以及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沉滞和偾张。家庭集群的结构方式既有单个家庭的细微和深切,易于展示真实的人情人性,又有集成大社会之后的恢弘和广阔,能够从历史的角度观照人的受伤和痊愈并揭示其命运沉浮的复杂原因。家庭集群叙事能够展示人的生物基因的多样性在社会进程中的变异和新生,因而它的社会性更加丰富。
《生命深处》或详或略、或明或暗叙写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家庭的喘息挣扎和生死沉浮,并把他们紧密地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大上海开烟纸店的小市民苏桂英一家、鲁西平原凤北村妇冯大娘一家和摆地摊拔牙的彭春一家,是通过端木路和端木槿的父女关系连接在一起的。都市工人端木宝、新疆支边的端木兰、大东北流民端木振、从鲁西平原流落到辽宁、山西的三妮以及鲁西平原私生子端木南,这几家是通过端木槿跟他们同父异母的血缘关系联结的。在清水县,城里干部家庭及之后高知家庭的秦越、家在贫困农村后来成为县级干部和军人家属的王风华、家庭关系混乱流徙数省的端木槿,这三家是通过她们从少年至暮年的同学加闺蜜的关系连接在一起的。浙东鱼米之乡的余细毛一家、凤鸣镇牲口贩子马向东一家,是通过婚姻和性关系连接在一起的。凤鸣公社卫生院老中医董先生、青年医生曲锋、魔道全及杏儿,还有中医院院长马任远、公社副书记张进军等,是通过医患关系、师徒关系、朋友关系、恋人关系、工作关系连接在一起的。端木槿和马平安一家是通过母女关系联结的。这些关系的起因普通平常甚至有些偶然,但一经联结就风生水起,彼此的生命相互羼入、融合。无论是痛入骨髓的冷漠、创伤还是瞬间的温暖,无论伤害还是成全都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剔除的一部分。这些家庭的贫困、打斗、挣扎、逃难、破碎以及坚持不懈的奋斗,像无数哀婉沉郁高亢的音符,像一群撞礁拍岸的惊涛骇浪,它们翻滚不绝、轰鸣不息、奔涌不止。如此一来,一些似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就成了社会事实和历史事件,形形色色的家庭结构关系就拥有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就是说,各种家庭生活场景构成一种表意系统,透过这种表意系统的各种实践活动,完成了一种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造。
尘石以单体家庭为基本元素组织小说的结构,不仅因为她作为女性作家的温婉和敏感,也不仅因为几十年的创作实践积累了对家庭生活描写的丰富经验,重要的是她创作的主旨要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探索和揭示人的生命深处的奥秘,企望在人类生活浩瀚无边的浪涛中筑起一座长明的灯塔,给那些泅渡的人指引道路。其道理在于:一个人出身的家庭是伴随人终身的胎记,家庭生活是浸入骨髓的人性基因。在我国文化中,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居五伦之首,亲属关系既是血缘关系也是最基础最长久的社会关系。从一个家庭内部的矛盾纠葛中能够从根源上看清楚人性的丑恶或美好,从同一个家庭成员不同命运的沉浮能够看清一个人对生命价值的选择和追求,能够更深切地反映时代的精神病变。这是一种穷形尽相的清晰,是一种原形毕露的真实。《生命深处》交错、纠缠的十几个家庭的变迁,向我们展示了广阔地域的民俗风情和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形态各异的家庭生活是人物成长的土壤、肥料或者天火、雷劈和虫子。如此一来,人物的性格发展史和曲折动荡的命运就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凝聚着沉郁的历史文化内涵,让我们看清人性的幽深芜杂,在诡谲无常的命运背后的长长的阴影里发现一缕的亮光。在这种意义上,主人公端木槿不再是孤立单薄的个体而成了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的代表,一个时代巨变的证人,一类向死求生的人生斗士的灵魂。
二、痛入骨髓的生命叙事
《生命深处》采用的是生命叙事。“生命叙事把对人类肉身生存境况的关怀逐步推进到类似宗教的境界, 它描述生命从物质到精神的孕育、产生的过程。在本质上,是生命从具体实在向形而上境界的升华。生命叙事的起点及归宿都是对蓬勃的生命状态的渴望和追求。”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喜欢宏大的社会政治叙事,1990年以来的小说又一度流行肉身叙事,从整体上看,还比较缺乏对生命存在维度的叩问和对生命深处事实真相的揭示。《生命深处》虽然有对重大社会事件的叙述但极为简略,它是作为人物命运沉浮转折的时代背景和一个因素来处理的。小说虽然也不乏对肉身刻骨铭心感受的描写但作家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把这作为一个攀爬的梯子或者泅渡的方舟。小说中描写低劣食物的匮乏、寒酸的衣服、逼窄破败的住房以及后来高大的楼房、华美的轿车,这些虽然也具有一定的认知价值但它更大的意义是展示人物的命运、孕育人物的性格。我们以月下拜把子、关系铁定、友谊保持终生的三个女生为例,青春期的秦越衣着破破烂烂、行为放诞诡异,这种描写是表达秦越对生命自由的渴望,怪异表象下是她渴望自由而不得的痛苦,她以此向社会公然反抗。王风华中学毕业后拉板车、出苦力,挎着粪篓子上台介绍经验,后来像乞丐一样募捐上项目,她追求的是生命的尊严。端木槿是作家浓墨重彩塑造的一个人物,从出身、衣食、居住、劳动、婚姻等有形的生活场景来描写她所经受的苦难和折磨,她九死一生、念兹在兹的是实现生命的价值。她们从肉身深陷的泥潭中艰难地超拔出来,穿过身体蛇咬狼撕般疼痛的惊涛巨浪到达精神的彼岸。作家把对人的肉身生存境况的关怀逐步推进到类似宗教般虔诚的精神境界。
小说中描述了端木槿从饱受生活磨难到追求生命价值实现的过程,这是生命从物质到精神的孕育、产生的过程,是生命从具体实在向形而上境界升华的过程。小说的巨大成功在于对这个过程的曲折回环、穷形尽相的细致描写。这种描写是建立在对人物生命的深切体验基础上的。作家对她的人物所遭受的一次次创伤,所作的一次次挣扎,无不撕心裂肺、感同身受。人物内心的孤苦绝望像雷击电火一样袭击着作家敏感的心灵,作家又把这种疼痛清晰地传达给我们,让我们也同样经受一场血与火的洗礼,一次次的死去活来,走完从炼狱到人间或者天堂的漫漫长路。不必说作家对人物内心的直接描写,她借助自然物象表达生命中的微妙幽深的细流或者地动山摇的惊涛骇浪同样震撼人心。作家写到了黑夜中的坟地,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荒郊野外的坟地,天上没有星星,地上没有灯火,一团漆黑,一片恐怖。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端木槿在深夜走进这样绝望的坟地,天地间没有她的容身之地。布满死亡的坟地正是端木槿内心的真实。作家写到了满天的大雪,这是北方寒冬腊月能冻死人的大雪,像是沉重的裹尸布从天而降。端木槿麻木地走进满天的大雪中,倒毙于风雪之夜,大雪将她掩埋。作家写到:四面树木皆白,天地披麻戴孝。作家写到了黄河水患,黄河中汹涌翻滚的水浪似恶龙肆虐,暴雨又万箭攒射,滩区一片汪洋,大堤岌岌可危。端木槿随着医疗队进入灾区,冲上大堤救人防疫。密集的雨注、山峰倒塌一般压过来的巨浪、泥水中挣扎的呼救声,似千万铁砧钢锤击打着端木槿的身心,她在这样的锻造中成就了坚强、干练和高尚。许多景物描写像是写景散文又像是抒情诗,但它又完全是小说,它完全成了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的性格。作家把对人物命运的深切体验和对人物心理的悉心揣摩融汇在景物描写中,实现了自然景物的人格化,或者说是实现了人物心灵的景物化。人物和景物一体,心灵和世界同化,一种命运就成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重大事件。
尘石的生命叙事是建立在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基础上的。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再苦再难也要实现它。她把这种人生的信念赋予端木槿,成为端木槿生命的灵魂和奋斗的力量。不仅如此,作家对她的每一人物都深深的理解并心怀同情和怜悯,她能发现每一个人物身上富于人性的光亮,哪怕只是微弱的一闪即逝。那堕落的人的主体性太阳的拯救才成为人间绝对的必要和可能。她甚至把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人的生命同样重要,它们的天性中都闪烁着神性的光辉。正是在这种道德认知高度,作家才能对人物命运体验得深切,才能把对人物命运的体验和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完美地深藏于感觉的每一个毛茸茸的细节中,才能运用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达出对生命中微妙幽深细流的真切感受从而写出生命的精魂大义。最终,她所展现的个体生命艰难曲折的行程才能揭示生命受虐和反抗、屈辱和高贵的事实真相,从而表达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处境的关怀、探索和思考。
三、叠床架屋的生命悲剧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序致》中说:“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学,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他的本义是用“叠床架屋”比喻治学累赘堆积。尘石把它创造性地用在小说创作中——情节连环紧扣、层层叠加、步步紧逼,充分展现人物命运生死浮沉的回旋跌宕,深刻揭示人物性格成长的艰难曲折,从而使人物性格更加丰满。小说情节叠床架屋如同黄河十八弯,弯弯激流陡转,处处惊险滔天。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小说只有叠床架屋,才能多方面地展现人物被命运卷入社会环境后的受伤和痊愈的磨炼过程,人物的性格才能充实、厚重,他在抵抗命运的多重打击时才能发出主体性的光辉。荀子说:“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荀子《劝学》)他虽然是讲治学修身的,但艺术形象的塑造深通此理,小说情节只有“全面”和“纯粹”,人物形象才能获得充沛的生命力量,“天见其明,地见其光”,从而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我们以端木槿为例来讨论“叠床架屋”的意义。端木槿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每况愈下的小店主家庭,她一出生就被母亲苏桂英抛弃了。她生活在父母不断升级争吵的恐惧和饥饿中。后来跟随父亲来到鲁西凤鸣镇,又被大娘一家人仇视,经常挨饿被打遭受欺辱,差点夭折只好跟着父亲跑江湖卖膏药。上学了又缺衣少食还经常停学。好不容易长大一点又因为父亲三娶而父女反目。她跑回上海找活路又被卖做童养媳。六年后逃回凤鸣镇,多次被人从居住的小屋赶出来。她为改变自己的命运拼命苦干,一个上大学的机会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又被公社书记徐光掉包。她烧掉了一箱心爱的好书,两次自杀,她对生命已失去任何希望,麻木地嫁人又常常遭受家暴成了泄欲的工具。不得已对抗着舆论的绞杀坚决离婚……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常冒出一个念头,这个尘石好狠心,何以对自己的人物痛下杀手?后来好了也更难了,端木槿把熄灭的火焰重新燃起,向着医术的高峰玩命地攀登,她一定要实现人生的价值。退休后去给女儿照看孩子,然而,她又遇到了从未有过的迷茫和失落,一种终生追求的价值正在坍塌。我们不能不佩服作家对当下生活感受的敏锐和深刻。这是正在进行中的生活,这是正置身其中的社会和家庭:一种计算逻辑正在加紧统治所有人的心灵,感受、情绪、心灵这些重要的人文元素被社会系统大量删除,一向崇尚的传统价值被消解得无足轻重,你所孜孜以求的在年轻一代看来真的无所谓,整个人类生活发生了断裂和变异。马平安虽然从小与母亲端木槿相依为命,在惊恐中艰难长大,共同经历了痛苦和心酸的煎熬。但她进入大学和毕业后工作已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她与母亲对所经历的苦难的理解迥然不同,对生命价值的选择更是大异其趣。她的爆发有深刻和普遍的社会内涵。端木槿人到老年又一次跌入别样虚无的精神的深渊。
尘石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端木槿的一生实行接连不断的、一次比一次更加沉痛的打击,从家庭的到社会的,从体制的到风俗的,从肉体的到精神的,每一次打击都发出震撼人心的钝响,发出令人头晕目眩的强光。端木槿从外到内伤痕累累,她反而倒成了“一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关汉卿《一枝花·不伏老》)端木槿从一出生就进入特定的家庭,卷入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她的已有性格与这些社会关系相互作用。一方面,她在这些社会关系中顽强地表现这种性格;另一方面,这种性格也在接受社会关系的考验和重塑,二者之间的互动就是她命运的深刻之处。端木槿的性格与各种社会因素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她的命运集合了同代人的许多共同的经历,她比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更集中、更典型、更能体现人类生活和精神的多样性、深刻性和创造性,她因而成为一个能够深刻地揭示出丰富的社会涵义的典型形象。黑格尔认为一个性格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是它的完整性,完整性“是由于所代表的力量的普遍性与个别人物的特殊性融会在一起,在这种统一中变成本身统一的自己”。端木槿就是这样一个能够积极体现出普遍力量、具有完整性的“个别形象”。她个人成长的酸辛悲苦和心灵磨难之中深蕴着一个时代的风云和一个民族的性格,就成为人间最令人神往的生命的风景。
端木槿的一生是悲苦的,她的悲苦产生于她对异化的感觉、体验和意识。她的合理的自然需要遭受压抑,她的人的本性、人的本质遭受各种糟蹋和摧残。因这种异化而产生的肉体和灵魂的强烈体验是她真正悲苦的根源。这种悲苦主要表现为她精神上的疼痛和灵魂上的煎熬。作家描写出了这些悲苦,向我们展示了这些悲苦,从而发出对生命的至真至诚的呼唤和无惧无畏的呐喊。我们在咀嚼这种悲苦的时候,脆弱的心灵常常如同掉进人性黑暗的深渊,但我们的主体性又不甘沉溺而挣扎着往上登攀。这时,作家的呐喊好像发射进来一道雪白的亮光,像一架坚实的梯子,鼓励我们向着人性的光明登攀。
“长日尽处/我站在你的面前/你将看到我的疤痕/知道我曾经受伤/也曾经痊愈……”(泰戈尔《飞鸟集》)痛定思痛,其感觉如五谷蒸煮发酵为酒,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化为清冽醇厚的浓香。端木槿跨越生命深处的险滩激流的背影可能会被流逝的岁月冲淡,甚至她经历的种种人生的痛苦也会被置身于物质包围中的人们所忘记。但是,我们被“小说人物在他们命运的黑森林中徘徊时发出的吼叫”所唤醒的心灵可能再也难以睡去。在漫漫生命长途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难免受伤,都渴望痊愈。谁不希望自己的生命在与环境不断的冲突、交流和抗争中坚定地挺立着,潇洒地展示出蓬勃强健的生命力量。那些消极的、非理性的、阴暗的以及羸弱的生命,一切萎缩肮脏的东西终究会被人所不齿。作家真实、复杂、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对人的生命的关切、构想和追求,这些明亮的音符所汇成的交响就会在我们的心中再次响起并久久回荡。端木槿在她非凡的个别的本性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一切人和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决定因素,一定会在另一些“人和时代的顶峰和界限具体化的极端的全面表现中呈现出来”,并把它发展到新时代的最高水平。这是毫无疑问的。《生命深处》所孕育的生命精神犹如一束雪白的光亮,在它的照耀之下,一切高贵的灵魂将会闪现出熠熠的光彩,而丑陋、孱弱的也将悔过、自强,人类的生命之路就在这雪白的光亮中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