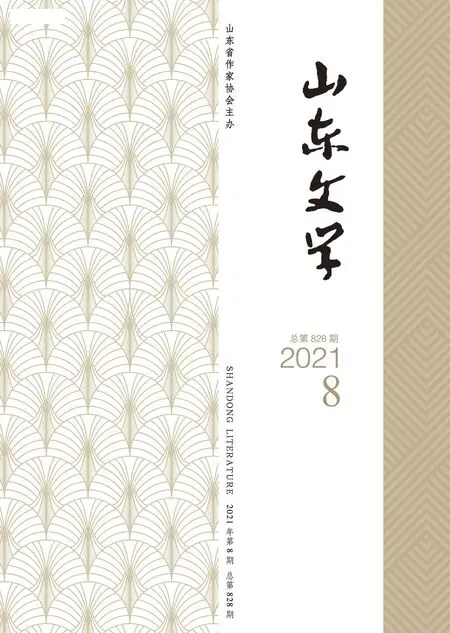斗 蟋
吴 苹
来人是被一个孩子领着过来的。
他俩进门的时候郑君恒正在给蟋蟀喂食。蟋蟀食是用玉米粉、大豆粉、脱脂奶粉、干酵母和鱼粉做的。每一种材料都是严格按照书籍配制的,配比精确到克。民以食为天,蟋蟀也不例外。蟋蟀的吃喝拉撒是郑君恒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大事。毕竟,它们体质的强弱关乎的不是它们自己,关乎的是他郑君恒下半生的荣辱得失。它们是他费尽心思捉到又千挑万选后才留下的,毫不夸张地说,桃园镇骁勇善战的蟋蟀有一大半被郑君恒收了编。桃园镇的人喜欢将善斗的蟋蟀称为斗蟋。镇上有一家养殖斗蟋的,为此那家人专门在一块良田上建了个大棚。尽管常有开着豪车的人光顾他家的大棚,但郑君恒打心里看不上他家的斗蟋:嘁,温室里生温室里养,就是只狼也会蜕变成羊。英雄起于草莽,谋士出于江湖。野路子出来的大多够灵、够狠。懂行的人都知道,灵和狠对一只斗蟋来说多么重要。作为一只小小的昆虫,不灵不狠哪行啊?田野里、阡陌间,四面八方的眼睛都在虎视眈眈,丛林法则时刻在上演,不灵不狠的早成了别人的口中之食了。
捉斗蟋要在夜间进行。那些人往往穿高筒雨靴,戴草帽,着长袖长裤。这般全副武装是为了防蚊子。野地里蚊子很多,又不能喷花露水。花露水、酒精之类有气味的东西对斗蟋来说是大忌。秋收后的草丛中、河滩上、废弃的窑坑里,越是鲜有人光顾的地方越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捉到的斗蟋要放到透气的陶土器皿里。郑君恒给每个盛斗蟋的陶罐都贴了白胶布,上面写着斗蟋的名号。如:猛张飞、李元霸、关云长、鲁智深、李广、吕布等。大将总是有名有号的嘛,没名没号的是小卒子。那只最彪悍的斗蟋是在一个偏僻的河滩上捉到的。郑君恒一到那里就被它们的鸣叫声吸引住了,嘀嘀嘀、嘀嘀嘀……高一声低一声,此起彼伏,在阒静的夜里尤为悦耳动听。郑君恒站在那里边听边想:斗蟋这个小昆虫真有意思,两套行头两个角色。叫蛐蛐时它是阡陌上的歌手,叫斗蟋时它又是好斗之徒。不过,在乡镇大舞台上斗蟋主要扮演哪个角色,决定权通常并不在斗蟋。听了一阵儿郑君恒听出了玄机。在众多的嘀嘀声中,有一个声音更浑厚更有穿透力,简直称得上是金石之声。郑君恒根据声音辨别出了它的大致方位,是在一堆碎石头后面。郑君恒走到碎石背面,嘀嘀声却停止了。拿手电一照,吓了他一跳,一条小花蛇正昂着头丝丝地吐着信子,不远处,果真有一只大个头的斗蟋。斗蟋显然发现了蛇,“噌”一下蹦到了石堆顶上,蛇爬向石堆紧追不舍。郑君恒看了一下四周,身边恰好有根树枝,他捡起树枝将蛇挑起来扔了出去。那只斗蟋比普通斗蟋大一圈,通体泛着深褐色的光泽。头部饱满,前额突出,斗丝明显,后腿健壮有力。尤其是那对大颚,粗大坚硬,如同锯齿獠牙一般。郑君恒如获至宝,给它取了个豪气冲天的名字——西楚霸王。
前几年,桃园镇靠近国道的土地被征收建了小区和工厂,田地减少了大半,很多人家去了城里打工,但郑君恒没有出去。他儿子郑方在济南一家公司做行政总监,女儿郑圆在县里教高中。他不用打工也够吃够用。去年女儿生孩子后,老婆淑娴去了县里帮忙带孩子,老家只剩郑君恒一个人。女儿为此不放心,时常说起让老父搬过去住的事,都被郑君恒拒绝了。一来他感觉在女儿家不方便,二来这里有他的斗蟋将士,哪有主帅放弃将士的道理?家里还有一亩多地,他都种上了芦笋。种芦笋主要忙在春季和夏季,到了秋季芦笋就给笋农们放了长假,待茎叶枯黄后拿镰刀一割就大功告成了。郑君恒正好趁这个时节操练他的郑家军。去年国庆节时,他的郑家军和郑家旺的斗蟋整整杀了一天,两家的斗蟋均死伤参半,到最后也没分出胜负来。今年他重新组织了一支更雄壮的郑家军,尤其是增添了虎将西楚霸王后,郑君恒对于干败郑家旺又多了几分把握。
桃园镇周边有几个斗蟋玩家,经常过来郑家参观,来的人大都带着斗蟋笼子,为的就是让它们比试高下。今天来的这位手里就提着笼子,提的还不是一只,是一手提一只。那人一进院子就笑着说:“听说郑大哥的斗蟋个个刚硬威猛,过来见识见识。”郑君恒笑说:“好啊,来的都是客。走,到屋里喝杯茶。”来人说:“不用忙,先看斗蟋。”来人的目光落在西楚霸王的陶罐上,说:“能否参观一下?” 郑君恒笑了笑,却打开了旁边张飞的盖子。那只叫张飞的斗蟋头大额突,牙齿硬实,一看就是善斗之辈。来人说:“真不错!”郑君恒依次打开罐子,来人每看过一只都点头称赞。到了西楚霸王跟前,郑君恒停了一下,说:“兄弟,本来我是不打算让你看西楚霸王的,因为它明天要迎接一场大战,大战前它是不能见光的。你既然大老远的来了,也不能让你失望而归,那就看一眼吧。”郑君恒将陶罐打开一道小小的缝隙,来人弓着腰,撅着屁股,眼睛几乎贴在了陶罐前。“果然名不虚传啊!”来人直起身,指着自己带来的一个笼子,说:“郑大哥,我也养了几只,其中一只叫豹子头,本来想着今天让豹子头和西楚霸王比划比划的,你刚才这么一说,我也不好意思提了。”郑君恒笑说:“兄弟,你要真想看它们玩儿,除了西楚霸王之外,其余的哪只都行。”来人摇摇头,欲言又止的样子。郑君恒说:“兄弟有话只管说。”
来人说:“郑大哥,我还得求你个事。我还带来一只雌斗蟋,能否将它跟你的西楚霸王配一配?”郑君恒听后连连摇头:“兄弟,这事真不行,西楚霸王明天将有一场血战,我不敢让它做任何消耗体力的事情。”来人见郑君恒的态度坚决,只得提着笼子离开。
郑君恒将来人送走后,用干毛巾将刚才打斗过的战场清扫干净。他清理陶罐时从不用湿毛巾,那样斗蟋会烂爪花。这世间万物有灵,哪怕是草木虫鱼。
将这些搞好之后,郑君恒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他在想以后再有人来斗蟋蟀,是不是一律得拒绝他们。他要对付的人是郑家旺,把其他人的爱物搞死搞伤的,有点犯不上。郑家旺才是他真正的对手,有好几年了,他就那么憋着一口气,这才逮住了一个机会。自从儿子春奇羽翼丰满后,郑家旺就将装饰公司的大权交给了春奇,自己转到了幕后。郑家旺的女儿嫁到了县城,他在县城买了一套别墅,在省城济南也买了一套别墅。平时省城县城两处跑跑,闲时旅个游玩个球,活得那叫一个滋润。这两年,郑家旺也赶起了时髦,跟其他有钱人学着斗蟋蟀,还玩上了瘾。郑家旺斗蟋蟀上瘾时经常半夜半夜地不回家,某次他的斗蟋被别人干掉后他竟跟人家翻了脸,还差点打起来。闻听此言后郑君恒就感觉自己的机会来了,郑家旺也不是金刚不坏之身,他也是有死穴的,斗蟋就是他的死穴,是他的七寸,他决定掐住郑家旺的七寸。
快五点钟时,郑君恒才想起来该去接老婆淑娴了。淑娴早晨打电话说下午四点半从县城坐车,五点钟多点就能到家。以往逢周六周日女儿休息时,淑娴都会趁这两天回家看看。利用这点时间给郑君恒蒸上一锅馒头,再将他的脏衣服全部找出来洗干净。明天是国庆小长假的第一天,她总算能多待上几天了。淑娴是郑君恒的高中同学,当年可是班花级的人物,那时他和郑家旺都看上了,为了追淑娴两人都下了一番功夫。郑家旺是直接拿东西砸,送文具、送影集、送鲜花,后来听说还送过丝巾鞋子之类的。郑家旺家里虽穷,但他本人并不穷。郑家旺的经济头脑犹如晴空下的玉石,即便是埋在土里也能冒出缕缕紫烟。还在小学时,郑家旺就懂得将红泥捏成各种小动物,放在灶膛里烧熟后再卖给同学。假期则是他的生意旺季,寒假时卖糖葫芦,暑假时卖雪糕。中学时就更忙了,每天晚上将作业匆匆写完后,便满宿舍跑着兜售圆珠笔和作业本。他曾让郑君恒帮他介绍过生意,报酬则是以比别人低一毛钱的价格将那些文具卖给郑君恒。在物质上郑君恒是处于劣势的,但郑君恒并不笨,他懂得如何扬长避短。他的长处则是自己的才气。他的文笔好,曾在市里的作文比赛中获过二等奖。那一阵子他将自己的那点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写给淑娴的情书都经过了字斟句酌,每个字都是滚烫滚烫的。那些情书上大都写有诗歌,有的是抄的名家的,有的是自己写的。他感觉淑娴不是那种太在乎物质的女孩,对此他还是有六七分胜算的。那是他和郑家旺的第一次较量,那场角逐的最后结局是他赢了,淑娴成了他老婆。
接淑娴的路上要经过村里的主席台。主席台原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批斗会用的,到郑君恒上学时主席台成了戏台。戏曲在乡村绝迹后,坍塌了一角的主席台成了小孩子玩游戏的地方。这两年恰逢农村搞建设的大潮,破烂不堪的主席台终于被洪流裹挟而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广场。变成小广场的主席台在村民口中仍是主席台。此时,黄昏拖着长长的金色尾巴正在小广场上逗留,跳广场舞的女人们随着音乐有节奏地摇摆着。广场东北角是夕阳红乐队的地盘。凉亭下,一个老头儿正扯着嗓子吼《青藏高原》,到了高音处显然没上去,还憋得脸红脖子粗的。郑君恒见此情景摇了摇头,心说,这唱功还欠点火候。旁边伴奏的人看到了他,忙说:“郑大哥,过来唱两首。”郑君恒说:“不了,还得去接老婆子呢。”
国道边有个小站牌,从县城发过来的2路车在那里停靠。郑君恒到站牌后约摸等了十来分钟,2路车就到了,淑娴提着行李从车上走下来。她穿了一件深红色的毛衣外套,显得身材颀长皮肤白皙。可能这两年不经风吹日晒的缘故,五十五岁的淑娴明显比村里的同龄女人要年轻。郑君恒接过她的行李,跟她打趣道:“哎哟,这可是越来越俏了,都有点跟不上你的节奏了。”淑娴笑着骂了一句:“你个老东西,越老越没正经形了。”郑君恒笑说:“老婆还是自己的好啊。”
在和郑家旺的第一次较量中,郑君恒赢了,赢得理直气壮。郑君恒每回味一次就像吃一次甘蔗,那感觉是干净的利落的脆甜的。淑娴和郑君恒确定关系后,郑家旺便娶了别的镇子上的女人。那女人刚结婚时看着还凑合,生孩子后越发地往横向发展。无论从身前看还是从身后看,郑君恒都觉她像背了一口袋面粉。今年春节她跟郑家旺回桃园镇时,穿着一身貂,两个手上黄的绿的真晃人的眼。只可惜山珍海味却没能将她滋养出好气色来,才五十来岁,两个大眼袋就像葡萄皮子似的挂在了脸上。要不说嘛,人的气质还真不是钱能堆出来的。
夫妻两个刚到小广场边上,就被跳广场舞的女人拦住了:“哎呀,两口子这个恩爱呀,整个唱了一出夫妻双双把家还。”淑娴停下脚步和她们聊了起来。郑君恒想拉着行李先走,又被亭子下唱歌的老头儿们叫住了:“老婆在这里,你回去干啥呀?唱两句唱两句。”话筒递到了郑君恒的手里。郑君恒走到亭子下,站定,清了清嗓子,唱了首《向天再借五百年》。一曲终了,掌声雷动。有人说:“老郑,功力不减当年啊!”郑君恒笑笑:“一般情况吧。”那人说:“老郑,以后到点就过来呗,不行我每天去叫你,大伙一起唱唱歌乐呵乐呵多好啊。”郑君恒说:“过了这一阵子再说吧。”郑君恒别的不敢自夸,吹拉弹唱倒是样样拿得出手。尤其是刚结婚那阵子,他家有一台录音机,农闲时村里的年轻人都爱往他家聚。大伙轮流登台献艺,你方唱罢我登场。那几年的日子倒也是逍遥自在。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后,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他承包了村里的鱼塘。人一忙,娱乐活动自然少了。两个孩子都考上大学后,郑君恒心里放松了一些,就和村里的文艺骨干们组织了夕阳红乐队。小乐队在每天太阳落山农民收工后才出场,因此而得名。尽管名字叫“夕阳红”,但乐队里也有很多年轻人。郑君恒是乐队的主力,每天晚上都要登台的,唱上一阵子再回家睡觉。网上不是说嘛,人唱歌时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久而久之,能让人积极乐观使人益寿延年。孩子大学毕业后,他就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尤其这两年他是彻底没那份心情了,毕竟,很多事情都是需要心情的。
当年,郑君恒家鱼塘里养的是清一色的鲤鱼。他不仅在池塘里养鱼,还养在家里的鱼缸里。鱼的寓意本来就好,更何况是跳龙门的鲤鱼?那年除夕,淑娴要在大门上贴门神,郑君恒不同意,硬将两张鲤鱼年画贴了上去。淑娴说,门神贴在大门上是驱邪镇鬼的,鲤鱼能干啥呀?郑君恒说,鲤鱼能带来好运,你那个门神能吗?在鞭炮噼哩啪啦的红光中,墙头上的鲤鱼灯和门上的鲤鱼年画遥相呼应,像两个心照不宣的同谋。从此之后,鲤鱼就在郑君恒家安营扎寨了,一直盘踞了二十多年。
郑君恒养鱼的时候郑家旺开始倒卖化肥农药。镇上的人常见他开着一辆机动三轮车,嘟嘟嘟地喷出一股黑烟,这边烟还没消散那边车子就跑远了。后来,郑家旺鸟枪换炮,不光换了新三轮车,还增加了摩托车和手机。摩托车骑在胯下,手机别在腰间,二者都很醒目,只要不是盲人都能看得见。郑家旺骑着车走到大街上,到了人多的地方停下来给老人敬烟,这边才说几句话,腰间丁零丁零地响起来。郑家旺就笑着说:“叔,我先接个电话。”郑家旺接电话时,人们的目光全在他身上聚了焦。通话结束后郑家旺将手机在腰间放好,说:“唉,没办法,又有要货的了。”老人说:“家旺行啊,成大老板了。”郑君恒斜睨着眼睛看着郑家旺,拖着长音说:“哟,郑经理,业务很繁忙啊,该配个女秘书啦。”郑家旺拍拍他的肩,笑说:“兄弟,你跟哥瞎闹啥。”
郑家旺一踩油门,摩托车窜了出去。郑家旺走后,街上的人接着聊他家的生意。郑君恒不愿多听,折身回了家。看到十岁的儿子在踢球,郑君恒黑着脸吼道:“就知道玩!作业做完了吗?还不滚回屋里写作业!”
后来,桃园镇的农民开始进城打工。郑家旺发现了更大的商机,当起了建筑包工头。一到年底,他家里就人进人出的,有找他要工钱的,有找他联系工地的。郑君恒感觉自己已经无法与之抗衡,只得将希望寄托在一双儿女身上。郑君恒一儿一女,郑家旺也是一儿一女,两家的孩子又恰好在同一个班级。每次大考之后,郑君恒问过自家孩子的成绩后,紧接着就问家旺孩子的成绩。孩子汇报过之后,郑君恒的脸上才会露出些许笑意。
郑君恒最扬眉吐气的日子是女儿郑圆考上大学时。那次,他专门在自家庭院里摆了十二桌鱼宴,鱼的香味飘满了整个桃园镇,连老鼠洞都被鱼香味塞满了。他家池塘里的鱼估计有一半粉墨登场了。村上有头有脸的全来了,连走路抬着下巴的村主任都频频向他敬酒。郑君恒望着在场的人,笑声像鱼卵一样成嘟噜成串地外冒。他女儿郑圆考上了省城的本科大学,而郑家旺的儿子春奇才考了三百来分。世上的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风水终归是轮流转的。
淑娴一边收拾着院子,一边唠叨:“搞了一院子蟋蟀,又供它吃又供它喝的,当初养孩子时也没见你这么上心。”郑君恒说:“养它有它的用处,你知道什么呀?”淑娴说:“你跟家旺较什么劲啊?咱儿子现在在人家公司呢。”郑君恒说:“别跟我提儿子,不提他我还不生气,那个没出息的东西。”淑娴说:“孩子愿意在那里干就让他在那里吧,换个新公司不是还得从试用期干起吗?”郑君恒说:“在哪里干也比在他那里强。给他俩钱就替人家卖命。还找他妈的屁锁阳,差点把命搭上。”淑娴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了。
郑君恒的儿子郑方大学毕业后应聘了一家报社,做的是临时编辑。那原是一份娱乐性的报纸,郑方负责的是副刊,每期的三两篇小散文夹在铺天盖地的明星婚史中,憋屈得像个受气的小媳妇。试用期刚过,报社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了效益副刊让位于娱乐板块,郑方重又走上了求职之路。后来,郑方应聘了一家企业的内刊编辑,应聘前说好试用期月薪四千,转正后六千。可是,转正后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还是四千,老总摊开双手说,企业效益不好啊,没办法啦。郑方又一次夺门而出。
就在这个时候,郑方遇到了郑家旺。郑家旺穿着一身硬壳子似的西装,坐在人才市场的展位后面,笑眯眯地望着手拿简历的郑方,怎么,大侄子,想跳槽啊?郑方红着脸,尴尬地笑笑。家旺说,招聘会马上就散场了,咱爷俩先去吃个饭,然后,再去我公司里喝杯茶。
郑方本来不想去,但郑家旺曾是他的救命恩人,如果硬是推辞不去,显然不太合适。那还是郑方四五岁的时候,他和几个孩子在池塘边玩耍,一不小心滑进了水里。郑家旺恰好从旁边走过,二话没说脱了上衣就跳了下去。郑方即将被水吞没时,郑家旺游到了他跟前。郑家旺一个胳膊夹着他,一个胳膊划着水往岸上游。到了岸上,郑家旺抱着他控了一阵水,他才缓过气来。
这几年,郑家旺父子一直是桃园镇人茶余饭后剔牙时的谈资,谈得最多的是春奇的女人。镇上的人说光被春奇称为老婆的女人就有五个,只是这些女人努力了这么多年,却一个孩子也没有努力出来。
郑君恒每次一回想起那个电话,身体都会不由自主地颤栗上几秒钟。明明是儿子的电话号码,传来的却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请问您是这位机主的家人吗?”
“你是……”
“我是甘肃武威的交警,从他手机里找到了您的号码,才给您打过去的。”
“甘肃……交警……我儿子他怎么啦?”郑君恒哆嗦起来。
“他在这边出了点车祸。不过,您别太担心,救护车已经过来了。”
“车祸……车祸。”
“锁阳,锁他××!到底是他×的谁的主意?”郑君恒每次问儿子,儿子都说:“你就别管了,这不都已经好了嘛。”
“还他妈的壮阳,活该他绝后!”
郑君恒问郑家旺时,他一直在电话那头打哈哈:“哪有什么其他的事?我大侄子当时是在出差。发生了那样的事,我也很心疼,他受苦了。你放心,我会加倍补偿他。”
“你补偿个×啊!差点出人命!孩子愿意在你那里干,我拦不住他。你给我听好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我跟你拼命!”
晚饭后,郑君恒给斗蟋喂了最后一次食,斗蟋食中加了些苍蝇头和蚊子,让它们吃点活物它们才有血性。他决定明天早上不给斗蟋喂食,稍微饿一下,饥饿状态下的斗蟋更有杀气。临睡前,他给郑家旺打了一个电话,平时他不想理郑家旺,这次他得确定一下家旺回来的准确时间。电话响了两声那边就接了,他说:“哎,我说,郑家旺,郑董,你这个大资本家发财了,明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该是你衣锦还乡的好日子啊。”郑家旺哈哈大笑,说:“你羡慕了?嫉妒了?当初你要和我做亲家,现在你也是大半个资本家了。怎么样,后悔了吧?”郑君恒说:“我后悔个鸟啊?我的日子可比你自在多了。你明天到底回不回来?我的斗蟋早就等着杀你的呢。”郑家旺说:“我昨天就从济南回来了,现在在县里呢。明天早晨吃过饭就回去,九点前一准能到家。听说你整了一只挺猛的斗蟋,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西楚霸王’,你知道我的斗蟋叫什么?”郑君恒说:“你爱叫它啥叫它啥。”“它叫刘邦!专干西楚霸王的。哈哈。”还刘邦呢,流氓差不多。郑君恒心说。当初郑君恒的女儿郑圆大学毕业后,郑家旺曾托人给他儿子春奇提亲,郑君恒直接把介绍人给怼了出去,也不知道今天他怎么提起这事来了。
第二天清晨,郑君恒早早起了床,换了一身衣服。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得以全新的面貌迎接这场战斗。他逐一检查了斗蟋的陶罐,他的勇士们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他心疼斗蟋们饿肚子,原想推翻昨晚的决定给它们喂点东西,狠狠心还是没有喂。他对着西楚霸王的陶罐说:“霸王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就看你的了。”西楚霸王嘀嘀了几声算是应答。一过七点钟,他就竖起耳朵听着门外的动静。吃早饭的时候,他的屁股几次离开椅子,搞得连饭都没有吃踏实。
早饭后,他打开手机,调出一些歌曲给斗蟋们听。是《大刀进行曲》《精忠报国》《好汉歌》之类的。要高亢嘹亮的,要大气磅礴的。以前战士出征都有文工团和宣传队鼓舞士气,现在他得给他的大军鼓舞士气。歌曲一响,他自己先进入了状态,跟着唱了起来。
九点钟了,郑家旺还没有回来。难道他不回来了?郑君恒原想给他打个电话问问,转念一想还是算了,要不然郑家旺又该笑他心急了。十点钟时,他实在忍不住了,拨了郑家旺的手机,奇怪的是无人接听。过了十来分钟,他又拨过了一次,还是无人接听。难道郑家旺在耍他?在玩失踪?关键是郑家旺没有理由玩失踪。还是再等等吧。
中午十二点时,郑君恒最后一次拨郑家旺的电话,仍是无人接听。他随后拨通了儿子郑方的电话:“方啊,郑家旺说今天九点前回来,怎么到现在还没到呢?给他打了几次电话也没人接。”郑方说:“回不去了,昨天晚上脑溢血了,一直人事不省,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里躺着呢。春奇正谈着的生意都不谈了,回县城照顾他爸了。”
怎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本来盼着的是一场生死角斗,没想到那边却挂出了免战牌,有可能会一直免战下去。他从此没有了对手,没有对手之后又该怎么办?他原地转了几圈,实在想不起自己该干些什么,又一屁股坐回了椅子上。一只猫喵喵地叫着跳到他的膝上,想在他那里讨一点爱抚,他嫌恶地将猫推了下去。
“吃饭了,你在那里发什么呆啊?早晨饭都没吃好。”淑娴叫他。他说:“明天一早咱俩去趟县城。”淑娴说:“这才刚回来,又去县城干什么?”他说:“家旺脑溢血了,在重症监护室躺着呢。”淑娴愣了:“啊!怎么会这样?”他起身往外走,淑娴问:“该吃饭了,你去哪儿啊?”他说:“不想吃了,出去走走。”出了门后,他任由道路牵着往前走。他走出村庄,走过工厂,走向远处广阔的田野。
田野里,玉米和花生已经入了仓,只剩下一地零零散散的叶子,越发显得苍茫寂寥。他走进大豆田,原本齐膝的豆棵现在只余两寸左右的茎秆,被镰刀割后的斜茬好似利刃,根根直立向上,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白光。他在满地利刃中穿行,利刃划破了他的脚,他却感觉不到疼。地中间的泡桐树罩下一片荫凉,犹如一座孤岛。他在树荫下坐了下来,背靠着大树,他有些困倦了……
秋后的田野如同镜子,太阳在上面反着明晃晃的光……阳光下的小河飘着一层淡蓝色的透明雾气,天上的白云散发着甜酒的气息,慢慢飘进了棉花地。白云在各自的茎秆上如花般绽放,千朵万朵,层层叠叠,压弯了枝头。隐隐有音乐声从天边传来……
“曲曲曲……”鸣叫声在他右脚边响起,扒开大豆落叶,一只蛐蛐蹦了出来,蹦上了他的大腿。是一只青色的蛐蛐,个头很大。他伸手去捂,青色蛐蛐蹦到前面去了。“曲曲曲——曲曲曲”左脚边还有鸣叫声,他再次轻轻扒开落叶,又一只蛐蛐蹦了出来。是褐色的,又是个大块头。不等他伸手,那只褐色蛐蛐也蹦走了。一青一褐两只蛐蛐在前面炫耀一般高声鸣叫。他起身去追那两只蛐蛐,走了两步感觉有些不对劲,长长的裤腿绊住了他的脚。身上的衣服越来越肥大,脚上的鞋子也在变大。他又走了两步,这才发现不是衣服在变大,是他的身体在缩小。两条裤腿像扫帚一样拖到了地上,使他举步维艰。他干脆将身上的衣服全部扒掉,扔到了一旁。他的身体仍在缩小,直到缩成了一个光屁股的孩子。
秋天的午后,一个光屁股的孩子在田野追蛐蛐。两只唱歌的蛐蛐。只是蛐蛐。
曲曲——曲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