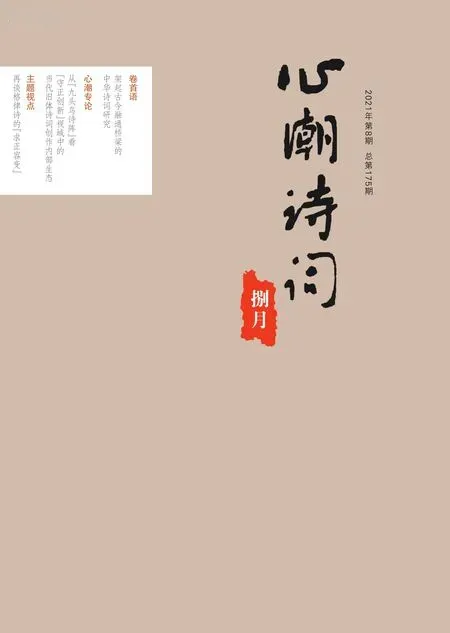写诗,是一种看世界的角度
李伟亮
一、写诗要有“情绪”
只有人的情绪注入作品之中,作品才会因为人的喜怒哀乐而变得生动鲜活起来。在“文以载道”的文化背景下,我们不否认艺术形式,但艺术形式的出发点就是情绪的生发。所以,“有情绪”是我判断一首诗是否合格的重要评判标准。
有情绪,是不以理智打动人,不能凭借“有意思”,而是作者内心不得已而又不得不发泄的感情。
诗人的神经是敏感而脆弱的,只有这样的特质,才能将所见所闻所感无数倍放到诗句之中,才能让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人悄悄地释放自己的观点、兴趣、态度。
二、诗的形式大于一切
文学作品的出发点是情绪,而向外表现出来的则是形式。比如我最喜欢的现当代的作家是鲁迅和汪曾祺,除去鲁迅先生的深邃和汪曾祺先生的通透,他们的文字真的是一流。每次阅读他们的作品,都有一种跨越时间的新鲜感。
就我个人而言,古典诗词的形式美是打动我的很关键的因素,选择坚持创作古典诗词,以旧瓶装新酒,也是因为对诗词的形式着迷。这种形式上的成就,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技术。只不过这种技术,需要在完成作品的时候,将技术的痕迹消减到不易被人察觉的程度。
杜甫“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给我的是一种直觉的触动,真的好。这样一种直觉,是诗词特有的姿态,这个姿态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个“诗味”。
这个诗味,不因语言古雅而教人生畏,也不会因为语言浅白而觉得油滑,问题的关键是恰到好处,符合诗人的身份、性格、阅历、偏好和当时所处的情境。
比如保定有一位老诗人曹庆华写过一首《老来学书偶成》:
未临上大人,羞摹孔乙己。
毫末自本色,立锥亦可喜。
注:“上大人”“孔乙己”皆旧时小学生学书临摹放影中之字样也,亦双关权贵与没落文人。
这首诗很有那种老派文人的性格特点,谦虚中带一点自得,严肃中带一点俏皮。有一种老顽童的那种孩子气。
比如河间诗友孙中英,他写了一首《生病自嘲》,其中有一联:“抽将一管男儿血,换取三联病号单。”
诗中嵌入了新词语,但他对新的词语进行了有效的筛选。筛选后的词语很能拉近诗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读着很亲切。但这两句“白话”诗,并不是刻意求新,而是在体现一种真实,这种真实就是他想要说的话,有时代的质感。对读者来说,这种质感是诗人在寻求当代人共有的感觉和味道。
而对于诗词中所谓的“古香古色”,我是持中立态度的。
现实中求之不得的东西,或许需要通过理想寻求。其实,这也是一种向善向美的力量的展现。但对待这种“古香古色”的词语,除了作为学习和模仿之外,我们仍然应该向对待新词语那样,在使用的时候,在真正的创作中务必要筛选,而不能照搬照抄,从古人的词汇和语境中去选取恰当的、同时还富有活力的词语。
三、诗中要有我
格调、深度,仁者见仁,但是好不好看,有不有趣,明眼人都知道。写诗可以没有方向,但不能失去了趣味。生命是严肃的,更是有趣的。
写诗于我来说,是一种看世界的角度,甚至影响了我的处世态度。
诗中有我,我认为这是写诗最关键的一点,因为所谓的“诗言志”也是自己的“志”而不是别人的“志”。即便宋词中有些作品(代言体)模仿女人口气写得委婉缠绵,亦属于在别人的角色里流自己的眼泪,未脱离此范畴。
认真思考生活的人都有诗人的潜质。什么样的年龄写什么样的诗最好,诗人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就是一树花,秋天就是一树果。所以,诗人的作品每个阶段不一样才是正常的。当然,无论哪个阶段都应该有“我”的独特性。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只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写出来的作品自然与众不同。
同时,这个我也是不断成长成熟的。写最真实的我,但这个“我”未必是最好的“我”。所以,诗人应该做的就是做最好的我,然后把这个向善向美最好的“我”写出来。
诗友李金明是一位农民,他写的《夏灌》:“水声汩汩欲谁听,麦地金黄渠草青。午后微风光影里,红蜻蜓与墨蜻蜓。”
把夏日辛劳的场景写得别开生面,诗中水影天光,诗人在自己的世界里,苦中作乐,感受着自然、感受着生活,仿佛这个世界只有他自己了,这种感觉很自我。
诗友王建强,在一首词中写道:“短信不需长,怕儿思故乡。”
诗人描写自己给孩子回短信的情形,这是作为父亲的真切感受。这位“父亲”和很多父亲一样,话不多,不善于在儿女面前表达。但此刻诗人却偏说怕儿思故乡,其实反过来也是怕自己太思念孩子。朱自清的散文《背影》里,他的父亲话也不多,但感情深沉而又动人,与这两句词中的父爱一样,说明人性中最动人的东西很多时候是相通的。
四、每临大事不言诗
我不是不写大事,只是写大事的时候比较谨慎。因为我觉得想要将大的事件写好非常难。关于这一点的阐述,其实也是对“诗中要有我”的进一步强调。
我不反对批评或者赞美,但我反对千篇一律的内容,反对即时性、新闻性的转化式表达。当我们没有时间和能力去消化大事件带给我们深层次的思考的时候,那些花哨的文学技巧,应制的灵感爆发,都显得那么容易和廉价。
诗言志。真正的好诗是写给自己的,或者说以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大的事件的书写必须要和我们个人紧紧联系才可以。
比如杜甫写安史之乱,写出来的是“三吏三别”。这是战乱之下,大的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遭遇。真实、琐碎,蘸着血和泪。杜甫写打败叛军,写出来的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欢笑、喝酒、赋诗,这是因为胜利带给他的是有家可以回、日子有奔头。其实,大的事件可以从小的角度去表达。
再如亲情的角度。古人写给母亲的诗,凡是写得好的,多关注日常的小事、小场景和小细节。比如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四句,多细小,多平凡。结尾的寸草春晖之比喻,又是多么直愣愣的。我们不觉得生硬,反觉得质朴。因为大爱无言,无法形容,如果真要写的话,直接说出来就好。黄仲则的“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亦同。
这不同于交游、唱和题材,可以尽可能极文采华丽、技巧绚烂之能事。拼才气、拼灵感、拼腹中学问。
我们能做到动心处落笔,真实一点,郑重一点,就挺好。
数年前,我收拾自己的诗稿,有两句诗:“一卷编年鉴真我,每临大事不言诗。”如果写不好,不妨放一放。有时候,不写,也是一种态度。
五、一切世法皆是诗法
如果要找出一句话来概括我对古典诗词的感受,我首先想到的便是顾随先生的那句“一切世法皆是诗法”。世态人情,人间烟火,都在那些刻意或者不刻意的句子中变得摇曳而丰富。
诗词写作对于我来说,应该是生存之外、精神世界层面坚持最久的一件事情了。自2006年开始按照平平仄仄的规则写下郎当的句子,至今断断续续已经坚持了十几年。而这个写作的过程,也是我不断认识世界、体味人生的过程。
我特别喜欢用“恍然大悟”来形容自己在诗词阅读和写作中的获得,这种“恍然大悟”其实是一种迟到的感觉。比如诗词最核心的抒情特质,我听了很多,读了很多,总觉得在理解上差了一点。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石家庄弓月先生那里听昆曲《牡丹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杜丽娘家的后花园中,春花年年开放,但只有她到了十六岁的时候,情窦初开的怀春年纪,才能看到这满园春花的寂寞。眼中景,心中情,合二为一,这不就是古典诗词中的内核嘛!
由此类推,我们的生命中有太多的事情,一如少女怀春一般,无法消除,只有由着这种情绪不断增长。当这种情绪不能实现的时候,自然就演变成为一种“万不得已”——丢不掉、舍不去。正如《蕙风词话》中所说:“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
我想,诗词的写作就应该去多多书写这种万不得已的个人体验。而这种个人体验和情感宣泄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内心中那一份美好。很不现实,很虚无。但人生本来就包含现实和虚无两部分。我们总是在不自觉地打造一个理想中的自我,或者在别人的眼中,或者在自己的作品中,而这个自我,是最虚无的,但也许是最真实的内心写照。
写到这里又想起了顾随先生《生查子》中的两句:“越不爱人间,越觉人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