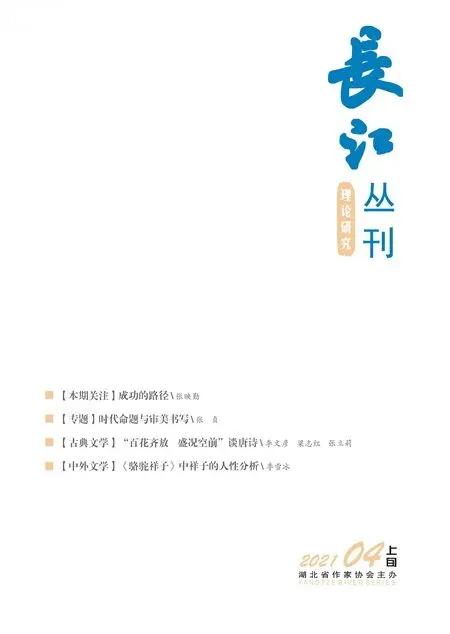挣扎在冬日
——读《飘雪的冬天》
■江妍逸
雷默的《飘雪的冬天》围绕着南田父亲——一个大半截身子已埋进黄土的身患绝症的老人的生死故事展开。小说开篇便是“这冬天怎么熬过去”的发问,定下沉郁的基调。老人终究在寒冬腊月里燃尽了生命的烛光,南田一家“循规蹈矩”地完成了他的身后事。
判断小说好坏的标准在于其“容量”以及所带来的思考想象空间的大小。《飘雪的冬天》是一篇极具生活况味的小说,作者将人性放在“生死”这个严肃的话题面前进行畅快淋漓的解剖,使一万五千字左右的篇幅拥有了沉甸甸的巨大容量。小说主线清晰简单,但作者的重点并不仅在情节构筑上,由主线所抽生出的枝枝蔓蔓,构成了一个宏大的为人性充斥的世界,这才是小说的重点、精髓所在。
小说主要有三部分场景,第一部分是父亲去世前的一段生活,第二部分是父亲去世后,亲戚朋友们料理其后事的经过,最后部分则是所有事情告一段落后,家人围坐小叙之事。在这些场景中,工作与家庭,婚姻与家族,亲情与利益,生死与宿命等被作者悄悄摊开,轮番研讨。
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生活使得主人公南田的生活重心呈现出多样化。南田明知父亲“命不久矣”,理应陪伴老人走完最后一程,却仍然选择奔赴工作岗位,回到妻、子身边。面对母亲提出的“打声招呼”再走的建议,他也以父亲难得安睡为由拒绝了。现实无法令人停下奔波的步伐,子女与父母间的情谊在逐渐复杂的生活内容里慢慢丧失地位。当父亲的一生即将划上句点,究竟是唤醒父亲,与他做一个周全的告别,还是以不打搅其“安好”的借口逃避诀别,这是一个无解命题,而人世的艰难也常在一刹那之间。
男性在情感方面向来比女性来的内敛,父子之间流淌的往往是一种坚毅却克制的情谊,而女性便常在这种关系中扮演涓涓细流。经历数天的阴霾笼罩后,南田需要来自小家庭,尤其是来自妻子的慰藉。而南田与其妻秀萍,却正在经历婚姻的冷淡期。秀萍并没有给他建构风雨后的温馨港湾,无论是南田看望父亲回家后,还是得知父亲去世后,秀萍似乎仅处于一个旁观者、边缘化的位置,参与度、热情度甚至不及丢失儿子的那对夫妇。文章末尾部分写到丈夫两兄弟与母亲讨论“人情簿”被秀萍撞见一事,秀萍的反应是“慌张”的——由此,儿媳与丈夫家庭的隔阂与疏远,此种互为推阻的婚姻关系借助父亲病逝的契机被置于台面之上缓缓展现。
回归到父亲之死。在本应肃穆的葬礼之事上,道士班子的挑选问题令二叔和堂哥大起间隙;入殓时的形式化和粗鲁草率的动作,仿佛“在合伙欺负已经不会挣扎的父亲”;做道场这场仪式,在南田舅舅眼里只剩“这道场卖力的,很热闹,钱花得值”;火葬场的老人用火钳捣碎头骨和肋骨……微带调侃的笔锋,描绘出了刺痛却真实的生活事实。除却至亲之人的沉痛哀悼,其余大部分参与者只将葬礼当做陪伴死者走完最后一程的仪式,或者一场利益纠葛、人情往来的机械化的形式。作者将亲戚间的纠纷安排在葬礼这个背景下,又多了一层疏离的意味,与“无甚关系”的“那对夫妇”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死是令人沉痛的。老人逝世,家里年少的孩子却不知伤悲,仍旧追逐嬉闹,令人反添哀愁。父亲临走的晚上曾说“我这两个儿子都送不到我的”,父辈养育子女一世,临终时终究是孤身而去。南田的哥哥南华在父亲火化时回忆起“十多年前,奶奶火化也是这个炉子”,此类简单的叙述,却都隐藏某种宿命般的不可诉说的神秘感。入殓时被错拿的皮手套,那对夫妇中的妻子高喊的“别进火葬场,看到炉子赶紧跑出来,不要留在里面”,母亲说的“你们爸爸死了还在为你们考虑”,听完丈夫火化之后的腿骨跟老虎骨头一样粗壮后很是受用等诸多细节,又使“生”与“死”通过活人的寄托与缅怀有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丧礼终于完毕,母子三人拿出人情簿,梳理完一系列人情关系后,母亲哭了。身体陡然放松下来后,对丈夫的怀念,对人情交往的担忧,对未来独居生活的恐惧,使得母亲的内心轰然倒塌。所幸这个飘雪的冬天里,还有热心乡人老郑的雪中送炭,邻居夫妇从始至终、尽心竭力的帮助,这些都使千里冰封的大地开出一树树梅花来。
小说文辞细腻,平静克制,虽无大喜大悲之词,却常让人在看似波澜无风之处潸然泪下。通过冷静甚至微带戏谑的口吻,作者为我们缓缓铺展开生活画面,道出了人性的复杂和对生死的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