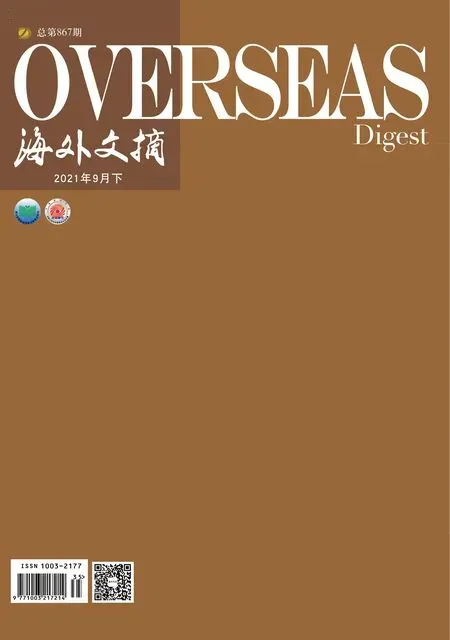《春秋》之孔子“春秋笔法”简析(上)
李冠龙
(天津戏剧博物馆文庙博物馆管理办公室,天津 300090)
《春秋》,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鲁国十二公的历史。当世之时,世衰道微,诸侯混战,周天子地位与日俱下。由于王室的衰弱,与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度密切相关的世卿世禄制逐渐遭到破坏,“政自天子出”逐渐变为“政自诸侯出”,而后甚至相继出现“政自大夫出”“政自臣宰出”等种种乱象,与之密切相关的宗法和礼乐被融入政治领域中,成为统治者实行统治的重要工具。孔子忧心这种状况,作《春秋》以正社会风气,以明伦理纲常。《孟子·滕文公下》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1 春秋笔法释义
春秋笔法,是孔子倡导的文章写法,意在文章记述中表现作者思想倾向。春秋笔法有狭义和广义之说,狭义特指《春秋》一书的“笔法”,广义还包括后世对《春秋》之“笔法”的应用发挥,本文特讨论《春秋》一书中的“笔法”。孔子把他一生的原则和主张,倾注于《春秋》一书,以期为后人所知。《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对于《春秋》之笔法,许多当代学者提出自己看法,江湄认为:“所谓史书‘义例’,其实是史书撰述中史‘例’和史‘义’的结合。‘义例’思想始于孔子著《春秋》。《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属辞’就是指遣词造句、缀辑文辞,如同是记战争,有伐、侵、入、战、围、救、取、执、溃、灭、败等不同写法。这种固定的写法或许在上古史官记述史实时已经具备,而孔子则将‘褒贬之义’即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史事作出的认识和评价贯彻其中,形成‘义例’。对同一性质的史事的不同写法,其实是表现了不同的或是或非的价值判断。”高希中指出:“中国史学的主要特征主要体现于《春秋》史观。所谓《春秋》史观,一曰记录史实,讲求信而有征;二曰倡言人伦价值,褒贬善恶,意在‘彰显’人物不朽于青史之中……《春秋》史观所主张的善恶褒贬,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标准,而这种道德标准也并不仅仅在于善恶褒贬,而是其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特有的历史意识、一种著史理念——公正理念和永恒理念、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信念,乃至一种信仰:‘坚信行善者即使生前有德而无福,多经苦难,也一定会获善报,会获历史褒扬;坚信作恶者即使生前无德而有福,多享富贵,也一定会遭恶报,会遭历史唾骂。’”
《春秋》笔法,深层次层面在于维持人类文明于不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无可厚非。为贤者讳,齐桓晋文,皆录其功,使人慕而心向往之,一定搜出秦桓晋文之过失而痛斥之,将天下之大,无可师法之人,世风之靡,岂可想象?以讦为直,发扬尊者之过失,痛斥亲者之微瑕,人心又岂能问?所以《春秋》书法褒贬之学,使中国史学到达一最高境界:维持人类文明,运载天地元气。史学之此而可发挥宗教性功能,令中华文明延续,人类文明发展,中华之“史”,通天地而不朽。孔子以后的中国史学家,大抵都能尊此“春秋笔法”不渝,历史之真价值,至此彰显。
2 《春秋》字字珠玑,讲究秉笔直书
《春秋》字字珠玑,“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左丘明认为《春秋》用词细密而词意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当为圣人所作:“《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字以成言。”孔颖达疏:“褒则书字,贬则称名。”晋范宁《春秋谷梁传序》给予“春秋笔法”高度评价:“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
《左传》记晋国史官董狐不畏权贵,坚持秉笔直书之事。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周太史辛有的后裔。董狐为史官,不畏强权,在赵盾族弟赵穿弑晋灵公后,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留下“董狐直笔”的典故。《左传·宣公二年》:“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后孔子称赞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加以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指责赵盾做为执政大臣,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据以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
此外,《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崔杼杀害国君,“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齐国崔杼杀害国君,一个“弑”字,定格崔杼的罪行。“杀”“诛”和“弑”字意义不同,“杀”,是指对方所加害的是无罪的人;“诛”,是具有绝对正义性和正当理由的,所消灭的是坏人;“弑”,则专指以下犯上的杀害君主或长辈的大逆不道行为。“杀”可指杀人,杀有罪之人,无罪之人,也可指杀动物。“弑”在古代指子杀父、臣杀君,一般指下杀上,对象只能是人而不能是物。“诛”为杀有罪,杀不仁者,可以下杀上,也可上杀下。“戮”的对象可以为有罪之人、不仁之人,也可以是无罪之人。崔杼杀死太史。太史的弟弟接着写“弑”,因而死了两人。太史还有一个弟弟又这样写,崔武子就没杀了。南史氏听说此事,手执照样写好的竹简前去,听到已经如实记载,这才回去。太史兄弟付出三条性命,只为在史书写“崔杼弑其君”五字,彰显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
3 《春秋》惩恶劝善,讲究微言大义
《春秋》讲究微言大义,《史记·孔子世家》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自见于后世矣!’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子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春秋》载:“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称“共叔段”为“段”,没有用全称,也没有用弟字,这是因为弟弟不尊重兄长,不遵守做弟弟本分,所以不提他乃庄公之弟,直呼其名以示批评;兄弟俩如两个国君,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失教,批评他没有尽到兄长责任,没有教育好弟弟,反而放纵然后精心安排,把弟弟推到造反的道路然后消灭。赶走共叔段出于郑庄公本意,便不写共叔段自动出奔,如此处理可见责难郑庄公。
又有《春秋》庄公九年载:“九年春,齐人杀无知。公及齐大夫盟于既。”《传》曰:“九年春,雍廪杀无知。公及齐大夫盟于既,齐无君也。”讲的是齐国公子无知杀掉齐国的齐襄公,自己当上国君,庄公九年的春天,无知被大夫雍廪杀死。鲁庄公和齐国的大夫在既地结盟,这是因为当时齐国没有国君。在这条记录中,孔子在无知的名字前没有冠以国名或公子的字样,表示这个人死有余辜。用“杀”而不用“弑”,则表示就算无知坐上齐国国君之位,也不被时人认可。
此外,《春秋》隐公十一年载:“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夏,公会郑伯于时来。秋七月壬午,公及齐侯、郑伯入许。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讲的是隐公十一年春季,滕侯、薛侯来朝见鲁君。秋季七月壬午日,鲁隐公同齐僖公、郑庄公一同攻入许国。这里讲齐、鲁、郑三军联合杀进许国的事。这里也有春秋笔法,使用郑伯、齐侯来称呼郑国国君姬寤生和齐国国君僖公,批评他们侵略别国。“入”字表示许国进行抵抗。
注释
(1)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J].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高希中.道德标准于当今史学之意义[J].学术论坛,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