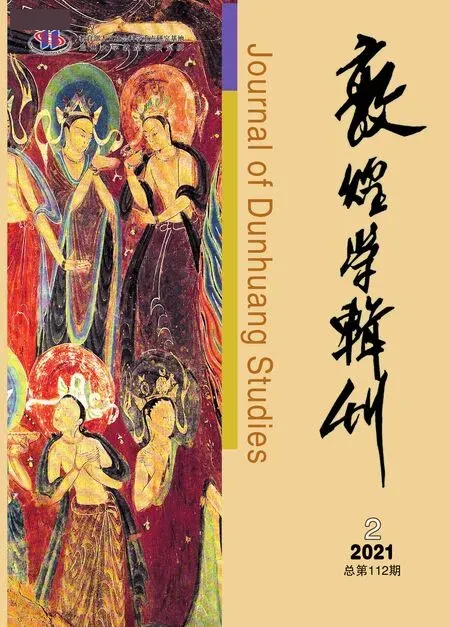敦煌写本P.2555卷 “马云奇诗”考辨
朱瑜章
(河西学院 文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敦煌写本P.2555是一部唐人诗集残卷。上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从巴黎抄回,惜生前尚未最后整理定稿,舒学在王录基础上,参照北京图书馆所藏照片作了进一步整理,将此卷中的 “佚名诗”59首、“马云奇诗”13首,共72首诗,以《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为题,首次刊布于《文物资料丛刊》(1977年),后又收作《全唐诗外编》第二编。其后,王重民遗孀刘修业女士将王重民录文遗稿加以整理,也分为 “马云奇诗13首”和 “佚名残诗集59首”,收入《〈补全唐诗〉拾遗》,并将王重民遗稿《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刊发在《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又将马云奇诗13首收入《补全唐诗拾遗》卷一,佚名诗59首收入卷二。此后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向达先生也曾从巴黎抄录了P.2555卷写本,后由阎文儒先生加以考订校释,以《敦煌两个陷蕃人残诗校释》为题发表了向达的录文和阎文儒所作的校释;①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4-219页。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柴剑虹《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伯2555)补录》、张先堂《〈敦煌唐人诗集残卷 (P.2555)〉新校》等都是校录考订的重要成果①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51-757页;柴剑虹《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伯2555)补录》,《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第146-154页;张先堂《敦煌唐人诗集残卷 (P.2555)新校》,《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5-168页。;台湾潘重规《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研究》,对残卷诗作了较全面的校录考释研究;柴剑虹先后发表《敦煌唐人诗集残卷 (伯2555)初探》《敦煌伯二五五五卷 “马云奇诗”辨》,对P.2555卷作了进一步的探索研究;高嵩出版了专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对P.2555诗集残卷的写作背景、所涉地名及入蕃路线等作了全面的考察研究,但错谬处甚多;其他学者相继对诗集残卷也作了一些深入研究。即就残卷中13首所谓 “马云奇诗”来说,各家研究结论众说纷纭,颇不一致,甚至争议很大。本人不揣谫陋,拟在前面学界研究基础上,对残卷中的12首诗作者、落蕃人入蕃路线、诗意解读等方面试作辨析考释,以就正于方家。
一、马云奇是否为12首诗的作者?
王重民认为残卷正面59首诗作者佚名,背面13首 “格调均相似,除第一首外,又皆咏落蕃事,故可定为一人作品。第一首下题马云奇名,作者殆即马云奇”。②王重民遗稿《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51页。王重民所说的 “第一首”指《怀素师草书歌》。舒学《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承从王说,将这13首诗都列于马云奇名下。向达和阎文儒也认为13首诗都为马云奇所作。陈尚君认为:“十三首诗从伯二五五五残卷中录出。第一首下题名马云奇。因为这些诗格调相似,其中有多首诗咏及被吐蕃拘系之事,故可定为一人作品。”③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4页。因此,马云奇是13首诗的作者这一结论成了学界的主流意见。柴剑虹起初并未质疑马云奇是这13首诗的作者④见柴剑虹《敦煌唐人诗集残卷 (伯2555)初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后来整理了P.2555卷的全部内容,并对其作了进一步考察后认为:“伯二五五五卷中马云奇的诗只有《怀素师草书歌》一首,其余十二首与另外五十九首一样,均是一位佚名的落蕃人所作。”⑤柴剑虹《敦煌伯二五五五卷 “马云奇诗”辨》,《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53页。潘重规认为舒学 “凭空添出一个陷蕃诗人马云奇,那是没有事实根据,不能成立的”⑥潘重规《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研究》,载 (台)《敦煌学》第13辑,第80页。。项楚先生认可柴剑虹和潘重规的意见,认为:“马云奇只是《怀素师草书歌》的作者,而不是陷蕃诗的作者。”⑦项楚《敦煌诗歌导论》,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236页。那么,陷蕃诗的作者是谁呢?柴剑虹、潘重归认为很可能是补作《胡笳十九拍》的毛押牙。王志鹏依据《送游大德赴甘州口号》等诗中有佛学因素,以及从敦煌僧人曾接受委派出使完成特定的政治任务的历史背景作了考察,认为:“P.2555卷背面的十二首陷蕃诗与正面的五十九首陷蕃诗,并非同一作者,马云奇也只是《怀素师草书歌》的作者,而不是陷蕃诗的作者。……包括《白云歌》在内的十二首陷蕃诗的作者是在唐朝和吐蕃战争中奉命出使而被拘系的一位佚名僧人。”①王志鹏《敦煌P.2555卷 〈白云歌〉再探》,载《敦煌文学与佛教文化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64页。学界对12首诗的作者还有其他说法,颇不一致,兹不一一列举。
马云奇是否为12首诗的作者,首先涉及一个焦点问题:即《怀素师草书歌》诗题后有 “马云奇”的署名,后属诗12首诗没有署名。王重民、舒学、向达、阎文儒、陈尚君诸学者依此认为《怀素师草书歌》后属12首诗的作者都是马云奇。当然,诚如潘重规所言:“单凭前一首诗作者的姓名,率然把接连一串无姓氏的作品认定是同一人所作,这种情况,在敦煌写本中是非常不可靠的。”但潘重规同时又承认:“事实尽管如此,但敦煌写本中,也并非连属上一首作者的作品,都不是同一人所作。”②潘重规《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研究》,第96页。敦煌写本作品作者署名的情况很复杂,有的在第一首诗题下署作者名,后属作品承前省去了同一作者名;有的后属作品不署名,但并不完全跟前一首是同一作者作品,此属个别情况;有的虽然是同一作者,但在每首作品题下均署作者名。不一而足。其中更多的是第一种情况,即抄写者在抄同一作者的多篇作品时,往往在第一篇题下署作者名,后属作品承前省去作者名。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此类例子:
例1:P.2567、P.2552卷 “唐诗丛钞”《邯郸少年行》题下署 “王昌龄校书郎”,后属的《城旁□□□》《送单十三晁五归□□》《巴陵别李十二》《送康浦之京》《长信怨》《题净燕师房》等6首诗均无署名,但可确认这6首诗的作者均为王昌龄。
例2:P.2567、P.2552卷 “唐诗丛钞”《答韩大》题下署 “丘为”,后属的《田家》《辛四卧病舟中群公招登慈和寺》《对雨闻莺》《幽渚云》《伤河龛老人》等5首诗均无署名,但可确认这5首诗的作者均为丘为。
例3:P.2567、P.2552卷 “唐诗丛钞”《题安王出塞》题下署名 “高适”,后属的《上陈左相》等40首诗均无署名,但可确认均为高适所作。
例4:P.3866卷为册子诗,首页题 “涉道诗”,下署作者名 “李翔”。这组诗共28首,后属的诗题下均无署名,研究者认为作者均为李翔。
例5:S.373“诸山圣迹题咏诗丛钞”《皇帝癸未年膺运减梁再兴□迎太后七言诗》题下署 “后唐庄宗”,后属的《题北京西山童子寺七言》《题南岳山七言》《题幽州盘山七言》《题幽州石经山》均无署名,但可确认这4首诗的作者均为后唐庄宗李存勖。
如果抄写非同一作者的作品,则在每一篇作品题下署上作者名,如在上述S.373卷署后唐庄宗的5首诗之后接抄了20首诗,这些诗分属于20位作者,则在每首诗题下都署了作者名。
以上情况在敦煌写本中很普遍,兹不一一例举。写本诗如此,写本文也有此类情况。例如P.2537《略出籯金》卷,在《社稷篇第十七》之后有作者题记 “宗人张球写时年七十五”,后面从《忠谏篇第十八》一直到整个写卷结束均无作者题记,但整个《略出籯金》的作者均为张球无疑。
根据敦煌写本作者署名的大概率情况,我们认为,13首诗连贯抄在一起,第1首题下署马云奇名,后属诗承前省去了作者署名,这应该是合乎逻辑的判断。抄写同一作者作品时后属作品承前省去作者名,很可能是敦煌写卷抄写的惯例,犹如写本中遇到叠词时往往承前省去相同的后一个字,用 “〃”类符号代替。王重民、舒学等学者依此认定12首诗作者是马云奇,是完全有道理的。
柴剑虹质疑《白云歌》等12首诗为马云奇所作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这12首诗在内容风格上与《怀素师草书歌》迥异,“却与写卷正面那五十九首佚名诗连贯一气”①柴剑虹《敦煌伯二五五五卷 “马云奇诗”辨》,第54页。。潘重规也认为后属的12首诗与署名马云奇的《怀素师草书歌》风格大不相同。柴、潘二人从作品的内容风格方面来认定12首诗非马云奇所作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仅仅是从表征上得出的推断,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就P.2555卷72首诗中的一些落蕃诗来说,都是在河西各地相继落蕃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作的,诗中所反映的山川地理物候环境,及落蕃人的悲苦、思乡、念亲、盼归等心理状态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王重民先生早已对此作过分析,他认为59首落蕃诗的思想倾向是:
作者的思想并不高超,只是哭愁、哭病、思念家乡,几乎在每首诗里都要“断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虽说偶尔流露出了 “触槐常有志”的话,但接着就说 “折槛为无蹊”,所希望的就是逃跑,或者 “缧绁傥逢恩降日”。对朋友则坦直的说出 “一介耻无苏子节,数回羞寄李陵书”的话。从这些表现,可以推断作者只是一个软弱文人 (或僧人),并没有什么较明显的民族思想和气节。
对马云奇诗的思想倾向,王重民的评价是:
马云奇的诗格较高,风节亦烈。当他被吐蕃拘系的时候,他时常想到他和敌人的斗争。他惋惜的是 “战苦不成功”,所以怀念祖国以外,还常想 “可能忠孝节,长遣困西戎”。他的思想和节操似比前一佚名落蕃人高一等。②王重民遗稿《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第51-52页。
项楚先生在肯定柴剑虹的研究有道理的同时,引其中的三首诗诗句作了分析后对柴剑虹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白云歌》中有两句:“殊方节物异长安,盛夏云光也自寒。”将殊方与长安相比较。结尾又云:“既悲出塞复入塞,应亦有时还帝乡。”“帝乡”即指长安。作者所熟悉,所思念的是长安帝乡,这和前五十九首时时系念敦煌不同。作者似乎是中原人士,而前五十九的作者是河西人士。
《至淡河同前之作》……淡河在今焉耆附近,……由敦煌至焉耆和由敦煌至临蕃,方向正好相反。因而陷蕃诗十二首诗的作者与五十九首的作者,很可能不是一个人。
《被蕃军拘系之作》……第四句 “战苦不成功”,透露作者是因为战败被吐蕃拘系的,这和前五十九首作者的被禁似乎不同。因此前五十九首陷蕃诗的作者和后十二首陷蕃诗的作者是否即是同一人,恐怕尚难作肯定的结论。①项楚《敦煌诗歌导论》,第244-245页。
其实,单单从内容、题材上判断数首诗是否为同一人所作是不科学的。情随事迁,诗人诗作的内容、题材必定跟着变化。内容、题材变化了,但手法、风格却常常表现出继承性,相似性。例如:《怀素师草书歌》是题赠送行诗,《白云歌》是落蕃诗。一是写怀素的狂草,一是写祁连山头白云。虽然内容、题材不同,但写作手法和诗作风格却表现出很大的继承性和相似性。试比较下面两段诗:
含毫势若斩蛟龙,握管还同断犀象。兴来索笔纵横扫,满坐词人皆道好。一点三峰巨石悬,长画万岁枯松倒。叫喊忙忙礼不拘,万字千行意转殊。紫塞傍窥鸿雁翼,金盘乱撒水精珠。——《怀素师草书歌》
白云片片映青山,白云不尽青山尽。展转霏微度碧空,碧空不见浮云近。渐觉云低驻马看,联绵缥缈拂征鞍。一不一兮几纷纷,散不散兮何漫漫。东西南北□驱驰,上下高低恣所宜。影碧池冰萤□底,光浮绿树霰凝枝。欲谓白云必从龙,飞来飞去龙不见。欲谓白云不从龙,乍轻乍重谁能变。——《白云歌》
二诗都用了比喻、夸张、铺排的手法,风格洒脱飘逸如行云流水。因此,仅仅从落蕃诗和非落蕃诗内容题材不同的角度否认《白云歌》等12首诗为马云奇所作明显理由不足,还应该从写作手法、风格上看其继承性和相似性。
柴剑虹认为12首诗非马云奇所作的另一个主要理由是,《白云歌》等12首诗与《怀素师草书歌》书写格式迥异,却与59首诗连贯一气,从而认为12首诗非马云奇作,而与正面59首诗为同一作者,很可能为作者自抄。②柴剑虹《敦煌伯二五五五卷 “马云奇诗”辨》,第54页。。这也是从表征上得出的判断。表面上粗看写本图版,背面13首诗抄写字体、大小、格式确实颇不一致,《怀素师草书歌》是稍大字体,后属的《白云歌》突然换成了小字体,接下来的《送游大德赴甘州口号》等11首诗又逐渐恢复为稍大字体,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非一人抄写而成。这种情况应从两方面去审视:一是不能用严谨的标准去揣度敦煌写本的抄写者。因为是写本,抄写者多为寺僧、学郎、下层文人之类的普通人,不是专门的官办的抄写者(如清代《四库全书》的抄写者),抄写的目的或为了学习,或为了习字,或为别人有偿抄写,抄写时并不十分严谨,有一定的随意性,如13首诗后抄写者又随意用更大字体临摹了王羲之临钟繇的《宣示帖》和唐玄宗诗《御制勤政楼下观灯》。二是要从微观上作精细的比照,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仔细观摩写本图片,就会有新的发现。下面从13首诗中抽取一些字列表作以比照:

字例 诗题 诗句 图版字 抄者相似的书写习惯《怀素师草书歌》还如明镜对西施西《白云歌》东西南北□驱驰“西”字第一笔与第二笔连写,第三笔横竖弯钩笔形一致。《九日同诸公殊俗之作》只知魂断陇山西《怀素师草书歌》直为功成岁月多为《白云歌》云飞入袖将为满“为”字用行草体书写,一笔写就,最后一笔内钩。《途中忆儿女之作》发为思乡白《怀素师草书歌》歌《白云歌》《九日同诸公殊俗之作》一人歌唱数人啼“歌”字左面的 “哥”旁头重脚轻,横笔较长,下面的 “可”竖笔较短。与通常写法 “哥”字头轻脚重的写法有别。《怀素师草书歌》不出湖南学草书南《怀素师草书歌》一昨江南投亚相“南” 字结体相似,呈“左上—右下”欹斜之势。《白云歌》东西南北□驱驰《怀素师草书歌》二月花开绿树枝枝“枝”字最后加一点。《白云歌》光浮绿树霰凝枝《怀素师草书歌》青草湖中起墨波《怀素师草书歌》三秋月澹青江水青《白云歌》白云片片映青山“青”字上部最后一横连笔下部,“”笔与左侧竖笔交叉。《赠邓郎将四弟》只是青山一棵松《怀素师草书歌》金盘乱撒水精珠乱“乱”字左右连笔。《白云歌》白云缭乱满空山

字例 诗题 诗句 图版字 抄者相似的书写习惯《怀素师草书歌》隐秀于今墨池在在《白云歌》石暗翻埋在云里“在”字起三笔横撇竖一笔写就。《送游大德赴甘州口号》为报殷勤好在无《怀素师草书歌》醉来只爱山翁酒酒《白云歌》栾巴噀酒应随去“酒”字右面的 “酉”字写法特点与 “青”同《怀素师草书歌》不出湖南学草书出《白云歌》遥望白云出海湾“出”字由两个 “山”字组成,与通常所见竖笔贯通的写法不同。
经过字体的比照就会发现:字体明显有二王书法的风格,但确也有抄写者自己的书写习惯。《怀素师草书歌》与《白云歌》虽然字体大小有别,但确为同一人抄写无疑,连同后属的11首诗确属同一人抄写无疑。因此,不能依据字体大小等直观印象认为其非一人所书。59首诗的抄写者与作者有可能是同一人,整个72首诗的抄写者也可能是同一人,但单单隔离出《怀素师草书歌》,说正面59首诗和背面12首诗的抄写者与作者是同一人,确实没有可靠的证据。落蕃人写诗是为了纪行,为了记录自己落蕃的悲苦、思乡、念亲、盼归的心路历程,而抄写者是为了学习、习字,二者不能同日而语。至于为何用大小字体互相轮换着抄写,只能理解为抄写者习字的随意性所致。
潘重规还在马云奇的年龄上大作文章。他从《怀素师草书歌》中 “怀素年才三十余”一句推断马云奇的年龄 “显然是超过怀素的”,并推理出敦煌陷蕃时马云奇必是六十岁以上的老翁,而后属的陷蕃诗全然没有流露老翁的口吻①潘重规《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研究》,第100页。。从而否定马云奇是陷蕃诗的作者。这个理由很牵强。从 “怀素年才三十余”怎能作出马云奇的年龄一定要比怀素大的判断?马云奇与怀素年龄相仿或年龄比怀素小也可以说 “怀素年才三十余”,因为这句诗是称颂怀素年轻成才,与马云奇的年龄没有关系。笔者倒是倾向于认为马云奇的年龄很可能比怀素小,因为马云奇比怀素年轻,故在诗中充满了对怀素的溢美称颂和仰慕之情。
《怀素师草书歌》等13首诗为何连贯抄写在一起?研究者们往往忽略这一问题,而只是从《怀素师草书歌》非落蕃诗而后属12首是落蕃诗的角度认为二者互不相干,从而质疑马云奇是后属12首诗的作者。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抄写者将13首诗连贯抄在一起是有道理的。我们可以从《怀素师草书歌》中发现一些能证明马云奇同时也是后属12首诗作者的一些线索。怀素是湖南一带人,擅长草书,交友广泛,李白、任华、戴叔伦、张谓、鲁收、苏涣等人都与他有交游,马云奇与怀素也是挚友。“闻道怀书西入秦,客中相送转相亲”,怀素要 “西入秦”,马云奇等好友置酒宴为他送行,大概席间怀素作书,马云奇等人作诗大赞其书法。怀素 “西入秦”,应该是实有其事。据《唐怀素 〈自叙帖〉》,开头说自己年轻时 “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仗 (杖)锡,西游上国”。怀素的好友任华在其诗作《怀素上人草书歌》中赞其在京都长安的交游:“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马云奇诗中说怀素 “西入秦”后,“君王必是收狂客”,皇帝必定召见怀素这位“狂客”。皇帝究竟召见怀素没有?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怀素西游到了长安,即使皇帝召见了怀素,也未必从此把怀素留在宫中。怀素生性狂放不羁,被朋友们誉为 “狂客”,一生喜好漫游天下,不可能长期在京都长安逗留。文人士子高僧大德们喜好漫游天下,是盛唐时代普遍的社会风气。“西入秦”并不意味着到长安为止,古代将长安以西河陇一带都视为秦地。怀素很有可能与他的 “一路人”从长安出发再到河陇地区漫游。唐代有 “追星”的社会风气,例如李白名震天下时,有两个年轻人任华、魏万不远千里追踪相从。马云奇可以说是怀素的 “粉丝”,很有可能步其后尘追踪怀素也到了长安及河陇地区,13首诗中的部分诗作就是在河陇地区作的。敦煌抄卷者手头必定有一个所参照的马云奇诗集写卷原本,而参照的这个原本很可能将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与他在河陇作的落蕃诗及其他诗歌连贯编在一起,于是抄写者依此连贯抄在一起,根据抄写惯例,后属的12首诗承前省去了作者,这应该就是事情的原委。
根据以上考辨推论,基本可以排除从抄写习惯、内容风格、抄写格式、字体大小、作者年龄等方面质疑12首诗为马云奇作的理由。认为12首诗作者是位佚名诗人或佚名僧人,或认为跟59首诗是同一作者的说法都缺乏正面有力的证据。在没有更可靠的证据出现之前,我们还是认可王重民、舒学、向达、阎文儒、陈尚君诸家说法,《怀素师草书歌》等13首诗的作者均为马云奇。
二、马云奇是否进入张掖军幕?
马云奇是否到过河陇之地并进入张掖军幕?除了前面根据《怀素师草书歌》作出的推论之外,我们还可以从《送游大德赴甘州口号》中发现更重要的证据。诗云:
支公张掖去何如?异俗多嫌不寄书。数人四海皆兄弟,为报殷勤好在无。
诗题下有注:“此便代书,寄呈将军。”这首诗是 “口号”诗,即随口吟成、 “口占”之意。研究者多依 “异俗”二字判断此诗为落蕃诗,而诗中的 “异俗”非指蕃地,而指游大德要去的 “甘州”,即 “张掖”。《旧唐书·地理志》:“武德二年,平李轨,置甘州。天宝元年,改为张掖郡。乾元元年,复为甘州。”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41页。在内地人眼中,张掖在塞外,唐人边塞诗常以 “塞上”“塞下”为题咏河西之地,那里物候风土人情与内地迥异,故亦可称 “异俗”之地。作者在诗中一般用 “殊俗” “殊方”指蕃地。 “支公张掖去何如?异俗多嫌不寄书”意为:您到张掖去前景如何呢?我担心你到了那个异俗之地不给我回信。由此推断马云奇肯定是在 “非异俗”之地即内地,送别游大德并随口吟成这首诗的。高嵩认为此诗为 “建中三年夏作于海北途中。游大德被番军遣回,目的不明。这首诗告诉我们,马云奇一行仅为 ‘数人’,而有些高级官员 (如 ‘将军’)尚留张掖。”②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页。此说是依 “异俗”为蕃地做出的判断,较牵强。如果说游大德和作者马云奇一起作为唐俘从张掖羁押到了青海,后游大德又被蕃军遣回张掖,此时的张掖已经沦陷于吐蕃,那位寄呈的张掖 “将军”十之八九也成了 “落蕃人”,或被羁押,至少失去了自由。那么,马云奇给 “将军”投诗 (信)有何目的呢?甚至游大德能否在张掖见到 “将军”恐怕都是问题。抑或张掖 “将军”已经投靠了蕃军,马云奇投诗给 “将军”,是否也想步其后尘?而这又与马云奇落蕃诗中所表现的民族气节不符。故高嵩之说不能成立。
游大德何许人也?他并不是姓游名大德,而是一位游姓高僧,在诗中称他为 “支公”。据柴剑虹考释:“晋高僧支遁亦称支公,见《世说新语·言语》,后世即以 ‘支公’代称高僧。大德,梵云 ‘婆檀那’,为比丘高年之称。唐赵璘《因话录》卷四:‘元和以来,京城诸僧及道士,尤多大德之号。偶因势进,则得补署,遂以为头衔。’”③柴剑虹《敦煌伯二五五五卷 “马云奇诗”辨》,第58页。这里说 “元和以来”一些高僧大德 “偶因势进,则得补署”,实际上有唐一代都存在这种现象,如玄奘从天竺取经返回后,受到唐太宗的优礼召见,太宗曾劝玄奘还俗入朝供职:“帝又察法师堪公辅之寄,因劝罢道,助秉俗务。……固辞乃止。”④[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9页。由此推知,游大德赴张掖,要面见张掖将军,显然也是这个目的,即进入张掖军幕 “补署”。所以马云奇就不会是在落蕃后在蕃地送别游大德的,应该在这之前,在别的地方。我们推测,大概早在安史之乱之前,内地某个地方,比如长安,好友游大德要去张掖 “补署”,马云奇口占一诗为他送行,顺便让他 “此便代书,寄呈将军”,即以这首口号诗代替书信寄呈张掖将军。马云奇为何要投诗 (信)给张掖将军?目的无非是要步游大德的后尘,希望也能入张掖军幕 “补署”。在唐代,通过投递诗篇给好友,表达希望得到举荐能够入幕的愿望,是士林中一种普遍的风气。如杜甫当年困守长安,仕途无望时,曾投诗给河西节度府任判官的田梁丘和掌书记的高适⑤杜甫的投赠诗有《赠田九判官梁丘》《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寄高三十五书记》。,委婉地表达希望得到他们的举荐也能入哥舒翰幕的愿望。
诗中还有一个重要信息不能忽视,即 “数人四海皆兄弟,为报殷勤好在无”,游大德不是只身一人入张掖的,是有 “数人”相伴一起到张掖的,且这 “数人”显然都与马云奇 “皆兄弟”,这与怀素 “西入秦”时 “寄语江潭一路人”很相似。当年怀素也不是只身一人入秦,而是有一帮人相伴一起入秦。所以马云奇在诗中寄语游大德等友朋,到张掖后要在将军面前多多为我致意,以报我的殷切候望。很可能经过游大德等人的大力举荐,马云奇顺利地进入了张掖将军幕府,12首诗中的 “落蕃诗”以及入蕃的路线就是有力的反向证明。
还有一种可能:游大德就是怀素 “西入秦”时那 “一路人”其中的一个,怀素是位 “狂僧”,游大德也是一位高僧,僧人们结伴而行,这 “一路人”和《送游大德赴张掖口号》中的 “数人”是同一帮人,也未可知。所以,《送游大德赴甘州口号》以及后面的落蕃诗可以说是马云奇入张掖军幕的重要证据。因为马云奇进入了张掖将军幕,张掖陷蕃后被蕃军羁押经大斗拔谷到青海蕃地,就构成了一条合乎情理的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
三、马云奇入蕃走的是西线还是南线?
马云奇入蕃走的是哪条路线?迄今学术界的讨论,可以概括为 “西线”和 “南线”两种说法。
舒学认为马云奇入蕃走的是西线:“马云奇大概是公元787年吐蕃攻占安西后,从敦煌出发,经过淡水,被押送到安西。”①舒学《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第48页。学界大多数学者也采纳这种说法。“西线”说建立在二个判断之上:一是马云奇等人是在敦煌落蕃的;二是入蕃路上渡过的 “淡河”在西域焉耆附近,所据为《新唐书·地理志》的一段记载:“西州交河郡,中都督府,……有天山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盘石百里,有张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渡淡河至焉耆镇城。”②[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6页。但学界早有人质疑过 “西线”说,前引项楚先生曾质疑经过焉耆的淡河与去青海的临蕃方向相反。③项楚《敦煌诗歌导论》,第241页。阎文儒先生援引向达先生对此曾有疑问:“以淡河为焉耆之淡河,因而马云奇不知何故押送西州、北庭,遂疑莫能释。如认为马云奇自敦煌陷蕃,过另一水味不咸之淡河,与焉耆者名同地异,则语不难解矣。”阎文儒先生根据向达先生的质疑认为:“马云奇过淡河,非焉耆之淡河,或在关内。”④阎文儒《敦煌两个陷蕃人残诗校释》,载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第215页。柴剑虹先生也质疑走西线说,认为 “‘淡河’似并不能作为安西陷于吐蕃之证。因为当时西域山川同名的甚多,如黑水、白山、金岭、甘泉之类,马云奇诗中的‘淡河’并非即是西州 ‘淡水’(即今开都河)”①柴剑虹《敦煌唐人诗集残卷 (伯2555)初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第73页。。但柴先生并未深入探讨马云奇入蕃到底走的是哪条路线。
高嵩首次提出了 “南线”说。他在实地踏勘调查了青海、张掖一带的山水地理之后,在《考释》中明确提出:“马云奇诗告诉我们,他是建中三年夏季在蕃军押解下离开张掖亲眷,过淡河 (今读音讹作 ‘大河’)入大斗拔谷 (今民乐扁都口),穿行祁连山隘路到达海北,复由海北东南行,沿湟水而下,到达临蕃一带的。”②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第2页。高嵩确认“淡河”在张掖南部。汤君则认为马云奇是在 “位于甘州西南约一百里处的”删丹城被蕃军抓俘的。马云奇 “并没有押往张掖 (甘州),而是自删丹城折而向南,过淡河,向吐蕃边界前进。”③汤君《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作者考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10月专辑,第244页。作者并不熟悉河西地理,将在张掖东南的山丹 (删丹)误作西南,而且没有任何证据断言马云奇是在山丹城被俘的。此结论不足为据。
判断马云奇被押解走西线还是南线,研究者都注目于《至淡河同前之作》这首诗题中的 “淡河”,诗云:
念尔兼辞国,缄愁欲渡河。到来河更阔,应为涕流多。
高嵩确认此 “淡河”即今民乐县城西的一条河流,当地人称为 “大河”。笔者深以为然。但高嵩解释为何叫 “淡河”时又望文生义搞错了。他调查发现这条河一年里多为枯水期,水不旺,所以他认为 “旺”的反义词就是 “淡”,“淡河,即是枯水河”④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第103页。。实际上 “淡河”就是固定的河名,不是根据河中枯水的临时称呼。这条河发源于今民乐县城南祁连山一支脉金山山谷,谷中河床及两岸多为红色的砂石,水冲砂石流出,色如渥丹,故古代又称渥丹河,后来俗称红水河,民间讹写为洪水河,久而久之将错就错,误将 “红水”作 “洪水”。清代编修的《甘州府志》,已经对此作过辨正:“洪水,城东南一百二十里,源出金山下谷中,径 (经)西水关入。土人云:‘谷中土石皆赤,水初出如渥丹。’本名 ‘红水’,讹云 ‘洪’也。”⑤[清]钟赓起著,张志纯、郭兴圣、何成才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19页。今民乐县城西的那条河已固定称为“洪水河”或 “洪水大河”,县城所在地为 “洪水镇”。洪 (红)水河古时水流甚大,又称玄川。魏明帝青龙三年 (235),“是岁张掖郡删丹县金山玄川溢涌”⑥[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3《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6页。。所以自古以来并不是一条枯水河。高嵩考察时,洪水河的上游已经修建了双树寺水库,水都被截流到益民干渠了,水库下面的原始河流自然干枯,所以给高嵩造成了错觉,以为淡河就是枯水河的意思。
这条河在马云奇诗中为何称为 “淡河”,有二种可能:一是把 “渥丹河”简称为“丹河”,马云奇用同音字 (声调不同)写为 “淡河”;另一种可能是方音上的误听造成的,当地人平时习惯将 “洪水大河”简称为 “大河”,当地人口音把 “ɑ”读为“ɑi”,把 “大 (dà) 河” 读为 “dài hé”,马云奇等落蕃人路过,从当地人口中又混听为 “dàn hé”,故写作 “淡河”,这种可能性很大。
其实,在基本确认马云奇等人是在张掖被俘之后被蕃军羁押往青海之地的事实后,入蕃的路线就不辨自明了。从张掖往青海方向,最便捷的一条路线就是:向南渡过淡河(今民乐县城旁的洪水大河),继续向南进入扁都口 (古大斗拔谷),翻越祁连山俄博岭大阪,就进入到青海蕃地。古代从中原西行的人常走这条路线,即从陇西、临洮、金城(兰州)向西南渡过湟水,到鄯州 (今西宁一带),翻越祁连山大阪,出大斗拔谷到张掖。这条路线也是古丝绸之路的支线之一。张骞通西域、霍去病第一次兵出河西奇袭匈奴、东晋法显西行求法、隋炀帝征吐谷浑后到张掖召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者,都走的是这条路线。唐代吐蕃经常骚扰掠抢张掖,也是兵出大斗拔谷。唐代在大斗拔谷驻军防守隘口,哥舒翰曾任大斗军副使。蕃军在张掖羁押了马云奇等人后只能走南线无疑,不可能舍近求远,把唐俘押解上向西千里迢迢到敦煌、焉耆折回向东再向南往青海去。
四、其他10首诗简说
学界往往将《怀素师草书歌》以下的12首诗笼统地称为 “落蕃诗”,这是不严谨、不准确的。也正因为研究者囿于 “敦煌”“落蕃”的背景,故在诗意解读方面常有牵强不确之嫌。仔细阅读揣摩这12首诗,就会发现,真正的落蕃诗只有7首。这7首诗陆续作于马云奇等被拘系从张掖出发途经祁连山大斗拔谷、翻越俄博岭大阪进入青海北蕃地期间,时间大概是从盛夏到秋天。高嵩将部分诗的写作地确认为青海湖及青海东部的“临蕃”,似无确凿的证据。其余5首是题赠诗,作于张掖陷蕃前,不能列入落蕃诗。下面将前面已作考辨的《怀素师草书歌》《送游大德赴甘州口号》《至淡河同前之作》等三首诗之外的10首诗,大致依写作先后顺序作简要解说。
1.《题周奉卿》,诗云:
明王道得腹心臣,百万人中独一人。阶下往来三径迹,门前桃李四时春。
阎文儒的解说是:“周奉卿不知何许人,但可能是汉官陷蕃者。陷蕃以后,他在敦煌或者是不做官了”“或者弃官而教读也。”①阎文儒《敦煌两个陷蕃人残诗校释》,载阎文儒、陈玉龙主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第214页。高嵩认为此诗 “作于张掖陷蕃之后”,释“明王”为 “张掖郡王某”②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第55页。。按,“明王”应该是亲王一类的人,称张掖郡主为 “明王”似为不确。柴剑虹先生援引残卷正面59首诗中的《梦到沙洲奉怀殿下》考证此“明王”是否就是彼 “殿下”,柴文据《册府元龟》记载考,肃宗至德元载 (756),“封故郡王第五男承宷为敦煌王”,他受封敦煌王后当可称殿下。①柴剑虹《敦煌唐人诗集残卷 (伯2555)初探》,第72页。但李承宷虽封敦煌王但没有亲自到敦煌的记载,说明仅仅是个封号而已。杨富学认为 “殿下”为 “金山(国)天子殿下”张承奉②杨富学、盖佳择《敦煌写卷 “落蕃诗”创作年代再探》,载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47-172页。。研究者往往囿于这首诗是 “落蕃诗”,落蕃地在敦煌,“明王”也必在敦煌,从而使研究钻入了牛角尖。其实,跳出 “落蕃”“敦煌”的局限,这首诗并不难解。诗中前二句称颂周奉卿是明王的心腹之人,是难得的人才,“百万人中独一人”是夸张手法;后二句称颂周奉卿居处幽远,风景优美。“三径”一般指隐居之地。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竹犹存。”可知周奉卿大概跟王维一样,在京城也过着亦官亦隐、半隐半仕的生活。观其诗充满溢美之词,应该是马云奇在长安时题赠好友周奉卿所作,“明王”是皇室的某位亲王。
2.《赠邓郎将四弟》,诗云:
把袂相欢意最浓,十年言笑得朋从。怜君节操曾无易,只是青山一树松。
阎文儒认为邓郎将四弟 “可能是未作蕃官者”③阎文儒《敦煌两个陷蕃人残诗校释》,载阎文儒、陈玉龙主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第214页。。高嵩认为:“此系甘州初陷时赠友之作,而非途中聚会赠答之作。”④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第55页。二人的说法还是囿于 “落蕃诗”的范围。按,“郎将”是武官名,唐时在中郎将之外,复设郎将一职。这位邓氏郎将在邓氏家族中排行第四,可能与马云奇为结拜弟兄。诗中称颂自己与邓郎将四弟的亲密友情,是经过了十年的培育。并称颂邓郎将四弟有像青松一样崇高的节操。与上首诗一样,都是题赠诗,应作于张掖陷蕃前的和平时期。
3.《同前已 (以)诗代书》,诗云:
故 (古)来同病总相怜,不似今人见眼前。且随浮俗贪趍 (趋)世,肯料寒灰亦重然 (燃)。
这首诗接在《赠邓郎将四弟》之后,“前”即指《赠邓郎将四弟》,“以诗代书”,意为以这首诗代信件送给邓郎将四弟。前二句古今对比,讽刺时下人们只重眼前的短视行为,更显出作者与邓郎将四弟 “同病相怜”友情的坚贞不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马云奇志趣高雅。后二句似乎意味着邓郎将四弟可能在仕途上受到了挫折,故作者勉励他暂且与世俯仰,等待时机,必有 “寒灰重燃”之时。阎文儒认为 “寒灰重燃”有“恢复汉族政权之意”⑤阎文儒《敦煌两个陷蕃人残诗校释》,载阎文儒、陈玉龙主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第214页。,可备一说。
4.《赠乐使君》,诗云:
知君桃李遍成蹊,故托乔林此处栖。虽然灌木凌云秀,会有寒鸦夜夜啼。
诗中的 “灌木”,舒学稿、向达稿都误录为 “灌水”,“灌水凌云秀”讲不通。高嵩依此释为 “灌水即今梨园河,发源于肃南裕固县之西”,更是误上加误。此字图版为,显然系 “木”与 “水”形似而误录,应确认为 “木”,“灌木凌云秀”才能讲得通。可见对于写本,如果最初录错一个字,往往使后来的解读者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阎文儒认为乐使君 “可能是流落吐蕃人物。敦煌陷蕃后,隐于教书后生的生活中”①阎文儒《敦煌两个陷蕃人残诗校释》,载阎文儒、陈玉龙主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第216页。。高嵩认为:“此诗作于建中二年张掖陷落后不久。吐蕃对于高级唐俘一般地比较优待。乐使君大概获准到灌水别业隐居。”②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第60页。这是没有根据的臆说。张掖已经陷落,连马云奇等一般官员都被羁押往青海蕃地,蕃军怎么能对一郡之主的太守 (使君)格外开恩允许他去隐居地度假呢?哪有证据显示吐蕃优待唐俘?马云奇在羁押中,已经失去了自由,几乎是终日以泪洗面 (“发为思乡白,形因泣泪枯”;“应为流涕多”),哪有心思去给远在张掖的乐使君赠诗呢?赠诗给乐使君又有何用意呢?
揣摩全诗,大意是说,您 (乐使君)人品高雅,弟子众多 (“桃李成蹊”用了李广典),并有别业在山林中,山林中虽然环境雅致幽静,但要面对着 “寒鸦夜夜啼”。“寒鸦夜啼”的意象或暗喻主人身处孤独冷寂之地,或暗喻时政的变坏,是否暗指张掖面临陷蕃的形势?诗情先扬后抑,乐观中有忧虑,应该作于张掖陷蕃前。
5.《俯吐蕃禁门观田判官赠向将军真言口号》,诗云:
题目的 “俯”即附着、俯身之意,前有 “俯”,中间有 “观”,即俯身贴近看之意。项楚说 “俯”为 “附”,脱一个 “近”字,似有化简单为繁琐之嫌。 “主君”,王重民依写卷录 “主君”,舒学稿、高嵩稿录为 “君王”,当从原卷作 “主君”。“颔”,王、舒、高均录为 “鸰”,徐俊、张先堂校录为 “颔”。按,此句句末依诗律应为仄声字,“鸰”为平声,不当;“颔”为仄声字,当是。“颔”即 “燕颔”。古人认为“燕颔”相为封侯之相。如《后汉书·班超传》记班超未出使西域之前曾请相者为自己看相,相者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③[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7《班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71页。南朝陈徐陵《出自蓟北门行》:“平生燕颔相,会自去封侯。”《三国演义》第一回写张飞的相貌:“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如巨雷,势如奔马。”马诗中以 “燕颔”赞向将军生相英武,有封侯之相。“直如弦”出自《后汉书·五行志》引顺帝时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④[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第3281页。意为性格刚直如弓弦的人结果凄惨死于道边,而那些阿谀奉承之人却最终能封王封侯。
这首诗较难解。阎文儒的解说是:“此向将军与田判官,可能都是陷蕃的人物。但向将军偏得吐蕃王的爱戴,而田判官又系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故能说出向将军是 ‘看心且爱直如弦’了。”①阎文儒《敦煌两个陷蕃人残诗校释》,载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第213-214页。向将军、田判官都是陷蕃的人物,这个判断没错;但要说向将军 “偏得吐蕃王的爱戴”,而田判官是 “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却无依据。诗中说向将军有 “燕颔相”,心如直弓弦,显然是赞美称颂之词,并无讽刺之意。潘重规的解说是:“俯伏着敌人禁门来遥观吐蕃的将军官吏赠送真言,还流露羡慕他们获得君王的宠爱。”②潘重规《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研究》,第100页。这个解说让人不知所云,“田判官”和 “向将军”怎么成了吐蕃的将军官吏?莫非吐蕃军队中也设有 “判官”这一文职?“君王”是唐天子还是吐蕃的赞普?高嵩认为:“此诗建中二年秋天作于张掖。田判官系作者同僚,他赠向将军的真言,是用佛家密语给向将军进的谠言。僚友轮观之际,马氏感而有作。向将军或指前面《送游大德赴甘州口号》一诗副题上所说的那位将军。”③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第54页。这个解说有道理,但仍是语焉不详。马云奇在张掖俯身看到了同僚田判官给向将军的 “真言”(佛家密语),怎么是在 “吐蕃禁门”看到的?张掖怎么会有一个 “吐蕃禁门”?“禁门”本指唐皇室宫门,这里借指吐蕃的衙门,或吐蕃军队的营帐。张掖有 “吐蕃禁门”,只能有一个解释:张掖已陷蕃,所以吐蕃在张掖设了禁门。
揣摩诗的内容,对诗意可作出如下的解读:田判官、向将军、马云奇都在张掖陷蕃后成了俘虏,都被拘押在张掖的 “吐蕃禁门”,向将军宁死不屈,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田判官乘机写了一个佛家的 “真言”给向将军以共勉,被马云奇俯身 (弯腰)看到了,口占一诗赞向将军。诗中高度赞扬向将军,说难怪他得到大唐天子 (主君)的垂爱镇守边防,将军生相英武,本有封侯之望,心性耿直刚烈,敌我分明,虽然被俘,但虽败犹荣。
当然,这首诗也可有别解:“吐蕃禁门”不在张掖,就在蕃地,田、向、马诸人已被押解到了蕃地,田判官乘机写了一个佛家的 “真言”给向将军以共勉,被马云奇俯身看到了,口占一诗赞向将军。又,田、向、马三人是否同在一起,也难以确定。也许先前田判官写给向将军的 “真言”贴在或写在 “吐蕃禁门”边,吐蕃卫兵既不识汉字,又不懂这 “真言”,并没在意,马云奇俯身贴近看到了,口占一诗赞向将军。
6.《途中忆儿女之作》,诗云:
发为思乡白,形因泣泪枯。尔曹应有梦,知我断肠无。
高嵩认为此诗为 “在蕃军押解下初出张掖之作”④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第56页。。当是。 “思乡”之 “乡”,同《白云歌》中 “帝乡”,表明作者应为中原人,他的儿女家眷应在内地。前二句写自己因被蕃军羁押而愁苦,以至于发白形瘦。后二句从儿女处设想,他们能梦到我因羁押而肝肠寸断吗!可以说,这首诗同《至淡河同前之作》,都是用血泪写就的落蕃诗。
7.《白云歌》是马云奇诗中最长的一首。原诗题下有序:“予时落殊俗,随蕃军望之,感此而作。”表明这首诗作于诗人落蕃期间。高嵩《考释》认为:“甘州张掖郡建中二年陷蕃,张掖幕府官员若干人翌年夏日被解往青海湖。此诗作于海北某处山头。”①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第49页。这个解说,显然依据的是开头的诗句:“遥看白云出海湾,变成万状须臾间。”“海湾”,一般让人想到的就是青海湾。其实,诗歌不是散文,有时不能实解、直解;诗歌中描写的景象有时是一种虚景,心中想象的景象。如王昌龄诗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站在青海湖边,无论如何是望不到绵延到祁连山的 “长云”和更远的玉门关,它表达的是将士们心中一种尽早结束征战回家的期盼。所以,“遥看白云出海湾”,同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是一样的手法,是一种想象之词。纵观全诗,《白云歌》似应作于作者一行落蕃人从大斗拔谷进入祁连山期间。诗中的 “殊方节物异长安,盛夏云光亦自寒。远戍只将烟正起,横峰更似雪犹残。自云片片暎 (映)青山,白云不尽青山尽。展转霏微度碧空,碧空不见浮云近”,描写的正是祁连山的景象。祁连山峰顶积雪终年不化,盛夏六月飞雪是常见的景象,当年隋炀帝大队人马夏日从青海去张掖,在大斗拔谷突遇大雪,冻死许多随从和战马。所以作者说 “殊方节物异长安”。这首诗最突出的特点是,将写景、抒情、说理很好地融为一体。祁连山头云蒸霞蔚,白云变幻万状,引起作者哲理联想,抒发一种人生莫测、动乱社会中人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感慨。格调悲愤而通脱,跌宕而飘逸。正如颜廷亮先生所说:“作者以犹如行云流水般的诗笔,把对人生的深切感悟和内心的感慨和希望淋淋尽致地表达了出来,使诗篇显示出一种落拓坦荡、飞扬不羁的风格,从而使这首《白云歌》成为全部七十二首陷蕃诗中最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痛苦的悲歌。”②颜廷亮著《敦煌文学千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94页。
8.《诸公破落官蕃中制作》,诗云:
别来心事几悠悠,恨续长波晓夜流。欲知起坐相思意,看取山云一段愁。
“山云”,高嵩本误作 “云山”。高嵩认为此诗为 “马氏一行唐俘解送到湟水后,被分押在昔日唐朝部队留下的古戍、旧垒、颓城。这些地方,本是陇右道军镇的驻地。但马氏称之为 ‘官蕃 (番)’说明这一带为了备蕃,曾有过设置府兵、轮番征戍的历史。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③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第59页。按,题目中 “官”字应上属,破落官,即指同时落蕃遭羁押往青海的 “诸公”,他们都是张掖官署军幕中人。蕃中,指进入到了蕃界。“山云”,指祁连山云。此诗仍应为进入祁连山蕃界所作。
9.《被蕃军中拘系之作》,诗云:
何事逐漂蓬,悠悠过凿空。世穷徒运策,战苦不成功。泪滴东流水,心遥北翥鸿。可能忠孝节,长遣阃西戎。
“徒运策”,王、舒、高本录为 “徒运荣 (蹇)”,张先堂校录、徐俊本录为 “徒运策”,与下句 “不成功”相对,当是。高嵩认为:“作于建中四年。马氏一行,久留海北,至次年春夏之交才到湟水边监押起来。他的监押地为临蕃城外之得倍 (青海省湟中县之多巴镇)”①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第58页。这个解说认为是次年所作,地点在临蕃城外之得倍,缺乏依据。这首诗应为进入祁连山蕃地所作。高嵩释 “凿空”为 “指解离张掖后,一路经过的许多深长的峡谷。”恐非。按,“凿空”句,用了汉张骞 “凿空西域”时遭匈奴羁押事自比。张骞西行,很可能走的就是这条道,出了大斗拔谷被匈奴抓获羁押。而今自己被蕃军羁押又从这条道上经过,思古伤今,其心可鉴。从 “泪滴东流水,心遥北翥鸿”二句可知马氏一行人已经翻过了唐蕃分界处俄博岭大阪,进入到了蕃地。“东流水”即水向东南流。大斗拔谷所在的这段祁连山,是汉地和蕃地的界山,进了大斗拔谷,越往南走,山势越险陡。俄博岭是分水岭,山北的水向西北流,山南的水向东南流。明清时俄博岭有界碑,上铭刻一首佚名的《俄博岭界碑竹枝词》:“鼠牙雀角何相争,山源划界最分明。水向北极归居延,顺流南下属青宁。”②民乐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民乐县志·艺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85页。“可能忠孝节,长遣阃西戎”,抒写一种悲情,意思是说,或许我们这些落蕃人胸怀一腔对大唐的忠孝之气,因为长久被困蕃部无法施展了。“长遣”意味着从张掖陷落,诸公被羁押驱遣到入蕃已经很长时间了。
10.《九日同诸公殊俗之作》,诗云:
一人歌唱数人啼,拭泪相看意转迷。不见书传清 (青)海北,只知魂断陇山西。登高乍似云霄近,寓目仍惊草树低。菊酒何须频劝酌,自然心醉已如泥。
高嵩认为:“马云奇盛夏之日到达海北,至重九尚未离开。看来是在等待吐蕃当局的审理和发配。依题,诗作于建中三年九月九日。”③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第53页。这个解释基本可信,但有点过实。这首诗无疑为九月九重阳节 “登高”“饮酒”之作,但诗作于哪一年的九月九?登的是哪座山?恐不好确定。大概马云奇一行落蕃人已经到了 “青海北”的某个地方,滞留在此地,“辞国”越远,有家难回,故有 “不见书传清 (青)海北,只知魂断陇山西”之悲叹。
五、结语
根据上面的考辨,下面给13首马云奇诗作一个简要的写作顺序表。由于张掖陷蕃的具体年代、时间、马云奇等人被羁押的时间尚难确定,学术界尚有争议。所以只能按13首诗写作先后列出一个大致的顺序表:

时间、路线 诗 作进入张掖之前《怀素师草书歌》《送游大德赴甘州口号》《题周奉卿》在张掖军幕期间或更早《赠乐使君》《赠邓郎将四弟》《同前已 (以)诗代书》张掖陷蕃期间《俯吐蕃禁门观田判官赠向将军真言口号》从张掖到大斗拔谷期间《途中忆儿女之作》《至淡河同前之作》进入大斗拔谷抵蕃地期间《白云歌》《诸公破落官蕃中制作》《被蕃军中拘系之作》《九日同诸公殊俗之作》
马云奇作为13首诗的作者,可是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没有其他资料可证,只有从这13首诗中略知一二。现在可以给马云奇作一个简要的介绍:马云奇,生卒年里不详,约生活在盛唐到中唐的年代里。他涉猎广泛,精通老庄哲学和佛理;交游甚多,与怀素、游大德、周奉卿、邓郎将四弟、乐使君等人有诗歌题赠酬唱交往。曾漫游西北,期间进入过长安,后到河陇地区漫游,进入张掖军幕供职。安史乱后河陇地区相继陷蕃,马云奇在张掖陷蕃后被蕃军羁押经大斗拔谷翻越祁连山到了青海蕃地。马云奇有很高的民族气节,一路上创作了一些落蕃诗,连同先前的题赠诗一起辗转转抄存于敦煌石室中。
从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看,敦煌P.2555唐人诗集残卷中的落蕃诗在唐诗中别具一格,“落蕃诗”填补了唐诗题材的一个空白。它真实地记录了落蕃人痛苦、悲伤、思乡、思亲、盼归、复国的心路历程,展示了河西走廊及青海一带的山河画卷,是大唐河西地区相继落蕃的 “诗史”性记录,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