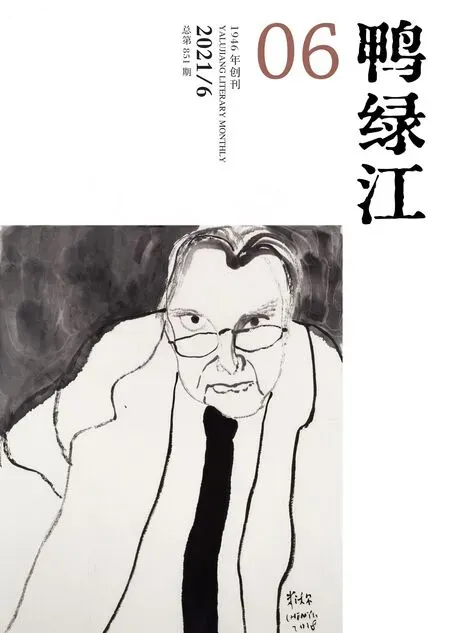遗落在日本的甲午战争碎片
侯德云
甲午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很多战争遗迹却历历在目,尤其旅顺口和威海,遗迹非常密集。这两个地方,现在都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前者我去过多次,我甚至还去看过当年的北洋舰队军营。后者只去过两回,现在印象有些淡薄。只记得第二回,2010年5月22日,我在刘公岛上看了一场电影《甲午海魂》,买过两本关于甲午海战的书。那时候,我对近代史有很浓的兴趣,视线已经触及洋务运动,距甲午战争只有一步之遥。
我是最近两年才知道,“蕞尔小国”日本,竟然也“供奉”许多甲午战争的碎片。我能感受到,那些碎片上,至今仍反射着命运的寒光。
2014年6月,《法制晚报》组织记者到日本,“寻访甲午战争的历史遗存”,归后整理制作了一套电视资料片和出版一本书。我没看过电视片,只读过《甲午遗证》一书。不瞒诸位,我从书中读出许多别样的滋味。
早在《法制晚报》萌发“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之前,近代史学者萨苏的“史眼”,已经将那些战争碎片仔细地巡视过一遍,并在《史客》杂志发表长文《寻找北洋海军的踪迹》予以介绍。后来我在祝勇的散文集《隔岸的甲午》里,也看到过一些类似的碎片。
此刻,我有很强的冲动,要说说那些遥远的碎片。我承认,此举是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
福冈,定远馆
福冈县,太宰府天满宫神社(中国游客称之为“日本的孔子庙”,供奉“学问之神”和“书法之神”菅原道真公,每年大约有七百万人到此参拜)内,有一座“定远馆”。确切地说,是一座带有庭院的单层别墅,只有六十平方米左右。它的大多数建筑材料,都来自清国北洋海军的旗舰定远。
定远舰,德国制造,长91米,宽19.5米,1883年下水。其装甲之厚,其吨位之重,其火炮口径之粗,均居世界前列。甲午黄海大战,“受弹百余而不沉”。确切地说,是中弹159枚。
日本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围攻定远舰的日舰松岛号上,有一个叫三浦虎次郎的水兵,战斗中受伤倒下,司令官过去查看,三浦抬起头,问了一句:“定远还没有沉吗?”听说定远已失去战斗力,三浦才含笑而死。日本有人据此创作了一首歌,叫《勇敢的水兵》,1895年开始传唱,一直唱到今天。这首军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还没有沉没吗,定远号啊!”
在这故事之外,还有一件每天都发生的事实: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儿童,都会玩一种叫“打沉定远”的游戏。
这两件事,说明定远舰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定远馆,也有故事可讲。
1895年2月4日,定远舰在威海港遭日本鱼雷艇偷袭,重伤搁浅。几天后,舰长刘步蟾下令炸毁该舰,随后自尽身亡。一年后,日本富豪小野隆介出资两万日元(相当于今天的两千万日元),从日本海军手里购买了一部分定远舰残骸,运送到故乡福冈县太宰府,以舰骸为建筑材料,建造了一座小别墅。小野后来把定远馆交给天满宫,天满宫先把它当作贵宾室,后改为神社职工宿舍。再之后,有人租借定远馆,在院子里开办玩具跳蚤市场。2011年,天满宫收回定远馆的使用权,不再出租,闲置至今。
据说,小野还把不少定远残骸赠送给别的寺庙和神社,以彰显日本在甲午年的赫赫战功。
2014年6月,《法制晚报》记者走进天满宫神社,正赶上定远馆在装修。记者在采访中询问装修后作何用,主人似乎并没有想好,只是说,希望它还能继续使用一到二百年,还说打算申请为当地的文化遗产。
定远馆里的定远元素,主要有以下几种:舱壁装甲板,被加工成大门,上面布满弹洞和修理时留下的铆钉孔;桅杆变成房间里的柱子;船桨变成房屋底座部分的横栏;弹药库的门变成浴室的门;船底板变成护壁,上面寄生的藤壶隐约在目;水密舱门变成隔扇;军官的座椅被拆散,变成栏杆;等等。
萨苏说他早年到定远馆考察时,是个下雨天,随行的一个女孩把雨伞举在定远舰的海兽雕花木栏上面,久久不肯离去。她说:“我是大连海边出生的人,让我给定远撑一会儿伞。”
那个名叫杨紫的大连女孩,让我心里一动。
有一种传闻,说北洋海军官兵的幽灵经常在定远馆里游荡。日本作家秋山红叶写过一篇文章《定远馆始末记》,说有人在定远馆过夜,半夜时分隐约看到馆内有走动的人影,都穿着北洋水师制服。还说有人半夜到定远馆拿东西,跟穿北洋水师制服的人相撞,当场吓疯。最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小偷夜闯定远馆,听见有人厉声喝问:“税?”这个“税”,在山东方言里是“谁”的意思,在我的出生地辽东半岛,也是“谁”的意思。
定远馆里的鬼故事,据说还有其他版本。秋山在文章中感慨:“定远舰当初负伤阵亡的士兵,就是倒在这些材料上,他们都是死战到最后的勇士,这样善战的定远舰的后身,有如此怨灵的传说,不是正常的吗?”
小野的后代在定远馆里设立灵位,“为那些尽管是敌人,但是只要不葬身鱼腹就开炮不止、对国家忠诚勇武的官兵们的冥福而祈祷”。这一举动,似乎夯实了那些灵异故事。
日文书籍《太宰府天满宫的定远馆》里有这样一段话:“定远馆为何物?在国防重镇太宰府,作为日清战争的‘战利品’遗留着清朝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的残骸。”这段话的汉语译文很别扭,不过意思倒还明确,定远馆是日本的“战利品”,是日本的荣耀。在这个话题上,我们无言以对。
大阪,真田山清军墓
在大阪府的真田山陆军墓地一角,有六座清军官兵墓,墓前有一多米高的石灰岩墓碑,部分已经酥化。墓碑形状为方形尖顶,跟旁边的日军墓碑完全相同,这是日本习俗中勇敢军人专用的墓碑形状。每一座墓碑前面,都有一个接近二十厘米高的瓷管。据萨苏观察,那瓷管是用来插花的。他当年考察这六座清军墓的时候,发现瓷管里有两束枯萎的鲜花。《法制晚报》记者前去考察时,给每个瓷管都插上菊花,默默祭奠清军官兵的亡灵。我为记者的举动而感动。那些亡灵,都是我中华民族的子孙嘛。
奇怪的是,每座清军墓碑上,都有大约三十厘米长的一段白色斑痕。萨苏考证,那块白斑所在之处,原本是“捕虏”二字,后被凿掉。为什么要凿掉?这里边有个故事。故事跟德国有关。这片墓地里,有一战时期德军战俘墓。那些战俘应该是被日军从山东捉来的。到二战时,日德关系亲密,驻大阪的德国领事认为德国战俘墓碑上的“捕虏”字样具有侮辱意味,请求日方凿掉,日方照办。据说,当时日方也考虑对清军战俘的墓碑做同样处理,不知为什么被耽搁下来。日本二战战败后,听说一个中国将军要来日本,墓地管理方担心清军墓碑上的“捕虏”字样会引起那位将军的不满,赶紧凿去。但传说中那位将军根本没去日本。
萨苏介绍,在这一传说遮盖下的事实是,一个名叫钟汉波的民国海军少校,利用他的特使身份,在日本工作期间自作主张,把遗落在日本的定远、镇远两舰的铁锚和锚链,以及两艘被掠的小轮船,都送回国内。可悲的是,送回国内的定远和镇远锚链,被官员当作废铁卖给了铁匠铺。其中的定远舰铁锚,现存于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
埋葬在真田山的清军官兵的名字是:吕文凤,刘起得,李金福,刘汉中,杨永宽,西方诊。前四位,墓碑上刻有“清国”字样;后两位,刻的是“故清国”字样。据考证,杨永宽和西方诊死于民国年间,所以被称为“故清国”。
吕文凤的身份是“朝鲜皇城内清国电信使”。中国海军史研究所所长陈悦介绍,清政府当时在朝鲜设有电报局和电报员,1894年7月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吕文凤应该是在那个时段被俘的。
刘汉中的墓碑上有“清军马兵五品顶戴”字样,是六位官兵中死亡最早的一位,葬于1894年11月。此君也可能是六位官兵中军衔最高的人。一位在日本当过多年报刊编辑的老华侨,从历史档案中找到刘汉中的身份资料,得知这个死时年仅23岁的小刘,祖籍辽宁,世代务农,是家族中第一个当官的人,难怪他至死也要把这份荣耀带入墓中。
陈悦告诉《法制晚报》记者:“刘汉中可能是日军从花园口登陆时俘虏的,也可能是从鸭绿江登陆的日军俘虏的。”这话当然没错。甲午年11月份,日本陆军已兵分两路侵入辽宁地界,刘汉中肯定是被其中一支部队所俘虏。
另有一位“河盛军步兵卒”李金福,陈悦认为可能是在山东战场被俘的。
六座清军墓中,有四座面向北方。萨苏的解释是,在日本的中国劳工曾经误以为,日本的北方跟中国接壤,因此都是往北逃亡。也许清军战俘也认为北方是中国吧。
真田山墓地自2013年起,不再设有专人管理。《法制晚报》记者看见,有不少当地居民在墓地附近遛狗散步。
在这块墓地之外,是否还有别的甲午战争清军战俘墓地?这事不好说。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新的发现。史料记载,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后,双方交换战俘,日方在当年的八九月间,陆续放还了清国被俘的官兵、洋员和百姓共计941人。这九百多人是不是战俘的全部,也很难说。
萨苏在考察中得知,在日本还有四处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的清军墓,位于广岛的比治山陆军墓地。这个墓地成分复杂,除了日军、清军,还有法军、德军等,都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各国官兵的遗骸。萨苏在文章中说,此处清军墓碑,跟周围日军的相比,质量低劣很多。
长崎,定远舰炮弹
长崎县第二大城市佐世保,有一座日本海军墓地。这里的一个特定区域,埋葬近五十位海军官兵,都死于1894年9月17日。那天,清国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激战。日本海军里那位“勇敢的水兵”三浦虎次郎就葬在这里。甲午年担任浪速号巡洋舰舰长,后来出任日本海军元帅,与陆军的乃木希典并称为“军神”的东乡平八郎,也葬在这座墓地,不过跟三浦等人不在一个区域。
定远舰上的四枚炮弹,在这座海军墓地矗立了一百二十多年。两枚实心弹,立在墓地路口;两枚开花弹,立在墓地之中。开花弹上,有甲午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的题词:“为慰灵魂”。每个字都有手掌大小。旁边刻一行小字:“清国军舰定远三十珊半之炮弹,海军中将伊东佑亨”。
这里是日本四大海军墓地之一。墓地管理员宫里说,每周的周一和周五,他都要打扫墓园,并擦拭定远舰的四枚炮弹。让宫里感到自豪的是,此处环境之洁净,在日本海军墓地中首屈一指。
宫里向《法制晚报》记者介绍,这座墓园,每年10月份都会举行一次大型祭祀活动,“市长是祭祀活动的主办人,日本国会议员、佐世保议员、战争老兵、阵亡海军家属等人员都会前来出席”。这个祭祀活动,最多时有上千人参加,最少时也有四百多人。
定远舰的炮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日本甲午战争研究专家原田敬一的解释是:甲午战后,日本成立了一个“战利品”研究会,负责把缴获的物品分发到学校、神社和寺庙等机构,以此激发日本国民的自豪感。
有关这座墓园的一份资料说:“今天的日本人甚至都不知道定远和镇远的名字,但在当时连小学生都知道这两艘清朝的铁甲舰。当日清两国局势紧张之时,日本国民多么担忧啊!”
与国民的态度完全相反,甲午年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发现北洋舰队时,海军官兵个个兴奋异常。时任松岛舰大尉的木村浩吉,在日记中记述,大家都兴奋地换上新衣服,等待战斗打响。
日本海军的气势如此旺盛,出人意料。
冈山,镇远舰主锚
冈山县吉备津市的山岭中,有一个小小的神社——福田海神社。这神社的神主是牛。据说,日本人好吃牛肉,他们希望那些被吃掉的牛灵魂早日升天,不要怨恨人类。
这个小神社里有一只巨大的铁锚,来自北洋舰队主力舰镇远,是镇远的主锚。《法制晚报》记者看见锚的“整个表面呈赤红色”,“在周围青山的映衬下”,那赤红色“显得格外刺眼”。
铁锚两边的石台上,端坐两尊石质神像。一尊持长枪,留长须,类似中国的关公;另一尊很像中国的十八罗汉造型。记者采访得知,这哥儿俩,一个叫“行之使者”,一个叫“理源大师”。
神像和铁锚放置在一起,什么意思?记者没说。
谁都一样,看见镇远主锚,不可能不想起镇远。
陈悦在《北洋海军舰船志》中这样介绍镇远:“黄海海战中,定远镇远二舰结为姊妹,互相支援,不稍退避,多次命中敌舰……(1894年9月17日下午)3时30分,镇远305毫米巨炮命中日本旗舰松岛,引发大爆炸,日方死伤近百人,松岛失去战斗力……”
镇远于1894年11月14日凌晨,在威海湾触动水雷浮标,受八处擦伤,不久旅顺船坞失守,这意味舰伤可能永远无法修复,舰长林泰曾为此愧愤自杀。1895年2月17日,镇远被日军俘获,修复后仍用镇远之名编入日本舰队,列为二等战舰,后来参加日俄战争,与俄国舰队对阵三次,分别是进攻旅顺、黄海之战和对马海战,之后被列为一等海防舰。1911年4月1日退役后充当靶舰。1912年4月6日在横滨解体。解体后遗留的部分船锚、锚链、炮弹等物件,有些陈列在东京上野公园里。
据陈悦考证,福田海神社里的镇远舰主锚是当时日军西京丸号舰长鹿野勇之进赠送的。镇远被俘后,由西京丸拖回日本,当时的主锚锚爪已断。镇远编入日本舰队时,配备了新的主锚。鹿野是冈山人,他把替换下来的镇远主锚送回老家,有纪念战争胜利的意味。
神社的讲解员长谷川悦子告诉《法制晚报》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政府号召百姓捐铁制造军舰,当地人决定把镇远主锚捐出去,可是抬不动,又决定将铁锚切割,可还没等切割,战争已经结束。
镇远主锚被福田海神社封为“不动尊”,“供祭祀所用”。长谷川悦子说,主锚所在之处,是神社的中心。锚重,锚下的大石头也重,两个非常重的大东西一起“镇在这里”,什么妖魔鬼怪都别想作乱。
《法制晚报》记者在报道中写道,镇远主锚“卧在这异国他乡的石台上,仿佛在默默地诉说着当年清朝战败的耻辱,却无人倾听”。
东京,旅顺要塞炮
东京,靖国神社内,有一座“游就馆”。馆名来自《荀子·劝学篇》:“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游就”,是“游必就士”的简称。这让我稍稍有些奇怪。明明是一座战争博物馆,怎么起了这么个文绉绉的名字?馆内的藏品,主要是日军在近代战争中使用过的武器、军用装备和战争资料等,有十万件之多,另外还有五千多张日军的影像。
这里有一件特殊的藏品,是一门大炮,炮口正对着博物馆大门。此炮口径十二厘米,通体漆黑油亮。展示牌上写着:“战利品,清国要塞炮。该大炮由德国克虏伯公司于1885年(明治十八年)制造,由清国将其安放在旅顺港港口要塞,以用来对旅顺进行防御。甲午战争后,该炮保存在位于大阪市辎重兵第四连队的军营(现为国立疗养所近畿中央医院)之中,后于昭和39年6月捐献给靖国神社。大炮的尾部刻有克虏伯公司三轮交叠的标志以及制造的编号。”
参观者喜欢一边阅读展示牌,一边抚摸大炮的炮口。炮口被摸得锃亮。
陈悦对《法制晚报》记者介绍,那门旅顺要塞炮不是陆炮,而是舰炮,很可能是北洋舰队广乙舰的主炮之一。陈悦说,这里边有个故事。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北洋舰队安装了仅有的六门速射炮,广乙舰更换下来的主炮被安置到陆地,成为要塞炮。读者注意到没有?陈悦的话,透露出一个不幸的事实:整个甲午战争期间,北洋舰队只有区区六门速射炮!而日本参加黄海之战的军舰,共有二百四十门大炮,其中多数是速射炮!
可怜的广乙,是北洋舰队第一艘为国捐躯的军舰,早在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时,就受伤搁浅自爆沉没。
现在我们一起重温旅顺军港的历史沧桑。
晚清时节的旅顺军港,由“卖国贼”李鸿章耗时十六年、耗资数千万两银子建造而成,被西方人称作“远东第一军港”。黄遵宪曾写诗赞颂:“海水一泓烟九点,壮哉此地实天险。炮台屹立如虎阙,红衣大将威望俨。”
1894年11月21日 拂 晓,日 本 陆军第二军向旅顺发起总攻。清军守军共一万四千人,仅一天时间,二十多个炮台全部失守。清军死两千多人,日军死四十人,失踪七人。从死亡人数的对比上看,我怎么也弄不清这仗是怎么打的。
11月24日,旅顺战斗的消息在东京广为散布,第二天,日本所有报纸头条都在报道此事,“渤海的咽喉、东洋的要害,世界之大军港被我军魂攻破”。日本全国各地,到处挂着国旗,到处是集会、游行,整个日本陷入狂欢。
没等这狂欢的气氛散去,一缕不祥的阴云就笼罩在日本头上。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纽约世界》率先报道日军在旅顺的大屠杀事件,随后更多媒体跟进,一时之间,日本的国际形象狼狈不堪。
据宗泽亚在专著《清日战争》中披露,旅顺大屠杀事件发生以后,整个清廷上下,竟没人出来为那些冤死的百姓说一句话,哪怕哼哼一声也没有!倒是那些被国人一向当作野蛮人看待的洋人,在遥远的异国,为清朝子民大鸣不平。这是甲午年间非常诡异的一个事件。说句让人寒心的话,那时候的清国统治者,可能并不认为日军屠杀百姓有什么错。
让我们把目光从历史深处收回来,回到游就馆。
《法制晚报》记者提到,他们在参观时看到一个日本人的留言:“日本现在是一个强大也是一个富足的国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成果,是先人拼了命换来的。日本是一个突破了很多灾难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些死去的人保护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日本才有了这样的突破。现在的日本人必须去怀念他们,必须去记住他们所做的事情。现在日本又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的危机,我们不能浪费对前人的思念,我们必须从这种长久的睡眠中苏醒过来。”
与此相对照,一位参观过游就馆的中国人在网上发布感言:“在馆里的观览是悲痛与气愤的,刺刀每展出一次,我都会浑身血涌,仿佛看到了无辜百姓的惨死。在馆外的留言簿上,很多日本人留言,大概(意思)是现在的好生活是先烈换来的之类的。日本的欺骗教育,确实为右翼及军国主义的复辟不断提供土壤。”
《法制晚报》记者还注意到,不少日本人从靖国神社门前经过,会停下脚步,毕恭毕敬地鞠躬,拍两下手,再鞠躬。鞠躬很好理解,日本人爱好这一口嘛,有事没事,都整天躬来躬去。可拍手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拍第一下,代表“人神之间的沟通”,第二下则是表达对神“深切的崇敬”。
我的目光在记者的这段报道上停留很久,然后轻轻叹一口气。
结语
遗落在日本的甲午战争碎片,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在《甲午遗证》的视线内,还有福冈的刘步蟾办公桌、冈山的平远舰炮弹、神奈川的致远舰机关炮、长崎的定远舰舵轮等等。但我不想再说它们了。不想。
审视上文提到的这几枚碎片,不难看出,它们之所以遗落他乡,有些是私人行为导致,如定远馆和镇远主锚,此外都是国家行为导致,如真田山清军墓、定远舰炮弹等。不管是私人行为还是国家行为,里边都凝聚着日本人的“自豪感”。随着时间的流逝,昔日那些“自豪元素”,又逐渐演变成前人对后人的所谓激励。当荒唐变成常态乃至被誉为神迹,令人警省,更令人深思。
最让我心动的一个细节,是在真田山清军墓,日本用国家行为表达了对清军亡灵一定程度的尊重。这个细节让我又一次陷入深思。当然,值得我和我们深思的,不仅仅是这个细节。
在隔岸的碎片之外,还有很多关于甲午战争的人和事,都值得我和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