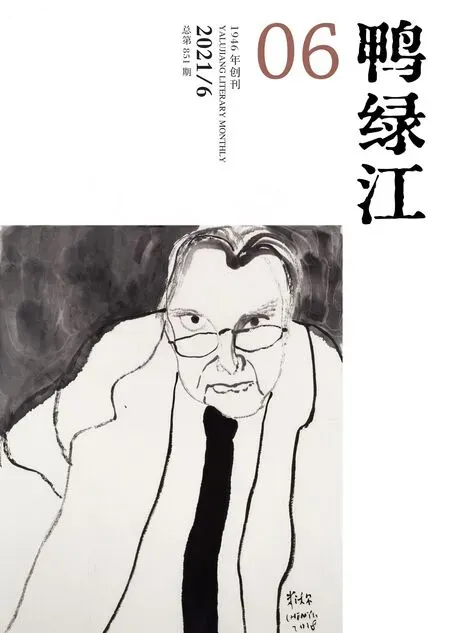战争中的人性探寻与精神超越 (评论)——重读王中才《最后的堑壕》
巫晓燕
军旅小说写作传统在我国由来已久,特别是“十七年文学”时期的红色经典小说,为读者提供了“典型”范式的军旅小说。通常说来,作品中会书写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片段,会引领读者体味高昂的英雄主义气概,并进而抒发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熟知的《红日》《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作品,还为我们呈现了最富有中国精神的英雄形象,如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优秀指挥员沈振新、传奇侦查英雄杨子荣等等。此外,小说中战役场面的恢宏壮阔、战斗描写的惊心动魄、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人物情感的真挚质朴,都构成了军旅小说的“典型”审美特质。但是这种典型审美特质,也为军旅小说的发展带来了局限:创作走向模式化与定向化,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只能表现单一审美效果的境地,军旅小说的生命力、艺术表现力逐渐固化。
1979年,在我国南疆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回想这场战争,我们可能会有陌生感。然而,战争的残酷、家国的荣誉、生命的代价、军人的职责,这些战争的共性特征却并不令人陌生。一度沉寂的军旅小说也因边境保卫战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南线战役为处于历史转折点的军旅小说提供了现实场景,为新时期军旅小说的全面突破提供了可能。事实上,战役打响后,解放军原总政治部、中国文联都以不同方式组织作家奔赴前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批反映南线战争的军旅小说集束出现,达百篇之多。这些作品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十七年文学”的红色经典的审美品格与表达方式,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与英雄主义气质,真切地表现了南线战争中许多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塑造了许多舍生忘死的军人形象,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和催人奋进的感人力量。这些作品较为集中地发表在《解放军文艺》《广西文艺》等刊物上,并逐步推广到各大文学期刊。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南线战争为叙事核心的作品更是精彩纷呈,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军事题材创作的又一个高峰。《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等80年代初期发表的军旅小说可以说已经成为令人无法遗忘的经典,即使在80年代文学复兴的洪流中也是熠熠生辉。正如在军事题材文学评论座谈会上有研究者总结的:“近年来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突破,最主要的表现是对束缚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发展的‘左’的思想和习惯性的条条框框的突破。从表现生活方面有两种扩大、两种深入:从军营扩大到社会,军营生活本身的扩大,深入到军队生活的激流和旋涡,深入到军人的感情领域和内心生活。在表现军事生活的矛盾方面既有胆有识,又有分寸感。在描写英雄人物的问题上,一方面摆脱了 ‘高大全’的模式,另一方面没有‘非英雄化’的倾向,比较稳定。艺术表现的手法和风格也逐渐趋于多样。”
在这样的军事创作热潮中,有一位作家的写作别具一格、独领风骚。他便是凭借《三角梅》(发表于《解放军文艺》1982年第6期)、《最后的堑壕》(发表于《鸭绿江》1984年第11期)两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军旅作家王中才。在同为作家的皮皮眼中,王中才首先是“婉约派”,皮皮认为“也许是由于大量的散文诗创作的影响,他后来转入的小说创作有着极为明显的唯美倾向,如果你不看写作日期,你会以为你在读的是30年代创作的作品,细腻婉转”。而在批评家眼中,王中才的军旅创作则体现了“力度、深度、分寸”的特征,“正是从这里,作家找到了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的这支军队及其成员们‘力’的源泉和支点,那就是当代青年军人那种在保卫祖国的事业中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以及他们身上所处处都能体现出来的由文化知识结构组成的鲜明的时代风采”。兼具诗人与军人气质的王中才,在他的获奖小说《三角梅》中创设了一种军旅小说散文化的写作风格,为80年代军事题材创作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做了最好的注解。他在另一部获奖小说《最后的堑壕》中,呈现出审美意识与精神情感的变化,正如作者本人所说:“军人的责任感,甚至可以说是军人的本能,使我感到婉约之力难以淋漓尽致地写出军人血与火的激烈生活,我渴望在自己的作品中多一些凝重,多一些深沉,多一些刚健。这就需要改变以往的风格。……转变刚刚开始,还要继续变下去。”重读这部作品,我以为《最后的堑壕》除了彰显了作家作为诗人、军人的气质风貌外,还含有哲人的智性思考,正是作品中的思辨性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一种超越意识和理性之美,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军旅小说较为单一的审美倾向。
1
《最后的堑壕》中的英雄形象是复杂的。我们先来看看作品中着墨不多的三连长,他有着传统军旅小说中军人形象的“典型”性格:愤怒时,他“两只大眼像冰雹,放射出逼人的冷气”。作战时,他无比英勇,左臂负伤,不下火线。对战友,他有火一般的热情,可以为其献出生命。他的这种勇敢、豪气,作者虽是简笔勾勒,但却刻画得极为生动。作家笔下的三连长能够打动读者,除了源于他所表现出来的军人的共性气质,还在于三连长的军人形象摒弃了“十七年文学”军事题材创作中对军人形象的绝对化描述,也与作者此前婉约派军旅小说中人物刻画有所不同,不再是《三角梅》《雨巷》《远岸》中充满理想主义气息和诗意风情的军人形象,三连长回归为现实的“人”,有脾气、有个性、有缺点,比如小说里表现了三连长的鲁莽、简单甚至粗暴和猜忌,“三连长当着上级机关的同志不断提起这件事,说我们自己的炮火,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打死自己的英雄,这不能不怀疑赵恂利用手中的权力沽名钓誉……”三连长对于与他同期入伍的赵恂,总是有些不满、有些嫉妒,当赵恂作为他的上级指挥作战时,三连长不仅不配合,反而在战后责怪团长赵恂的决策和判断有误。三连长这样一个鲜活而饱满的军人形象有着真实的“人”的性格逻辑和心态,正如作家王中才多年后的一篇文章中所说:“战士的英勇顽强、有我无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气概,战争文学往往视为英雄主义精神和战争道德的典范,而极少深究其追求生存快感的潜在意识。”这里的“潜在意识”即指应从人的根本问题出发,对生命的存在状态、人格的内在肌理做真实的再现。三连长这个人物虽然不是80年代军旅小说中具有突破性的形象,但是在还原军人形象的“真实性”方面具有独特的意义。
小说中,作为矛盾冲突核心人物的李小毛,是一个有意味的形象。他是贯穿全文的线索式人物。开篇,战士们在战后沉寂的战地寻找着什么,每个人都痛苦、愤怒、焦急,特别是主人公赵恂以及他的下级三连长,两人“目光砰然相撞,互不退让,僵持不下”,读到此,读者深陷在一个个谜团中: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战士们一定是在找寻战友,那么在这个消失的战士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团长赵恂和三连长有着这么大的矛盾?为什么团长赵恂会这么痛苦?接下来,小说由团长赵恂的追忆引出了这个被寻找的战士李小毛。时间回到战前:警卫员李小毛因细致入微地照顾首长起居,深得首长信任。然而这个李小毛确偏偏要“试试首长”,看看首长知不知道在吃中药时要剥掉蜡壳,结果首长将带着蜡壳的中药囫囵吞入肚中。这个行为引发了军官们的争论,小说主人公赵恂认为“他(李小毛)说不定是块将军胚子”,并且发出这样的议论:“我觉得,敢不敢冲下敌人的第一道堑壕,是一个战士起码的标准;敢不敢直接指出首长的失误,却是一个指挥员的起码标准。就像战士冲上第一道堑壕那样,这是走向将军之路的第一道堑壕。”至此,小说不仅引出了李小毛这个有胆量的小战士,还引出了小说中富有象征意味的有关“堑壕”的思考。事实上,纵观全文,赵恂所说的“堑壕”除了具有隐喻意味之外,还成为后文矛盾冲突的焦点,成为小说反思“战争数学”、表现战争残酷性的一个起点,更是为小说的思辨式结尾预设了一个伏笔。
我们回到李小毛的故事,小说里李小毛因赵恂的“举荐”,被首长送到了三连长所在的英雄连,以利于“李小毛锻炼成长”。战争开始了,作家把李小毛作为焦点人物进行表现,而且用侧面表现的手法续写这个人物,李小毛真的成为孤胆英雄,冲上了敌人的“第一道堑壕”,接受了由“战士成为将军”的第一重洗礼,但这也使他成为小说开篇描写的那个“消失的战士”。在作家精巧的艺术构思中,李小毛的成长故事伴随着他的牺牲结束了,他的牺牲无疑是悲壮的,是惨烈的,因为是一个人冲入敌营,没有后援,最后在我方的密集火攻中,连李小毛的遗体也无法找到,只能靠未被炸毁的背在他身上的水壶确定其已经牺牲。无疑,在李小毛身上,汇集着南线战争中诸多战士的英勇故事,他们青春的剪影镌刻在一座座坟茔上,那是由一个个英勇男儿的血肉身躯、一段段悲壮的英雄故事、一张张青春的笑脸凝聚而成的剪影。李小毛的人物形象中饱含着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我想,这源于作家对南线战争的真实感受,也源于作家自身的意志品质和性格特征。作家的友人曾经写道:“听到云南边防前线战事紧张,(张中才)立即会同诗人程步涛,要求到前线去,很快就得到批准……1984年5月去云南边防前线11天,竟写出了一部中篇报告文学、三个短篇小说,其中《雨林中的山群》获昆仑文学奖,《最后的堑壕》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现在他正准备写边防前线生活的一部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这表明,作家是怀着巨大的热忱和丰沛的情感体验来书写南线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人”的,这场战役带给作家的心灵震荡,投射在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上。
2
在讨论《最后的堑壕》这部作品的文本意义之前,我们有必要明确其正身处于80年代的人道主义文学潮流之中,军旅小说是一种特殊的文学题材,但是,特殊并不意味着其排斥那些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命题。相反,由于战争是一种更激烈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会激发作者更深切的人道主义思考。《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啊,索伦河的枪声》等这些20世纪80年代初的重要军旅小说都不同程度地突入人道主义领域,思考战争中人的价值、尊严、生命感和复杂的人性。这些作品在写出属于军事题材的英雄主旨、历史意识之外,更追求灵魂的呐喊、精神的拷问、理性的思辨和生命价值的探索。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有关人道主义主题的军旅小说创作中,也存在着某种“失度”,正如研究者指出的:“这些年来,我们的战争小说(特别是一些描写中越边境战争的小说)之所以出现某些‘失度’或‘失衡’的现象,譬如流露在作品中的那种廉价的人道主义描写,那种不着边际的温情主义色彩,那种脱离了战场实际的抽象而空洞的人性张扬,其原因大都在于小说创造者对于战争理解的单一、片面或肤浅。他们往往以一种幻想的或一厢情愿的眼光来审视战争(或战场生活)的存在景况,以至于忘却了战争是一架残酷而充满了噪声及惯性的机器……”但是,80年代初期成功的军事题材小说创作,都较好地处理了有关人道主义、人性、人情等问题,在表现军人这一特殊群体时,都能够在战争的残酷性与人的复杂性中进行开掘。此外,战争在强化人与环境的冲突、人与自我的矛盾方面,成为重要的叙事要素,往往使得军旅小说比其他题材小说创作产生更为强烈的审美冲击力。
王中才的军旅小说最初的风格是婉约的、诗化的,战争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但是,当他前往云南前线后,他的创作开始发生变化,战争深刻影响了他的叙述风格,从抒情的、理想的、浪漫的叙事基调转向理性的、思辨的、深沉的。《最后的堑壕》正是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作品,显示出作家敏锐地把握生活的能力,以及对于艺术富于个性化的认识与追求,从而实现了小说意义向主体性的回归,使得作品呈现出有关生命价值的诗意探求和悲壮情怀。
小说中的主人公赵恂,是现代军人的典型代表,可谓有勇有谋,部队考核对其评价总是“富有创造性”。作为一个懂得军事战略、具有战争智慧的现代军人,他却没能在战争中跨过“最后的堑壕”——如何在理智与情感中进行抉择的“堑壕”。小说中,赵恂作为团长原本指挥着一场并不难打的战斗,只要他果断下达炮火支援的命令,胜利就势在必得。然而,一道艰难的选择题突然摆在他面前。三连长要求停止炮火支援,只因为一个战士、一个英勇的战士攻入了敌人的堑壕,如果赵恂下达炮火支援的命令,就意味着要把这个英雄“和敌人炸成一堆”!赵恂清楚地明白战争数学的冷酷,他不能因为一个人而牺牲更多人的生命,但是他犹豫了,他犹豫是因为“无力抗拒感情的诱惑”,这个孤胆英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欣赏的、军长亲自派到连队锻炼的、大名鼎鼎的战士——李小毛!炮火支援在“感情的诱惑”下暂缓了,然而……战争终究是残酷的,不存在任何侥幸,五分钟过后,一个早在他预料之中的恶果如期而至,因为他的错误决定,伤亡人数上升到了十八人!为了一个战士,又新增了十八人的伤亡,“在战争的数学中这将是一个不可宽恕的错算”,赵恂作为指挥员,因为“感情用事”,因为短暂地将理性让位于感情,终是没有越过战争中“最后的堑壕”!小说中,赵恂认识到了自己所犯下的致命错误,在他被免职时,内心却刮起“一阵温暖的风”,“眉心的三道竖纹舒展开去”……显然,他愿意为自己错误的决定接受处分。
小说所表现的不仅仅是战争的残酷、赵恂的选择与命运,更重要的是引发读者思索人在战争中的存在状态以及生存困境下人的不确定性和两难境遇,这是对人道主义精神和情怀的深度展现。由此,《最后的堑壕》可以说为军旅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为新时期初人道主义命题提供了精彩的一章。小说以独特的书写角度,涉入当代军人的心灵世界与精神苦痛,这份精神的挣扎是军人的,难道不也喻指了现代人的心灵灼痛吗?赵恂的艰难抉择,虽然是以战争为背景,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人普遍遭遇的情与理的碰撞、灵与肉的冲突以及精神的困境。特别是小说的结尾发人深省。赵恂免职的命令是由军长电话告知的,军长坦陈了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为了平复战士们的愤怒,满足战士的感情需要,因为战士们认为赵恂用自己的炮火打死了自己的英雄!军长向赵恂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和你一样,都无力越过最后一道堑壕。”与此同时,在战争中极端不理智的三连长却因其坚持不能用自己的炮火打死自己的英雄,取得了士兵们的信任,拥有了很高的威信。正如有研究者所说:“这一合情却不合理的现象告诉人们:在现代战争的环境下,战争之法固然为最高之法,但传统的观念、情感的因子、现实的积重,依然钳制着人们,如何跨越情感与理智、传统与现代这一观念的‘堑壕’依然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严峻课题。”
《最后的堑壕》可谓现代人的人情与社会性焦虑的军旅式呈现,小说中的人物面临的困境,有来自自我的心理原因,更有普遍的社会的心理原因,这些多重原因聚焦在人物的选择和性格中,进而扭结成一种内在的矛盾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具有了某种心灵辩证法的意味。正是因为作家富于思辨性的写作与人性深处的叩问,使得小说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引发人们的共鸣,这恐怕是这部作品获得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3
历经40年时间,回望《最后的堑壕》这部作品,我们仍会深深为其所营造的悲凉的凝重的审美氛围打动。在本文最后,简单谈谈这部作品艺术上的探索。
首先,小说注重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的表达。作品开篇就展开了惨烈的战后场面描写,“还原”了战争的原生状态,令人震撼。但作家不是为了描写残酷而写残酷,而是将战后的惨烈场面与主人公赵恂内心巨大的伤痛交融,这样,小说就流露出主观化、体验式的叙事倾向,在战争残酷的“真实”表现中,凝聚了悲壮、凄凉、惊惧等多重情感体验。显然,作家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了,或者说不再按照“十七年文学”的红色经典革命战争小说的“现实主义”来理解了,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在作者笔下,它更是一种审美精神、一种情感体验,现实主义的意义被拓宽了。
其次,小说非常具有艺术表现力。作家利用蒙太奇及记忆闪回的方式来展开情节,形成富有跳跃感、交错感的表现效果。小说以赵恂在战后敌方的堑壕找寻李小毛的遗体开篇,然后追溯这一场特殊的战役,再追溯李小毛走向这场战役的因由和过程,最终以赵恂去祭奠李小毛的坟墓(坟中只有李小毛的水壶)做结,小说构思精巧,突破了传统战争小说的线性写法,叙述角度自由变化,为军旅小说创作提供了不少新写法。
此外,小说的语言很有感染力。作家之前作为散文家,语言充满诗情和灵动之美,在他的以婉约风格著称的军旅小说《三角梅》中,他以梦幻的、典雅的、优美的语言来创设人与景、情与境的契合与交融,处处蕴含着悠长而婉转的抒情风格。在《最后的堑壕》中,作家的语言是有力的、厚重的,强悍的,但仍然充满感情,只不过这感情悲壮而豪迈。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寓深层的象征意蕴于战争的表象之上,无论是李小毛冲进去的第一道堑壕,还是主人公赵恂与军长难以跨越的最后的堑壕,都具有象征意味,这些存在于战场的堑壕,总会令人想到现代人面临的无数冷酷的“堑壕”,小说在这种富有象征性的描述中,呼应了现实中不可回避的矛盾和紧张关系,小说的美学张力和精神意义也在重重关系中得以彰显。
从《三角梅》到《最后的堑壕》,作家王中才为当代军旅小说提供了写作的多种可能性。一路走来,他不断超越军旅小说的题材疆域,在作品中注入时代与人性、社会与自我的双重思考,丰盈了作品的精神容量。其创作中特有的抒情基调、心理深度与艺术探索,都可以视为80年代初期文学最美的收获。在《最后的堑壕》之后,王中才又创作另一部力作《黑马》,小说以更为平静、节制的情感进行叙事,并因多重的意义指向以及复杂的象征隐喻,具有了更深邃的美学价值。回顾王中才的军旅小说创作之旅,深感80年代作家艺术创作的真诚与执着,正如王中才在一篇人物小传中所写:“君不知,爱英贤,易也:写英贤,难也!”
注释:
①平纪.军事题材文学评论座谈会在京召开.文学评论.1983年第4期,第142页。
②皮皮.王中才印象记.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第123页。
③黄国柱.力度·深度·分寸——从《黑马》看王中才小说审美品格的变异.山东文学.1985年第12期,第75页。
④王中才.错杂弹.小说选刊.1985年第8期,第144页。
⑤王中才.最后的堑壕.鸭绿江.1984年第11期。以下引用原文部分出处相同,不另做注释。
⑥王中才.战争文学和生存意识——关于战争心态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3期,第74页。
⑦胡世宗.他向往天涯——王中才印象.山东文学.1985年第8期,第51页。
⑧周政保.战争小说的审美与寓意构造.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第106页。
⑨陈思广.20世纪80——90年代战争小说人性探索历程透视.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41页。
⑩王中才.张正隆其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3期,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