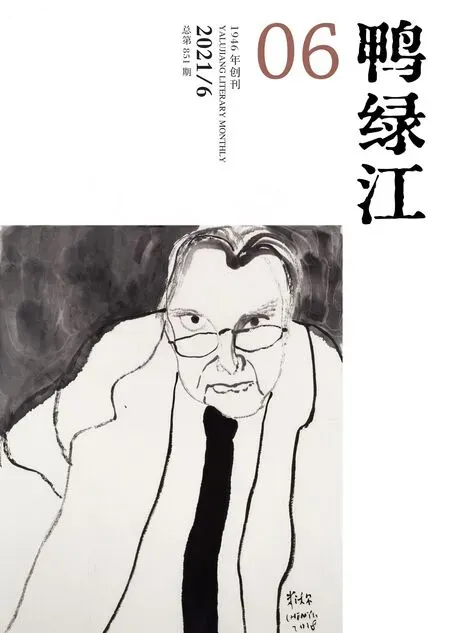柳沄:“像风那样随便”
丁 燕
谈论柳沄的诗歌,于我可能是危险的。我和诗人从未谋面,素不相识,仅凭数十首短诗和一个简历便放言评骘,无异于高空走钢丝绳。没有背景材料,没有注解说明,这就好像,走进一间屋子,除开四壁挂着的一幅幅画作外,再无任何抓手可为倚凭。所以,写在这几句话之后的所有文字,都是我基于这些短诗而生发的想象,若与事实不符,若太过想当然和不靠谱,还请诗人及读者见谅。而我之所以敢斗胆开启这次评论之旅,又是因为在我看来,一个写作者真正牢固和有效的凭证,除了人生经历,只应该是也只能是他的作品,甚至,作品比经历更靠得住。事实上,诗歌就是诗人的精神自传,一首首诗歌就是一把把钥匙,只要使用得当,唯有它才能打开诗人的心门。
从简历中获悉,柳沄出生于1958年,然而,在他的诗作中,我却没有嗅闻到朦胧诗的味道,而中国当代的诗歌现实是,即使像我这样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在诗歌写作的初始阶段,也免不了为北岛舒婷们所吸引影响。柳沄出生并工作在东北,且现在依旧定居那里,然而,他的诗却没有明显的东北特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高粱、大豆、金灿灿的玉米、一望无际的雪原和辽阔无垠的黑土地……没有,这些符号,至少从未出现在我所读到的他自己较为认可的数十首诗中。20世纪90年代,发轫于新疆、甘肃和青海等地的“新边塞诗”,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边疆诗人创作出来的那批作品中充斥着大漠、戈壁、红柳和拓荒者的意象,然而,同样身处边地的柳沄,其创作似乎也未受影响。柳沄出生于军营,且自己还曾应征入伍,然而,出现在他诗歌中的词语,也没有明显的军营元素。我们知道,即使舒婷,刚出道时,也还有过一个厦门女工的身份。而柳沄,却从不以任何方式强调自己的身份——他既不是军旅诗人,也不是地域诗人,还不是流派诗人……一系列的“然而”,能把这一切外在的包装都砍削得干干净净,让他只作为诗人而独立存在。
柳沄曾创作过一首长诗,名曰《虚构一把匕首》,但我无缘阅读,故而不敢妄加评判,只能为这耐我寻味的诗题而怦然心动一下并提及一笔。我以为,柳沄的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玄学诗,即由某个场景或念头诱发而出的哲学思考——《景致》《无题》《这里》等都属于这类作品;另一类是意象诗,即以某个具体的意象为核心点而展开联想——《瓷器》《梅》《飞天》《废园》《杨树林里的花楸树》《想栽一棵树》等均属此类。在我看来,柳沄的意象诗在美学高度上似乎更甚于他的玄学诗。也许,这是因为,意象是基于一种实实在在的客体而生成的,而由这个客体引发出来的遐思是具体的,有边界的,不像玄学诗那样容易天马行空漫天飞舞。显然,柳沄是个有才华的诗人,他总是高举智慧之光搜寻客体,而他的视线是敏感和细腻的,又总能细致地照亮客体的多个棱角。这个照亮的过程,就是他铺陈诗歌的过程。他不仅能很好地把握分寸,还能因深思而为读者带来意外的惊喜。
为了破解柳沄的诗歌,我找到了两件武器:一件是“不一样”;另一件是“像风那样随便”。“不一样”这三个字,也许是柳沄诗歌的核心词汇。在他的这些短诗中,能看到他为寻找各种“不一样”所做出的各种努力。这三个字有力、直接而坦白,像一个杠杆,能撬动起整个词语世界。“像风那样随便”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诗人念兹在兹的大美境界,也是他对诗歌乃至人生的终极追求。这两者互为因果——正因为有了“不一样”,才能诞生出“像风那样随便”。
和海子喜欢“麦子”“骨头”之类的词语一样,柳沄也有独属于自己的词汇表,譬如“落日”“天空”“树林”“风”“石头”。然而,他最喜欢的还是“不一样”。这个词就像压舱石,沉甸甸地搁在舱中,让他的诗歌之船变得沉稳。“不一样”的对面是“一样”:一样的人生,一样的思维方式,一样的喜怒哀乐——由此可见,柳沄是反叛的,他不仅反叛既定的规范,还反叛千人一面的中庸。但他又不是普通人的对立面,而是作为普通人的一分子,去与普通人共同构筑一座普适的大厦。他试图打破陈词滥调,捣毁概念框架,让词语回到原点,让事物裸出根本。在那个理想的世界里,一切都将脱胎换骨般地得到新生。
茂密的杨树林里
生长着一棵
跟杨树不一样的树
不但叶子不一样
枝条不一样;甚至
连摇摆的姿势
也有些不一样
——《杨树林里的花楸树》
一只麻雀飞过的天空
与一群麻雀飞过的天空
是一样的
一群斑头雁飞过的天空
与一群丹顶鹤飞过的天空
是一样的
甚至乌鸦飞过的天空
与苍鹰飞过的天空
也是一样的
但我仰望的天空
与鸟儿飞过的天空
肯定不一样
——《天空》
雨落在寂静的院子里
院子里的车棚、石凳,以及那只
反扣在墙根下的铝盆
让一样的雨,发出
不一样的声音
——《落在院子里的雨》
山里的石头真多啊
跟城里的人一样多
高的和矮的
坐着的和站着的
跟人一样多的石头
跟人根本不一样
它们沉默了那么久
却仍在沉默
——《山里的石头》
这里是天堂
是让心肠不一样的人
一样安静的地方
——《这里》
“像风那样随便”,是诗人塑造出来的一种状态,因了这种状态,诗人和常人有了差异——他是单独的、个体的、敏感的和倔强的。而此刻的“随便”,又并非通常语态中所指涉的那个“不随便”的反义词,相反,这个词蕴藏了很深的韵味。像“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像“此身安处是吾乡”,不正是诗人王维与苏东坡的“随便”之态吗?在风一样自由的随便的对面,是纪律、窠臼、规则、划一,是人类为自己建造起来的各种藩篱各种囚笼。无疑,作为从小生活在军营且有过军旅生涯的柳沄,太渴望从这些刻板的日常中突围,去营造独属于自己的那种状态了。
首先,柳沄是通过特殊的语言来塑造“风一样”的状态的。柳沄像贾岛,对词语是精心雕琢的,但这种雕琢又不牵强附会,而充满了智慧。他的用词独树一帜,既不像学院派那样借鉴西方,充满了翻译体的生涩,也没有过度过分地口语化,以致下坠到清浅的境地。他的诗歌多为短句,似箴言般紧致,一环套一环,只凭借内部的力量向前推动,并无太多繁复的描述。他的诗句一点也不张扬不花哨,但却不乏切金断玉之警言隽语。他的诗既不属于高蹈慷慨的振臂一呼,也不属于沉迷自我的低吟浅唱,而是属于一位收放得体的谦谦君子,言辞文雅,仪态中正,行为冷静。在这个过程中,他极喜欢的艺术手法是“顶真”——用上一句出现过的词语,作为启动下一句的开关,借此去获得一种回旋往复的音律之美。这种手法在西方被称为“重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耶利内克在《钢琴教师》中将这种手法用到了极致。但我想,创作诗歌时的柳沄,倒未必想到过耶利内克。
雨停了。风还在吹
一些事物悄悄离开
另一些事物
继续摇晃
秋天的风
像秋天那样凉
太阳瞧着风中的花朵
花朵们瞧着
啪嗒啪嗒掉落的花瓣
天空因此更空
比起一条拉链
一座又长又窄的拱桥
雨后的彩虹,似乎
更适合用来裹脚
一位脚步细碎的老妪
恰好经过这里。她的脸
像旧时代的疤痕
那么深远
当她
被一道下坡路带走
夕阳在一辆漏油的公交车上
找到了更多的轮子
——《景致》
这首名为《景致》的诗歌,极具“柳沄风格”。“秋天的风/像秋天那样凉”“太阳们瞧着风中的花朵,花朵们瞧着/吧嗒吧嗒掉落的花瓣”——前面出现的“秋天”和“花朵”,是后面相同词汇的引子,这两个相同的词汇表达的含义却不同:在递进中蕴藏着意外的拐弯,充满了诗人的遐思,也显现了诗人对于词语的超强的敏感度。到了“天空因此更空”时,最后一个“空”字,已有了一锤定音之感。最后,“当她/被一道下坡路带走”中的“下坡路”,既是物理意义上的一段路,也隐喻着人生的最后阶段,起到了双关效果。整首诗歌,用词朴素而内敛,情感尖锐,技艺超群。
这里是墓园
是睡着了,就
不想再醒来的地方
这里是墓园
是忽高忽低的林涛声
与忽低忽高的鼾声
相互混淆,甚至
相互替代的地方
是时间停下来的地方
苍松与翠柏
不得不肃立的地方
是额头上的皱纹与松柏的年轮
缠绕在一起的地方
在这里,阳光的亮度
始终无法超过
它对墓碑的照耀
而墓碑上的名字
刚刚被一阵雨声提起
——《这里》
《这里》有一种谣曲的感觉,像儿歌般天真,有股透明的力量。“这里是墓园……这里是墓园……”这样的重复,并不让读者感觉惊悚,反而有种意外的笃定,像在忙乱中突然安静下来,开始思考人生。而“林涛声”加“鼾声”“相互混淆”后,将会出现怎样的奇景呢?哦,是“额头上的皱纹与松柏的年轮”“在一起”“缠绕”!然后,最终——“在这里,阳光的亮度/始终无法超过/它对墓碑的照耀”,这一句实在是水到渠成,发人深省。“时间停下来的地方”“不得不肃立的地方”——通过“地方”这个词的反复出现,勾勒出一个又一个场景,让整首诗像一条手工编织的围巾,有着明确的经线和纬线,既实实在在,又真真切切,而疼痛感全都密匝匝地糅在了词语和词语的经纬之间。
其次,柳沄试图用一种“孤悬”的感觉来塑造“像风那样随便”。在他的诗歌中,始终徘徊着一种“孤悬”之感,这个发现令我大为惊讶。多数情况下,只有身处异乡的人(如我这样从新疆南迁到广东),才会对这种感受尤为深刻,然而在柳沄的诗歌里,总能渗泄出“孤悬”之感。虽然他也提及“妻子、女儿、不大的房子”,但那种和现实的格格不入,那种一心想要超越的心态,造就出的仍然是诗人“孤悬”的决绝。一个人能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找到这种感觉,真是让读者触目惊心。这种“孤悬”之感,也许不少人都有体会,但是到了柳沄这里,却被他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他总能将那种痛苦情绪精细化和完整化,最终再将那个消化疼痛的过程呈现出来。借此,一个再生的、复活的世界出现了——这是诗人用词语,用血和泪打造出来的新世界。
和大多数中国诗人迷恋修辞不同,柳沄似乎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简约。他不拘泥于传统的表达手段,而总是努力地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在创作方法上,他采用的是非传统的混合、叠加、错位、象征和隐喻,以期达到反权威、零散化、拼贴化的审美效果。在柳沄的诗歌中,人从自己的身份和家乡中抽离出来,只是一个纯粹的人,像一缕风或一朵云,并不固定在某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上。因为,柳沄想要表达的情感,是一种类同于蒸馏水的物质——经过了各种提纯,只剩下最本质和最原始的元素。故而,柳沄的诗歌主题更多地涉及死亡、自然、和时间。他敏锐地观察生活,面对面地凝视疼痛。当他试图表现刺心之痛时,选择的不是火辣辣的、繁复的表达方式,而是极简、冷峻,乃至冷淡的表达方式。他试图将强烈的情绪折叠在节制的语言中,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呈现出来。
诗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和他所身处的整个时代是分不开的。当下,整个中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转型至工业社会的大变革中。此种时空下的人,早已不再是自然之子,而成为工厂中的齿轮螺丝。乡土诗人们脚踩田野,心怀故乡,强调的是大自然和信仰。而身处转型期的诗人,则要面对工业和科技的反噬。乡土诗人更喜欢描述眼睛所看到的外部世界,而转型期的诗人则更愿意描述内心世界。一个向外,一个向内;一个追求宏大,一个看重自省。柳沄的诗歌小巧而精致,既有传统乡土诗歌的影子,但又从乡土之中脱胎出来,蕴藏了现代经验,甚至具备了后现代的风格。这种风格,恰好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内心嬗变。
对柳沄来说,诗歌肯定是至为重要的,或许还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不仅是他情绪发泄的一个出口,还是他诉诸生存、证明存在的方式。他把自己的痛苦、挣扎、顿悟和渴望写在纸上,让自己的生命充满独立意识。作为特立独行的人,作为勤于思考的人,柳沄很像一只不惧疲惫无视孤独的顽强飞鸟,心无旁骛地在黑夜里寻找光明。如此,柳沄便没有当然也不会成为诗歌的功利主义者——他从未大红大紫过,从未被主流诗坛完全接纳过,从未享受过“诗歌福利”。一方面,他并不想成为时代的传声筒,但这并不表明他不思考时代,在他的诗歌中,对于时代的思考,也像他对于生命、死亡、时间和自然的思索那样随处可见。同时,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一个宣扬自我的诗人,并不一味地彰显私人化的感受。所以,他的作品,便仿佛被卡在了中间地带——既不是典型的宏大史诗,也不是彻底的自我吟诵。他像一个局外人,偏安一隅,孑然一身地观察和写作。然而,这种寂寞、冷峻却自由的状态,难道不是诗人自己认可的状态吗?在《瓷器》中,他这样写道:
因此就不难明白
为什么瓷器宁肯粉身碎骨
而拒绝腐烂
是的,瓷器太高贵了
反而不堪一击
在瓷器跌落的地方
遍地都是呻吟和牙齿
瓷器粉碎时
其愤怒是锋利的
它逼迫我的伤口
重新绽开
当然,这些都只是我想象中的柳沄。可这样去想象一位出色的诗人,实在是件愉快美妙的事情,如此,对于真实生活中的柳沄我是否继续一无所知,也就变得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