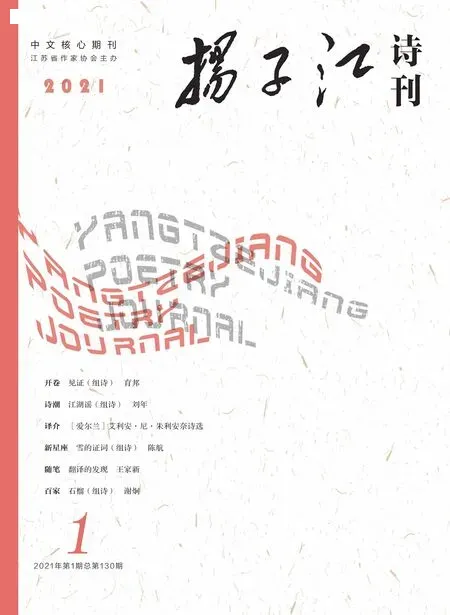翻译的发现
——一位美国诗人关于白居易的书写及其翻译
王家新
十年前的一个初春,我应邀在意大利古老的大学城博洛尼亚讲学。讲座和朗诵完后,学生们的欢迎声还未停,一位当地的诗人即上前来问我为什么只讲到李白、杜甫而没有提到白居易,因为蒙塔莱特别推崇他的诗。“是吗?”我笑着问他。这我可没有想到。
我没有提到白居易,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我觉得他的大部分诗过于“平易”,不合我们这一代经过了现代主义艺术洗礼的诗人的志趣。记得七八年前我们访问白居易在洛阳龙门石窟斜对面的墓园时,一位诗人朋友甚至还不愿在墓碑前合影:“我认为我的诗就是比他的写得好!”
“是吗?”我又笑了,“也许他有些诗没有你写得好,但他那些写得好的诗呢?”
我这样说,是指《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原上草送别》《卖炭翁》等名篇。我对白居易的了解也不过如此。不管怎么说,我们自身中有很多东西都有碍于我们去发现这样一位诗人。
对这种疏忽,直到我读到由王佐良先生翻译的美国诗人詹姆斯·赖特关于白居易的一首诗时才有所警觉。作为一个从西南联大出来的诗人和杰出译者,王佐良对英美现代诗的译介、尤其是对受到中国古典诗歌和超现实主义影响的美国“深度意象”诗人罗伯特·勃莱、詹姆斯·赖特的“发现性翻译”,一直使我和许多中国诗人受惠。现在,我们来看他翻译的赖特这首《冬末,越过泥潭,想到了古中国的一个地方官》:
白居易,落发纷纷的老政客,
何苦徒劳呢?
我想起你
惴惴不安地进入长江三峡,
纤夫拉着你的船逆流而上,
送你去忠州城里,
混一个什么官差使。
我猜想,你到达时,
天已黑了。
但现在是一九六〇年,又快到春天了。
明尼阿波利斯城的大石头,
造成了我独有的沉沉暮色,
也有纤绳和激流。
元稹在哪里?你的好友在哪里?
大海在哪里?那曾经溶化了整个中西部的
无边寂寞的大海?明尼阿波利斯又在哪里?
我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那株可怕的
经冬而愈黑的大橡树。
你在山那边找到孤零人的城市了吗?
还是紧握着那条磨损了的纤绳的一头,
一千年都没有松手?
这样的诗,一读就让人难忘,让我们不仅对原诗和原诗人,也对如此优异的翻译和译者充满了感激。为此,我甚至还找来了原诗对照阅读。原诗题目很长,带有某种叙述和交待性,本身就很像是一些中国古诗的诗题。诗前引诗,王佐良未译,如译出来就是:“生于恶魔的日子,又新经历了一场惨败,我怎能向命运要求恩惠?——(白居易)写于公元819年”。
不过,纵然如此,我还是惊讶于王佐良对诗本身那高度洗练而又富有创造性的翻译。在谈到对赖特诗作的翻译时,王先生自己曾说:“我的译文尽力保持这些令人惊奇的比喻,即磨损了的绳子和怒放的花朵”(王佐良《论诗的翻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4页)。不仅是令人惊奇的比喻,译文全篇都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语言的刺激:“落发纷纷的老政客”“何苦徒劳呢?”“混一个什么官差使”,等等,这种洗练的、活生生的口语与“那株可怕的/经冬而愈黑的大橡树”“明尼阿波利斯城的大石头,/造成了我独有的沉沉暮色”这类意象相结合,使全篇的译文有了一种独具的张力和味道。
王佐良之所以翻译得好,在我看来,更在于他对“语感”的敏感和出色把握,“作为一个译者,我总觉得有一件事忽略不得,即原文的口气”(《论诗的翻译》,第66页)。在老一代翻译家中,很少有人关注诗歌的语感、口气和音调问题,但是我们来看王佐良的翻译:“何苦徒劳呢?”一句充满同情心的劝慰,一下子为全篇定了调!
正是以这样的语调,一个译者有了翻译中最重要的前提:“理解之同情”。而这也正是另一位中国古典诗歌杰出的译者、美国诗人雷克思洛斯(王红公)对翻译的主要看法,在一篇《诗人作为译者》的讲演中他声称:“把诗歌译成诗歌是一种饱含同情的行为——以一个人自己来体认另一个人,以自己的言说来传递他的声音。”他之所以一再推崇美国诗人、中国古诗的译者宾纳,是因为宾纳所译的元稹写给亡妻的《遣悲怀》“是最好的美国诗歌之一。这首诗传达出了宾纳对原作者写作心境的强烈体认,这种体认感压倒了一切”。
在王佐良那里,在赖特那里,我们都可以真切地感到这种发自生命内里的“同情”和“体认”,以及由此产生的感人的抒情力量(“元稹在哪里?你的好友在哪里?”)“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人们往往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但正是以这样的“同情”和“体认”,自我进入了他者,生命织进了彼此,过去与现在相逢,千年前那条“磨损了的纤绳”又被握在了今人的手上!
这也就是一位美国当代诗人何以被中国古典诗歌和白居易所吸引,显然,他从中体认到的,是作为诗人的共同命运。他所发现的,不仅是一个闲适的白居易,也是一个身处逆境的白居易。那么,他读到的,是哪些白居易诗的英译?他又是在什么背景下写这首诗的呢?
从赖特这首诗来看,诗中描述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逆江而上、到忠州(今重庆忠县)赴任的情景。这就需要我们了解一下。白居易(772—846),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贞元进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藩镇势力在长安公然刺死宰相武元衡,白居易上表吁请严缉凶手,这被视为“擅越职分”;而且,白居易平素多作讽喻诗,也令朝中权贵不悦,因而被贬为江州(现江西九江)司马。司马为刺史的助手,属于变相发配。对他被贬后的抑郁心情,我们完全可以从他在江州所作的著名歌行体长诗《琵琶行》中体会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看上去似乎是“时来运转”,白居易奉诏由江州司马任忠州刺史,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升迁”。虽然作为“远郡”的忠州(现重庆忠县),地处偏僻荒蛮山区,难有作为,但他还有什么可选择?“忠州好恶何须问,鸟得辞笼不择林。”(《除忠州寄谢崔相公》)
白居易的一些重要诗篇,包括赖特所读到的,都是在由江州沿江而上赴忠州的旅途中写下的。此行重要,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一路陪同。途中,他们还意外地与元稹在西陵峡相遇(宜昌附近的西陵峡现存有“三游洞”)。一路“一千三百里”,沿途的名胜古迹,一个个先贤浮现出面孔,尤其是凶险艰辛的三峡水路,使他经历的宦海浮沉、人生荣辱、困厄乖舛的命运一一再现,成为了他的“存在的地形学”。他写下的一系列诗篇,也都带上了他的身世之感和前所未有的力度,如《初入峡有感》:
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岸间,阔狭容一苇。瞿塘呀直泻,滟滪屹中峙。未夜黑岩昏,无风白浪起。大石如刀剑,小石如牙齿。一步不可行,况千三百里!苒篛竹蔑篙,欹危楫师趾。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常闻仗忠信,蛮貊可行矣。自古漂沉人,岂尽非君子。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常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
我不能确定赖特读了白居易哪些诗的译文,就引诗“生于恶魔的日子,又新经历了一场惨败,我怎能向命运要求恩惠”来看,很可能就是该诗最后四句的意译!
我之所以全文引出白居易这首诗,不仅因为它是赖特所依照的背景,也因为我刚刚从奉节归来,我真是感到它写得真切刻骨。而白居易写了《初入峡有感》这首力作还嫌不够,继而又作有《夜入瞿塘峡》一诗。李白的《朝发白帝城》被称为“天下第一快诗”,那是他的天才和遇赦后狂喜心情的写照,实际上千里江陵是不可能“一日还”的。对一路跋涉、战战兢兢的诗人来说,由初入峡到最后“夜入瞿塘峡”,他才得以感受到命运的全部威力。瞿塘峡为三峡中最西边、最险要的一个峡,那也是杜甫所说的“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长江二首》)、“险过百牢关”(《夔州歌十绝句》)之所在:
瞿塘天下险,夜上信难哉!
岸似双屏合,天如匹帛开。
逆风惊浪起,拔篙暗船来。
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
瞿塘天下险,何况是在夜里逆水而上!“岸似双屏合,天如匹帛开”,两岸山崖在夜色中像屏风一样向内合拢和挤压,接下来一个“开”字,又在遮天蔽日之中透出一线光亮,它同时也更加反衬出这峡中的漆黑和莫测。这一开一阖、充满明暗对比的一联,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但我本人更惊异于接下来的“逆风惊浪起,拔篙暗船来”。“拔篙暗船来”堪称是全诗最为惊人的一笔。我不由得想起六年前我在南京陪两位美国诗人夜访扬子江的经历,那时我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幽灵船 ——给哈斯和布伦达,纪念我们的一次访问
南京城外
夜色中的扬子江
黑沉沉的江面上
一艘接一艘驳船驶过
(是一些运沙船吗)
没有灯光
没有马达的突突声
我们都不说话
也说不出话
好像是李白他们知道我们来了
一艘艘幽灵船从我们面前无声地驶过
在那个漆黑的细雨夜,眼望着一艘艘幽灵船从我们面前寂静无声地驶过,甚至连因江边路滑差一点跌溜进江里的诗人马铃薯兄弟也不吱声了。
不过瞿塘峡里的“暗船来”更令人心惊,它不仅恰切地传达出舟行峡中的诡异氛围,也暗示了命运的明枪暗箭。据传民间也有一种迷信习俗,凡船行至险处,皆保持静默和敬畏,“瞿塘滩上有神庙,尤至灵验。刺史二千石经过,皆不得鸣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触石有声,乃以布裹篙足”。而这是为什么?怕惊动水底的神龙怪兽?
因而诗人最后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古来多少民歌作者、舟子和诗人都曾咏叹过这个巨兽般的“滟滪堆”!它立于两岸逼仄、涡流湍急的瞿塘峡口中间,成为了多少过往船楫的生死关和葬身之地!这里顺带说一声,因为有碍航道,滟滪堆已于1959年被炸掉,但是,命运之凶险和诡异,从此就被消除了吗?也许,它潜藏得更深了。
这就是白居易的三峡之旅,一段逆流艰辛而上的人生之旅的真实记录。它成为诗人生平和创作的一次重要转折,在赖特这样的诗人看来,它也成为了人的命运的更深刻的写照。而我本人,因为赖特的诗,也因为白居易的这些三峡诗,更真切地触及到一位诗人的脉搏和心跳,也更真切地感受到白居易那种“言直而切”“用常得奇”的大家风格。
不管怎么说,我们得感谢翻译的发现和翻译为我们提供的另一重视角。一位美国诗人关于白居易的书写和王佐良的优异翻译,不仅促使我们重新发现传统,它们其实也重塑了中国古典诗人的形象,并使我们在今天得以审视自身。他们的书写和翻译,不同于一般的文化猎奇和描摹,而是在同情中有审视,在追怀中有对话,比如诗的一开头:“What's the use? ”(直译为“这有什么用呢?”)赖特就是这样以一位西方诗人的个人视角来看志在儒家的“济世”却又苦于在仕途中挣扎的中国古诗人的,而王佐良的翻译“何苦徒劳呢?”又平添了一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苦涩,至于接下来的“混一个什么官差使”,这原诗字面上没有的“混一个”,不仅有些无奈,也显示了对权力和历史的某种超越。
但纵然如此,他们的书写和翻译都深深体现了上文所说的“理解之同情”。《冬末,越过泥潭,想到了古中国的一个地方官》,王佐良把原诗的“Puddle”(“水洼”)译为“泥潭”,显然意在强化诗人处境的艰难;而到了第一节的末尾“我猜想,你到达时,/天已黑了”又显现了一个重要时刻:奉诏赴任的诗人迎来的不是升迁的荣耀,而是人的命运的真正显现。作为一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诗人,赖特不仅把投向古中国的视线拉回到自身,从事一种蒙太奇式的并置和切换,更重要的,是从一个更大的时间和宇宙的超越性视角来反观人的存在及其悲剧性(为此他还给了一个新的身份“isolated men”,王佐良译为“孤零人”),由此来书写世事沧桑和命运的力量。最后,这一切都化为了“千年一问”:
你在山那边找到孤零人的城市了吗?
还是紧握着那条磨损了的纤绳的一头,
一千年都没有松手?
这种询问是当下的,也是超越时空的。一切都化为了一种共同的恒久的命运。王佐良的翻译也真是好:“一千年都没有松手”,他把原诗的“握着”(“holding”)译为“没有松手”,并且把它放在了全诗的最后!
也正是这样的书写和翻译,让我们对一切都要刮目相看了。它刷新了我们的眼光,也激活了我们的读解。的确,一切正如美国诗人罗伯特·克里利所说:“我们将在语言中沉睡,如果语言不用它的陌生性来唤醒我们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