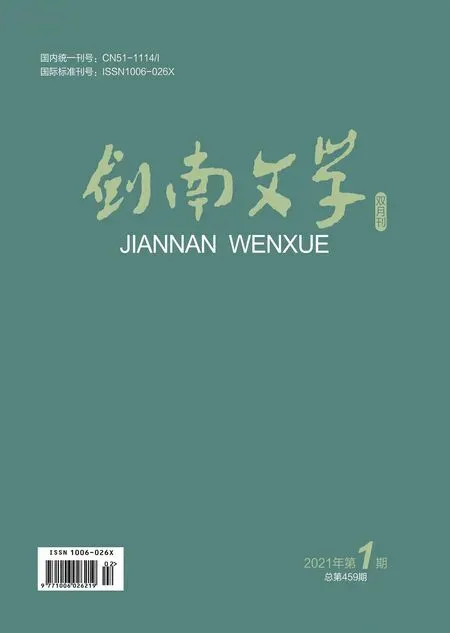山河卷曲,沉入细胞(组诗)
□陈维锦
见山
群山移师我的经验
我模仿聂鲁达进行拆分
抒情的植被
因海拔而丰厚或贫瘠
高耸与低洼的巨大落差
传来瀑布的淙淙声
水雾让周围花草逼真
当我们到达山顶
风景与山腰多么不同
弯曲在细胞里的忧虑
突然被林立巨石
和绕树三匝的风拉直
我撞见了真理
也撞见了吾师
寺庙
通往山中寺庙的路
有一段落满银杏叶子
有一段落满厚朴叶子
有一段落满青杠树叶子
余下的一大段
落满神的影子
远望
在万籁俱寂中
总有什么伸展出去
及至天边又随鸟群归来
它们太久了
熟悉了灵魂的弯曲
和身体的衰微
但偶尔,那鸟群中的一只
总会逆风而行
它们太久了
以致如此密集
唯有古老的时间
才能孵化新鲜的露珠
(当我照耀,身后万物无垠)
“没有谁可以落进去
也没有谁能干净地走掉”
当我再次辨认红字碑
那不知年岁不问东西的花草
正腐蚀着坚硬
野山楂
植物访问我如同侵袭
无论牵绊还是阻挡
都是消极的指认
我用手杖剥开它的茂密
那细微的魂灵穿过我
在我的手指留下多处血珠
它们带出了我身体的潮湿
野山楂吞进了我的身体
“像一次酸楚的恋爱”
它红色的绒毛是温良的隐喻
换一个角度看
我们要的就是不确定的事物
我们不像自己太久了
最消极的指认也让人心惊
我是更大的我更多的我更摇晃的我
而野山楂,也不只是野山楂
石头
我身体里的石头叮咚作响
它们似乎是要迎合树叶上的水滴
成全“水滴石穿”这个成语
如你所闻
山涧放大了群山的容量
群山从近至远得到休憩
悲情的西西弗斯
也被拐点支撑
我甚至不敢停下
“我和非我有细小的缝隙”
因为露珠殷勤
它丝质的长度把我的头脚串在一起
仿佛我真是一个完整之人
可以作为群山之间的那个小数点
成全它们繁复的结构和起伏的诗意
岩洞
寻找去岁的岩洞用完了余下的时间
它粘在我脚上如莲花
当我把脚伸进水里
一群特别小的鱼儿围了过来
它们也需要精神食粮?
可我打不开自己了
我的简陋与光滑无法承载更多信息
我也没法揭开屋外黄连的身世
只有随着溪水绕圈
把植物们编织得密密麻麻的
我甚至无法看穿松散的山体
正波涛般送我到达山脊
那里可远观过去或未来的命运
倘若不计较厚薄远近
“松鼠也有跳得高的跳得低的”
没有谁可以把命运颠倒
一颗松果砸中脑门
无法悟出万有引力
苔藓
如毯的苔藓
从乌桕树下漫进来了
如梦中的铜钱越来越多
假如我们舍得进入记忆仓库的第三层
进入书本泛黄的页码
群山应该会把我们荡起来
荡开我们与万物的距离
假如我们一直甘于与细节为伍
那么作为磁场
将无处不在又无处存在
我采了一些苔藓抛向空中
仿佛有气流从敞开的漏洞流出
我多么渺小啊
竟不能阻止微小的伤害
不能区分空旷中那甜绵的柔软
有多少是地气与光线融合的雾气
有多少只是我们内心的影子
我接住一些
在空中的短时间
它们竟如同获得先知的授意
生长出自己的思想
“我将住在那里,光安静的内部! ”
我已停止抒情有些时候了
而编织叙事的花环
需要我再次用到柔软的针线
沼泽
在沼泽的边沿
天空深得令人恐惧
时间抱着我落了进去
在上岸之前
我先捞起了时间
虚无的影子划着小船
它轻轻地晃动
惊走了我的半个人间
在我的破碎上
一些叶子无法沉沦
一些叶子无法起身
露珠
仿佛有什么提着我,穿过我
使我如同年轻时的理想大而无用
我并不比一只山鸠知道得更多
即使藏起自己比藏起粮食更重要
露珠照出我的虚胖
“那一直是自我的认知”
是不是可以这样比喻
我的眼睛需要装满群山的影子
才能通往灵魂的暗处
万物皆有两个部分
指向身体的沉重和指向精神的超然
“你需要沉默清洗嘤嘤嗡嗡的可笑”
当我闭上眼睛,我是多么丰富!
万物我们十知一二
山外之山也许不过虚无
群山跟了我很远的路
终于消失在文字尽头
这沉默的傲慢
也许可以解释通灵与量子纠缠的未知
“某一天,我在这里打上的记号
远没有这里打在我身上的记号丰富”
覆盆子
我吞下蓝色的覆盆子
吞下黄色的覆盆子
它们在我体内兵分两路
黄色的喜悦,蓝色的忧郁
而这分割,正是左边山坳的光亮
和右边山坳的阴暗对比
那无处不在的
是初雪咀嚼万物的声音
我的呼吸在大片的直线上打结
我依然胆怯
作为万物的一种
它若穿越我
会不会留下空洞
野花
我采了很多野菊花
这是我最能把握的真实
它们在我的背包里蠕动并私语
由于声音太小
我没能听懂它们交流的美与实用
我喝下它们
直到繁星从我胃里升起
我眼睛清亮
掌握了内外接应的技能
什么才是花最好的命运?
是开在山中人未识
还是遭遇眼睛并相互治愈
出山
在旷大如迷的群山中
我仍然如此局限
因进化的完美
而与自然有无可递进的隔阂
即使安静在我们内心居住良久
我们仍然要不断找寻它的来处
如同在海水中找寻火苗
在野花中找寻群山
鸟声旷远
衔着夕阳的分子和季节的谬证
我们终于走出山林
回望几乎九十度的绝壁
就在刚才,无路的困境仿佛尖刀
立在我们的经验之外
我只是抽出自己未被融合的部分
未被淋湿的部分
浓雾瞬间就合上了
一切归于完整
唯有衰老是紧密的
有无法塌陷的硬度
尾声
一切都很真实
“像爱”
我的爱
被山风吹出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