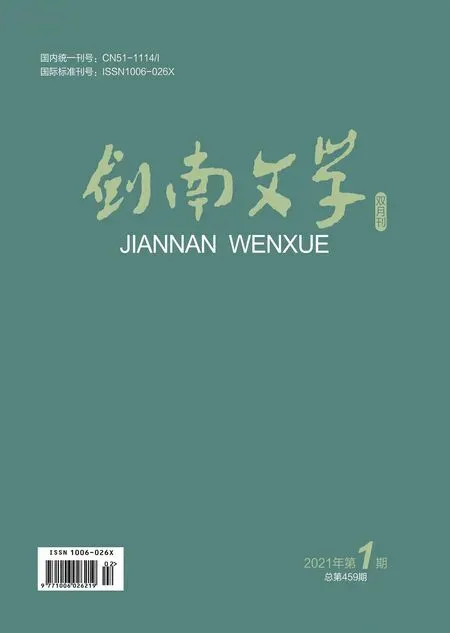烟火
□徐三保
单位门口,一对中年夫妻开了一家排档。
我刚上班,住单身宿舍,人懒,很少烧饭做菜,附近虽有几个排档,但只对这家印象深。
老板姓胡,矮胖,走路快了肚子上的肉直抖,见人总是咧嘴笑,同事给他起个外号“武大郎”。他是住在附近的农民,以前闲时常到我们单位捡没烧透的煤炭。看别人开排档,他仗着在生产队多年红白喜事炒菜的底子,也开起来了。
老胡虽胖,做事却有条不紊,切菜虽不能细如发丝,也均匀细长,经常边和人打招呼边切菜,根本不看手底下。老胡动作快、记性好,顾客再多,很快就把烧好的菜端上桌。
老胡家的招牌菜是大肠烧咸菜。没有丁点土腥味,大肠嚼起来嫩滑,咸菜点缀着红彤彤的尖椒,端起来好看,辣火火的味道,口感好,下饭。很多人盯着老胡配料炒菜,回家照样炮制,就是烧不出那个味,请教老胡,他只是呵呵笑,不说话。也有人提起老胡排档,头摇得像拨浪鼓,说老胡家的桌面什么时候看都油腻腻的,多少年了,从没抹干净;老胡胸前的围裙虽经常洗,但油污斑斑洗不掉,看上去脏兮兮的。老胡烧菜喜欢用食指尝尝味道咸淡,看着就不干净,倒胃口。当时的我,只在乎菜的味道好、分量足、价格好,至于卫生嘛,我自我安慰:“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后来,我渐渐成了老胡家的常客。
老板娘个子也不高,动作麻利,做事迅疾而不慌乱。见人笑嘻嘻的,嘴甜,老远就打招呼,恨不得把坐着的人喊站起来,本不准备来的顾客,碍于老板娘的热情也走进来了。熟客觉得价格贵,老胡一般龇着嘴,憨厚地笑,不吱声。老板娘弯着腰,凑上来,讨好地笑着说:小兄弟啊,您好福气,大概不去菜场买菜吧? 什么不涨价? 真是只挣个辛苦钱,您不好意思让我亏本吧? 下辈子如果像您有这样一个好单位,打死我也不干这个辛苦活! 您不知道,真哈比(好像)讨饭。当然熟客结账时一般零头都会抹掉。
我经常和关系要好的朋友去排档,有时也和机车组的同事去吃饭、喝酒,天南海北地闲扯。周围几家排档都吃过,有的烧菜味道仿佛水煮似的,干巴巴的;有的分量少,端起来的菜就盘子中间浅浅一层,不够吃。老胡烧的菜味道重,舍得倒油撒辣椒,端起来满满一大盘。我来的趟数多,也知道些窍门,老胡炒菜时配的便宜白菜偏多;烧锅子时,牛肉、羊肉等值钱的荤菜也就飘在上面好看,便宜的烫菜放得多,看起来分量足。
我每次去,老胡夫妻俩笑脸相迎,倘若忘了带钱,或者手头拮据,饭前跟老胡讲一声,让他记个账,我约定时间肯定还。老胡刚开始记,看我从未失约,再去,老胡手直摇,大声地说:“不记,不记,兄弟,人品是最好的账本! ”有时空闲,夫妇俩当着我的面长叹,有些和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欠了几百块钱账,天天推三阻四,一个屁三个谎,嘴里没有一句准信,更夸张的,欠了钱干脆不露面,躲几百块钱债,为啥就没有三保一半靠谱呢?
排档边,偶尔也有衣衫褴褛的乞讨者,有的排档老板手直挥,嘴里已经吐出好几个“滚”,满脸厌恶。每次到老胡家排档,老胡笑着倒上一碗热饭,赶一点剩下的大锅菜。乞讨者讨好地笑着,不停地弯腰点头,千恩万谢地离开。老板娘噘着嘴,嘀嘀咕咕,说有些人要饭是装的,都是好吃懒做的现世东西,埋怨老胡给得多,开个小排档,还真把自己当有钱老板。老胡不说话,仿佛一阵风吹过,装着没听见似的,继续埋头炒菜。老板娘倘若嘴里呱啦呱啦唠叨个没完,老胡就把眼一瞪,锅铲在锅里敲得当当响,吼道:“哪个不是逼得没路走,才出来靠门边(讨饭)? 我们当年落难的时候,也比讨饭好不了多少! ”老板娘被一顿抢白,眼圈有点红,想发火,咬着嘴唇忍住了,低头忙手里的活。
我搬到更远的宿舍,甚至结婚成家住到市里,偶尔也去老胡家排档吃饭。有一次,我从市里坐公交车赶来上班,钱包被偷了。周围没熟人,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老胡排档,吞吞吐吐地说明了来意,老胡爽快地拿出一百块钱,笑咧咧地问:“够不够,不够拿两百? ”我连忙说:够了,谢谢。老胡装作生气地说:“三保,见外了,不要说拿一百! 拿一千,我也放二十四个心! 但有些人借一块我都不会给的! 这么多年处下来,我还不了解你? ”老板娘在择菜,也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只是点点头,沉默不说话。我连忙看着老板娘说:“下次上班肯定还给你! ”老板娘笑着一边夸我的人品好,一边感叹现在生意难做,什么都涨价,利润小。我去还钱的时候,老胡笑嘻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看着老板娘,提高声调说:“三保做事,吐口唾沫是个钉,手头紧,你再来拿,没事! ”老板娘脸上堆着笑,兄弟长兄弟短说个不停,赞叹我的人品好。
我也见过老板娘不高兴的时候。几个平常在其他排档吃饭的熟客,老胡夫妻俩笑脸相迎,热情接待。这样的顾客,一会儿说菜价格贵得离谱,一会儿说味道不对劲,老板娘脸上的笑容没有了,但忍住没说话。吃完后,又要打折。老胡依旧带着笑说,小本买卖,利润少。便不再言语,继续忙着烧菜。老板娘扔掉手上正择着的菜,撸了撸袖子,站到前面来了,板着脸,双手叉着腰,翻着白眼大声地说:“开个小排档容易吗?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挣两个辛苦钱,大哥哎,你要是嫌贵,下次不要来,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算什么呢? ”话说到这份上,几个吃客再不好说什么,低着头,掏钱走人。老板娘的白眼也给添油加醋地传开了,人们夸张地学老板娘翻白眼,私下里起了个外号“白眼鸡”。一段时间后,上次的顾客,又笑嘻嘻地跑到老胡家排档,老胡夫妇依旧笑脸相迎,大家都心照不宣,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老胡夫妻俩最悠闲的时光是午后。最后一批客人走完,老板娘不慌不忙地洗碗择菜,为晚上作准备。老胡斜躺在旧藤椅上,整个人松软了下来,泡一杯叶子大、味道浓的廉价茶,按下旧的小录音机,听听叨叨戏(庐剧)。老胡仰着头,闭着眼睛,手不时地在空中比画着,身子随着节奏轻微摇晃,有时还跟着小声地哼唱,满足的样子,好像这是人世间最享受的事情。老胡说从小爱看戏,听说哪里搭台唱戏,走多远的路、多累,都觉得值。有一次,他晚上跑到别的大队看戏,回来的时候和村里伙伴走散了,天上看不见月亮,迷路了,岔到一个坟堆旁边,周围死一般寂静,只有风呼呼地在耳边刮,吓得他双腿直打哆嗦,拼命地跑,跌倒好几跤,折腾半夜才回到家,躺在床上,吓得捂着被子不敢露头,浑身还在抖。过几天,听说有戏看,还是跑去看,只是跟紧了同伴。现在好了,买个磁带,想听什么选什么,倘若哪天要是没听上几出戏,胳膊腿总感觉不舒坦,似乎生活中缺了点啥味道,心里空落落的。
老胡夫妻俩开了近二十年的排档,起早贪黑挣了不少钱,在村里盖起了三层楼房,装修得也不错,门口围了个大院子。只有一个宝贝儿子,长得跟老胡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只是比老胡洋气,今天染个黄头发,过几天又染成红的,穿个破了洞的牛仔裤,两只胳膊上刺了青龙白虎,嘴里经常斜叼着根烟。夫妻俩原本希望儿子认真念书有个好的前程,不再干这种辛苦的活,人模人样做个办公室的体面工作。可惜儿子根本不是读书的料,虽然也花钱补课,成绩还是在班上末尾徘徊,经常在学校惹事。儿子初中毕业,花钱上了个职高,分到开发区工厂上班,吃不了苦,换了几份工作,最后都不了了之,到处闲逛。
有一次,老胡的儿子在排档里帮忙,和我们单位一个脾气暴躁的年轻职工言语不和,打得别人头破血流。老胡只得找人斡旋,花了不少钱,总算平息了这件事。那段时间,每次看见我,夫妻俩都满脸愁容,唉声叹气。老胡担心地和我诉苦:“这个小搪炮子(指儿子)的,不晓得还会给我惹什么麻烦! 念书不造,干事还怕吃苦,挣不到钱,花起钱来像淌水一样哗哗的,吃要吃好的,穿要穿好的,以为他老子是沈万三! 我就是个开小排档的农民,都是他妈惯出来的! ”说完,老胡板着脸,狠狠地瞪了一眼老板娘。平常有些强势的老板娘,这时却低头不停抹眼泪说:“小家伙不懂事,哪个小家伙不惯?懂事就好了吧! ”夫妻俩苦口婆心劝了多少次,要儿子收收心,好好上班挣钱! 儿子依旧满不在乎,老胡最后狠狠心,买了一辆车让儿子跑出租,又给儿子娶了一位老实巴交的媳妇。儿子结婚第二年,添了小孩,总算渐渐安定下来,不再四处闲逛。
几年后,城区统一进行环境卫生整顿,老胡家排档被迫搬离到较远的地方。单位对面盖起了崭新的小区,饭店一条街开得红红火火。老胡和其他几家排档生意每况愈下,陆陆续续关门了。
最近,在路上碰见老胡,头发全白了,见了我依然咧嘴打招呼。老胡夫妻俩,一个在小区里做清洁工,一个接送孙子,买菜烧饭。我和他闲聊了一会儿,老胡看了看手机抱歉地说,要去接孙子。夕阳照在马路边的梧桐树上,洒在老胡秃顶的脑袋上明晃晃的。老胡肥胖的身体努力地往前赶,仿佛在追赶着什么巨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