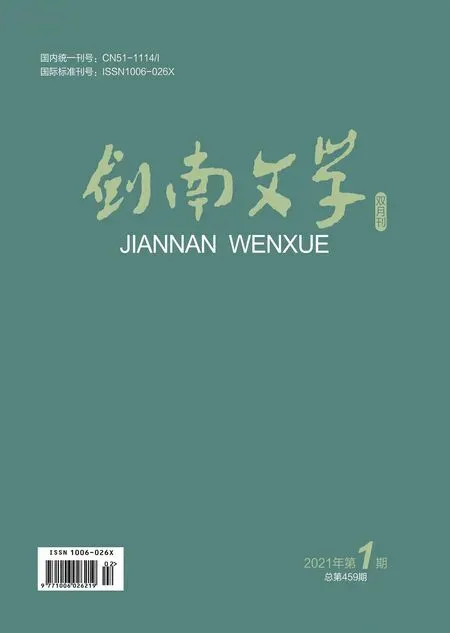千里待归
□王琴
一
一个人从失踪那天算起,只要到当地派出所报案了,自报案之日起,四年后就算死亡了。
杨幺娃1990 秋天失踪,到2019年秋天,整整二十九年,这期间,没有谁去报案。磨刀河旁边的每一个人都晓得这一件事:杨幺娃跑了。过了十多年,人们用猜测的语气说,杨幺娃可能死了哦,好多年都没有回来过了。又过了十多年,磨刀河边的人没事闲聊的时候,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杨幺娃肯定死了,都二十多年不见了。
2008 年地震,很多外出打工的人走烂了几双鞋磨破了双腿都回来了。我父亲一听说某某也回来了就叹气说,幺娃子肯定不在了,不晓得死到哪个地方了。他的理由站得住脚:四川发生这么大的地震,磨刀河是震中区域,要是幺娃子没有死,就是个木头人,也应该回来看看,大大小小几十口和他有着直系血缘关系的人就生活在磨刀河,人心都是肉长的。
幺娃子是1990 年11 月18 日走了的。这个日子父亲记得清清楚楚。挨着这个日子的前一天,1990 年11月17 日,父亲还看见了肩膀上担了两桶猪粪的幺娃子,他要把猪粪担到田里撒肥田。父亲还和他说了几句话,无非是一些家常,吃了没有,最近在做啥子之类的话。作为幺娃子二哥,父亲心里着急幺娃子还没有成家,也不好问,于是经常让我的母亲多想办法请媒人多介绍几个女人。父亲说,要求不能高了,结过婚的也可以,有个家比没有家好。这一天父亲没有想到以后会有几十年的时间见不了面,他和幺娃子的聊天还是不咸不淡的那么几句。
1990 年11 月18 日,父亲的三弟家里找了几个人背柴。那时候,磨刀河居住的人家生火做饭都是用山里背回来的木柴,一般是青杠树,大小软硬都适合塞进灶膛里。青杠树长在很远的山里,需要人砍了树剔掉指头粗的小枝丫,再端端正正一根根地码在背篼里背回家。父亲也去帮忙了,他说忙了一会儿总觉得少了一个人,他埋头剔柴,才想起原来少了幺娃子。以前兄弟姐妹家的这些粗活总是少不了他,只要他闲下了无论看见哪个还在忙都会跑过去说:我来。父亲没有听到“我来”两个字,才想起幺娃子没有来帮忙。他问他的三兄弟: 幺娃子咋个没有来呢? 得到的答案是,幺娃子出门了。自此,幺娃子走出了磨刀河,走出了父亲和其他人的视线,一走就是二十九年。
这二十九年间,磨刀河变了很多,河水变小了,两岸的树林更密了,那些他浇过粪的田被人承包了,田间地头他走过的泥巴路变成水泥路了。更重要的变化是,他走时锁好门的那一间旧房子不见了,被一栋两层的楼房取代,而这栋楼房是村里另一户人家拆了旧屋新建的。当然,比如我,他的亲侄女已经人到中年,再比如他的二哥我的父亲已经成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年人了。
所有人都以为幺娃子死在外面,于是,跟他有关的本来属于他的房产田地都被一个女人给处理了。旧房连带房前宽敞的晒坝卖给了一户山上想修房又没有屋基的人家;田地她自己种了,好些年后又承包给了在村里搞农业的生意人。这一些都做得心安理得,因为大家都估计“幺娃子死了”。这个女人是幺娃子的大姐,亲的,我喊大姑。
幺娃子是我的幺叔,我父亲最小的弟弟。他们一家六兄妹,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父亲是老二,给我外爷外婆当了上门女婿。他们的母亲去世时,幺娃子才两岁,怕养不活,就送给了镇上姓杨没养儿子的人家,他十多岁懂事后又跑了回去。除了幺娃子,其他五个兄妹都成家立业,这一家族建了一个微信群,偶尔过节时发个红包聊几句天,平常大多数时候都是静悄悄的。
2019 年7 月30 日,我在下乡,中午吃了饭,在镇上的政务大厅里蹭空调,几天前已经进入大暑,热得很。我刷手机,看见久无动静的家族群里有人在喊: 幺娃子找到了! 同时,几个人一起问:在哪里? 不可能哦。微信群炸开了锅,几乎所有的人都冒了出来,还有几个问幺娃子是哪个? 时间太久了,久到家里添丁进口,久到幺娃子这一个大活人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一个不存在的存在。
至此,那个叫幺娃子的人离开磨刀河接近三十年后,在微信群里复活。
二十九年了啊,时间跨度很长,我只有慢慢来捋捋,家族里所有的人,所有和幺娃子有关的信息都要捋一捋。不,幺娃子是我的父亲那一辈人喊的,我应该喊他幺叔。
二
说“幺娃子找到了”的是我大姑的儿子,一个小时候最喜欢下河摸鱼的小伙子,我们喊他小名 “小鱼儿”。小鱼儿说磨刀河乡镇上来了两个人,找到大姑,问她认识杨幺娃不?大姑说,认识。来人又问,你晓得他在哪里不? 大姑翻了一下白眼,粗声大气地说,几十年都没见过了,肯定早死到外头了。来人就笑了笑说,没有死,要回来了。大姑当时就从板凳上跳起来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蠕动了一阵,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我觉得小鱼儿说话有点夸张,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到重要的事情上,就毫不客气地说,莫说那么多废话,直接说人在哪里,现在咋样了?
云南,楚雄,救助站,不知道。小鱼儿干脆地说了这些字。
云南楚雄,多么陌生的地方。我百度了一下:楚雄,位于云南中部偏北,东靠昆明,西接大理,南连普洱,北临四川凉山。这就是地理位置上的楚雄,现在,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有了另外一个意义: 我的一个失踪了二十九年的至亲可能在那里。
我回头再看小鱼儿的话,还有三个字“救助站”——这三个字在网络上出现的频率不低。我所看到关于救助站的信息,大多和出走、遗弃、低智、肮脏、落魄、伤残等词有关。怎么也想不到,某一天,我也和这些词有了最近的接触。幺叔都在救助站了,情况肯定不乐观! 我脑子中出现了一个满头乱发、 衣服又破又脏、拄着木棒、流着口水、满脸呆滞的人。
印象中的幺叔不是这样的,他出走那年我已经初中毕业了,我记得起他当年的模样。即使隔了二十九年的光阴,我已经走到了中年,记忆中的幺叔还是活在二十九年前——那是一个中等个子、 肤色偏白、衣着整洁、脸上经常露出笑容的人。是的,幺叔长得不丑。
脑子里,两个人影换来换去地出现,一会儿是那个干干净净的年轻人,一会儿又是那个落魄潦倒的老年人。
幺叔和父母最亲近,他随时都会出现在我们家里的任何一个时间点,有时候是清晨,有时候是黄昏,有时候是半夜。我其实不清楚他经常来是不是和相亲有关,偶尔也会听见母亲对父亲说,幺娃子太挑了,一会儿嫌人家个子矮,一会儿又说人家长得黑,他也不晓得看看自己,就那么一间破房子几亩田地的,还挑个啥子。
母亲总是问幺叔为什么不喜欢那些女子,问了一次又一次,幺叔被问烦了,就说,莫得感情。
农村里的婚姻有没有感情的成分在,我不清楚。我听到过父母一些话,当我再看他们时就有了一些打量的意味。父亲说,你这个地主崽儿,要不是我,没有人敢要你。母亲很不以为然,她鼻子里哼一下:你以为你有人要,一个讨口子的儿子,要啥莫啥。我问母亲,爸爸咋个是讨口子呢? 父亲倒毫不避讳,他说,他的父亲是当年讨口逃荒到了磨刀河,给张家当了长工,后来张家给他娶了另一个逃荒而来的女人,这就有了一家人。母亲就有些得意了,她家里是磨刀河的原住民,家里有一个颐指气使的老太太,曾经半个磨刀河的田地都是她家的,哪怕到了后来只有三间茅草屋,老太太半夜半夜地被弄出去挨批,到了后辈人口中,隐去了苦难,只剩下骄傲了。
即便这样,我还是认为,父亲需要母亲,母亲也需要父亲,于是他们走到一起了。至于感情,有或者没有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日子自然是要过下去的。
幺叔自然也是讨口子的后代,可惜他没有像父亲那样多读几年书,没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家里两间破烂的房子只有一间属于他,另外一间属于我大姑。挑媳妇,更没有资格了。我是见过一次幺叔相亲的。来了两姐妹,姐姐说给我们村一个姓李的大个子,也只有一间房子,隔壁是他的另一家亲戚居住。妹妹打算说给幺叔,个子很矮,背后还搭了两条长长的辫子,人就显得更矮了,五官就像没有长开,挤在一起。我在旁边看,心里就想上去把那些长在一起的眼睛鼻子嘴巴掰开挪一挪位置。幺叔和那个姑娘相对而坐,中间隔了一张饭桌,母亲在厨房里煮糖水蛋。我把手揣在兜里,母亲喊我把糖水蛋端出去,我没动,她就笑骂我不懂事自己端了出来。我以为幺叔要站起来接过这碗糖水蛋,他没有,他坐在那里也不看谁,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倒是那姑娘站起来伸手端了过去。母亲让两个年轻人表个态,姑娘小声说她没意见,就看他了。幺叔没搭话,过了一会儿,姑娘站起来把糖水蛋放在桌子上,走了,碗里的蛋一个没动,连水也没喝一口。姑娘的姐姐相亲成功了,当天晚上就住在了李大个子的家里。第二天,几个女人凑在一起,装着小声其实很大声地说,就那么一间屋,能睡到哪里去,还不到半夜,就听到那女人的哭叫。
曾经有一个朋友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有时候对生活将就一点,说不定,生活回馈给你的是丰盛的不将就。现在,姐姐和李大个子都老了,她的两个女儿也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幺叔如果当年也将就一下,现在肯定不在云南楚雄的救助站,跟李大个子一样儿孙绕膝的可能性更大吧?
你看,命运总是这样小气,只要某一个事件上你没有顺从它,它就狠狠地惩罚你。但是,谁又能说幺叔现在以六十多岁的年龄出现在远离磨刀河的一个叫楚雄的救助站不是命运真正的安排呢?
幺叔有一门手艺,他是个漆匠,会漆所有的家具,我们家很少的几样家具就是他漆的。我没见过他漆的过程,但是当我回家看到漆过的桌子板凳就惊喜地叫了起来: 好漂亮! 实话说,贫穷真的会限制一个人的想象,我脑袋里也只有“漂亮”这个词了。光滑的桌面亮得可以照见人影子,朱红的色调在简陋的屋子里显得很高贵。我问幺叔,哪个教的这手艺? 他笑嘻嘻地说,哪里需要人教,多刷几道就可以了。我去镇上住校读书,要带一口木箱子装东西,幺叔知道后,花了一天的时间给我的木箱子上漆。父亲用自行车把这口上了漆的箱子送到了我的宿舍,和其他没上漆的箱子摆放在一起,那种显而易见的不同让我很是神气了一阵子。
幺叔出门了。父亲以为他不过是出去几天挣一些钱就回来,也没在意。只是每一次经过幺叔的房子看到门上的锁,回家就会对母亲说,幺娃子还没有回来。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那把锁一直锁着。父亲着急了,跑到幺叔住的院子里,一家一家地问: 晓得幺娃子走哪里去了没有,幺娃子走之前说啥子了没有? 也不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有人说,幺娃子说过要出去挣钱,恐怕要出去很久。也有人说,幺娃子说过要去云南,说那边割胶可以挣钱。
父亲很多时候都在自责,为什么1990 年11 月17 日那天,就没有看出一点苗头来呢,这个哥是咋个当的? 他在自责中回忆那一天的每一个细节,一点点地摸过去,一次又一次地说,幺娃子担了两桶猪粪,还和我说话了的呢,我也是忙着回来,没有和他多说几句,多说几句说不定提前就看出点啥子了,说不定我多说几句他就不会跑了。父亲的话没啥逻辑也不利落,一句话都可以说清楚的事他翻来覆去地说。
一年又一年,幺叔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有一天,父亲看见幺叔的门开了,赶紧跑过去进屋就喊幺娃子。出来的是大姑,她说,门上的锁子是她用石头砸开的,这么久没人住了,打开看看。
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幺叔一直没有出现。
初中时,我学过一篇课文,《我的叔叔于勒》,那时候幺叔还没有出走。教语文的何老师讲得干巴巴的,一会儿让我们齐读一会儿让我们分角色朗读,一会儿又分段归纳中心思想。我右手拿着笔左手捂住嘴巴打了好几个哈欠: 那个于勒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工作后,有一次全县举办初中讲课比赛,我抽到的课文是《我的叔叔于勒》。还记得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县城初中三年级的教室外,还是夏天的模样,一树树的绿荫,不远处,涪江的河风也吹了过来。我说,同学们,今天的天气真好,我们和这么多老师一起在这里阅读一篇小说,希望这篇文章带给你的不只是和这天气不一致的寒冷,或许还有一点其他的东西需要你们想想,一会儿我们来聊聊各自的感受。课文中,有几段是“我”的父母见到叔叔于勒后的的不同反应,还有“我”的一些内心独白。那些内容,我读了: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我心里默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读到后面,有泪水流出来,幸好我有眼镜,那些泪水没有被听课的老师看见,也没有被学生看见,我还是想起了杳无音讯的幺叔。那一年是2003 年,和1990 年有着十三年的距离,和2019 年又隔了十六年的距离。
我一直在说距离,其实我不知道时间能不能用“距离”来表示,我只是想不到更好的词了。
现在,我的叔叔幺娃子时隔二十九年,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时,重新以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形象出现了。我又想起那篇课文那些段落,一时有些想落泪了。我想,我和我们给幺叔的不应该是那十个铜板。
三
父亲退休后喜欢玩乐器,是真的玩,小孩子一样,买支笛子吹一吹,没成一首曲调又说要学弹琴,于是花几百块钱买回一个电子琴,没事时就敲几下,一首老歌还没练熟悉,又开始敲另一首。他不会玩手机,连接个电话也嫌麻烦。
群里说幺娃子找到了时,正是中午,父亲弹了半首曲子,母亲就喊吃饭了。母亲喜欢玩手机,她听见“叮当”一声响,就会拿起电话看一看,生怕哪个儿女给她留了信息没及时看见。母亲看见那个信息了,她大声地喊: 特大新闻,幺娃子找到了! 父亲端起碗正在往嘴里扒饭,他边吃边问:哪个幺娃子? 母亲说,还有哪个幺娃子,就是你的弟弟啊,杨幺娃! 父亲停顿了一下,继续吃饭,还是边吃边说:不可能哦,咋个可能啊,都几十年了,恐怕骨头都化成灰了。
这些都是正好在家休假的侄女告诉我的,她还拍了视频传给我,说,爷爷好淡定哦,他弟弟找到了都没有激动一下,我婆婆倒是激动得很。视频里,饭桌边放着电子琴,父亲端起碗正在吃饭,表情正常。我给侄女打了一行字:注意点,那么大岁数了,内心不一定淡定。
我随时都在和侄女联系,问怎么样了? 侄女说:爷爷在笑,哈哈大笑,边笑边说,找到了就好找到了就好。一会儿侄女又说:爷爷在流泪,边流泪边小声说,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哦,但愿不是骗子哦,现在骗子多得很!
我还没有看见幺叔,只是在微信群里看见了有关幺叔找到了的信息。我也不敢给父亲打包票,不敢说这是真的,千真万确,谁会去装一个需要求助救助站的人来行骗呢!
没有了幺叔的这几十年,父亲很多时候心情不好。看见和幺叔同龄的人,看见多年外出打工回来的人,看见村里来的那些外乡人,他都会自言自语地说几句: 幺娃子要是还在,也是这么大了,幺娃子要是在外面找个女人结了婚安安稳稳活到起就好了,幺娃子不晓得还在不在哦? 就是这些话,说了又说。
父亲不是一个大方的人,幼时早早失去了母亲,又处于特殊的年代,吃饱肚子几乎不可能,他对粮食比一般人还要爱护,饭碗肯定是一颗米也不会留下,吃不完的菜只要不坏,热了一顿又一顿。我们告诉过他,不要这样吃,现在不缺粮食了,以健康为主,不要吃剩饭剩菜。父亲不听,边吃那些剩菜边说,你们是没有饿过肚子,哪里晓得粮食的金贵。父亲也很少请客,他心里有一本账,觉得请客吃饭是浪费。
就是这样一个很吝啬的人,对外来的人却格外大方。有一年,村里来了一个卖草药的人,无处落脚,父亲请到了家里,腾出一间屋子给他打地铺,还拿了竹竿把挂在墙上的腊肉取了一条下来,洗得干干净净的炖上干萝卜给他吃。母亲是有些抱怨的,那么好的腊肉,那么干的萝卜卷给不晓得哪里来的外乡人吃了。父亲说,幺娃子也可能跟这个人一样哦,在外头漂的人,苦啊。
我是明白父亲心意的,他把每一个漂泊的外乡人都想成了他的弟弟幺娃子,他帮助了那些外乡人,就像帮助了他的弟弟幺娃子,心里也就稍稍有了些安慰。
外乡人在家里呆了整整一周,他背的麻袋里装了些生中药,味道很浓,村里偶尔也有三五个人来找他抓一副中药去泡酒,和外面地摊上看见的一样,无非是治疗跌打损伤关节肿痛之类的药。父亲和他摆龙门阵,也问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外乡人说,从青海那边来的,走到哪里算哪里。父亲就又开始叹气说,这么远,真不容易。
外乡人要走了,父亲让母亲炸了一碗腊肉饼,晾冷了装在口袋里让他带上。我们都巴不得这个人快点走,家里的那种生中药味太难闻了。父亲跟着他一起走,给他指路,告诉他走过右边的那道山梁,最多半天时间就到另外一个镇了,那个镇上人多,要是想回青海,也要经过那里,车也多,方便。
父亲每一年都会说几次同样的话:“幺娃子要是回来了就好了。”我有时候也会跟着说,幺叔说不定哪一天就出现在田坝里的那条路上了,拖家带口的,风风光光的。这话不是用来安慰父亲,我心里也这样想。不管是现实还是戏文里,离家出走几十年又回来的事也不是没有,说不定幺叔就在外面安了家,有了老婆娃儿,经济一宽松就回来了呢。父亲听我这样说,笑了,他说,那就好那就好。隔一会儿,他又说,不可能哦,连信都没有一个,说不定就死到哪个边边上了。
2010 年,父亲退休了,他郑重地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宣布他的计划:他要去找幺娃子。我问他,去哪里找。他说,先去云南,再去山西,那边煤矿多,说不定幺娃子进了黑窝子了,我去找找,把他带回来。
母亲不同意,她说外面的煤窑子那么多,你晓得是哪一个? 父亲冲母亲发火: 不是你的兄弟你不晓得心疼,要是你的亲兄弟你早就跑出去找了。母亲也气急了,大声说,不是我的亲兄弟啊,我那几年操的心比你们这些亲兄妹还多。你说,我给他说了好多个亲,你们哪个真正关心过,但凡有人真正关心他,也不会跑出去这么多年不回来。于是,父亲又闷着头,不说话了。
父亲就像一个唠叨的女人,总是把“我要出去找幺娃子”这句话放在嘴边,就是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去找。母亲背着父亲和我说,还是给你爸爸找点事情做,他这么闲下去要疯。于是,我就旁敲侧击地鼓励父亲打牌下棋,他也主动要求给他买笛子买电子琴,只是总是没有一样能坚持住。
四
家族群里,每个人都在问,每个人都在设想。
三爸的儿子说,不晓得身体还健康不。
大姑的儿媳妇英子说,不管健康不健康,回来就好,人老了总得叶落归根。
母亲就艾特了英子,用了一个大拇指给她点赞。
我说,大家都安排好时间吧,一起回去。
这么热闹,大姑一句话也没有说。
二十九年前,大姑和幺叔住在一起,那是两间老屋,大姑一间,幺叔一间。他们两姐弟总是爱吵架,大姑骂得很难听,说幺娃子就像个尿桶,被人提着甩来甩去。幺叔就说,我晓得你不安逸我,我不回来两间房子都是你的,我一回来你就只有一间房子。老子想回来,老子也是张家的人,这个房子也有老子的份。说着说着,幺叔就给大姑充老子了,大姑拿起扫把就开始撵着幺叔打。
打是打了,骂也骂了,一煮了好吃的,大姑还是扯起嗓门喊: 幺娃子,过来吃饭。
我想,大姑可能也是有点不安逸幺叔吧?她已经结婚了幺叔才从杨家回来,于是,她不得不把一间旧房让给他住。我还记得大姑的那一间房子隔成了三格,最里面是厨房,中间是卧室,外面是堂屋。幸好农村的房子进深长,也不显得拥挤,但是有两间这样的房子肯定比一间好多了。
幺叔好些年没有回来,大姑忍不住了,一块石头就砸开了那间锁着的门。父亲看见打开的房子里出来的是大姑,气冲冲地回家了,一回家就大骂:一点都没有姐姐的样,门就那么给砸开了,想干啥子? 啥东西?
大姑想修新房子。她是个能干的女人,不安心只从土地里刨食,跟着别人做生意。她从成都荷花池进一些便宜货——毛线、毯子、床单这些农村里用得上的东西,跑转转场,哪个乡镇逢场就去哪个乡镇卖货。渐渐地,有了一些积蓄,她就想修新房子了。她看中了保管室的三间房子,独门独院的宽敞,想把老房子卖了去那边修新房。母亲对父亲说,那可是你们张家的老祖业啊,卖不得,要是幺娃子回来住哪里?
大姑能干,也敢干。她没有一点犹豫,也没有和她的哥哥妹妹商量一下,就把老房子卖了,连带幺叔那一间。父亲除了在家里干生气,一点办法也没有。
现在,大姑在保管室新修了三间两层的新房,比以前住的老房子宽敞多了。
母亲是个爱多管闲事的人,对于这件事,父亲的兄弟姐妹们都有意见但是又都不说,只有母亲找到大姑,问她:你把幺娃子的那一间房子卖了,幺娃子要是回来了咋个办?
大姑没有回答咋个办,开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喊起来,说她的二嫂和她争夺家产来了,二哥本来就是个倒插门是个上门女婿,凭啥子来管闲事,有你啥子屁事,你管我卖不卖老房子,你就是想要钱嘛,给你说,钱一分都没有了,就是有也不给你一分,你凭啥子要,你有啥子资格要?
不仅如此,大姑见人就说母亲的不是,说母亲心口子厚眼皮子薄,见不得人家好。
母亲气得在父亲面前摔东西,说,以后大姑休想进这个门,莫得这个亲戚。
母亲和大姑实实在在生分了几年,逢场碰见了也各自把脑壳扭到一边去,大姑甚至还要朝地上吐一口口水,吐得很响,还发出“呸”的一声。
母亲对幺叔的好,父亲知道。幺叔也不是个省心的人,有一年他跑出去几个月,灰头土脸地回来,还是个冬天,一回来就半夜摸到我们家,敲开了门,把家里人吓了一大跳。母亲抱了一大把干柴在堂屋里生了火,让幺叔坐在火边。幺叔说,二嫂,你给我做点好吃的,我饿惨了。母亲只熬了稀粥。她说,饿久了的人肠胃经受不起油气大的饭食,要先喝几顿稀粥养养胃再吃肉。那一次,幺叔在我家住了很久,直到他又恢复了体力,才回磨刀河。
但父亲还是说母亲的不是,说她毕竟是嫂子,也该大量点,不该和大姑吵架。
母亲总是说幺娃子可怜,生下来奶都没吃几口妈就死了,送给别人心里还是想着自己的家,一回来也没个人真正为他操心一下,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越活越没意思,不跑才怪。
这是母亲给幺叔出走找的理由。她说,一个人心里没了念头,就破罐子破摔了,走一步算一步,幺娃子就是这样。
微信群喧闹了一阵,就又沉寂了。
父亲不放心,让我给小鱼儿打了电话过去。小鱼儿说,三姐,快莫问了,我妈不准我到处宣扬我幺舅找到了。我说,这是好事啊,为啥子不准说。我妈说,丢人!
父亲也听到了小鱼儿的话,他冒火了,大喊:丢啥子人,有啥子好丢人的,那么大个人又不是一个东西可以藏起来,啥子东西,当年不是她天天骂幺娃子,他咋个得跑?
母亲说,哪里是怕丢人嘛,是根本没想到幺娃子会回来,房子卖了,她在担心。
母亲对大姑早就有意见了,趁这次机会,好好地宣泄了一番。父亲没有多说什么,还不时地点点头,表示母亲没有说错。
大姑卖了幺叔的旧房子,没有与任何一个和幺叔有关的人商量一下,她不需要去说服他们,房子本来就是留给她的。其他几个兄弟姐妹结婚后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幺叔是从抱养他的杨家中间跑回来的,房子本来就没有他的份。这些话是大姑和磨刀河其他的人说的,当然,这些话又一阵风地传到了父亲母亲的耳朵里。母亲表示不满意:房子是老一辈留下来的,不管怎么说,幺娃子都是这个家的人,再怎么也有他的一份。大姑又对外人说,幺娃子那间房子的钱她存着,等幺娃子有朝一日回来了给他。
在农村,不少人都热衷于和自己无关的家庭的家长里短,在母亲和大姑之间,仿佛有一两个传话的通道,母亲的心思大姑晓得,大姑的小九九母亲也清楚,于是就彼此看不惯彼此不安逸了。
大姑卖了老房子那一年,大哥遇到了一个选择,要么读委培生,要么到镇上的一个镇办工厂打工。大哥肯定想读书,但委培费要几千元。母亲要父亲去向大姑借钱,这么大的事不要耽搁了。父亲不去,他说,要去你去。于是,用母亲的话说,她厚着脸皮去了。没借出来,大姑说钱她用了。母亲回家后,是流了眼泪的,她骂大姑也骂父亲,说他们一家没有一个好东西。
后来,其他人又告诉母亲,大姑赶集时,见人就说母亲的不是,心里在琢磨她的钱,那是不可能的,一分都没有。
大哥终究还是没有去读书,他去了镇上的花岗石厂。某一日,大姑遇见大哥,笑呵呵地说,这就对了,读那么多书干啥子,还是早一点挣钱好。
现在,幺叔找到了,不管是母亲还是大哥,都说,这下大姑该把钱拿出来了。大姑的家和很多个农村家庭一样,一家人大多都在外面打工,家里新修的楼房除了过年过节其他时间都锁起的。我们两家走动得很少,春节也很少在一起吃顿饭。母亲还是会抱怨大姑,事情做得绝。这一次,幺叔可能要回来了,旧事重提也就变得理所当然。
母亲对父亲说,幺娃子回来总得有个地方住吧,住哪里呢? 总不可能把那么大个活人贴到篱笆上,你妹妹总得想个办法。
我插了句话: 也不是大姑一个人的事,这么多亲戚。母亲吼起来:不是她的事,是哪个的事? 哪个喊她把房子卖了的,还一分钱都借不出来,害了好多人。
我只好闭嘴了。
五
7 月30 日,我请了半天假,回父母家。家里只有老父老母,哪怕是有电话有微信群,我也觉得不如当着面说话好。我才走到半路,电话就来了,是母亲的电话,她说,你爸爸让我问问你有时间回来不? 我说,再半个小时就到了,我和大哥一起回来。
回到家,父亲坐在堂屋里的沙发上,电子琴装在袋子里放在一边。他坐得很端正,看见我和大哥进了门,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是假的,幺娃子不可能回来,都二十九年了,一个消息都没有,咋个就说到救助站了呢,恐怕是同名字的人。
我的一个姓陈的小学同学在磨刀河当村主任,小鱼儿说就是他带人去找我大姑的。我当着父亲的面就给陈同学打了个电话,父亲催我问,好久送回来? 可不可去接? 陈同学说,你们都放心,一站一站地送,过两天就送回来了。那个黑煤窑子,这一次一起解救了一百多号人,全国各地的都有,每一个都要送回家。
果然是黑煤窑子! 父亲说了这一句话,就靠在身后的沙发背上,连连摇头: 不晓得幺娃子遭了好多孽哦,狗日的黑心肠的煤老板啊!
我说,爸爸,幺爸回来就好,这么多年我们都以为他早就没在了,现在人在就好,你就不要多想了,好好耍你的,想弹琴就弹。父亲抬起手,很无力地摇了摇,不弹不弹,吵得很。
大姑一直没有表态。幺叔回来住哪里,这是个问题,不管怎样高兴,幺叔的生活应该怎么继续才是个大问题。62 岁,算老人了,可以进敬老院,可以申请五保户,如果身体健康也可以自食其力。
我不让幺娃子进敬老院。这句话父亲是从喉咙间喊出来的,用了很大的力气。
喊完这句话,父亲哭了,他又是摇手又是摇头,嘴里喊着:幺娃子太遭孽了,在黑煤窑子关了几十年,还没有回来就又说送敬老院。后面这半辈子,我们两兄弟还要在一起摆条,我要他好好活几天。
父亲的心情我是体会不了的,他对幺叔的情感比我们这些晚辈深得多,他内心的起伏,我再试图去了解也够不着。
父亲说,不要去怪你大姑了,她命也苦,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挣钱供娃,她那个脾气一辈子也改不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给你幺爸温暖,让他有想头,不要人还没有回来就去安排他,那他回这个家有啥子意思呢?
大姑的脾气很大,不温和,无论对谁,只要说到钱,她就六亲不认。我们都担心幺叔回来,她不会给一个好脸色,几句话不合,说不定又要喊幺叔滚了。
父亲不说,我们心里都有的那句话也说不出口,大姑既然卖了幺叔的房子,现在人回来了,就应该让幺叔在她家住,田地收回来,分红也该分给幺叔。
这话除了父亲,没有人有这个权力去对大姑说,可是父亲,这样的话他不会说出口。
母亲想得很简单,人都还没回来,想这么多有什么用,还是等幺叔回来再商量。
再过一天就是8 月了,我看了最近一周的天气预报,下一周都是雨。
幺叔还在云南普洱,从云南到成都,从成都到绵阳,从绵阳到磨刀河,两天的时间,跟二十九年相比,这点距离不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