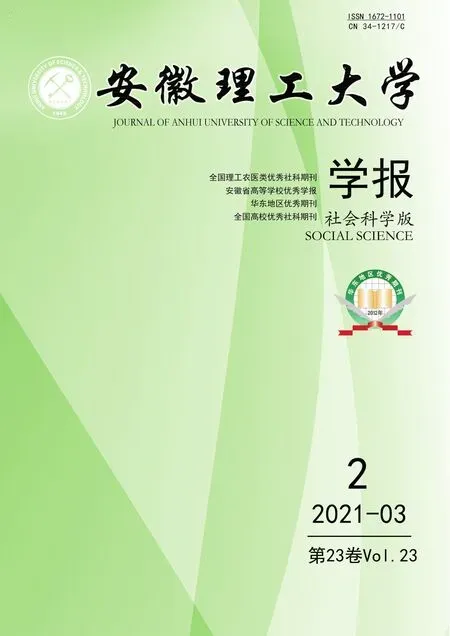论《战国策》对比兴文学创作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夏芳莉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合肥 231131)
比兴是文学创作中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关于比兴的研究成果较丰富,主要是结合古人对比兴的理解阐述比兴内涵,或是探讨比兴作为创作表现方法对诗、词、赋、散文、小说、绘画等文艺创作的影响意义,或是揭示比兴的基本特性,分析比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但选取先秦散文为比兴承继研究对象的文献不多,着眼于以女性为喻体的自比,分析文本与香草美人传统之间关系的作品尚不多见。《战国策》无论是谏辞,还是外交辞令,都经过了精心的构想,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语言效果极强。在诸多篇目中,谋臣策士仔细地揣摩沟通对象的心理特征,常以女性自比或以女性相类的人物做比喻,且多以坚贞、聪慧、楚楚可怜的形象作比,进而实现沟通目的。故本文选取比兴手法使用较突出的《战国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书中比拟女性形象的内容作为依据,意在从细处着笔,探寻《战国策》与屈骚香草美人比兴的承展关系。
一、《战国策》以女性自比的功能分析
《战国策》作品以女性自比所起的文本功能既有为自身洗脱冤屈、避免君臣间生出嫌隙的,也有借以向君王诉说衷肠的,还有以柔弱女子形象示人、希望在困境中不被人落井下石的,当然也不乏借来比喻君臣关系、迂回向君王谏言献策的。无论是为自己辩解,还是百转千回地表达对君王的依赖,无论是乞求他人包容的露怯示弱,还是含蓄劝谏君王的绕指柔情,作品中的谋臣策士都不惜舍弃身份,将自己与女性的形象相联系,以良好品德的女性形象比喻自己对君王的忠诚,以思妇做吴吟暗指对君王的倾慕,以贫困弱小的使女比喻自己的无害,以新妇不知己任、妻妾爱夫君借指朝堂上的君臣之道等。
(一)为己做辩解
身处七雄争霸乱世的谋臣策士为了朝堂中的地位,谋求更多的利益,往往倾轧、诋毁其他人。“楚人有两妻”(《秦策·陈轸去楚之秦》)和“思吴则将吴吟”(《秦策·楚绝齐齐举兵伐楚》)两则故事都是源于张仪在秦惠王面前的挑拨,陈轸通过两则故事成功地予以化解。
如何巧妙而不着痕迹地为自我辩解,从而赢得君王的信任呢?在《战国策》中,“忠且见弃”(《秦策·张仪又恶陈轸于秦王》)、“楚人有两妻”(《秦策·陈轸去楚之秦》)、“忠信得罪”(《燕策·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均以女性自比,尤以楚人有两妻的自我比喻最为有趣:楚人有两妻,在其生前,邻人挑逗二妻,年长妻痛骂,年轻的妻则笑着接纳并和邻人私下往来;楚人死后,有人问挑逗二妻的邻人选择哪个为妻时,邻人选择的是那个痛骂自己的年长妇,而不是早已私下与自己有所往来的年轻女。
谋臣陈轸被张仪诋毁将投奔楚国,其先以“仆妾售乎闾巷”“出妇嫁乡曲”的直白语言表明自己的忠贞,又用“楚人有两妻”故事解释了男性愿意给别人戴绿帽子却不愿意给自己带的大众化心态,生动形象地将自己比作女性,将王比作愿娶之邻人。陈轸以此比喻自己若是那之前就与人私下暗通款曲的人,必定不为君王所看好,最终会落得弃之如敝屣的下场。由此得出结论:如若不忠怎会有人愿意接纳。陈轸通过这则故事深入浅出地为自己做了有效辩解,进而获得主上的理解。
(二)委婉诉衷肠
君臣之间既有嫌隙,也有相互倾慕。君思慕臣子,臣向君主表衷心,以什么方式表达不失君子气节,又能表达思慕之情呢?“思吴则将吴吟”(《秦策·楚绝齐齐举兵伐楚》)故事体现得淋漓尽致,为张仪构陷的陈轸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贞终于去了楚国,齐楚间要有战事之时,楚王听从了陈轸的建议,派陈轸前往故国与秦讲和。秦王推心置腹地问道“以其余为寡人乎?”流露着秦王对贤士十分倾慕的恳切态度和争取忠贞不二之臣青睐的忐忑内心。而陈轸的回复采用的是委婉含蓄的方式,拟女子态讲述了吴人之游楚的故事:楚王深爱的吴人病中被问及是否思乡,左右告诉楚王吴人思乡会做吴吟。接着,陈轸又告诉秦王将为王吴吟,十分含蓄地向秦王传递自己思慕秦王、思归秦土的心意。
陈轸并没有直白回复秦王思慕之心,而是将自己和楚王深爱的吴人相对应,楚王爱吴人,譬喻秦王珍视陈轸;吴人思乡做吴吟,陈轸为王吴吟,隐喻陈轸自己思乡怀人。语言不能详尽,通过思吴做吴吟的故事传达复杂的内心情感,意蕴隽永,耐人寻味。
(三)示弱求保全
“江上处女”《秦策·甘茂亡秦且之齐》即是欲实现示弱求保全的典型。江上处女(使女)贫困没有蜡烛,被其他使女嫌弃、驱赶,身处困境的使女曰:“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何爱余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何妨于处女?妾自以有益于处女,何为去我?”直接阐明清楚了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我买不起烛火,所以经常早起打扫房子铺好席子,你们为何不愿意赐一点照在四壁上一点余光给我呢?这对你们又有什么妨碍呢?我自认为对你们是有用的,为什么不收留自己呢?
在“江上处女”这段文字中,甘茂将自己比喻成给人做工、窘迫可怜的使女,将苏代比喻成和自己一类、只是处境或比自己略微优渥些的使女,二人同是为诸侯王服务的身份。以此比喻传递信息:自己虽困顿却无害于他人,借他人烛火的光亮并不损害他人利益,反而能为其他人分担繁重的工作,尽心尽力为君王服务,期望他人能衡量利弊,容纳自己并给予自己立足之地。而苏代正是认同了甘茂“江上处女”的观点才愿意为甘茂奔走相告,先以甘茂累世侍奉秦王、尽知秦要塞为由说服秦王相迎甘茂,再以此为契机证明甘茂的贤能,说服齐王留下甘茂。
(四)迂回献谏言
同样,在《战国策》“卫人迎新妇”“邹忌修八尺有余”等篇章里,也能看到谋臣们借讲述新妇或者妻妾、门客故事来向君王出谋献策。
如“卫人迎新妇”,新妇出嫁临上车前嘱咐仆从不要鞭挞借来的骖马;车至门口,又嘱咐送妇者灭灶火以防失火;将要进入洞房时看到门旁的舂米石臼,叮嘱左右移至窗户下不要妨碍行走。新妇的三句嘱托都是十分正确的,然而却为主君哂笑,全因为早晚失时。卫人新妇在新婚之日,不忙于与主君耳鬓厮磨,却忙着操持家务,虽然桩桩件件都管理妥当,但让人感叹这新妇并不像个新妇。新婚之日只潜心于细琐的家务,春宵一刻值千金,新妇难道忘却了?将新妇比喻为人臣者,主君当是君王,以此隐喻朝堂之上的士大夫们,在君王面前为人臣子说话应注意分寸、时机、场合,需认清自己的身份,做符合身份地位的事情,不要忙活一些与时局、格局不符的工作,到头来被人讥笑。
文中,以夫妇之道暗喻君臣之道,以妻妾、门客待主君的态度讽喻群臣对待君主的态度,既建议为臣者谨守本分、不逾矩越轨,又告知君王遇事要有自己的判断,因为群臣出于各种原因,观点并不一定完全正确。
二、《战国策》作品自比女性典型形象分析
(一)忠贞信义的化身
无论是“楚人有两妻”(《秦策·陈轸去楚之秦》)里的陈轸,还是“忠信得罪”(《燕策·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中的苏秦,用以自比的女性形象都具备忠贞信义的特点。面对君王的责难、他人的质疑,谋臣策士们并不急于为自己辩解,通过引用通俗易懂的故事,以妻、妾自比不仅传递出了对君王忠贞不二的态度,也保全了责难、质疑者的颜面。作品里的女性,一为誂者愿娶、在楚人生前不愿轻许誂者的詈人者,一为阳僵弃酒、上活主父、下存主母、忠信得罪不免于笞的妾。二者都有着令人钦佩的品格:敢于痛骂誂者的泼辣刚烈,忠于夫君不为所动的恪守妇道,存活他人化解危机的机敏智慧,甘愿承受笞罚的果敢担当,这都与屈原作品中的坚贞女性相似。陈轸和苏秦用比喻语言向君主塑造了集忠贞信义于一身的女性形象,谋臣策士以此自比,不仅明确君臣之间的关系,更容易打动君主信服其辩解的言辞,相信他们忠于君主的人品。
(二)楚楚可怜的弱者
出现以女性自比的情况多由于士人处于困顿的境地下,或被人排挤或遭人怀疑或被闲置不用,境况凄凉。以女性自比,且以身份可怜、地位低下、任人摆布的弱女子为比喻对象,更可助自己博得更多的同情,赢得他人基于同情的信任,进而走出困境。
“江上处女”《秦策二十五·甘茂亡秦且之齐》中的女子家境贫寒到连蜡烛都没有,为众多使女打压排挤,甚至可能连使女的生计都将不保;“楚人有二妻”(《秦策·陈轸去楚之秦》)中的女子在夫君生前为人所誂,夫君死后又任人嫁娶,身世如浮萍一般可叹,虽有坚定的信念,却只能依附夫君生活;“忠信得罪”(《燕策·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中的仆妾为救主父存主母,既无处争辩又无力反抗,两难中别无他法只能自己佯装倒地打翻毒酒,虽有机敏的头脑,终免不了被笞的惩罚。以上士人用来自比的女性,或贫困或窘迫或无助或无奈,与屈原用以比拟的弃妇形象相近,皆为楚楚可怜的弱女子。
(三)含蓄内敛的智者
士人们考虑应如何为人臣呢?向君王直接表达还是含蓄婉转透露更合适呢?与屈原作品的“怨”相似,同样以女性形象来比喻。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邹忌以谋臣身份讽谏齐王,用妻私、妾畏、客有求于己的事例来提醒齐宣王纳谏;“卫之新妇”中策士们用卫人新嫁娘不顾新婚身份三次安排工作为人所笑的故事,告诫为臣者要时刻清醒自己的身份地位,不逾矩不做不合时宜的事情;“思吴则将吴吟”中陈轸用楚王所爱吴人思吴做吴吟,向秦王传递自己思乡、思君之意。这样既避免直白地批评君王的“喜新厌旧”“见利忘义”“不纳谏言”,又能将自己的个人情感、为政策略、建议见解寄托于所述故事中,婉转地向君王表达思想、情感。
三、“比”的内涵及《战国策》对比兴传统的继承
比兴之比,是将所指不易描述或者相对抽象的事物具象化或者形象化地展现,也是一种比喻、象征、打比方。拿来相比较的两者之间有类似的地方,二者往往表现为类似或存在着某种联系,通过具象化或形象化的事物描述,使得抽象隐晦的内容变得明朗生动,从而起到强化表现效果的作用。《战国策》谋臣策士自比女性,即是将本意以较为含蓄的方式,通过女性形象具体地表达出来。
比兴一直为文艺批评所关注,《文心雕龙》“比者,附也”“附理故比例以生”。《诗品》“因物喻志,比也。”朱熹《诗集传·螽斯》“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刘勰、钟嵘认为“比”为附着情理而生,可以凭借外物来比喻志趣,比的运用目的是托物言志,喻事于理。王夫之《薑斋诗话》“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司空图《诗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在文艺批评者看来,运用隐喻的方式表达文意更为难得,也值得推崇。古人常以此为审美的重要标准评价诗和散文。《战国策》以“比”表达谋臣策士的内敛、深层的情感观念是符合传统审美要求的,受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用比喻不道破谋臣的深层情感,既显得委婉又表意真切。探究《战国策》如此创作的深层次原因,得出作品受到了屈原香草美人创作传统、汉对楚文化的传承发展以及社会现实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
(一)屈原香草美人自比手法的影响
运用比兴手法作为文学创作的手段,自《诗经》起就为中国古代文人所常用。战国末年屈原将比兴运用到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开启了用香草美人自比的时代。游国恩《楚辞女性中心说》认为,《诗经》虽为比兴之源头,但以“女人”做比兴素材的文学表现技巧起源是屈原的《楚辞》。游国恩还在《楚辞论文集》中指出,屈原最重要的比兴材料就是女人。用女人象征作者自己,用被心仪的男子辜负抛弃的女人象征自己的遭遇。
而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屈原“正道直行”,事君“竭忠尽智”,面对“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残酷现实,岂能无怨?作品在作家所处环境、身世、心境的影响下,自然也形成了与之相称的语言风格。司马迁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文约”“辞微”而“指极大”“见义远”,意指屈原运用比兴手法以表达自己坚贞忠信的情感。“女以喻臣。言己虽去,意不能忘,犹复顾念楚国无有贤臣。”(王逸《楚辞章句》)王逸认为屈原自比弃妇,以冰清玉洁、信而见疑的弃妇形象象征怀才不遇的贤臣。这种创作方法可以“多称昆仑冥婚亦妃虚无之语”(班固《离骚序》),以细腻、入微的笔触,淋漓尽致地表达无法以男性身份表达的哀怨、眷念、关切、激愤、埋怨等多种情愫。使用比兴的创作方法还可超越法度、经义,运用“诡异之辞”“橘怪之谈”“捐狭之志”“荒淫之意”的表现方式发愤抒情,寄托其内心的复杂、充沛的情感,更加显得其对于君王的情感缠绵徘恻,真实感人。文约、辞微的创作手法指的是其通过细碎微小的香草、美饰指称佩戴、喜爱它们的人品格高洁,用不值得为人称道的男女情感托喻君臣之义,开创了用香草美人自比的先河。
(二)楚文化对汉文化乃至《战国策》编撰的影响
屈原的作品集中代表了充满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的巫祀文化。屈原是中国最早、最伟大的诗人。《文心雕龙·辨骚》对屈原的评价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对后世影响深远。另一方面,汉文化实质上是楚文化的延续,楚汉并未因战乱而分割,在精神上、在文艺上,均表现为高度的统一。譬如,西楚霸王项羽的《垓下歌》、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都可以说是对楚文化的沿袭。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方面,汉基本承袭了秦的体制,但在文学艺术领域,汉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特点。楚汉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汉在艺术上的表现。
《战国策》在西汉成帝年间被整理成册,而非战国、秦或者楚汉争霸时期。由刘向所述的《战国策》成书背景可知,此书各篇的作者并非一人,各个散落的文本经过多人多年的收集、加工。汉成帝年间,刘向对这些留存于世的资料做了校正、编辑,采用了按国别分类编排的方式,编辑汇总成书《战国策》。虽然经历了多年的流传,又经多人收集整理,但依然不能忽视最终编撰成册年代对其的影响,成书年代的文艺领域对楚文化的承继关系在作品的最终成型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三)作品展现的社会环境影响
作品与其展现的时代和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应是相吻合的,《战国策》各篇作品也应在客观条件和主观作用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与战国时代背景相符的语言形式。要全面、理性地看待谋臣策士以女性自比的缘由,也应该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样才可以透过作品表达看到作品反映的社会环境。
《礼记·王制》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士原属于贵族的最底层,社会地位比较低。但随着周的式微,各诸侯相互征伐的活动越来越频繁,社会环境相对松散。战事频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侯王求贤若渴、养士之风日盛等诸多因素,促成了士阶层的兴起并不断的壮大。士阶层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游弋于权贵、君主之间,他们对君王的心理把握得尤为精准,对各势力群体的利害关系有着敏锐的洞察。在统治者重视人才、渴求人才的前提下,当时社会逐渐形成了士人与统治者之间的某种人身、情感依存关系。
在诸侯争雄、战乱频仍的春秋战国时代,丈夫与妻妾、主君与门客、君王与臣子的关系都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这不仅为屈原以香草美人自比提供了现实参考,也为《战国策》的创作者提供了现实依据。
综上,《战国策》对比兴传统的继承主要体现在:首先,承袭香草美人传统,以女性形象作为比兴材料,在比拟形象上与屈骚相近,是表达情志、寄托主观思想的媒介。其次,传承了楚文化的艺术特点,以浪漫主义的色彩加工艺术形象,将虚构、想象、夸张发挥到了极致,塑造的形象鲜明生动、富于艺术创造,叙写对象具有着寄托思想的功能。第三,在创作背景相同的社会环境下,受君臣关系、情感依附等因素影响,以男女之情喻君臣之义,以女性坚贞、淳朴、娇弱的特点喻士人忠贞、守一、卑下的现状。
四、《战国策》对屈原香草美人自比的发展
《战国策》在以女性自比方面虽然与屈原香草美人在比类对象、表达情感上相似,但整体上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一)比兴对象由神圣到平凡
屈原的香草美人形象多为高洁、神圣、完美的神女化身,以香草以比喻自己高洁的情操。譬如云中君赴约前在撒满兰花的汤池里沐浴;湘夫人用桂木、木兰、辛夷、薜荔、芷草等美好的花草搭建爱巢;山鬼身着薜荔衣,以石兰、杜衡等香草为装饰;离骚美人以荷叶为衫,芙蓉为裙,香草为饰。高洁的美人形象传递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乎世人的傲然。与此不同,《战国策》作品中谋臣策士的自比,卑微低贱,以使女、吴人、楚人妻、新嫁妇等平凡人做喻,并不标榜自己的高尚情操和铮铮傲骨;仅仅以求得生存为出发点,但求与为难自己的人和谐同处一室,不要同室操戈;对于君王的情感也是发乎情止乎礼,不似屈原作品中“怨”的情感;《战国策》中的士人只求君王理解自己,消除君臣疑虑,不再怀疑自己有异心。
(二)情感表达由激越到和缓
和屈原激越的情绪表达不同,《战国策》中士人的情感表现方式更为写实,也更为理性。屈原的《云中君》《少司命》《山鬼》莫不是塑造完美的女性形象,哀怨、痴情地等待着真命天子的到来与眷顾,文笔凄厉动人,发愤抒情,情感激越。如“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的落寞凄苦;“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悲愁离忧;“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的腹诽怨怼。而《战国策》各篇章中谋臣策士较多冷静而客观地阐述故事里他人的境况,仿佛不关乎自己,却间接地影射着现实的自己,情感表达含蓄内敛,看起来波澜不惊,一副无风雨也无晴的坦然景致。
(三)创作背景由出世到入世
“屈原放逐,忧心憔悴……以泄愤感,书写愁思。”屈原遭放逐,心系国家命运,感情激荡不可遏制,如果说屈原的创作是一种情绪化的宣泄,那么《战国策》则是作者理性酝酿下的产物。前者重在表现情绪与情感,后者通过设喻传递理念与方法。屈原的作品是怀着愿为理想而慷慨赴死的心态创作的,而《战国策》描写的众人却是带着苟活于乱世的心态。前者志在高远,后者活在当下。屈原表达的是自我内心,士子们表达的是处世方式。一为理想而引吭高歌,侧重自我欣赏;一为务实而作小服低,重在解围脱困。
(四)表达方式由独白到宣言
屈原的香草美人喻君臣关系,士人们的江上处女、二妻形象,同样也定位为服务君王,不同的是形象地比喻了同僚关系。屈原的作品更似写给君王阅读的表白信,如《橘颂》由描写橘树的外在之美,转而赞叹内在之美“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通过歌咏橘树内外兼修之美,进而剖析表白内心,向君王传递其独立不迁、从一而终的忠君爱国品质。《战国策》中的设喻更似士人想与他人分一杯羹的求和宣言,只为了更好地合作相处。无论是江上处女的无害,还是阳僵仆妾的忠信,都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基础上的主动示好。
(五)艺术表现由抒情到叙述
艺术表现上,屈原“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其作品《湘夫人》《云中君》《山鬼》《少司命》画面感强,描绘众神女思慕夫君之情,为了凸显高洁形象赢得青睐,她们以香草为饰,纵横四海遍寻心上人,却终未能相爱相守。屈原作品叙事性不强,人物具体所指亦不明朗,抒情成分居多,极力营造心悦君兮君不知的情绪氛围,在如歌如泣的凄美语言、惆怅笔触中,蕴含着作者坚贞如磐、清雅似兰的精神品质。《战国策》中的士人更多地以通俗性的语言叙述一个个简单易懂的故事,故事性强,但抒情、修饰性词语不多,通过简洁的叙述与暗喻的方式,旨在只言片语中打消别人对自己的恶意,语言表达中示弱求和的因素多过清高的傲骨之词。
通过《战国策》与屈骚比较明显的差异,可以归纳得出《战国策》对比兴创作手法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含蓄委婉,自然真实。如羚羊之挂角,人工刻意的痕迹淡化了,流露感情更加自然真实。由以神圣高洁形象自比发展到选取普通平凡的女性为比拟对象,增强了事件的真实感,弱化了作者与读者的对立感。《战国策》中所描绘的女性形象,减少了主观的情感投射,以一种意蕴深远、自然而然的方式来喻意,营造了较含蓄丰富的艺术意境。二是文本叙事功能增强。屈骚运用艺术烘托、艺术夸张手法,以环境氛围渲染为主,烘托主体情怀,侧重抒情。《战国策》以事明理,通过叙事增强比兴部分的可读性、故事性,起到暗喻的作用。三是文体由诗歌发展到散文,运用范围逐渐扩大。从单纯的抒情诗,逐步扩展到有叙事功能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