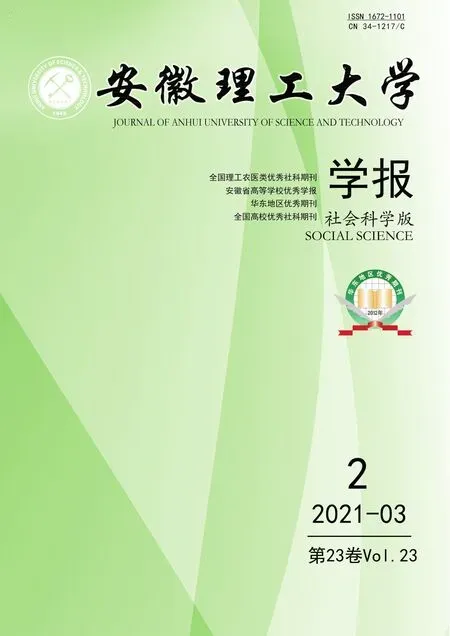符号表征视域下的区域形象传播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
何梦婷
(安徽艺术学院 新闻播音系, 合肥 230000)
符号伴随着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传播革命的演进也始终离不开人类使用符号所从事的意义生产与表征活动。从信息传播视角而言,人类传播是一个以信息为媒介的社会互动过程,社会信息是由符号和意义构成的,符号是信息的外化形式或载体,实现了信息传递与意义建构。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化的世界之中,符号无处不在。从象征性社会互动视角而言,人与人之间正是在不断地制造象征符、传递象征符、解读象征符的过程中完成意义的表征与建构的。
然而,符号体系一旦形成,也具有相对独立性,作为能动的力量作用于现实社会。比如语言符号是人类创造并掌握的第一套视听符号系统,但今天的语言符号也能够规范和制约人的行为。这是因为语言符号体系的内容和意义是人类在长久的生活实践中以“社会合约”的方式逐渐形成的,具有很强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这种建立在“合意”基础之上的符号表征体系已经不仅是人类意识的体现,同时也具有某种“社会规范”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符号具有不可变性。作为人类意识的产物,符号是人为赋予意义的外在表现形式,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旧体系的部分乖离和改造以及对新事物内涵与外延的双重建构。
一、传播符号与区域形象塑造的关系
(一)对区域形象的认知
在我国,省份区域是由不同地市级城市所组成的公共空间。从这层意义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区域空间中包含了多重的城市空间。对于城市空间的阐述可以追溯到美国建筑学家、人本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他在对城市空间的研究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城市意象”概念,并在《城市的印象》中就“区域”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即“区域指的是观察者心理上所能进入的城市较大面积,并且本身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可从内部去认识。”以凯文的定义为参照并结合我国的行政区划界定,本文认为区域形象可以理解为是人们对一个区域中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土人情等形成的整体印象和看法。
不同于单一的城市文化符号与城市形象建设,区域的范围更加宽广,其形象塑造也更具复杂性。但是由于历史文化、行政区划和现实发展等因素,作为具有地理接近性和心理接近性的城市而言,他们在追求彼此发展与开创特色的同时也必然保留了某种一致性与和谐性,而这正是塑造区域形象与传播区域文化的基石。区域形象的建设离不开区域范围内所辖城市的协同发展。拥有不同风格属性但又具有密切地理关联的城市,共同构成了区域形象传播的空间媒介样本。简单来说,安徽省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只取决于某一座城市,而是来自于安徽省下辖的十六城。古徽州的景观建筑、舌尖上的美味徽菜、安徽的风土人情等等,这些人们所能够感知到的一切“安徽元素”共同构成了对安徽省形象的综合认知。从城市空间上而言,这十六城是各具特色的独立个体;从区域空间上而言,它们在政治圈、经济圈与文化圈中都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结。所以,区域的发展既需要各个城市的力争上游,也需要彼此间的协同合作。
(二)区域形象的内核与外化
区域形象的建构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内化的文化意义与外化的表征形式。内化的文化意义又可以包括三个层次,即“表层文化、中间层文化、深层文化”。表层文化指的是区域内通过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文化,由可感知的有形物质文化组成;中间层文化是一种行为文化,包括法规制度、道德准则及其它行为方式中体现出的人文因素;深层文化主要指的是精神层面的文化,包括价值体系、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
外化的表征形式应当是一种“携带意义的感知”,这也是符号研究者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对符号的解读。符号是城市与市民进行沟通的一种直观方式,是城市内涵的延续,是历史积淀的外化。从区域形象塑造与传播角度而言,符号既可以表示存在着的物质实体,又可以表示各种非实体。具体来说,作为意义感知而存在的符号在区域空间中主要包括建筑、景观、雕塑、方言、服装、美食、习俗、戏曲、标语、吉祥物、宣传片、摄影作品、文字作品等。具有标识性的区域符号承载了区域的时代特点、形象定位、文化内核和发展愿景。内化的文化意义必须通过符号来进行表达,没有无符号的意义,也没有无意义的符号。
二、区域形象传播中的符号表征体系构建
(一)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建构
区域形象的有效传播应当建立在拥有一套完整的符号表征体系基础上。符号的早期研究者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人类提供了认识符号与建构符号的具体方式。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任何语言符号都包含两个方面,即能指和所指。能指是声音和形象部分,所指是概念及意义部分。比如“杯子”的能指是它所具有的外形特征,包括它的形状、颜色、大小等元素,即区别于水壶、盘子等的独特形象。杯子的能指还包括它的发音,比如中文“bēi zi”、英文“cup”等不同的声音语言。“杯子”的所指是指它具有的某种意义,即它具体的使用功能和它具有什么特殊象征含义。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指出,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建立是人为的,也是任意的、武断的,没有具体的规则可言,是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但是这种人为建立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经过一定时期的传播、使用和积淀,便会成为具有较稳定形态的符号,不会随意变更,除非再次获得集体的认同与赋权。
因此,区域形象的构建不仅可以使用原有的能指和所指关系,也可以根据区域内的城市发展、文化创新、未来愿景等建构全新的能指或所指。安徽省的部分城市拥有独具代表性的城市吉祥物,比如黄山市的吉祥物“豆豆”、滁州市凤阳县的吉祥物“凤凤”和“阳阳”等,都是通过建构全新的所指来进一步塑造城市形象和深化城市文化传播。作为保有原始徽州特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安徽省,可以以省级区域为支点,借鉴已有的文化内核所指,构建全新的吉祥物能指。
(二)含蓄意指的“神话”建构
意义的传递与获取需要受传双方完成对符号的编码与解码,而具有共通的语意空间是完成信息传递的基础。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认为符号的浅层功能是“直接意指”,在直接意指层面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义相对贫乏。在文化传播中,能指与所指被放置在了新的语境当中,原有的意义被部分淡化,新的意义被注入到能指与所指的建构中产生新的能指或新的所指。这个新的意义是对原有意义的扩展和延伸,而这种延伸又是与新语境相关联的。
在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看来,新的意义产生的过程是一个“神话”的过程。这里的“神话”并不是指神话故事或宗教神话,而是指意识形态的建构。当一个区域所倡导的某种主流观念进入符号的建构过程中,建立起能指与意指间的连带关系,使编码和解码能够有效完成意义的传达和转化,“神话”便在意义建构中完成。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化的有效传播不仅要求人们要具有共通的语意空间,还需要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价值体系。省级区域中的人们不仅具有地缘亲近性,还具有相似的文化习俗。正基于此,区域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才有其“神话”赋权的共通空间和赖以建立的基础。
(三)区域形象传播中的符号提取
区域形象传播中的符号可分为三类,即历史性符号、标志性符号和叙事性符号。历史性符号,是指区域历史沿革中留存下来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符号。这种文化符号具有不可逆性,除语言符号形式外,主要以实体景观作为符号的呈现形式,其能指和所指之间“约定俗成”的解释较为稳定,是一种相对固定的存在。历史文化符号是文化传承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一个区域、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与定位。标志性符号,是指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根据文化定位和传播方针人为建构的新的能指或新的所指,包括城市新地标、文化标语、吉祥物、其他文创产品等。它们是区域文化建设发展的新产物,也是区域文化传播的外在集中体现。这类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对固定,即他们在一定时期内行使着较为统一的表征意义。叙事性符号,是指需要依靠人来进行含蓄意指建构和传递的文化符号,包括戏曲、音乐剧、话剧等影视作品乃至人们日常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人的能动性特征决定了人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其它静态符号所不可比拟的“流动”角色。在人际传播或大众传播过程中,人们对于文化的叙事性解读和演绎才真正让文化变得鲜活而生动。“叙事是人类的自然冲动”,它既是一种表达欲望的展现,也是一种最直接的文化传递形式。在叙事中完成的文化传播具有其他文化符号无法比拟的自然性与说服性。
安徽省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性符号,但是在标志性符号和叙事性符号的建构上缺乏一定的体系和前瞻性。而且,即使拥有丰富的历史性符号,但在面对其他同样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承的省级区域时,由于各区域的历史性符号都独具特色故伯仲难分,这就更加要求安徽省在进行区域形象塑造和传播时,必须重点建构标志性符号和叙事性符号。比如通过建构新的能指着力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和代表性的形象标识,在原有文化基础上创新标志性符号。除此之外,还要善于运用“流动”的叙事性符号。良好区域形象的传播离不开区域内人的“活代言”,因此加大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人才的培养,对安徽形象的传播具有深远意义。匠心独运的符号提取既是安徽省区域建设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区域软实力的应有之义。
三、区域形象传播中的视觉修辞框架识别
视觉图像作为人类交流和传播的表征符号,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人类具有“爱观看”的特征。“无论我们将有所作为,或竟是无所作为,较之其它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 理由是:能使我们识知事物, 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者为多。”但是早期对于“视觉”的研究认知,主要体现在艺术实物上。比如切萨雷·里帕(Cesare Ripa)在《图像手册》一书中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艺术作品中的隐喻。 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从电影理论入手, 探讨了电影中的视觉文化。 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H·Gombrich)在《艺术与错觉: 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中, 从心理研究角度剖析了艺术中的视觉再现, 预示了视觉文化研究的出现。 以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研究者对视觉文化的研究更为严谨。结构主义者提出了视觉文化的转向研究,他们从社会建构角度出发,认为视觉研究应当从艺术史、文学史向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现象学等领域交错发展。基于此,日常传播背后的视觉修辞和隐喻以及视觉符号的建构越来越被研究者们重视。
相较于非视觉符号,视觉符号在感官上能够给人以冲击之势,营造更为深刻的“鲜活”之感。而视觉符号的意义实践需要在特定的修辞框架中得到呈现。在区域形象的传播过程中,被选择和提取的传播符号一般具有意指建构的可塑性。而在当下的“图式社会”中,含蓄意指想要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还需借助具有视觉刺激的“像化”形式来呈现。“像化”的过程不是单维的意义生产,而是多维融合的意义实践。
(一)场域识别:图式与认知
当下信息的传播方式正逐步演变为以“像化”为主的视觉生产与传递。图片、动画、短视频、直播无不在以直观的视觉体验建立起与受众之间的联结。“图式”成为媒介信息和大众文化呈现的主要形式。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预言的“地球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这个“重组的部落社会”中,我们正迎来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关于“图像世界”的预判,即视觉图像以及那些并不必然具有视觉性的事物的视觉化在戏剧性地加速发展。图式工业时代悄然而至,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从一种身体体验关系转变成一种视觉体验形式,而视觉场域也被大众传播媒介聚焦为意义生产和争夺的重要场所。
在视觉场域中,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图式化”识别并不是毫无章法的,这种识别所遵循的规则主要来自于人们对过去生活经验的总结。按照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框架分析》一书中对人们认知世界提出的“框架”概念,“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框架”理论类似于皮亚杰(Jean Piaget)所提出的“基模”概念,它们都强调“认知结构”在人们识别事物过程中所扮演的某种具有制约效力的角色。因此,视觉场域中区域形象的传播也不可避免会受到人们已有认知框架的制约。
在安徽省的区域形象构建中,最广为人知的形象认定即“徽文化”。徽州文化是极具历史传承和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形式,给人以“低调”“严肃”“庄重”“古老”“朴实”等感受,主要体现在徽州古村落群、徽派建筑、徽州文化、徽州民俗风情等方面。虽然古徽州的一府六县在地理区位上并不等同于现在的安徽省,但安徽省文化传播和区域形象的建设根基离不开徽州文化。对于着力寻求现代化发展的安徽省而言,“徽州”的认知框架既是对安徽省深厚文化底蕴的认同,也是对安徽形象固化的刻板认知。
(二)属性识别:实体与要素
在视觉修辞框架的识别过程中,“外在”的形式特征是形象建构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决定人们认知的视觉符号呈现。属性识别是对区域形象外在领域的表层辨识,它一般以直观、浅在的表征符号来体现。但是视觉观赏者在识别过程中接收的并不是一个个单独的要素,而是有多重要素付诸其上的实体。
实体部分具有独立性,是能够离开视觉场域而自持和呈现的。比如在《中国一分钟·地方篇》系列短视频《安徽一分钟》中出现的“城楼、黄山、金佛、宏村、茶园、梨园、高铁、‘墨子号’、浮法电子玻璃、液晶面板、“四大件”、光伏电站、孩童、气球、风车、单车、大鼓、帆船、黄梅戏、文房四宝、徽商宅院、游客、新安江、小岗村、毕业生、安徽电视台”等等,它们都是具象的、可以被对应的、能够独立存在和呈现的个体,但是它们也可以从属于更大的整体。在视频中,这些个体就从属于更大的整体——“安徽印象”。
要素与实体不同,它不能独立存在,需要依附实体而存在,要素只有伴随实体呈现才具有“言说”的价值。比如《安徽一分钟》中黄山的“奇绝巍峨”、宏村的“古朴静谧”、孩童笑脸的“天真烂漫”、毕业生抛帽的“兴奋”、戏曲演员的“演绎”、城市建筑群霓虹灯光的“五彩斑斓”等等,这些要素对应的是抽象物,无法单独呈现,需要付诸实体部分存在并被经验。
基于视觉感受中的形象构建需要观者将实体与要素进行联结认知,即进行属性识别。因为虽然实体可以自持并独立呈现,但观者对实体性质的理解取决于付诸其上的要素。要素可以对实体进行意义赋予,否则实体的呈现将失去其意义表达的能力。比如孩童作为实体,孩童的“表情”作为要素,“微笑的表情”与“悲伤的表情”直接决定了观者对孩童这个实体意义的认知。在《安徽一分钟》中,茶园的绿意盎然勾勒出安徽省的茶文化形象,“四大件”的极速下线建构着安徽省家电生产基地的产业形象,“墨子号”卫星的发射被解读为创新高地的城市形象……可以说,观者正是在对实体与要素统合的“像化”识别过程中,实践着对视觉场域的基本认知。
(三)隐喻识别:在场与缺场
“符号是信息的感性坦露和外在表征”,作为一种“外化”形式,符号所提供的形象传播是显性的、在场的,而意义的呈现并非都以“明见”的“在场”方式来传递。所以,观者在认知过程中不仅要在视觉场域中识别明处的形象图景,还要于视觉场域以外的“缺场”中窥见隐性的形象意指。
视觉修辞并不单指图式化的呈现方式,视觉修辞包括“语言视觉修辞、图像视觉修辞以及综合视觉修辞”三个方面。如果单纯地将视觉修辞理解为纯粹“图式化”的呈现方式,那么形象符号的意义将变得肤浅化和贫瘠化。所以观者在对视觉对象进行信息处理时还需要注意关照视觉感官以外的“缺场”信息。刘丹凌在研究国家形象的视觉识别框架时提出,无论是静态的文本(新闻图片、漫画等) ,或动态的文本(形象宣传片、纪录片、电影电视、短视频等) ,“它们至多框定了某些人物、事物、景观、视角面、状态、过程,或者经历,但是却难以自足地构成一个深邃的意义体系。”
因此,对于区域形象的传播不仅需要对文本中已经出现的在场信息进行解读,还需要将被观看的对象放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时间、地点、环境中进行整合理解。其实质就是通过对“缺场”信息的联想,解读特定符号背后的隐喻。尤其是在区域形象的构建过程中,多数是具有隐喻意义的符号暗指。比如《安徽一分钟》中“文房四宝”是“书写徽风皖韵”的隐喻,“黄山”是“安徽如画,迎客天下”的隐喻,“浮光电子玻璃”是“科技创新之城”的隐喻,“粉墙黛瓦”是“风景如水墨之画”的隐喻……这些缺场的隐喻符号是观者进行思想联结的起点、中点或终点,与显性的在场意义共同建构出形象符号的表征体系。
(四)情感识别:触点与共情
对于形象传播的信宿同时也是视觉场域中的观者而言,形象传播最终所产生的认知效果还取决于来自个体的情感识别。
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等人在“伊里调查”中提出了“IPP”指数,在对IPP指数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中,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发现信宿个体对信息接触是“有选择”进行的,并据此提出“选择性接触假说”。“选择性接触”机制的存在说明,受众在信息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是具有能动选择性的。约翰·伯格(John Berger)也认为:“我们只看见我们注视的东西,注视是一种选择行为。所以从选择性接触机制而言,并非形象文本中的所有视觉元素都能够获得观者的关注。意义的传递也并不都是完整或有效的。那么,哪些视觉元素可以触动观者的视觉神经并引起共情,是值得文本建构者和传播者进行探讨的。
在视觉场域的文本建构中,“共情”是对文本框架的基本理解和认知,是普遍意义的唤醒。触点是可以锁定观者目光与意识的聚焦点,通过激发观者内心深处的情感色彩,引导观者进行强烈的能动性识别。一个强烈印象的形成,需要适当地加强某些提示。所以,触点往往是对观者内心与记忆深处的碰触。具体来说,触点可以是“像化”视觉呈现中的一个元素,比如形状、色彩、文字、表情、动作等等;也可以是以文本为整体的视觉呈现,如塔川秋色。同样是徽州古村落聚集的地方,但每年秋季的黟县塔川因其绝美的秋色吸引着大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乌桕树上的“塔川红叶”在薄薄雾气中影影灼灼,粉墙黛瓦的徽州村落在片片红叶中投射出斑驳光影。塔川秋色是安徽形象文本中视觉修辞的直观呈现,也形成了对自然风光怀有探寻之心的观者的触点。但并非所有的形象视觉文本都能够给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产生理想的共情效果,也并非文本中所有的视觉元素及其外观展示都能够吸引观者的关注。所以,寻找能够产生情感识别的触点与共情之处,是继续深发安徽省区域形象传播与发展的可探路径之一。
四、小结
区域形象的建设与传播有赖于建构具有凝练意义和深度价值的符号表征体系。从地缘上和心理上而言,区域本身是存在边界的。但是这个边界并不影响观者对不同区域形象的认可。观者对外部的认知主要来源于每个人对客观物质世界概括所形成的心理图像。在符号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观者不仅可以观赏到风格迥异的视觉图景,也需要在纷繁复杂的符号元素中建立印象与认知。
作为一套完整的表意系统,区域形象符号不仅可以表征为物质符号与精神符号,历史性符号、标志性符号、叙事性符号,还可以表征为实体与要素符号、在场与缺场符号、触点与共情符号。这些符号体系之间并非是严整的、环环相扣的,它们不一定表现为并列或递进关系,但它们可以以不同的角色出现在区域形象的建构过程中,独立或者共同作用于观者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