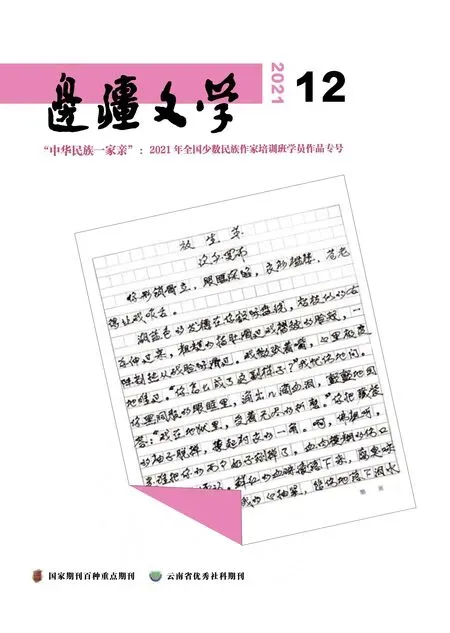莒洲,莒洲
朝颜(畲族)
一
被酷日无声炙烤的大地,缓慢流淌的河流,颓败倾圮的老屋……七月下旬,一座古村撞入我的视野,从无际无涯的竹海中,逐渐显露远古的面貌。
在南方,几乎所有的村落,都缘自一场因由各异的迁徙。一群人,抑或三五人,带着疲惫的肉身和惊魂甫定的内心,带着鲜少的衣物和为数不多的口粮。有时候,是躲避侵身而来的灾祸;有时候,是重新开辟一块生存的天地。深山、密林、僻远之所,是多数迁徙者热衷的安居标配。那里有自在的鸟兽、虫豸,有繁茂的植物、花朵,有足以哺养人畜的清溪,自然,还有适合生长五谷的土地。
放眼四望,我所身处的莒洲古村,委实拥有农耕生活所需的一切美好条件。古村坐落于资溪县西北部的高阜镇,像襁褓中的婴儿被群山层层包裹。地处闽赣交界的资溪县,县境内横亘着武夷山脉,耸立着鹤东峰、月峰山、野鸡顶、排尖嵊、犁头尖、笔架尖……自古便是层峦叠嶂之地。连绵起伏的山峰成就了资溪接近百分之九十的森林覆盖率,高居赣鄱之首。
村庄古称榉洲,因河畔、田畈多生长榉树而得名,后来更名为莒洲。我试图寻找它和古莒州即当今山东莒县的关系,未果。询问当地人,被告知只是为了简写而改成同音的莒洲。村民以邓姓为主,依着泸溪的流向,他们将村庄大致地分为上莒洲、中莒洲和下莒洲。置身于青山脚下,恣意生长的草木之间,我忽然想,这片土地被选中,被开垦,被越来越多的建筑填满,被道路、桥梁、小巷、房屋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人类活动区间,几乎是一种必然。
六百多年前,一位邓姓的先人,和天地合谋并确立了这样的必然。据史料载: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邓氏十二世守八公自小坪(今金溪县黄通乡)迁于泸溪之上莒洲,为莒洲迁居祖。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邓氏显四肇远公因避兵祸举家迁至泸溪三都茶园坑(今资溪县高阜镇莒洲村牛角尖),其长子邓福昌公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又迁至下莒洲,是为下莒洲开基人。自此,邓姓一族在上、中、下莒洲繁衍生息数代,耕作经商,布泽施恩,广结善缘,成为当地名门大族,历代进士、贡生、举人有一百二十五人之多,入朝为官者众,于清乾隆年间达至鼎盛。
如果将目光投向时间的纵深处,当年的邓公多么像一粒种子,落入一块天然肥美的土地。然后,风也调,雨也顺,天时地利人和一并簇拥着他,在这里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直到建立庞大的根系,在大山深处开出一朵清雅的梅花。是的,村里的老人说,这里曾经就是个梅花型村庄,人口众多。
这众多的人口在莒洲世代耕作,丰衣足食,送儿读书、学医、出仕,像中国大地上无数恭顺的良民那样,依从着帝国的价值标准,一步步寻求上升空间,在通往家族壮大的道路上勤勉而执着。
只是今天,一个曾经兴旺繁华的村落终究走向了没落。在村头的一块木牌上,我看见一份古村的简介:现有常住人口二十户六十余人。与之相对应的是:现存祠堂两处、牌坊一座、官员旧宅十余栋、古桥一座、古水车一座、古井一口、寺庙一座。自然,还有村头村尾蔓延丛生的杂草,倾斜的破屋上掉落的青瓦、豁口的阁楼、被遗弃的竹木器具……
没有往来的人群,没有田间劳作的景象,没有鸡犬相闻的热闹,村庄清冷得像一个遗世独立的孤寂老者,那些旗杆石、拴马石都安静了下来,那些手推磨、老水井都停止了使命的履行。而我,也只能从那些幸存的古老建筑、繁复的雕刻图案和门楣上的字迹中,依稀辨认村落旧时的繁华光景。
二
鹅卵石的古道,牵引我走向一座古老的牌坊。时间似乎是静止不动的,燥热的空气围裹成一个铁桶,没有一丝风可以扯破一个口子。我仿佛听见草籽炸裂的声音,是的,在牌坊的里里外外,见缝插针地长满了野草。
一座曾经风光无限的清代古建筑,正用它现世的荒芜暗示一个女子荒凉的一生。
这是一座节孝坊,高大的石门楼上,刻有“旌表儒士邓江屏之妻李氏坊”几个大字,两侧有石刻对联一副:“淋德荷纶音一片冰心昭日月;清操辉庙貌千秋壸范峙山河。”门楣上,还雕刻着精致鲜活的人物和凤鹤芝兰的图案。呵,这些充盈着道德感的词汇,这些彰显着高风亮节的图案,这些代表着王朝价值观的褒奖,让我如何联想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具体的人?可是,我仍然千方百计地想要找寻关于她的故事,想要将她从高高的云端上请下来,还原为一个真实的女人。
值得玩味的是,一个重要到让嘉庆皇帝赐建贞节牌坊的女人,竟然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族谱上,只记载着她的简易生平,生于1744年生,卒于1803年。人们只知道她是李氏,因为她的丈夫邓江屏在十二个兄弟中排行老八,村民们又称她为星八婆。是啊,一个婆字,昭示着她终其一生,都只是一个男人的附属。作为贞节牌坊的主人公,她的荣誉,她的光辉,她被刻在石匾上的生命轨迹,也只是由于她对邓李氏这个身份的执着坚守。
史载,邓江屏生于乾隆乙丑年(1745年),自幼敏而好学,博览群书,妙笔生花,名噪一方。乾隆己丑年(1769年),邓江屏出门求学,途中染疾客死他乡。这一年,其妻邓李氏年仅二十五岁。从十六岁过门,到六十岁去世,邓李氏与丈夫相守的时光只有短短九年。也许九年亦是一个虚词,因为男人要读书,要谋出仕,想必经常从这僻远的山区走出,从妻子不舍的目光中走出。九年了,他们还没有一个子嗣,李氏守着空房,等待着丈夫传来高中的喜讯,等来的却是丈夫病逝的噩耗。
可以想见,邓江屏一家在莒洲村当属大户人家。李氏面临的处境是封建时代众多失夫女性的困局,离开,抑或留下?无论哪一种选择,都难以朝向理想的路径。是她自己决定矢志守节的。她还年轻得像一朵盛开的鲜花,却从此收紧了身体里的花瓣。自然,她赢得了村民们的盛赞。几百年过去,没有人能够揣测她当时的真实心思,也许时代的规训早已在她心中设下了紧箍咒。但我宁愿相信,她的确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出路。
此后,李氏抚养叔伯之子为嗣,尽心养育教诲,勤俭持家,备尽辛劳,守孝三十五载,直到儿孙均有所成。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她不仅侍奉公婆勤勉孝顺,还以一己之力,培养出了两个庠生,终以贤孝品德感动了族人。她去世后,下莒洲有一位名叫邓超然的正八品修职郎,恰为太学生,在皇宫陪读,就把这个故事在宫里说了,不日传到嘉庆皇帝耳中,遂于嘉庆甲子年(1804年)建此牌坊,以旌表邓李氏节孝,并鼓励世人效之。
站在牌坊前讲故事的人还持有另一个版本,言及李氏过门前,邓江屏便已去世,因为父母已答应将自己许配给邓江屏,李氏认为必须遵守婚约和父母之命,坚持嫁入邓家,守节一生。在查到史料之前,这个貌似可以感天动地的升级版故事让我难过了许久。我想象一个俏生生的南方女子,她也许有粗而长的辫子,有小巧玲珑的身体,有怎么也掩饰不住的饱满和鲜活,然而她却有一颗磐石般的心,她骄傲着自己拥有所信守的一切美德,她将一生都活给别人看了。那些夸奖她,甚至以她为榜样的村民呢,谁曾关心过她的憧憬,她的梦想,她被生生按压在深宅大院里的青春和欲望。人们看着她一天天在枯寂中老去,熬成一盏孤灯,慢慢熄灭。人们关心的是她的贤孝品行,并引以为荣。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氏甘愿抑或无奈的牺牲,恰好是莒洲村过往繁华的一个注脚。
跨过石门楼,里面的房屋俱已荒废,萋萋芳草间残存有一块木牌,上书“贞节牌坊”几个大字。木牌不知何时碎成了四瓣,一个没有名字却名气很大的女子,在时间中面容模糊。
事实上,这样的贞节牌坊,在我到过的诸多古村落中,并不鲜见。在瑞金市九堡镇密溪村,有奉乾隆皇帝旨意为罗大璜之妻钟氏所建的节孝坊;在宁都县肖田乡郎际村,有乾隆皇帝传旨为萧行三之妻黄氏所立的节孝坊;在会昌县筠门岭镇羊角村,有乾隆皇帝命县衙为周道明之妻蓝氏所立的节孝坊……
这林林总总的贞节牌坊,背后无不印刻着女性的辛酸、坚忍和不忍卒读的一生。自然,还有更多与她们命运相似的女性,持守着同样的信仰,承担着同样的牺牲,但是并没有留下这样的牌坊。几千年的光阴里,女人们无不在一种看似坚固的信念中沉浮,演绎人生的悲喜剧。她们怎么会想到,终有一天,她们视若生命的女德会在时代的进程中轰然坍塌。
三
一声叹息,被村头的莒水收留。这条水量并不算丰沛的小河,应该比古村存在的时间更为久远。当年那个四处寻觅,匆匆赶路的邓公,想必就在此处听见了淙淙的流水声,然后蹲下身来,洗了把脸,也许还掬了一捧微甜的溪水以解干渴。我猜,正是莒水的清澈与灵动,牵引了山谷间升起的第一缕炊烟,草地上搭建的第一个简易居所。
农耕时代,大地上的生存无外乎开垦田地,栽种粮食。一座上古的水碓矗立在莒水之上,仿佛农耕文明的切片,将时间的遗存醒目地摊开在世人面前。回溯遥远的古代,人类的生存与繁衍,迁徙或安居,文明和进步,几乎都是被流水牵动的。在现代机械被发明之前,古人的智慧在水碓这样的器具上得以充分展现。
我曾不止一次听祖母谈起过踏碓的艰辛,为了吃上白米饭,人们在碓前消耗了漫长又繁重的劳力。往往是清早挑着一小担谷子去往碓寮,正午才能顶着烈日回返家中。其间一双脚踩着两块木板,周而复始,不停地踏啊踏,踏完一碓又一碓,仿佛永无止境。待从碓板走下来时,整个人踉踉跄跄,好像腿脚已不属于自己。许多年以后,当碾米机在村子里轰隆隆地鸣响,祖母已经不在人间。我遍寻不着一座祖母提到的人力碓,但总不能忘怀她说起过的那种苦。
水碓,应该是中国最早使用水轮的机械。它究竟是优于人力碓的一种智慧改进,还是与人力碓始终并行的一种工具,我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目前可知最早提到水碓的是西汉桓谭的著作《新论·离车第十一》:“伏义之制杵臼之利,万民以济。及后世加巧,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又复设机用驴骡、牛马及投水而舂,其利百倍。”其中所言“投水而舂”,即是水碓。
那真是以一当十,事半功倍的进步啊。没有物理学科,没有能量定律,也没有力的公式,却如此巧妙地借用了自然之力。不得不说,发明者的灵光闪现和奇思妙想近乎神迹。一座水碓被能工巧匠安置于河岸,流水推动着构造精巧的木质水轮,水车转动,形成一股强大的力,带动四个木槌错落起伏,不停地捶打着石臼里的谷物,舂出细碎的米糠,舂出白花花的大米。人们得以从繁复而低效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只需要耐心地等待就够了。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水碓房里的水车日夜不息地旋转,带动着人世的烟火,生生不息。
直到今天,莒州村的老人还记得从前的俗语:“斗米三下碓,不完就是碎;碓打磕头山,人丁就兴旺。”从前的莒洲村,在莒水的上中下游依水势分布着十一座古水碓,人们将之形象地称为蟒碓。可以想见,莒洲村的女人们,无须像我的祖母那样踏着人力碓辛劳地操持一日三餐的饭食。莒水的天然落差和莒洲村的物质富足,促成了农耕文明的发达。而我的祖母则没有这样的幸运,整个麦菜岭,鲜有适合安装水碓的地理条件,全村连人力碓都屈指可数。祖母需要去往几里外的地方,找大户人家借碓舂米。这些艰难,是后来父亲讲给我听的。当我接受了我们的村庄和家族曾经贫穷如斯的现实,也便对莒洲古村多了一份钦羡和敬意。
家庭、村落、地域的差距,从来不曾在时间中完美均衡过。就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村人都使用黄牛犁地,平原地区已经用上了耕田机,而我们一家还在用锄头一锄一锄地翻地。当打谷机震响四野时,总还有人裹着围裙,站在禾桶前一把一把地摔打着新谷。如今我已远离乡村,仍然愿意相信,慢生活和低欲求并没有影响人类的生存。只是对于节奏和效率的追求,对于高科技带来的舒适体验,人们无法拒绝,还在朝着更先进的方向孜孜以求地迈进。
从前,山村里安装水碓,是和风水有关的。一座水碓不歇地运转,意味着阴阳不断更新,生机无限。而碓声高起,则象征着声震山谷,妖邪勿近。另外,水碓的功用,远不止舂米。那些药物、香料、矿石、竹篾、纸浆、木梓、花生、豆子……凡是需要捣碎的物料,都可以交给水碓。傍晚挑来倒入石臼,任水车慢悠悠地转,木槌一声声地捶,清早起来,估摸着时辰差不多了,女人们便去收归屋场。
想来这样的场景,我是无缘得见了。而祖母终身没有使用过一次水碓,我的心里隐隐有一丝疼痛。我多么想和古时的女人那样,迎着朝阳从容地走向莒水,替祖母取回煮饭的粮食,哪怕一次也好。抚摸着略显粗糙的石臼内壁,我有一些恍惚。它本该在日夜的捶打中变得光滑洁净,可是现在,它被现代化的快节奏抛弃了,像一块寂寞的化石。包括那一架大型的水车,那一整个水碓房,如今都只是矗立在村庄的一道景观,一种装饰。
当所有的繁琐工序一律交由工厂和机械,对速度的追求越发天经地义,人们将袋装的白米如此便捷地从商场运回家中,还有谁会像古时的农人那样,耐心地等待与守候一抷粮食?当世界充满了急躁不安,慢反而显得如此珍贵和稀有,一幅手工的绣品,一杯石磨的豆浆,一块手雕的玉石……渐渐受世人追捧。然而,愿意为之耗费光阴的人,是少之又少了。
四
太多的荒凉,缠绕在莒洲古村的每一个细部。紧闭的门窗,斑驳的墙体,长满苔藓的青石板……能朝外走的人都走了,我环着村庄走了一遭,没看见一个孩子、一个年轻人,只有零零星星的老到无力出走的老人,还坐在老屋的木门槛边,好奇地打量着我。
踏着暗灰色的台阶,走上一个破落的院子。我以为无人居住,一抬头,却遭遇一双深井般的眼。老人坐在一张旧竹椅上,眼神孤寂、落寞,仿佛已放弃任何人世的抗争。这偌大的屋子,只有他一个人。竹篙、桌椅、扫帚、柴火、衣物,一切都零乱地散放着。老人瞧见我的到来,启动干瘪的嘴唇,开始了方言的叙说。他一定是难得遇到一个倾吐的对象,一直喋喋不休地诉说着什么,他似乎想告诉我他的境遇,他的一生,或是村庄的秘密,亲人的去向……可惜那方言于我是如此艰涩。在一个本地人的翻译下,我才勉强知晓:老人已经九十二岁了,三个妻子俱已去世,儿女们全都去了外面,只剩下他独自在村里生活。幸好有一个人,每天来帮他做饭,简单地操持些家务。我猜,那个人,也是老人,只是略微比他年轻一些而已。
站进厅堂里,有难得的凉风吹上身来。我看见神龛上摆着一幅放大的女人黑白像,她属于老人的第几任妻子呢?没有人告诉我。但可以猜测的是,她一定在这个家庭里留下过子嗣。毫无疑问,屋子从前是气派的,四壁是厚实的木板,房梁上有粗壮的木头,大门左右还踞伏着方方正正的拴马石和旗杆石。我想象从前的生动与繁华:一家人其乐融融,儿孙绕膝,宾客盈门,有时候,客人的马儿被拴在门前,也许还有稚童前来投喂草料。昔日的繁华还写在墙头的砖雕和窗棂的木刻上,从前的人,如何能预知,最后只剩一个垂暮老者勉强撑持着一幢大屋。
要知道,莒洲古村曾经是资溪县城官道城墙所在地,村头至今仍堆砌着进城大门的残骸。它指向一个历史事实,村子里曾经走出过不少显达的官员,他们在故里修筑了足以迎来送往的官道,修筑了宽阔的庭院,营建了属于大户人家的生活规模。如今那些深宅大院生机寥落,门锁多半已锈迹斑斑,墙内墙外荒草相连。一位暮年老者最后的留守,愈益加深了古村的荒凉感。
就在莒水边上,一条青石铺就的古驿道朝向村外延伸。这条近十公里长的古驿道,北通南城县,南接福建省,是当年外界进入莒洲村的必经之路,也是两省商业往来的交通要道。那些盐啊,茶叶啊,布匹啊,草纸啊,人们生活所需的一应物资,便是从这条古道上源源不断地传输着。可以说,这条路见证了莒洲古村曾经的重要地理位置,也见证了莒洲古村商业发达的辉煌过往。
在莒洲古村,曾有几百年的手工造纸传统。这里有郁郁森森的竹木,有不息流淌的溪河,具备造纸的天然优越条件。老人们的回忆大多来自上辈人的口口相传,据说,曾经的莒洲古村,商人络绎不绝,曾经的莒水也比现在水量丰沛,其间运送草纸的排筏满河穿梭,热闹非凡。自然,莒洲也有众多商户,他们沿着古道和莒水南来北往,在城乡之间不断开拓着商贸事业。
一代一代出仕或经商者,使得莒洲古村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着异乎寻常的繁荣兴盛。莒洲古村的讲究和地位,从遗存至今的道路和建筑名称便可见一斑。譬如步云路、登科巷、文元巷、郞官巷、千善巷、官厅、外翰第、大夫第、千户第……无不透露着昔日的鼎盛。譬如一座有着二百五十多年历史的古石桥,亦出自本村一位任职于官府的要员。他告老还乡之时,恰逢六十大寿,各地乡贤和他曾经扶助过的人,带来丰厚的寿礼寿金,为他祝寿。他却将收到的礼金全部捐出,在莒水之上修建了一座石桥,取名“六寿桥”。这样的建筑,在莒洲古村不止一座,作为一种独具乡土特色的公益事业,它将古时乡绅官员“中国智慧式廉洁奉公”的传统以建筑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一个如此繁华的村落何以走向荒凉和破败,人们试图用各种方式阐释其中缘由。于是,我又听到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相传邓守八携妻儿在水草丰美的莒洲安顿下来后,幸运地遇到了聚宝盆,村子渐渐兴旺了起来。莒洲殷富的消息传到朝廷后,皇上派了个太监下来调查。这个太监走到关山口,路边有两株枫树,原是宝盆所生,经山神点化,枫树的枝丫刚好形成一人多高的门状,凡过往者,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方得顺利进村。但是太监恃着皇命在身,坚决不肯下马,结果官帽被挡,掉在地上。他一气之下,拿着尚方宝剑把枝丫劈断,回去还做了一番假汇报,夸大其词,说是万国九州,莒州占一州,竟然没有交过皇粮国税。皇帝未辨莒洲与莒州之别,着令莒洲解军船,运漕粮,从南城运到北京,一年一运,一运两船。一个村完成一个县的漕粮,其惨状可想而知,莒洲就此败落了下来。
民间传说亦真亦假,自然不可作为正史来听。事实上,在工业文明逐渐取代农耕文明的时代进程中,由乡绅维系的传统秩序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必然要走向衰落。
五
一座古村将走向何方?当她渐渐成为人们逐梦的束缚,奔逃的居所,那些祖先的耳语,厚重的日月,光辉的片段,被莒水灌溉过的梦境,该如何被记取,如何靠近一个匆匆的现世?
回望莒洲古村的前世与今生,她似乎不算走运,被深情庇护过的子民遗落在大山深处;但她又足够幸运,在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和土坯房改造中完整地存留了下来。除了自然的衰败,鲜有人为破坏的迹象。现在,她将全部的骄傲与伤口都裸露了出来,像一只伤痕累累,威风不再,等待发落的虎。
是的,众多保持原貌的明清古建筑和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使得莒洲古村和一只真正的虎一样,已经为世间所稀有。
我注意到古村重新被珍视,是在修葺一新的星六公祠里。推开老旧的木门,祠堂宽阔,天井明亮,屋瓦和椽檩呈现新旧色交杂的状貌。显然,修复后的祠堂长年有人打理。刷得雪白的墙壁上,郑重地挂着几位重要的先祖画像和邓氏家规。其中图文并茂,追溯着莒洲邓氏的来历,记载着开基祖的荣光,感念着先人的功德。祠堂的一角,还被布置成农耕文明的展示厅,那些旧时的犁、耙、斗笠、蓑衣、石磨、风车、土灶……有序地陈列于此,模拟着古村从前的烟火日常。
另一幢建于清乾隆庚午年(公元1750年)的超然公祠,则在不久前被小心翼翼地拆除。我站在祠堂的原址前,脚下踩着鲜红的爆竹碎屑,听说,一个隆重的重建启动仪式刚刚在这里举行过。超然公祠,是莒洲邓氏的总宗祠,乃当年朝廷为表彰邓超然的功德,批准由建昌府出资并主持修建而成。祠堂原有上中下三厅,正面门楼分左中右三道,巍峨气派,拆除前仅剩前厅门楼和三面墙体。即便如此,它仍然是莒洲古村最重要的人文景观之一。
如前文所述,这位被赐建祠堂的邓超然公,即是直接促成邓李氏贞节牌坊修建的重要人物。他外任为官时,出资于甘泉源上修筑二善桥,结束了村民进出需涉水过溪的历史。他荣归故里后,又致力于宗族和村庄的整治与缮建,修族谱、建宗祠、立族规、兴教育、办书院、造路桥,在乡邻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
现在,人们将各种古老的构件细心地拆卸下来,其中有雕刻着祥云、龙凤、麒麟、鹤、鹿、鱼、花草和达官贵人等图案的石板,有雕刻着皇家所赐“恩荣”二字的长形石匾,还有雕刻有精美对联的整石门框……人们打算以修旧如旧的方式,重现超然公祠的雄伟原貌。不仅为缅怀先祖,纪念宗族曾有过的昌荣,也为修复和保留前清留下的珍贵文物。
2017年8月8日,莒洲村入选第一批江西省传统村落名单;2019年6月6日,莒洲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接连到来的转机,为超然公祠和莒洲古村启开了一道重生之门。
一幢庭院深深的邓氏祖居,则被精心规整和修饰,挂上了“国医馆”的典雅牌匾。听说,主人已联系好一位知名的老中医,准备邀请他在村中住诊。院落内,石墩、石门、石地砖,无不透露着时间的风霜。一位干净利落的老妪迎了出来,她的一头花白长发束成马尾甩在脑后,若非问询,我不敢相信她已八十高龄。就在这座青砖黛瓦,已经无法考证年头的老房子里,女主人送出了数位新中国的科级干部。房屋的厅堂遵循古意而陈设,内室则安装了现代化的水电设施。老人说,在林场上班的小儿子,每天下班后都回来住。其他在县城工作的子女,则隔三叉五返家团聚。这种既拥有高古风情又享受现代舒适的生活,着实令人心生向往。
就在大多数乡村和城市长得越来越像时,人们发现,乡愁无处可觅。如莒洲古村留守老人这样的原生态生活,已经成为一种奢侈。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保护和珍惜那些古老的即将消逝的事物,越来越多的人从城市涌向乡村,吃柴火灶烧的饭菜,住充盈着古味的屋子,或者带孩子去田里玩一次泥巴,在小溪里戏一次水……人们需要暂时慢下来,去广阔的天地间安放疲惫的身心,松开绷紧的神经。
穿行在莒洲古村的角角落落,看篱笆墙内玉米正在抽穗、豆角爬满了竹架,房前屋后指甲花开得自由烂漫,柚子树垂挂着累累果实,阳光下有摊开晾晒的红辣椒,屋檐下有堆成小山的劈柴。我在沉寂中渐渐嗅到一种生机,它似乎正在悄悄滋长,不动声色地蔓延开去。这些年,通往古村的水泥路修得四通八达,曾经被大山团团围住的村庄,已不再有车辆进出之虞。
人们将莒洲村称作没有围墙的古村博物馆,意欲整村修复,增添配套设施后开放旅游。这或许就是她此后的命运了,像多数的珍稀之物一样,在人为的保护下,存续于世,供众生观瞻。是的,几乎所有的原始村落,都被打造成了旅游景区。而那些决绝进城的村民,又迎来一种新的选择。他们渐渐对放空许久的老宅产生兴趣,思谋着回归抑或经营。谁能想到,人们争先恐后抛弃的,代表着落后、闭塞的村庄,如今竟成为时代的香饽饽。一座寂寞多时的古村,又将重新热闹起来。时间啊,一直在大地上排演着大起大落、命运翻转的戏码。
从莒洲古村走出,我又一次遇见潺潺流动的莒水,想到邓氏族人的来与去、沉或浮,恰如溪河汇入汪洋大海,恰如光阴中的亘古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