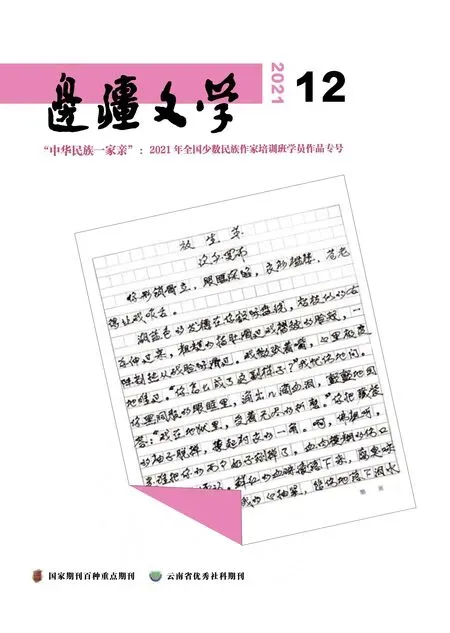萨家的月亮
帕蒂古丽(维吾尔族)
福州朱紫坊22 号萨家大院里,有月亮的晚上,非常适宜听萨家人说故事。从先祖萨拉不花,说到元朝著名诗人萨都剌这个在福州做官,将雁门认作故乡,在他的《雁门集》里无处不提西域的诗人。尤其是萨琦这个一生多变的人,他内心世界经历过的变化让我着迷。出于好奇,在福州见到每个萨家后人时,我不断地把话题引向萨琦。
“看历史如同照镜子”,萨琦为这句话做了一个很有意味的注脚,自从了解了萨琦,找到了一面可以照亮自己一生的镜子。看历史不是单纯地看过去,是以历史对应现在。对于我来说,看历史就是看未来,看一个家族的未来、一个民族的未来。
说到萨琦就应该说说他的大梦山。这座山过去被称为萨家山,那时西门住着看管着萨氏宗祠的人,萨家人每到清明,都到大梦山扫墓祭拜祖宗。
萨都剌的侄子萨仲礼是入闽第一代,从元代算起,萨氏入闽至今已有七百多年。一个民族迁徙到另一个地方,住所、饮食、衣着、出行都得变,依照一般规律一般三代以内,语言、节日习俗基本不变,萨琦恰巧是入闽第三代,萨家俗变从萨琦开始,他晚年尊崇了朱子家礼。
萨琦色目习俗未变时,捐资重修过清真寺,在朱紫坊萨家大院斜对面的清真寺里,有一面萨琦为重修清真寺捐资的碑,上面清清楚楚地刻着捐助者是“萨琦公”。清真寺原来很小,萨琦捐钱重修后的清真寺变大了。
晚年萨琦一改色目人的习俗,在皇帝赐他的坟茔旁修造萨家祠堂,变成了热心于重修《萨氏族谱》的人。也有返祖的,清朝康熙年间,萨家还有人信伊斯兰,这里也可以看出历史上的萨家人在习俗上的摇摆不定。
晨雾中寻梦大梦山
去看萨琦大梦山墓莹,是一个大梦初醒的清早,我拽着藤条爬上山丘,好不容易寻到萨琦撰写的摩崖石刻,与其合影留念。我唯恐不赶紧拍下它们,一眨眼它们就如大梦一般散去。好在散去的只是山腰的晨雾,我窥见大梦山仿佛沉睡了一夜的男子,醒来后正要换掉昨夜的睡衣。
晨光送我拾级攀上山顶的亭子,一位男子背对着晨练者们在拉小提琴,先是华尔兹,后是一支新疆舞曲,有个大学生模样的新疆女孩忍不住甩开裙子随音乐跳了支维吾尔舞,托花帽,飞旋,下腰,移颈,再飞旋,曲终,她的舞步戛然而止。世界之大,无巧不有,不料想竟在这大梦山的亭子里,看到妙龄少女被一支新疆曲子感染踏乐起舞,给睡在这方福地几百年前的故乡人舞一曲胡旋,萨琦应不会怪罪她不敬吧。
家族中唯一有迹可循的唯有萨琦做过确认身份的梦,对确认身份家族恐有各种争议。皇帝赠大梦山为萨氏墓茔,萨琦随了汉俗,建造祠堂,祭拜祖宗,身份之梦随之被隐藏于大梦山,埋葬于大梦山,萨家这一场历史大梦几百年不觉。
明朝与前清萨家人埋葬都在大梦山,宗祠修在大梦山下。1946年抗战胜利时,因痛恨福州汉奸萨福畴,萨家祠堂被学生烧毁。萨家出名人,尽是堂堂正正的,唯独出了个萨福畴,败坏了祖宗的风水。
如今大梦山萨氏宗祠已不见踪迹,皇帝赐的坟茔亦消失得无迹可寻,唯有我拍下来的山间摩崖石刻,是萨琦留下的印痕,注解着大梦山曾经是萨家山的历史。与萨家坟茔旧址遥相对应的,是亭子里华尔兹与西域舞曲,七百年,一种文化又一种文化交叠而来。没有什么是停滞不变的,历史的车轮辗过来,天可翻,地可覆,哪有不觉之梦?乱梦三千,终有醒时。醒来,已换了人间,萨家人开始进入另一场梦。
在故事里慢慢变老
萨本珪住在一处老旧的小区里,他曾任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离休后在小区里开起了图书室,带学生写写书法,弹弹钢琴。老人性格开朗,顺手拿起省艺术学院教授萨本琼作词作曲的《海军世家之歌》乐谱,弹唱了一曲。
他从书柜里抽出《萨氏族谱》,一边翻着,一边埋怨纸张那么快就变黄、变旧、变老了,似乎心有不甘。这个饱受汉文化浸染的萨姓老先生,刚刚为北门外“万寿园”石碑写完第一百个“寿”字回来。其实,无论他在墓园里写下多少个寿字,无论寿字写得多么巨大,多么苍劲,人也挡不住他和那些寿字一起慢慢变老,最后老得跟石碑一样。
萨家有那么多人名字刻在了石碑上,走进博物馆、纪念馆,故事都在发黄、变老。希望变老的故事能一直流传下去,这才是萨本珪追求的那个精神意义上的家族寿命吧。就精神来说,人类的创造中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比如萨都剌的诗歌,被人们记了千年,也就足以佐证他精神的长寿了。
人不管浸染在什么样的文化里,乡情是贯穿一生的。2017年与子女一起去雁门关寻根,萨本珪带回了一捧祖籍地的泥土,现在就在朱紫坊萨家大院第三进,伯父萨君豫遗像前供奉着。他相信雁门的泥土能滋养祖上的精魂,也能让萨家不忘初心。虽然史料有记载,萨家真正的远祖是西域色目人,萨家还是认了雁门这个时间和空间距离都相对离他们近一点的地方,作为自己的故地。
当我问他,为何不去新疆取一把泥土祭祖的时候,他的表情变得凝重。他相信自己的祖上是色目人,却不知道去到新疆哪里寻根问祖,他根本就没有去过新疆,他对新疆这个最早的祖籍地,一直停留在诸如沙漠狂风、草原游牧的想象中。那种想象长满了他的一生,那是像荒草戈壁一样辽阔的想象。去一次新疆原本不难,难的是让想象铺满一生,让沙漠覆盖一生,或者干脆让自己的脑海变成无垠的沙海戈壁,日日夜夜随想象在上面驰骋。不近乡,也不情怯,这么难的事情,他这一生几乎做到了。
我理解了这位老人,长达近七百年二十几代人的想象,已经让那个遥远的故乡悬置在生命的高位和顶端,成了永远不敢攀爬涉足的圣顶。西域,色目人,这样的字眼,只留在梦里,存于心间,祖先的一切,那是用来膜拜的。他们让回不去的故乡成为圣境,生怕到达和踏入都会亵渎了它,这个灵魂的远方,他们不再妄想接近,只适合留在梦中作为一份念想。
横竖讲不清楚
萨兆沩完全赞同陈垣先生1923年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中科学的论断,萨都剌先世为“回回教世家”,即西域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后裔。
有史料记载,萨都剌先世为蒙古人开始西进时占领的哈剌鲁王朝内的“答失蛮氏”。答失蛮氏,是哈剌鲁王朝由贵族组成的氏族支系。在蒙古人继续西征时,“自其祖思兰不花,父阿鲁赤,世以膂为起家,累著勋伐,受知于世祖,英宗名仗节钺,留镇云、代。君生于雁门,故以为雁门人”(干文传《雁门集·序》。
萨本珪对先祖的一切选择非常体恤,“入闵第三代萨琦时,有萨氏信伊斯兰,后来血统交叉混杂。汉族人居住固定,一定居就是几百年以上,姓萨的游牧民族住蒙古包,跟着风沙跑,大风刮来,行囊一裹架在驼背上就跑。跑到有水的地方,蒙古包一扎,再住下来”。
萨氏先祖萨拉不花娶了第一个妻子后,就抛妻别子随成吉思汗西征,至于他的子女们与何族何人成婚,如今恐已难考证,不过,后代混血是确认的,且品种之优,萨本珪言语中也很肯定。
萨本敦上初中时接到通知,萨姓改汉族身份为蒙古族。父亲吃惊地解释,萨氏是色目人。那应该是1961年的事,他至今记得。
有语言学专家认为,萨都剌这个名字是信阿拉伯话借来的,这个名字维吾尔族现在仍在用。萨家对祖先的认识停留在色目人,一个离开西域在内地繁衍了六七百多年的家族。他们认为,能够牢牢记得祖先是色目人,这一点已经足够了。
2016年有剧组在朱紫坊萨家大院拍摄纪录片时,发现屋顶的狼图腾,瓦脊上还有个元宝,厨房里还嵌有佛龛。尤其是狼图腾这稀奇的宝贝,整个福州仅朱紫坊22 号有,可萨家人一直以为那是祖先用来镇宅的。
纪录片《大海边的蒙古人》里拍了萨家蒙古化的祭祖,献的是绿色哈达。这是蒙古礼仪。镜头从草原习俗过渡到海边,十分有跨度,从草原文明跨越到海洋文明,这也是萨氏祖先实现的从北到南的文化大跨越。
狼图腾也好,元宝也好,佛龛也好,哈达及其他都好,对于萨氏家族,文化就这么交叠混杂,时而一种覆盖了另一种,时而一种淹没了另一种,时而一种沉落。另一种浮出历史水面,任何时候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种文化在萨家,自古就互倚共存。
“西北的民族问题研究专家来过,上海研究萨都剌的专家来过,内蒙古大学教授也来过,清史稿两处写清萨氏‘是回回’,又写‘实蒙古人也’。只有萨氏是色目人,这一点毫无疑问,更确切地说,是蒙古化了的色目人后裔,我们也讲不清楚,真的讲不清,没办法,横竖是讲不清楚。”萨本珪也为难地摇头。
萨本敦说:“我们是萨氏后人,不是民族属性专家。上世纪60年代初认定我们是蒙古人。萨家大院的建筑上发现蒙古族的狼图腾后,民族属性的架从50年代吵起吵到了现在,他们吵归他们,我们没有多少发言权。”
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萨氏后人对祖先认识模糊,或者说,对民族这个概念不怎么去穷根究底。其实,无论究与不究,根底就在色目人那里。追踪来追踪去几百年了,萨家似乎也累了,最终也放弃了追个究竟。近七百年的历史长河洗刷,萨氏的血管里流着各种民族的血液,萨家是什么民族变得不再重要,反正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之中的一员,重要的是这个家族的成员为国家、为社会做过的那些贡献。
汉民族修家谱这个习惯真好!《萨氏族谱》清朝修过,30年代萨镇冰编过一次,1987年再编过,2007年新编之后,又不断增补、续谱,只要萨家有人出世,他们就想方设法找到,中国台湾及香港,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的萨氏悉数被纳入族谱。萨本铁夫妇去世后,六个子女到现在联系不上,萨家从未放弃寻找。萨家在这方面固执地持守着,萨家人一个都不能丢。
月光里的朱紫坊
萨家大院门前的安泰河,是福州城内的护城河,上世纪70年代还船来船往。建萨家大院的材料全从河运过来。安泰桥下,护城河畔,朱紫坊老巷子里,萨家的月亮从古到今,圆了又缺,缺了又圆,阳晴变换。津泰路护城河两岸的高院深巷里探出月亮的脸,也是冰冷的,一如深冷的历史,靠现世活人的血微温着。
也许是因为夜色,也许是因为月光,元宵前夜的话题,放下了萨门英烈,祖上荣耀,回到萨家大院里,变得离生活很近。刘新法讲述时的表情变得很柔和,他妻子在茶桌边忙碌的身影变得很轻快,笑容也时不时闪现在院子里。小孙子在桌子周围转着,不肯回房做作业,嚷着要听萨家先辈的故事。这么近的传奇,这个敏感的孩子怕是用了整个童年在听,只是家族的冷暖,历史的兴衰,到了孙子这辈,也只是爷爷口里讲述的故事罢了。
刘新法母亲的爷爷萨子安是一个大盐商,明末清初买了这一处房子,萨家大院从他30 岁时修建整整修了18年。萨子安从这里送萨镇冰去马尾船政念书。萨镇冰与萨子安小儿子萨君豫又是忘年交,萨镇冰与朱紫坊的关系就有好几重,可谓有不解之缘。
刘新法认为,“萨家家训是写在纸上的,有的东西是在基因里的”。萨家人不与人争名利,懂得谦让礼让,以忍为上,不在争抢费心思。人的一生精力有限,某些方面做到不争,在有些方面才能做出贡献。退让虚的,反而有实在的所得历代有成就的人辈出。萨家人个个沉静儒雅,做事有原则,也许萨家产生那么多人精英的原因,就是能顽强隐忍下来,这似乎已经成为他们骨子里的基因。刘新法的母亲就是萨家的女儿,他的记忆中母亲生活乐观,即使特殊年代惨遭迫害导致双目失明后,还织毛衣、学英语,甚至让人制作了框架书写书信。
刘新法懂家族源流,是深谙萨家的人。在刘新法的记忆里,大院落家教很严,不说粗话,冬天烤火、夏天乘凉,大人都讲故事。谁买了吃的,都会分给大院里住的人。小时候,左右邻居都是亲戚,无论谁家的小孩都会被照顾,一碗饭可以从一进吃到三进,吃好几家的,每一进的大厅里都摆着饭桌,来客人大家帮忙招待。
刘新法退休后,常与发小、早年同事在这里聊天,中秋节萨家一大家人吃饭,朋友看到这场面十分感慨,真希望萨家不要散去。这样四世同堂的大宅院,如今在福州也不多见了。
萨家大院大门上贴着“私人住宅,谢绝参观”,但游人还是常常探了进来,多是为着这里挂了抗日英烈“萨师俊故居”的牌子而来的。
第三进里供奉祖先牌位和遗像桌前,摆着一个红色铁漆盒子,上面白底黑字写着“雁门关泥土”,我猜测那是萨本珪去雁门寻根带来的那一抔泥土。
萨家大院是闽变最早的议事点之一,福州迎解放的三份安民告示,也是从这里由萨镇冰手书后送出去的。以前这里花厅也曾是个达官贵人聚会的要地。萨家大院里最多时住150 人,每进一个厨房,解放前,都是萨家人住,刚解放时出租,部分被收为公房。2013年,公房部分的住户搬走了,剩下的萨家的人继续守着祖先留下的房产。现在一个大院子住着三户人,几十间屋里,只有十来个人,没以前热闹了,显得很冷清,空寂。
萨家未保留先祖任何民族的风俗,完全浸润汉文化传统里的萨家,早已习惯了在祠堂里祭拜祖宗。已经没有祠堂的萨家节日没地方聚会,萨家联谊会商议定萨家大院第三进作为祠堂。现在福州的萨姓,每逢正月初五都会来此祭祖。每年五大节日祭祖都在此,五遍响鼓敲过之后,萨家的祭祖仪式就开始了。摆上祖宗香位、贡品桌,蓝色花瓶插上正月十五的白黄红三色菊花,多少年来,只有花瓶的大小和颜色在变,自刘新法记事起,这三色菊花是从来也没有变过的。
大院第三进的大厅背面,原建有公婆庵(先祖檀香木牌位,高40 厘米,宽15 厘米),刻先祖名字、辈分,可惜1966年被毁。自那时起,怕愧对祖先,再也没人敢打开过公婆庵,但谁都知道那里面早已是空的。
将刘新法先生的介绍当成画外音,闭上眼睛想象那些萨家大院里过去的生活画面:头进墙头泥塑是西游,花厅是三国,二进是西厢,墙上是彩色泥塑,墙围一圈是黑墨壁画故事。那萨家大院的墙头壁画、墙头泥塑,“破四旧”的火烧了一周,现在残留的痕迹依稀可见。
萨家大院里的光景
朱紫坊萨家大院里,刘新法每日面南而坐,一张八仙桌上摆着茶具,官宦宅邸,迎来送往,行的还是大户人家的礼,只要主人在,三重门常开着,来了人请茶,客走送到院门外,作揖,眉恭目虔。刘新法举手投足,也浸润和传承了萨家人的儒雅。
也许因着刘新法被萨家大院那种悠远刻骨的爱感染,我对这东南老宅由衷地心生爱恋。清早和晚夕都偷偷跑去探望,走走老巷子,坐在安泰河畔,听榕树上的鸟鸣,呼吸萨家门口的空气。虽是榕城异地,这萨家大院里的人,最早却是来自西域的色目人的骨血。几百年历史更迭,如今他们已是福州萨姓了。或许历史的衬底本是冷硬的,只因了人类热血的灌注,才变得温软和暖了许多。
刘新法一直活在对萨家的回忆里,他的生命跟萨家的一切密不可分,他母亲是萨子安六子的小女儿。刘新法原配妻子过世后,他娶了自己的表妹萨玲,萨玲的祖父萨君豫(第十子)和刘新法的外公(老六)是亲兄弟。刘新法把自己的后半生与萨家紧紧地绑在一起,儿时表妹跟在他屁股后面长大,其间,一个很微妙的心理恐怕是夫妻俩共同拥有关于萨家的记忆。
缘由这婚姻,沉淀在他生命最深层的记忆又被从根底打捞起来,这些回忆成为他们作为萨家人共同的基因延续着,即使有一天他们搬离世居的朱紫坊萨家大院,也会被他刻进骨子里,并在他们耳濡目染的儿子、孙子身上延续下去,这是祖先赋予的精神遗产。
刘新法牢记母亲临终嘱托,“萨家待我们不薄,要看好家,守好业,让远居美国的亲人回来时能找到家。”
现在刘新法跟儿子儿媳孙子一家三代,还住在那一间厢房里,他与这里总有种割舍不断的情思。
刘新法的外婆杨鹤龄(冰心母亲的同胞妹妹)晚年,靠商务印书馆给萨本栋(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按月送来的稿费版税生活。她至死都不知道儿子英年早逝,以为儿子从美国寄钱来了;她到死都住在萨家大院,似乎大院在,儿子就会回来。
萨本栋的妻子黄淑慎1979年回来,婉拒政府邀请和大学的安排,一定要住在萨家大院。萨本铁在世时总每次写信来,都说他很想回到朱紫坊。萨本祥(女)——刘新法母亲的姐姐从北京带着寿衣回来,在朱紫坊住了两年,执拗地要在这里度过人生最后一段时光,最后被儿女接回北京。漂泊在外,他们把这里当作了故里,能回朱紫坊看看,在这里住住,是萨家人的期望。
夕阳下的仁寿堂
福州名人太多,2004年修三坊七巷,福州有十一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萨家大院是其中一处。福州的三山陵园有萨师俊衣冠冢,厦门大学有萨本栋公园,他和夫人的墓就在公园里。福州萨镇冰公园有萨镇冰雕像,冶山公园有萨镇冰晚年故居仁寿堂。萨氏名人在湖北的、山东的甲午海战博物馆,清华大学的校史馆,福州中山舰博物馆、马尾船政博物馆均有陈列。刘新法建议我去看看。说起萨家的名人,刘新法如数家珍,平静的脸上禁不住涌上骄傲的激情,他全然把自己当成萨家人了,并且以此为荣,他很珍视萨家祖上的荣耀。
闽侯县南通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遭受水灾,萨镇冰救灾,都叫他萨菩萨。后来为了纪念他建了萨公桥、萨公长寿亭,镇里开了很多饭馆,好多以萨镇冰命名。罗源、霞浦和太姥山、闽江出海口等处还有萨公堤、萨公岭和他的题词石刻,央视播出的《百年中国》《船政风云》《北洋水师》《东方有大海》《大海边的蒙古人》等电视片和电视剧都有讲到萨镇冰的。
萨本珪回忆:“我叔公萨镇冰30 岁夫人去世,独身一人,清廉无房。抗战时他在重庆,抗战结束,叔公回朱紫坊住。1948年福建乡绅集资修了仁寿堂,作为90 周岁寿礼赠送给萨镇冰。叔公与马夫和萨姓穷亲一起住,叔伯姐姐本康,哥哥本昆,还有我们全家5 口人,祖母、父母还有我和弟弟都一起住在里面。我父亲抄抄写写,当萨镇冰的私人秘书。我在福州一中念书时,弟弟去厦门修水堤。我住仁寿堂到萨镇冰去世为止,才搬到姑母那里。我去浙大土木系工程系测量专业上大学,跟萨镇冰拍照了最后一张照,这张像我现在还珍藏着。”
夕阳西下的时候,适合去冶山春秋园看萨镇冰先生晚年的居所,通过省文物局修复,现在已经变成冶山公园的一处景点。这栋木结构亭子式建筑,像一个悬屋,一座孤岛,更像一艘船舰。为了给这座房屋找一个切合它形象的比喻,我连去了三次,都是在黄昏,最后一次,在草坪上坐到天黑,感觉萨先生随时都会从楼梯上走下来。最终等到一位修自行车的老人,瘦瘦的,谈吐淡泊,黑暗里我想象照片上萨老先生骑马的样子,无论如何与眼前修自行车的老人联系不到一起。
这艘船舰型的建筑,两层木楼在舰头位置,木楼前留有阳台,像船甲板,舰首位置是一个防空洞,洞口突出来,洞顶龟背纹的石头砌成一个乌龟的形状,从前面看,像一只巨型海龟驮起整座舰艇。
木楼背后,是一丛石山,山体上多有摩崖石刻,后人修复时,书法用红漆刷过,异常醒目。这丛山像是船舰上满载宝藏,使得船头的木楼和船尾的石山,在重量感上实现了一种视觉平衡,让危岩上的建筑有了一种平稳感,仿佛这艘瀚海稳进的船,由于海龟的驮举不至于沉没。船舷右侧是上楼的石阶,靠外侧以绿漆石栏杆护围,像是船舷,石阶外一块绿草坪,草坪边是银白沙石,从上往下看,给人一种碧海沙滩的错觉。萨镇冰,这个中山舰的舰长,航海人家的后裔,以贩盐发达的盐商后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恐怕晚年一直都沉浸在他最光彩夺目的航海生涯中。
两棵古榕像两只结实的锚,将这艘“中山舰”牢牢地拴住,固定在了这一片福州人海,恐怕萨镇冰的心应该至死都在航行。
萨本溁的黄巷
黄巷萨家大院入口遇见萨本溁,虽一介市民,却斯文不减,一看他就是萨家人的模样。空出的房子里,有人在出售花灯。他守住院门入口,不让东张西望的游客和路人进到里面。他坐在门口守住的架势很熟悉,有点像终日坐在萨家大院里的刘新法,我忽然明白,那是一种守的姿势,似乎他们要守住的不仅仅一个入口,似乎他们的肉身坐在这里,就能阻止世界上的一切震荡和变动,挡住街市上汹涌而来的潮热气流。
萨本溁的黄巷是萨家第二支的居住地。萨家十八世萨本溁,就出生在这里。院子里的住户,非姓萨的前几年都已搬走。他带我看民未清初到现在三百多年的萨家老房子,那些木雕已然保护得很完好:
“我祖宗的房子,萨镇冰13 岁以前还住这里。1952年以前我在福州火柴厂童工,1953年收为国有。妻子也在厂里,双职工,那时候搬出去,厂里给我们分了宿舍。后来又让我们搬进来了。1998年,房子木头烂了,快倒了,我把房子部分墙面改成砖墙。住了20年,现在我们也要搬出去了。”
尽管萨家院落在黄巷是第一家,隔了一堵墙,便是两重天,把市场喧嚣的气息挡在了外面。空空的旧院里,屋子的顶、墙面,地都在整修,三间屋子,住在过去书宅的位置,从这里看出去,古旧的韵味从照壁每一块砖上透出来,从天井的杂草和青苔里渗出来。
从幽静的黄巷萨家大院出来,便是喧闹的三坊七巷。出门的时候,看到那个卖花灯的,生意极好,萨本溁说:“一个过去的住户在这里卖花灯,初一卖到十五,今天元宵节,晚上有灯会,福州风俗。”
萨本溁送我出了大门,站在黄巷46 号的大门前向我挥挥手,他未知觉自己正站在萨家的一个故事里,像一张发黄的老照片。
他送客的姿势也像守在朱紫坊萨家大院的刘新法。
夜里,推开朱紫坊萨家大院沉重的老木门,刘新法端坐在空无一人的院子正中一把太师椅上,面前八仙桌上摆着茶壶、茶杯,他似乎一直在等谁。他似乎能这样坐到地老天荒,雁门旧地早已老去,祖上西域的天也已荒远,雁门萨氏的故事,也随刘新法一起,在朱紫坊萨家大院里慢慢变老。
萨家的月亮躲在榕树背后,独独地亮着。让人想到萨都剌的《登石头城》里,那一轮元朝的月亮:
寂寞避暑离宫,
东风辇路,芳草年年发。
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
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
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这个月亮一直追赶着迁徙的萨家,从西域追到雁门,从雁门追到闽土。元宵夜的月亮,照着萨家的过去,也照着萨家的今朝。历史上的月亮,与今晚萨家的月亮一样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