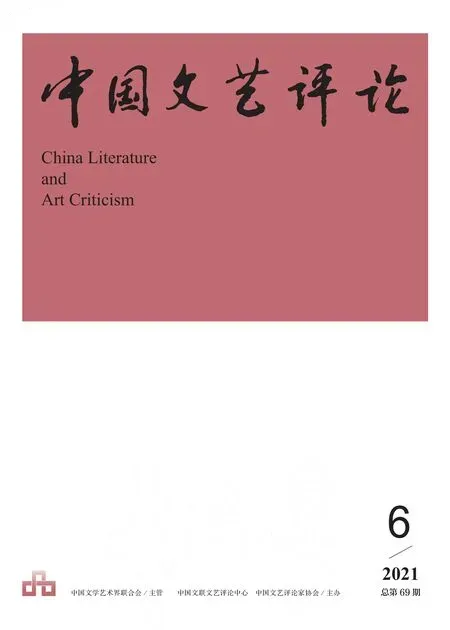“被看见”的煤矿女工
——论刘庆邦小说《女工绘》中的华春堂形象
陈 斓
刘庆邦的煤矿题材小说中有很多对女性形象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于煤矿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特殊环境下女性现实命运的观察与思考。在谈到理想女性形象时,刘庆邦曾这样表述:“至于心中最理想的女性是什么样的,我开不出一个单子。任何理想都是概念化的,理性的,抽象的。我对女性的判断比较注重感性。”《女工绘》则打破了概念化、抽象性的女性形象,以煤矿年轻女工华春堂工作、恋爱的曲折过程为主要线索,讲述后知青时代一群青年煤矿女工的青春和生活,表现了作者对于煤矿女工命运的关切和同情。作为千千万万煤矿女工的缩影,华春堂的形象极具艺术感染力,她不再作为“他者”被爱、被安排,而在家庭场域、社会场域、恋爱关系等方面充分发挥主体性。
一、作为“被看见”的煤矿女工形象
“被看见”在这部小说中是指煤矿女工进入当代社会场域从而被看见。戴锦华与孟悦的论著《浮出历史地表》比喻女性进入现代社会领域,是从“不见”到被“看见”的变化过程。戴锦华指出,如果有女性进入社会场域,她就必须化妆,像花木兰那样化妆成男人,或像穆桂英那样作为一个特别的传奇性存在。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的天空还局限于传统的家庭关系、婚姻关系中,在社会身份认同方面跟男性有很大的差距。当代女性是社会化的女性,她们不再像之前的女性那样拘囿于家庭内部的生活中,而是走出家门,来到广阔的社会,参与社会性的工作。《女工绘》中的华春堂虽处于后知青时代,但其身份的设定是走出家门的社会化女性,脱离了传统作品中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
《女工绘》中的华春堂形象是刘庆邦的长篇煤矿小说首次以煤矿女工作为叙事主体。煤矿工作环境因岗位种类、劳动强度、井下环境等所限,以男性居多,女工们的生活、发展空间较小。男女之间权力的悬殊在煤矿这一特殊场域中尤为突出。女性要在这样狭小的场域生存、发展,需要付出更多的能力和智慧。作者设置这样的对峙,则是有意突出具有自主意识的女性话语。
在刘庆邦以往描写煤矿女性的小说中,女性大多是作为矿工家属或其他间接关系生活在煤矿周边的农村妇女形象。如《走窑汉》的小娥,《哑炮》的乔新枝,《家属房》的小艾等,这些女性作为农村传统妇女形象,大多是被动地生活,被动地爱,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没有独立自主选择生活的权利和觉醒的意识。即使开始有了女性自我觉醒的意识,也不够彻底和主动,缺乏理性的思考,她们懵懂地抗争,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在作者看来也是不够可爱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所描写的卫君梅、杨书琴、郑宝兰等女性,是作为矿工家属出现的。小说讲述了在一场透水安全事故中失去丈夫的女人们,怎样从依赖丈夫的角色,逐渐成长为成熟有担当的女性。《血劲》讲述了具有反抗精神的矿工妻子四真,不顾母亲反对,想要过上幸福的生活,主动要求嫁给煤矿工人。但其实她看似主动追求和抗争,实际上却是沉溺于自我的欺骗,是一场堕落的闹剧。因此,四真成为刘庆邦嘲笑的对象:“她的嫁入煤矿,看起来是对于传统和世俗观念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却是给人一种虚妄的感觉。”作者对于女性这种缺乏理性和失去自我的抗争方式,是持批判态度的。
华春堂在小说中不再作为矿工家属或跟煤矿有间接关系的人出现,而是以工人阶级女性的身份进入社会场域。她一出生就在矿区生活,户口是矿区户口。她生活的区域是在具有城市雏形的矿务局——周围有医院、学校、商店等城市居民必备的生活场域。在矿务局的生活场域中,她没有自己的土地,吃商品粮长大,生活来源在于挣工资、领粮票、烧蜂窝煤。初中毕业,接受过基本的学校教育,这些身份的设定都不同于作者以往描写的相对落后的煤矿女性形象。因此,不同于对四真这类女性的批判和嘲讽态度和小说《黑白男女》中对矿工家属坚韧品格的赞扬,作者对《女工绘》中的女性始终充满爱意与欣赏,正如其在小说“后记”中所说,“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女工绘》是一部爱的产物”。
二、独特的女性自我奋斗的形象
在社会文化的公共场域里,性别与阶级互相构建,女性话语往往也同时和阶级话语联系在一起。从“五四”时期到21世纪的今天,尽管时代变迁,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现当代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始终表现出这一点。较典型的如《李双双》《人到中年》《杜拉拉升职记》中三个不同时代的女性形象,在这三个不同女性形象的变迁中,“父权的面孔也是生动的,在李双双那里,表现为父亲一样的老支书;在陆文婷那里,是和她一样书生气的孙主任;而在杜拉拉那里,则是明察秋毫的老板。如果女性的问题总是只有在这些‘上级’的干预下才得以提出并解决,那就意味着只要这种制度存在,女性就永远不能通过她们自身的意愿和能力消除问题本身”。刘庆邦的华春堂形象的独特之处在于,打破了对已有历史女性叙事的重复,体现了具有自主意识的女性话语。
不同于以往传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女工绘》华春堂所处的家庭中,父亲的位置是空缺的。尽管这个家庭还有弟弟这样一个男性,但他的性格是懦弱的,且处处表现出对姐姐的依赖,最终这个家庭还是以女性为主导的。在煤矿的工作场域中,作者安排华春堂的工作中面对的男性,包括她的上级人事科长、化验室主任、她的三次择偶对象,均未被赋予父亲的角色。这表明作者有意展现女性在传统家庭、工作场所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的自我奋斗之路。
华春堂的自我奋斗主要表现在家庭、工作、择偶等方面,她始终主动掌握着自己人生的节奏和方向,尽可能地不让自己陷进被动的泥沼。家庭方面,她在失去了父亲的四口之家中,担任主事人的角色,替代了父亲在家中的地位;工作方面,她主动要求到灯房、宣传队、化验室等地方工作,展现煤矿女工的独特风采;择偶方面,她主动追求李玉清、魏正方、卞永韶三个优秀男青年,不再以柔弱作为吸引男性的特质,而是展现青年女性的能力和独立自主的意识。当面对生活的磨难、心仪对象的拒绝、初恋对象的离世,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她没有半点自怜和哀怨,没有林黛玉式的感伤,没有少年维特式的自我怀疑,而是表现出越挫越勇的气势,仿佛她骨子里天生就带着勇往直前的性格。这种独立自主的女性气质是新鲜的,极具生命活力的。因此,华春堂的生机勃勃同压抑、狭小、黑暗的煤矿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形成了刘庆邦煤矿题材小说中独特的女性形象。
华春堂在家庭场域中是一个早熟的年轻女性形象。在父亲死于矿务局医院的一场锅炉事故后,身为二女儿的她却成为这个四口之家的主事人。家里大小事务的发言权和决定权都由年轻的华春堂掌握,当家人的职责也落在了她身上。对此,小说开篇作者就作了详细的交代,“他们这个四口之家,目前主事的人是华春堂,诸事最后一锤定音的也是华春堂。……全家人没有开过会,没有投过票,也没有进行过举手表决,当家人的职责不知不觉间就落到了华春堂头上”。在这个失去父亲的四口之家中,掌管家庭事务的不是男性,也不是年长女性,而是一个年轻女性。作者通过端阳节包粽子、帮姐姐调工作等家庭生活中的事件,展现华春堂性格和思想的早熟,以及如何掌握家庭话语权。小说开篇写妈妈和姐姐之间因为端午节是否包粽子而争执不下。“别人家过节都包粽子,妈要是不给咱们包粽子,她心里过不去。吃不吃粽子在其次,包粽子包的是节气,一包就把节气包住了。”华春堂以一句简单的话就将两人争执不下的问题解决了,体现了她的细腻和机灵。父亲因锅炉房事故去世后,姐姐华冬梅获得顶替父亲在医院工作的机会,结果却被分到了洗衣房。因不满洗衣房艰苦的环境,不甘心当洗衣机器,她自己找医院人事调动工作无果后,在妹妹华春堂的帮助下成功调换到中药房工作。她的这一能力,令姐姐华冬梅感慨:“爸爸不在了,妹妹代替了爸爸,妹妹比爸爸还有能耐呀,还厉害呀!”作为失去父亲的家庭,华春堂凭借心思缜密的性格和个人能力,一步步奠定了作为家庭主事人的地位。
当女性进入工作场域,也就进入了和男性共处的空间。传统的女性叙事中,她们大都是被当成男性的附属品或者处于一种边缘性的社会地位,被动地等待着男人的挑选、定义、重组。而华春堂则呈现了不一样的女性风采,小说中以华春堂三次主动调动工作,展现其在工作场域的自我奋斗历程。去东风矿报道的第一天,20岁的华春堂就以机灵的话语、揣摩人心的机智、看人的精准,在东风矿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话语权。王科长作为华春堂进入东风矿第一个接触的男性权力的拥有者,他有调动岗位的权力。别的知青来矿上报到,根本没有自主选择的机会,只能服从于王科长的分配,家境、出身普通且毫无特长的华春堂按理无从主动选择工作。然而当王科长给她安排岗位时,她拒绝了炊事员、理发员等岗位,而为自己争取了灯房的工作岗位。在这次以情动人的交往中,她不仅敢于跟王科长商量,甚至表现出了拒绝,这体现了她非凡的勇气和主动性。
矿上成立了宣传队,虽然这不是一个正式工作岗位,但能进宣传队,是矿上年轻男女的梦想,对华春堂来说,不仅能短暂地脱离灯房枯燥、繁重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证明自己的优秀。当同样在灯房上班的同学张丽之被选进了宣传队时,华春堂心生不平,发出“怎么可以没有我呢”的感叹。于是,生性要强的华春堂为进入宣传队开始主动争取。她以给宣传队队长魏正方打扫宿舍为由,借此打探他进宣传队的事。在她细致周到地打扫完宿舍后,魏正方被她的责任心和细心打动了,同意她参加宣传队的合唱节目。进入宣传队后,华春堂从队员周子敏那儿看到了化验室上班的好处:穿着白大褂,比灯房上班要干净多了。她萌生了去化验室上班的念头,但是化验室是煤矿技术含量较高的一个岗位,作为连英语字母都没学过的人想要去化验室工作,简直比登天还难。华春堂却并未放弃,而是敢想敢做,以勇气和策略,一步步从灯房到宣传队,到化验室,实现了她工作岗位的跨越。
三、从“他者”走向“自我”的女性主动择偶的形象
波伏娃在《第二性》的前言中指出“他者”指的是那些处于被支配地位,失去独立人格被异化的人。一方面,主体决定了“他者”是否存在,女性作为被依附于男性存在的身份,显示了女性身份的被动性。波伏娃认为,女性之所以成为他者,是因为男性在将自己定义为自己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作为其他女性的地位。女人并没有成为一个与男人相对立的存在,当男性与女性群体结合在一起,女性只不过在群体中处于附属地位。另一方面,女性的“他者”身份是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华春堂的恋爱史,则体现出女性从“他者”走向“自我”的女性主动择偶的历程。华春堂在恋爱关系中始终牢牢把握着主动性,不再处于附属性地位,而是更多地展示自身和丰富的世界。甚至在很多时候,她还给予男性以温暖的力量。她不再作为弱者存在,不再作为被男性定义、被男性改造的他者的身份出现,而是始终作为一个大写的人充分发挥着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想要的自由生活。
在第一次谈恋爱之前,华春堂是有计划地、理性地提前做了观察工作。“她敏感地像是一台灵敏度极高的感应器,对每一个男青年都有感应。……感应之后,她又像一台接收器,把每一个男青年的信息都接收下来,包括身体信息、相貌信息、步态信息、语言信息,等等。矿上二十几岁的男青年有几十个、上百个,她做到了一个不落,把所有男青年的信息都接收了下来。……经过反复筛选、过滤和剪辑,目前她脑子里给李玉清的镜头是一个特写和定格。”她把自己的家庭与李玉清的家庭作了比较,经过一番精打细算、深思熟虑之后,才确定了第一次恋爱的对象——李玉清。她没有通过别人介绍等方式了解李玉清,而是自己主动了解恋爱对象。她在李玉清每天必经的食堂的路上等待,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跟他打招呼,又以借书、送零食等方式接近李玉清,华春堂就这样与李玉清建立了恋爱关系,并在这场关系中牢牢占据主动的地位。这种主动性的恋爱方式,在当时后知青时代是具有女性解放意识的。后来,李玉清因一场机运事故身亡,华春堂在一场痛哭后,又开始重新面对生活。在此期间,李玉清的同学马成学有意跟她表达爱意,但是她在看清他的身上惜力、心上没劲时,以自己心情沉重,暂时不想恋爱为由,果断拒绝了马成学。
第二次恋爱,华春堂把目光投向了会读书、组宣传队、会写材料的魏正方。华春堂通过各方面的观察,对他表示欣赏,并在他遇到困难时,给予鼓励和安慰。一次是宣传队要解散时,心气很高的魏正方重新回到了井下掘进队,她以找魏正方借《红楼梦》为借口,安慰魏正方要坚强,要把目光放长远,经得起磨难与考验。另一次是魏正方在挖地洞时受了轻伤,华春堂不避嫌地给他端来肉汤面。当魏正方被借调到矿务局的政工组帮助工作后,华春堂想主动追求魏正方。尽管魏正方对华春堂的能力给予了认可,但最终还是以她身材矮小为由拒绝了她。对于这一点,华春堂并未流露出任何自卑的情绪,她坚定地认为,问题并不是出在自己身上,而是魏正方的问题,是他带着偏见,拿她当牛羊作比较。
被魏正方以身材矮小为由拒绝之后,要强的华春堂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择偶之路,她对自己小巧玲珑的身材充满信心。华春堂发誓要找一个身材高大的男朋友,这次也是华春堂恋爱史上最后一次主动出击。因为篮球队的卞永韶身高是矿上的“第一高度”,所以她把目光投向了矿上的篮球队。尽管身高的差距让两个人看起来不太可能,但是华春堂又一次争取到了主动权。当魏正方知道华春堂和卞永韶在一起之后,也对她表示了由衷的赞叹。
华春堂三次有计划、有目标的择偶历程展现了她作为独立女性的积极主动性,即她对于个人家庭生活的憧憬和选择,完全是基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屈服于男性。
四、结语
女性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有了很大的成长空间和地位的转变,她们作为独立的个体逐渐“被看见”,“浮出历史地表”。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的解放仅仅局限于传统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寻求男性对身份的认同,但针对女性社会化的叙事较少。刘庆邦这部长篇小说《女工绘》的叙事重心,则是对女性作为独立个体在家庭生活、工作场域进行发掘,在突出具有自主意识的女性形象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刘庆邦以往描写煤矿女性的小说,女性是矿工家属或其他间接关系生活在煤矿周边的边缘性位置,《女工绘》中华春堂则作为后知青时代的煤矿女工,进入社会场域从而被看见。作者通过华春堂这一崭新、丰富的女性形象,有意识地建构男女话语体系的平等,来“写千千万万中国女工乃至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华春堂一出场即处于失去父亲的家庭环境,是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女性。在时代和命运的裹挟下,华春堂没有被动地选择顺从,而是在家庭、工作、择偶等方面有着追求自我、建构理想生活的强烈愿望和实际行动。不管在失去父亲的家庭场域,还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煤矿工作环境中,华春堂始终以平等的两性观念,牢牢把握着主动性。即使在遭遇挫折时,她并不是选择依靠男人去解决,而是追求自我,勇于抗争。华春堂靠自身的能力在煤矿生存、发展,不再以弱者的形象出现,被动地去爱,其自我奋斗之路展现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生命的解放。
作为后知青时代的女性叙事小说,尽管作者塑造了华春堂的女性主体性形象,但是女性在社会秩序中的弱势地位,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秩序中并不能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小说的结尾安排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带走了华春堂年轻的生命,令其自我奋斗之路被永远定格。这表明刘庆邦在塑造华春堂勇于追求自我的女性形象时,陷入了时代和伦理的困境,因此小说结尾以这种戛然而止的方式,结束了“被看见”的女性自我与“他者”在同一个叙事空间的冲突和对抗,展现女性自我觉醒的独特价值。尽管小说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但华春堂的意外死亡,令她短暂的一生在悲剧性的毁灭中得到了升华,也留给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如女性的自我解放之路、作为自我的女性和他者的男性之间在家庭、社会等场域的关系等。